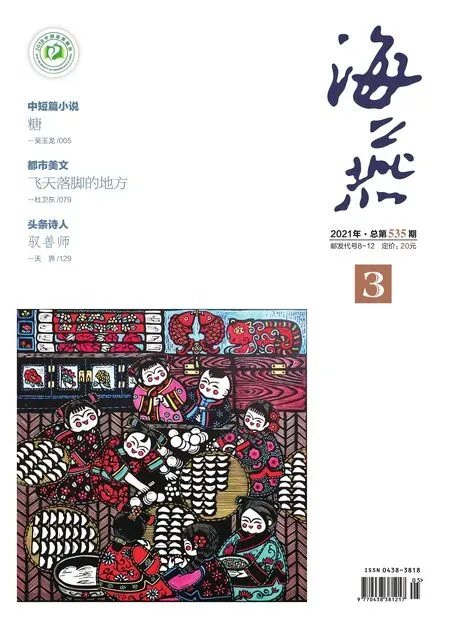指纹里的往昔
我呼吸到人生之旅的第一缕空气,有着潺潺水流映照植物的芳香,五月植物与太阳的浓荫熏染了我的最初生命——以至于后来的我总是主观感觉,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自己才对各种植物花卉发自内心地喜爱,仿佛是我生下来,她们就已然在我的生命中了,与我不可分割……
据母亲说,我小的时候,内向得很。六岁还怕见生人,到哪里都不说话,被人打了不会还手,被人骂了不会还口,母亲为此很是担心,她常常对着我无奈地说:“从小看看,到老一半呐。”她担心我长大以后会很没出息,不知要遭人怎么欺负。村里有好几个像我一样大的女孩子,都很野,会打架,跟男孩子一样动手就打,唯独我不会,我每次出去玩,母亲总是不放心,要让哥哥或姐姐跟着保护我。可那时的我,对她说的这一切好像还没有认识。
我是母亲的第三个孩子,她生了我后,就没再生了,我在家排行老末。后来得知,母亲生我的房间,距离户外的河流只有十几米远,河岸旁长着榆树、野蔷薇、槐树、枫杨……母亲回忆说,就在她要“与我见面”的那会儿,她感觉到我的身体瘦长,头发细软。
我脑海里,记了母亲曾讲述我的许多的童年趣事——那时农村,生活虽然清贫,但都重风俗讲情意,谁家结婚办喜事,或生了大胖儿子,都要在全村挨家挨户发喜糖和红鸡蛋以示庆贺,同时也是为讨吉利。每一次有人来家里送喜糖和红鸡蛋,我都高兴得不得了。有一次,估计是我惦记别人家的喜糖和红鸡蛋了,但我不直说,我只是问母亲,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人家办喜事、没有人结婚生儿子呢?那时的我,大概是七八岁的年龄。
我那时胆子小是出了名的,胆子小的人一般都比较乖巧。母亲说,小时候他们跟我说啥,我都说好,从来没有脾气,不惹父母生气,平时一看到父母训骂哥哥姐姐,我就识相得很,早早躲得远远的了,不添乱。
那个时候,食用油很金贵,一年到头,村子里很多人家总是不够吃,而那时我们心中的美食就是油拌饭,生香的黄豆油或是菜籽油,往饭上一浇,再洒上一点点酱油,咸、香、鲜交融一体,让我们欲罢不能,如果能够隔三岔五吃上一碗油拌饭,就满足得可以别无他求了。我那时也很想吃油浇饭,但我都会事先报告母亲,而她每次都会很快准允我。只有一次,不知母亲为何不同意,当时还想,怎么每一次她都是很爽快就答应我的。那次,我缠了她半天,她就是不答应,她不答应,我更馋了,我就继续缠着母亲,她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到最后,母亲忽然就笑了,她用怜爱的口气对我说,你呀,真是没用,去看看,你姐姐一句话没有问我,一碗油浇饭已经吃完了……
我姐姐我是佩服她的。春天时她和我一起割草,她的篮子里一会儿就装满了细嫩的青草,然后又很快地把我的篮子也装满了青草;她拿哥哥做弹弓的水牛筋缠上了母亲织衣服用的细毛线,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黄色的,姐姐用缠了彩色细毛线的水牛筋给我扎辫子,既漂亮,又不会粘住头发让我生疼;她带我捉蜜蜂,教我怎样将蜂蜜撕开,吃到它那一滴晶莹的蜜,在油菜花地里、紫云英地里、石墙边,我们都一起撕吃过蜜蜂,同时还撕吃过紫云英和槐花。紫云英和槐花的吃法相似,把一朵花撕开后,花托部分甜度最高,我们把花托放到舌头上,同时感到生活给我们微微的甜;为了做毽子,姐姐带我一起追别人家的芦花大公鸡,抓住了就把大公鸡按在无人处,拔它尾巴上的毛。我还清晰记得,那一刻的心情是激动、欣喜和恐慌。我估计大公鸡也是感到疼的,它咕咕咕地叫着,在我们手中挣扎,我们也不敢拔太多,一是担心它会死,二是怕被它的主人发现,到时如果要找我们,那就麻烦了。被拔过毛的芦花大公鸡脸红红的,它一定很冤,想骂我们,却又没法开口,等我们一松开它,它抖抖身子,赶紧逃走了。我们也松了一口气。转身赶紧找到合适的书本,把鸡毛小心翼翼地先夹放好。
村上有两个男孩子,老是喜欢欺负我,母亲曾为此教我,让我也要学凶一点,这样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了。有一次,住在河西头的“拖鼻涕”一直追到家门口来,火柴盒里装条毛毛虫,又想欺负我。姐姐为了帮我出气,老账新仇一起算,出门就跟他打上了。“拖鼻涕”比我大两岁,比姐姐小一岁,按辈份我们得喊他叔。这个喜欢欺负我的叔叔根本打不过我姐姐,他落荒而逃,被我姐姐一直追过那座小水泥桥,看着他慌忙地把自己关进家门,又把门闩上。
我十一岁那年春天,整个村子都在桃红柳绿的掩映里,这个时节,可以插养的花很多。屋前岸旁的桃花、樱花、玉兰、梨花,以及田野里的油菜花,这些花水养容易,起码可以存活三天以上。这时低处的河流也最是好看,到处都是花和植物的倒影,红的、绿的、白的、黄的,一丛丛,一片片,还有绿油油的青麦苗,也荡漾在深深浅浅的河水里,无论目光落在哪儿,都是一幅幅生动的油画……
木制的大衣橱上,那面右上角雕刻了金边牡丹花的镜子中,我看见那时的自己,瘦削,短发,眼光清亮而又略带忧郁。至今仍记得,四月里紫色风铃花一直开到木楼外的水泥晒台上,落花的夜里,睡在床上会听到花朵落到水泥地上的声响,花朵与地面的接触,“噗突噗突”,像某种很难形容的语言,就仿佛我心中,命运过早灌给我的——沉重与忧心……
午后发亮的阳光下,微风和煦,独自往田野里踱步是我的去处之一。大片的青麦苗和油菜花堪称浩瀚,粉红色的紫云英,细小的蓝色婆婆纳,更低处的潺潺河流……我觉得它们都是长了心的,在我和它们说话的时候,它们也在即时回应我。那些芳香的春天与我心息相通。有时我走累了,就挑一侧干净的田埂坐下,抬头看蓝天上飘过的白云,低头看身旁美丽却道不出名字的小野花,心中有默默的赞叹与遗憾,而这样的赞叹与遗憾——同样只是与春天分享。
一个长久以来都没有忘记的真实梦境:同样的春天气息,令人无端有些兴奋与欢喜。不远处的农田里,各种植物的混杂味道交织着不断漫上来……在梦里如此清晰。那一刻发现自己又回到儿时,一群不到十岁的孩子,在邻居家二楼的水泥地板上捉迷藏。春天明亮的阳光从头顶的石明瓦窗户里打进来,长条的阳光里,细小的尘埃在闪烁舞动,能够闻到屋外低处河水的味道。
我看到自己东张西望寻找其他伙伴,他们全都躲起来了。结果时间到了,我一个人也没有找到,我输了。所以我又蒙住眼睛,趴在他们家有一架缝纫机的墙壁旁边,数到十以后,我又楼上楼下前前后后开始找。这一次,我从邻居家花布帘后的马桶旁找到一个,从大衣橱里找到一个,在楼下灶间菜橱的旁边找出两个……我很快就把他们全部找了出来,他们被我找到后,一律站在楼梯下面的天井里。细雨一样的光线倾斜,把他们照得那么耐看,我甚至清楚地看见他们脸上的细小汗毛与雀斑。他们身上沮丧与愉快的双重情愫感染着我,让我在那一刻的梦里,感到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欣喜与满足……这是被我记住了的梦,还有一些梦,醒来就忘了,再也想不起来。
夏天时,田间地头,满眼都是开了花的马兰,一簇簇、一丛丛,高高矮矮,疏密有致,像紫蓝色的火焰。马兰花被采回家来,养在装了水的瓶子里,一天过去,第二天花瓣就开始萎谢了,蔫蔫的再也打不起精神。有时也会心血来潮,用一只蓝白的瓷碗来养花,通常这样做母亲总是要说话的,她嫌养过花的碗,再用来盛菜总是有点异样,而我却不觉得。母亲见形状像小向日葵的马兰花不挺刮了,有时就自作主张,不经我同意就赶紧将马兰花倒掉了。
木质的长台上竖着几枝荷,那时感觉养荷一定要用玻璃瓶子,大半瓶水在里面晃漾发亮,插在瓶子里长长的茎看上去有些异样,碧绿的,特别粗。荷是从出村那条石板路尽头的野塘里采来的,我还记得那些夏天,她们在晨风中摇曳的样子,虽然不是很大的荷塘,荷的长势却很好,满满一池,周围空气里是淤泥跟荷混杂的气味,除了香,还有一股涩涩的刺鼻的辛辣。
由荷让我想起的还有那个年轻疯女人。她家就住在那个荷塘旁边的拐角处,家门前有片不大的水泥场地,一个井台。至今没有忘记疯女人的脸长得很好看,但表情又是一副很凶狠的样子。不得而知,她从何时起开始变得神志不清,那时只是听大人们说,她是因为谈了一个恋爱谈痴的。搜索记忆,竟没有她正常时候的样子,似乎是从我认识她开始,她就已经疯了。还记得她的父亲中等个儿,背有些驼,目光是浑沌的,她的母亲做事说话都很快,纤细的身材,脸上的皮肤白皙,不太像一个典型的农村女人,不知怎么,我总很难把那个疯女人与她联系起来,我甚至有些不相信疯女人会是她的女儿。
关于疯女人,还有一幕至今没有忘怀。那是一个盛夏的正午,疯女人被一根铁链条锁住双脚,锁在井台上,她的母亲是想帮她洗洗,却一时忽略了她的两只手还会动,更不曾想到她会忽然间就把自己浑身上下的衣服全都撕脱干净,力大无比……她脱光了的身体那样丰满,我至今还记得她母亲,为此那一脸的羞愧与苦楚,她说我造了什么孽呀,丢人现眼啊。她本来是舍不得将自己疯女儿的两只手也绑上,没想到闯了这个大祸,她对所有路过那儿围观的人说,你们不要看了,快走吧。一边连哄带吓把她的疯女儿拉回家去。
盛夏午后,户外几乎看不到人。太阳光照得地面发白,就差没有烧起来了。午觉后起来,人恹恹的,好像还没有睡醒。坐在木门前的小矮凳上,什么也不想,只是发呆,一阵细小的穿堂风这时从皮肤上走过,感觉也是热热的。
凤仙花小小的花朵此时浓艳,无论红色或白色,在屋檐下和河滩边散发着独特而强烈的自身气味。狗尾草毛茸茸的尾巴到处都是,我常常在夕阳中和它们凝神相望,人世的炽热与深浓,就藏在光线中它们给自己围上那一圈金边上……
等入了秋,房前舍后的鸡冠花就开足了。鸡冠花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形象了,太像村子上大公鸡的鸡冠了,有时看着一只“油亮脖子金黄脚”的大公鸡昂首挺胸从家门前走过,就又一次觉得,它的头上像顶了一朵移动的鸡冠花。很奇怪我养过的花中,为什么从来都没有鸡冠花,似乎它生来就不在我关注和接受的范围之内。
金黄的小野菊这时最受我的青睐,她们绚丽夺目地盛开在河岸旁、某处的石堆上,或是田间地头,每次看到她们,我的心情都会为之喜悦振奋,像马兰花一样的头状花序,花朵要比马兰花略微大一些,花瓣也要密集一些,小野菊被我水养在碗里或玻璃瓶里的灼灼样子,这一刻仿佛就闪耀在我的眼前。
中秋前后,桂花树上的桂花开了,细细密密的,乳白或乳黄色,这时的空气仿佛是流动的香液,哪个角落都能闻到桂花的甜味。这时我要想水养几枝桂花就更容易了,剪下来的桂花枝杆硬硬的,不用像对待其他花那样,要格外小心翼翼……桂花养的时间最久,起码一个星期不成问题,有时看着花已经泛黄了,但养在瓶里依然好看,走近了闻,发现还在飘香。
到了冬天,那些花花草草全不见了。而这时,家门前河塘四周的芦苇花却开了,白色的,飘逸空灵,随意剪下几枝来插放,就感觉心里多了欢喜,而自己也就更像自己了。
那时的冬天,每年都下雪。下在河滩边、圩埂上、田野里、石堆上、房顶上……脚踏积雪的声音,咯吱咯吱响在我的耳畔,可以复活已然远去的那些光阴。雪过天晴,阳光亮得异常,照着被雪覆盖的一切,让人晃眼,这时发现自己的手指也被冻得很冷,有些微红透明的感觉,每个人讲话时,嘴边都冒着一缕缕热气……
印象中有那样的早晨——醒来时,发现周围异样安静,整个室内的光线都特别亮。下楼梯时,母亲已从南边地里回来了,她的竹篮子里,油绿的青菜上有残存的白雪和旷野里的寂寥与寒冷……
是的,这些纵然远去的生活,就是一个地方,记忆不灭,从那里升腾而无从遗忘。唯一的童年以及少年,它们犹如那一道道指纹,镶嵌在我的手指上,任何时候,我只要拿起来看上一眼,就会发现自己在这个天地间的身世与气质,犹如是我的肌肤与我长在了一起,同样独一无二,她带着我的呼吸和体温,所有关于我的往昔都一一藏在那里,时隔多年,我依然像受了召唤一般,指纹里的往昔——随时都要我将它们热切地细细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