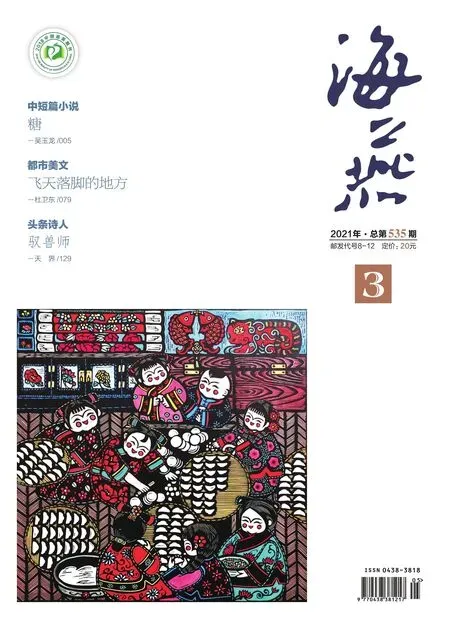读诗记(九)
超现实的光明的对称
希腊诗人奥德修斯·埃利蒂斯有一篇广为人知的文章——《光明的对称》,它是诗人创作理念的表白。这里,我们先简单概括一下他的基本观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的诗作。
诗人认为:他并不是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彻底追随者,超现实主义对谵语和“自动写作法”的迷信,他无法接受。然而,超现实主义有极大的合理之处和创造价值,它冲破了统治西方的僵化的理性主义传统,将人们的头脑和感觉洗刷一新,给垂死的世界注入了生气。而这些合理成分可以吸收和转化到希腊文化的光明之中。
在具体的写作方法上,埃利蒂斯从来不乏味地还原事物,而是接受由想象力激发的语言的奇异指引,道出一种内在生命的感觉。这种超现实主义诗歌使人惊愕、迷醉,在瞬间开放心智、感官,有突然来电的感觉。他强调自己一直在追求诗作的“透明”,这种透明非关理性和逻辑的清晰,而是诗人的生命意志与自然邂逅中达成的超自然的“光明的神秘”。在此,透明是指澄明朗照的生命诗学之光,它“在某个具体事物后面能够透出其他事物,而在其之后又有其他。如此延伸,以至无穷。这样一种穿透力正是我努力追求的。”诗人相信,这种透明将具有摆脱陈旧束缚的现代魔力,引导我们发现真正的现实。
对照上述说法,我们可以感到他一生的写作是有方向感的,拿他早期的《疯狂的石榴树》来看:
在这些刷白的庭园中,当南风
悄悄拂过有拱顶的走廊,告诉我,是那疯狂的石榴树
在阳光中跳跃,在风的嬉戏和絮语中
撒落她果实累累的欢笑?告诉我,
当大清早在高空带着胜利的战果展示她的五光十色,
是那疯狂的石榴树带着新生的枝叶在蹦跳?
当赤身裸体的姑娘们在草地上醒来,
用雪白的手采摘青青的三叶草,
在梦的边缘上游荡,告诉我,是那疯狂的石榴树,
出其不意地把亮光照到她们新编的篮子上,
使她们的名字在鸟儿的歌声中回响,告诉我,
是那疯狂的石榴树与多云的天空在较量?
当白昼用七色彩羽令人妒羡地打扮起来,
用上千支炫目的三棱镜围住不朽的太阳,
告诉我,是那疯狂的石榴树
抓住了一匹受百鞭之笞而狂奔的马的尾鬃,
它不悲哀,不诉苦;告诉我,是那疯狂的石榴树
高声叫嚷着正在绽露的新生的希望?
告诉我,是那疯狂的石榴树老远地欢迎我们,
抛掷着煤火一样的多叶的手帕,
当大海就要为涨了上千次,退向冷僻海岸的潮水
投放成千只船舶,告诉我
是那疯狂的石榴树
使高悬于透明空中的帆缆吱吱地响?
高高悬挂的绿色葡萄串,洋洋得意地发着光,
狂欢着,充满下坠的危险,告诉我,
是那疯狂的石榴树在世界的中央用光亮粉碎了
魔鬼的险恶的气候,它把白昼的桔黄色的衣领到处伸展,
那衣领绣满了黎明的歌声,告诉我,
是那疯狂的石榴树迅速地把白昼的绸衫揭开了?
在四月初春的裙子和八月中旬的蝉声中,
告诉我,那个欢跳的她,狂怒的她,诱人的她,
那驱逐一切恶意的、黑色的、邪恶的阴影的人儿,
把晕头转向的鸟倾泻于太阳胸脯上的人儿,
告诉我,在万物怀里,在我们最深沉的梦乡里,
展开翅膀的她,就是那疯狂的石榴树吗?
(袁可嘉 译)
尽管诗人声称自己不是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彻底追随者,但这首诗有着浓郁的超现实主义色彩。诗人笔力纵横、神思迸涌。诗中所有的奇幻语象都紧紧围绕着一个核心语象“疯狂的石榴树”展开,有着统一的设问句式,但它并不使人陷入某些超现实主义诗歌的混乱的“意象随意并置”之误区。“疯狂”,既指石榴树在风中激烈摇荡的身姿,也指诗人豪放而热烈的生命意志的喧哗与冲动。它的“疯狂”舞蹈朝向一个奇异而博大的引力源:太阳。此诗写了几个与“石榴树”“阳光”有关的意象群,但结构线索却是“透明”的:从时间上是由清晨到正午;从空间上是由庭园——草地——奔马——大海——飞鸟——天空……以至到达更远的地方;从维度上则是旋转式地“向上”的飞升。总体把握了这些后,我们似乎不必再时时驻足于局部的华彩音符,而应吻合作品强劲掀动的总乐章,体验诗人滂沛的气韵贯通感和欢乐而迷人的奇思异想。
“石榴”是象征主义诗人喜欢观照的物象之一。它是对诗歌中智性结构细密和经验鲜润饱满的隐喻。而埃利蒂斯歌咏的不仅是石榴,更是带着累累石榴果实的“疯狂的石榴树”。也可以认为,他要挖掘的是比人的智性更为深邃、更具活力的原始生命力之源。
诗人通篇以设问句的方式表达,其用意之一乃是呼唤人们:告诉我,在艰辛的生存斗争中,我们能否“不悲哀,不诉苦”,像“那疯狂的石榴树/高声叫嚷着正在绽露的新生的希望?”一个真正的诗人就是要按照内心的尺度,在这种张力中捍卫他灵魂的圣洁和超越精神。
埃利蒂斯的诗,是一种生命诗学的宣示。
再看《我们整天在田野行走……》:
我们整天在田野行走
同我们的女人、太阳和狗
我们玩呀,唱呀,饮水呀
泉水清清来自古代的源头
午后我们静坐了片刻
彼此向对方的眼神深深注视
一只蝴蝶从我们的心中飞出
它那样雪白
胜过我们梦尖上那小小的嫩枝
我们知道它永远不会消失
它根本不记得养过什么虫子
晚上我们燃起一堆火
然后围着它唱歌
火啊,可爱的火,请不要怜惜木柴
火啊,可爱的火,请不要化为灰烬
火啊,可爱的火,请燃烧我们
为我们讲述生命。
我们讲述生命,我们拉着它的双手
我们瞧着它的眼睛,它也报以凝眸
如果这使我们沉醉的是磁石,那我们认识
如果这使我们痛苦的是恶行,我们已感受
我们讲述生命,我们前行
同时告别它的正在移栖的鸟群
我们属于美好的一代人
(李野光 译)
说起来这不是埃利蒂斯的代表作,也不是他的重要作品。然而,诗人精神境界的恢宏和谐仍然令人称道。
“我们整天在田野行走/同我们的女人、太阳和狗/我们玩呀,唱呀,饮水呀/泉水清清来自古代的源头”。
意象饱满、情感丰沛、色彩浓重,又粗犷又细腻,亮丽得耀眼。这场景,这饱含着世俗风情韵味的叙述,唤起了我们对生活的回肠荡气的迷醉,启动了我们的感觉和想象。
这是积极健康的现实生活,这是脚踏实地的行进。
然而,当“午后……一只蝴蝶从我们的心中飞出”,诗人突然把这世俗性画面涂上了超现实主义油彩。通过这一转换和提升,别开生面地把我们带入心灵的层面。在延续下来的暖色基调上,让一只雪白的蝴蝶——温情、希冀和精神存在的化身——作“永远不会消失”的飞翔。“胜过我们梦尖上那小小的嫩枝”,虚幻、晶莹、迷离。当我们怀着从田野感染到的同样的热情和欢愉,注视着这一新意象的引领时,我们又突然发觉已被升腾到生命的形而上的国度。
晚上我们燃起一堆火
然后围着它唱歌
火啊,可爱的火,请不要怜惜木柴
火啊,可爱的火,请不要化为灰烬
火啊,可爱的火,请燃烧我们
为我们讲述生命。
在这形而上的世界里,白蝴蝶隐去了,作为譬喻和象征的火燃烧起来。这是生命之火,红彤彤灵动的生命之火。面对这火焰,诗作原来浓郁的玫瑰色语境中渗进了丝丝缕缕形而上的惆怅与焦虑。诗人突然亢奋地呼吁人类珍惜这火,别怜惜木头维持这火的热烈,不要让这火熄灭,要让这火永远燃烧……诗人暗喻当黑夜降临时,只有生命是光,是歌,是延续,是黎明,是翌日……
要知道,诗人写作这首诗的时候,并非太平盛世。那时欧洲和整个人类正陷于最黑暗最疯狂的浩劫之中。一方血腥屠杀、一方浴血奋战,生命遭受到最冷酷的摧残。而就在这一时刻,诗人舍弃了主导性的现实背景资料,以超越时代的姿态,选择了颇具思维张力的光明的一端,高昂地举起了生命诗学的旗帜,向我们唱起了他的不朽不泯的生命之歌。他深情地叙说:“我们讲述生命,我们拉着它的双手/我们瞧着它的眼睛……”
这首诗让人共振和佩服的,是诗人的话语姿态和高度。面对这个充满灾难的宇宙和活跃着邪恶的世界,诗人坚信并坚持生命的价值,诗人坚信罪恶的猖狂是暂时的,并不构成生活的本质,而拥有光明和欢乐的生命则是坚不可摧的。至少,诗人是在希冀和祈祷着它的永远和永恒。诗人的这种信念、认知和善良,鲜活地体现了诗歌精神的一种真髓。
“我们整天在田野行走/同我们的女人、太阳和狗……”是的,我们,我们人类,一直,也将继续这样走下去。充满欢愉,充满信心。不论是灵、是肉;不论形而上的,或形而下的,我们的整个生命,特别是我们生命中属于诗歌那一范畴、那一瞬、那一种存在,将像诗人呼吁的,将继续它的行程。我们知道我们在奔向哪里,我们知道什么在迎接着我们。我们不仅为了目标而兴奋,这一行进的过程本身也是欢快和迷人的。
希腊诗人埃利蒂斯这样宣示。
也只有诗人有能力永远这样说:“我们属于美好的一代人。”
最能代表埃利蒂斯诗歌成就的,是他的长诗《英雄挽歌》,原诗三百余行,我在这里选录两章:
4
他躺倒在烧焦的斗篷上
让微风在寂静的头发上流连
一根无心的嫩枝搭着他的左耳
他像一所庭园,但鸟儿已突然飞走
他像一支歌曲在黑暗中钳口无言
他像一座天使的时钟刚刚停摆
当眼睫毛说着“孩子们,再见”
而惊愕即变成石头一片……
他躺倒在烧焦的斗篷上
周围的岁月,黑暗而凄冷
与瘦狗们一起向可怕的沉默发出吠声
而那些再次变得像石鸽的钟点
都来注意地倾听
但是笑声被烧掉,土地被震聋
也无人听到那最后的尖叫
整个世界随着那尖叫而顿时虚空。
在那五棵小松树底下
没有其他像蜡烛般的东西
他躺在烧焦的斗篷上
头盔空着,血染污泥
身旁是打掉了半截的胳臂
他那双眉中间
有口苦味的小井,致命的印记
那儿记忆已经冻结
在那黑红色的小井里。
不要细看啊,不要细看那地方
那儿生命已经沦丧
不要细说啊,不要细说是怎么
梦的轻烟是怎么上升的
因为就这样,那一顷刻,一顷刻
就这样啊,一顷刻将另一顷刻抛弃
而永恒的太阳就这样从世界走开了。
12
在茂盛的芳草上迈着清晨的步履
他独自上升,满脸霞光熠熠……
采花的顽皮姑娘们偷偷向他挥手
向他高声说话,声音在空中化为雾气
甚至树木也爱抚地向他低首
将枝头的鸟巢撩入了两腋
枝叶浸在太阳的油彩里
奇迹——怎样的奇迹呀,下面大地上
白种人用天蓝色的犁头切开田野
山脉如电光在远方闪耀,而更远处
是春天的群山那不可接近的梦寐!
满脸霞光熠熠,他独自上升
喝醉了阳光,亮透了一颗心
以致在云中也能看见真的奥林匹斯山
而朋友们的和散那在周围浮沉……
现在梦比血液跳得更快了
动物在羊肠道两旁聚集成群
它们像蟋蟀般吱吱叫唤
仿佛说整个世界实在是庞大无垠
是一个逗弄自己孩子们的巨人。
水晶之钟在远处长鸣不歇
明天,明天,他们说,是天上复活节!
(李野光 译)
《英雄挽歌》副题为“献给在阿尔巴尼亚战役中牺牲的陆军少尉”。这首长诗写于1943年,出版于1945年。1940年,墨索里尼军队入侵希腊,埃利蒂斯作为一名希腊陆军中尉,参加了在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战争。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就是这场战役。
“挽歌”是一种古老的诗歌体裁,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顾名思义,挽歌的题材与风格都是有特定范畴的:死亡与哀思。一般地说,“挽歌”的内容多倾诉死之哀怨、世界之苦难以及对神灵慰抚的祈求。但埃利蒂斯笔下的“英雄挽歌”对此做了偏离,有所创造。这首诗的风格是崇高壮烈的,它哀而不怨,苦难而无悔;而且无须外在神灵的慰抚,牺牲的战友本身就完成了神圣的升华——“他独自上升,满脸霞光熠熠……”“明天,他们说,是天上复活节!”这就是埃利蒂斯创造的挽歌——赞歌——圣歌的异质混成的结合。
诗中没有以叙述性话语交代陆军少尉的牺牲,而是采用了现实感受与超现实想象的结合,达到了诗人内在体验与具体事象难分彼此的更高水准的“真实”。诗中写到,那个色雷斯群山的儿子牺牲了,微风在他寂静的头发上流连,一根嫩枝搭着他的左耳,在他的眉宇间那口苦味的小井冻结了,乃至太阳遁驰,万物呜咽;“他像一所庭园,但鸟儿已突然飞走/他像一支歌曲在黑暗中钳口无言/他像一座天使的时钟刚刚停摆”,这些既写出了他牺牲的悲壮,又写出了这牺牲的伟大意义。这正是感情、智性与物象在瞬间凝合后的精彩表达。这是那种简单“记叙”或滥情的诗歌无法比拟的。英雄死于正义战争,他的死是伟大的永生,用不着神灵的慰抚,他本身就是云中新的奥林匹斯山的神祇。诗人还采用了隐喻的变奏与回旋方法,如前面写过的“一根嫩枝”,至后来已成为茂密的林木向他垂首;前面那“突然飞走的鸟儿”,至此已返回,“将枝头的鸟巢撩入了两腋”;前面的“一支歌曲在黑暗中钳口无言”,至此已成为“朋友们的和散那(指希腊人用来赞美神圣的歌声)在周围浮沉”;前面的“天使的时钟刚刚停摆”,至此已成为“水晶之钟在远处长鸣不歇”;而前面写的“太阳就这样从世界走开了”,至此已是“满脸霞光熠熠,他独自上升/喝醉了阳光,亮透了一颗心”。
如上隐喻的变奏和结构上的精心承接,使“超现实”在此完成了超越现实表层直抵其核心的任务,或者说内外现实达成统一,抽象世界和具体世界凝成了更神奇的“绝对现实”。这首诗的语言神奇而精警,结构宏伟而严密,气度与想象力不凡。它无愧于阵亡的战友,无愧于风云激荡的时代,同时也无愧于诗歌——作为一种古老而常新的人类神圣话语方式。
纵观全诗,诗人没有采用叙述性话语交代战争场面,而是以对现实的感受加上超现实想象的变形和融和,写了一个为正义战争而捐躯的陆军少尉,以及他的战友、人民乃至天地同参的万物对他的哀悼、缅怀和颂扬。在这里,挽歌——赞歌——圣歌凝为一体,作品思想的深刻与技艺的精湛均令人叹服。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会反对诗歌反映时代、表达诗人立场。但是,这一切必须是以诗自身的方式来“反映和表达”。那些以粗鄙的分行“纪实”和标语口号式的诗句去行使诗歌社会功能的人,既是对诗的亵渎,也是对时代的不恭。“技艺,考验着真诚”,这“真诚”是指向诗艺也同时指向诗人情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