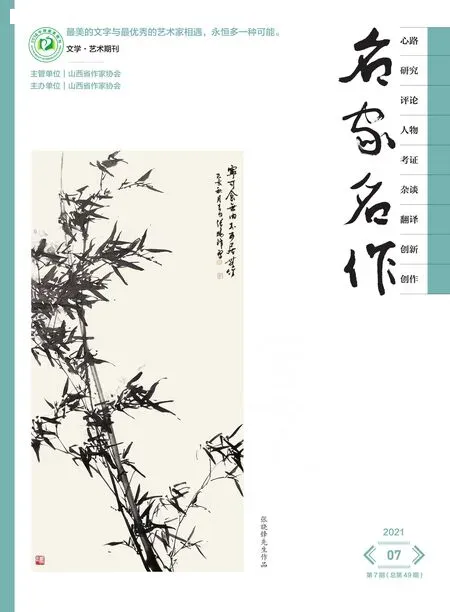现代城市文明冲击下的乡土牧歌——论宋庆莲短篇儿童文学作品
梁谷语
在湖湘儿童文学作家中,宋庆莲有一个特殊身份:一位现代农民。她是湘西古丈县一户贫穷农民家的女儿,意外失去高考资格后,在母亲的鼓励下,怀揣着文学梦从农村来到城市,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但城市中生存竞争激烈,不到半年,宋庆莲的生活陷入困窘,只得接受现实回到乡野,一边接过母亲手中的锄刀、镰头,重复父辈躬耕乡野的生活;一边为孩童书写她熟悉的田野,笔耕不辍。短暂的城市生活与漫长的乡土生活成为其写作内容的主要来源,“故乡—离故乡—归故乡”的人生循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作品风格。如果说其同乡沈从文对乡土社会的书写事实上已经是“都市人”的回望,那么宋庆莲则始终是以在场的“乡下人”之眼看乡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笔下乡土社会的全然真实,相反,恰恰是囿于农民对土地的黏着,囿于写作对象——孩童的特殊性,宋庆莲笔下的乡野人事充满着理想化的牧歌色彩。现代城市文明与乡土社会的尖锐冲突虽然也得以呈现,但在文本中往往得到不同路径的柔韧缝合,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宋庆莲的短篇儿童文学作品是一曲现代城市文明冲击下的带有一定理想色彩的乡土牧歌。
现代城市文明对乡土社会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被视为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在宋庆莲的短篇儿童文学作品中,这一冲击主要表现在乡土社会的自然生态环境变化与乡民主体心理变化两个方面。而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冲击,都最终被作家予以一定程度的弥补,呈现出“常—变—常”“喜—悲—喜”的圆形故事结构。
一、乡土社会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及缝合
现代城市文明对乡土社会的冲击首先体现在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生态环境在塑造文明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势必引起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而引起社会环境的变化。相比城市,乡野农村拥有更丰富的尚未开发的工业资源与生态资源,城市发展初期,要依靠发展工业带动经济进步,势必向乡土社会发起资本主义式由外而内的掠夺。在《银鱼来》和《宝丫的米》中,作家分别集中呈现了工业文明对乡野自然生态环境的冲击。所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要由外来的城里人进行掠夺而造成,后者主要由已经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的乡下人自身造成。相应的,作家所采取的弥补路径也有所不同。
首先,以《银鱼来》为例:扯布寨里的三噶公患有眼疾,宝丫相信喝够109条小银鱼的鱼汤,三噶公的眼睛就会好起来,因此每年都坚持为三噶公捕银鱼。但问题就在于每年捕获小银鱼的数量一次比一次少,“第一次 31条,第二次27条,第三次19条”,待到外来者侵入小溪,借助炸药炸鱼,借助打鱼机打鱼,借助农药毒死鱼,宝丫和“娘”就只能捕到2条鱼了。而这些外来者中,“有的人是从城里来的,有的人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的”。他们所借助的高效率的现代进步工具,是对扯布寨乡民所使用的虾筢和小水桶的碾压,事实上也象征着现代城市文明对乡土文明的碾压。在这种碾压之下,扯布寨的自然生态环境,从曾经的梦幻美景变为了“整条小溪都是死鱼,白花花一片”的恐怖景观。
在表现城市文明对乡土自然生态环境的冲击方面,较之一般作品,宋庆莲更为高明之处在于她从“以自然为舞台”的角度出发,对比展现了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灵自亲密至疏远的过程。因此不仅是美景变恶景,更是乐景变悲景。
就人与人关系而言,当外来冲击尚未发生时,每年一度的“鱼王嫁女”对扯布寨乡民而言更像情感交流与释放的自然平台,“男人们……坐在溪水里露出水面的石头上,有的抽烟,有的说笑话。女人们提着鱼篓,在离自家男人不远的地方拉家常,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很闲散。孩子们在月光下和自家的猫狗玩耍”。因为银鱼的充足(也即生存资源的充足),所以不必担心自家捕不到鱼。摆脱了利益心的束缚,寨民也才能以“闲散”“说笑”的姿态,将这场年度盛事视作“拉家常”的快乐时刻,而不会出现日后喜宝因自家白送银鱼给三噶公而“心里好长时间都老大不痛快……朝三嘎公翻几下白眼,就绕道走开了”的举动。然而当银鱼稀少时,寨民就失去了一个情感联络的平台,人与人的关系相对有所疏远,曾经是人人都在溪畔盼鱼王嫁女,而后来则只有宝丫和娘;曾经狐狸、水鸟、水蛇欢聚一堂,后来都不见了身影。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在生存资源的匮乏中疏远。
资源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现代工业文明思维,这与“捉一放三”的山寨礼俗全然不同。“捉一放三”是封闭环境下乡村为保证生态资源的充足与循环而得出的经验。在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生活中,个体面对的“学习”内容是有限而较少变化的。因此长辈、老人等“过来人”的经验就异常可靠,代代相传以后,即成为具有权威的传统礼俗。当古老的乡土环境不发生改变时,后人遵从前人礼俗,传统经验与其代言人——德高望重的老者就依旧拥有权威。这也是“山寨里的人派高阿公巡逻小溪”的原因。然而当乡土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都发生改变,“捉一放三”的传统礼俗已经无力应对外来冲击时,就需要引入新的保护机制——由国家政治权力保证实施的法律。在《银鱼来》中,作家正是引入这一力量使故事由悲变喜:“那些来小溪用炸药炸鱼的人,用打鱼机打鱼的人,往溪水里倒农药的人,都被抓了起来。小溪里的鱼是不能用炸药炸的,不能放毒倒农药的,也不能用打鱼机打鱼。高阿公又开始在小溪里巡逻,他现在是河长,守护着小溪,守护着小溪里的鱼类。”“抓”“不能”“河长”(官方赋予的职位名称)都透露着国家对乡土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而这一力量或许也正是宝丫娘说出“放心!鱼死不绝的”的底气。
而在《宝丫的米》中,面对被扯布寨的人砍掉的丛林,“……光秃秃的山头,光秃秃的山头,山上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一只鸟,也没有看见一只红狐狸”。作家引入的缝合路径是“自然报应”:“有一次下大雨发洪水,小溪对岸的山体滑坡了,掩埋了小溪,掩埋了山下几户人家新建的房子,幸好人都安全。”只有这样一场更为强硬的来自上天的暴力惩罚,才能促使已然被现代工业文明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被现代城市文明思维异化的乡民感到自发的后悔,才能让乡民们选择重新在那片山上栽种小树苗。作家借助自然生态循环的客观逻辑,对文本中的悲伤情绪进行稀释冲淡,在对不复返的“碾坊”记忆的遗憾追溯中,仍旧使故事情节结构达成一定程度的完满,文本因此透露出虽有遗憾但更为温柔的气息。
二、乡民主体的心理变化及缝合
诚如前文所述,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势必带来乡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乡民主体的心理活动也造成冲击。在宋庆莲的短篇创作中,其笔下人物对“名字”的重视就像一条线索贯穿于其中,提示着乡土人物心理的异变。
“名字”的诞生,是出于定位个体主体身份的编码需要,也是主体被他者破译的首要入口。换言之,“贵姓大名”是出于陌生而使用的。在传统“熟人社会”乡村中,“名字”如何,是否文雅并不重要,乡民并不需要通过“名字”去判断他者。这是因为人与人的熟悉在“无名”状态下已然发生,并不因日后名称的改变而变异。熟人社会中“名字”的使用,仅仅是必要时刻的指称需要,加之文字教育的缺失,未遭受现代文明侵袭的乡民对“大名”是陌生的,对“小名”却是熟悉的。“小名”背后,烙印的是日积月累的情感联结。这也正是《有个女孩名叫小板凳》中,长期陪伴在女孩红红身边的父亲养成了称呼她“小板凳”的习惯的原因,也是《给99颗花草一个小名》中,抚育男孩时光长大的母亲不愿意改掉称呼他“赖赖”的习惯的原因。相应的,“妈妈叫女孩红红,可是妈妈在外面打工,一年也叫不上她几声红红”,对时光而言,也只有在镇上读初中、接受了现代文化教育的姐姐称呼他大名。
然而,被传统乡民冠以“小名”的新一代乡民,对此是不乐意的。女孩红红想要让人记住她叫红红而不是“小板凳”,“女孩想,要是有一天她也能上学读书,她一定要告诉老师,她的名字叫红红……她自己是不能忘记自己的名字的”,男孩时光也十分不满于母亲叫他“赖赖”,因之长期以来与母亲生着闷气。在作家的长篇代表作中,作为农民象征的米粒芭拉的主体觉醒(认为自己与其他米粒不一样)也正是以自我赋名开始的。对于接受了现代文字教育,受到现代城市文明影响的“孩子辈”而言,文雅而富有意义的“大名”有着呈递进关系的双重意义,而其背后是作为“陌生人社会”的城市文明思维与“文字下乡”的影响。
一方面,“名字”首先意味着主体性的解放。对于《米粒芭拉》《有个女孩名叫小板凳》中的主人公而言,对自我姓名的坚持意味着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源自渴望在集体中将个体与他者区分开来的欲望。对于红红而言,“小板凳”成为她残疾人身份的确证,却无法真正为她自身代言。在熟人社会中,由于长期的经验积累与情感联结,“小板凳”这一语汇的所指可以顺利抵达女孩自身,但在陌生人社会中——如女孩与老师、同学的交往中,“小板凳”这一语汇的所指却更可能抵达“残疾人”这一群体类别,而无法指向女孩自身。如同前文所述,确证自我的需要,更多是陌生人社会也即城市的产物,这是因为现代城市中人的流动性极大,城市人面对的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封闭环境与固定群体,而是日新月异的开放环境与流动的陌生人。因此主体需要频繁向他者确证自我的存在,“名字”则成为主体呈现自我的首要选择,也成为他者破译个体的首要入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已然遭受现代城市文明冲击的新一代乡民而言,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掠夺与被掠夺的对立关系,而呈现出互为“围城”的荒谬景象。新一代乡民也不再是单纯的乡下人,相反,他们在以成为准“城市人”为目标来塑造自我。在红红的梦中,女老师两次询问她的姓名,折射的不仅仅是女孩对于上学读书的渴望,更是困囿于封闭的熟人小圈子社会中的女孩对于面向更广阔世界(也即城市)的渴望,“红红”就像她的名片,是她在可预想的“陌生人社会”中确证自我存在的武器。
另一方面,当每一主体都热衷于凸显其存在意义,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便走向紧张,“主体我”同样也是“对象我”,“他人即地狱”的现代生存命题,在乡土社会中也有所渗透、延伸。对于《给99颗花草一个小名》中的时光而言,他不喜欢“赖赖”这个小名的原因主要是村子里的同龄孩子在叫他“赖赖”时,实际上是以“赖赖”的谐音“癞癞”来取笑他是“癞子头”——即头上长疮疤,局部区域没有头发的人。当村中长辈叫他“赖赖”时,他尽管不高兴却仍旧回应,这是因为时光知道长辈叫的就是“赖赖”,而不是充满取笑意味的“癞癞”。因此事实上,时光抗拒的不是小名“赖赖”,而是其抬高自我主体的欲望与他人贬抑其自我主体的事实之间的冲突,是注视他人的“主体我”与被他人注视的“对象我”之间的冲突。
时光误将这一冲突定位为其与为他赋名的母亲之间的冲突,事实上是将“母亲”与“同龄人”混为一谈,统统归为其家乡“他人”类别之下。对此,作家在母亲这一人物上设置突变情节,使得“母亲”形象在时光的世界中突然凸显,唤起“母亲”与自我——而不是他人与自我之间的独一无二的深刻情感联结。当“赖赖”这一称呼不再被赋予来自他人的贬抑意味时,当他对“赖赖”的理解从被同龄人注视的“癞子头”转向为被母亲注视的赖在母亲怀里需要保护的小孩子时,时光的“主体我”与“对象我”也就达成了短暂和解,故事走向圆满。
三、结论
宋庆莲的创作往往呈现出“常—变—常”的喜剧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对于农民的苦难生命的无视和对乡土社会异化事实的淡化。在童话《稻草人妹朵的心窝》中,作为农民麦儿用沾满泥土的双手亲自扎出来的稻草人,妹朵也可以被视作农民的象征。妹朵短暂而充满奉献牺牲精神的一生,也正是农民渺小而伟大的一生的象征;在《宝丫的米》中,作家并未回避“碾坊”所象征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已不再,人与狐狸(自然)的关系已渐行渐远的事实,这一点从作家并未安排宝丫和狐狸妈妈的相见以及结尾处正面抒发的对“碾坊”的怀念可见。只是作家选择令此种遗憾情绪退居于第二位,而以情节上的接近完满冲淡了乡土社会异化事实所生发的浓稠忧伤,因此具有一定理想色彩与牧歌气息,作家的短篇创作因此普遍具有一种“美丽温柔、淡淡忧愁”的气质。一来,是由于作家预设的写作对象为儿童;二来,或是因作家本人天性中的不忍之心的渗透所致。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即便是《宝丫的米》中对导致寨民重新种树养林的那场关键性的滑坡事故的简单描述中,作家也要加上一笔“幸好人都安全”,如此细节,或为天性的自然流露;三来,作家对土地的深沉热爱也是原因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作家短篇创作中情节的反弹往往是借助外部力量促成的,即便是主体力量凸显相对明显的《给99颗花草一个小名》中,时光的态度转变也经由了母亲生病与父亲的训诫等外部事件的刺激。在某种意义上,这或与沉淀在作家基因中的农民集体性格有所关联,值得研究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