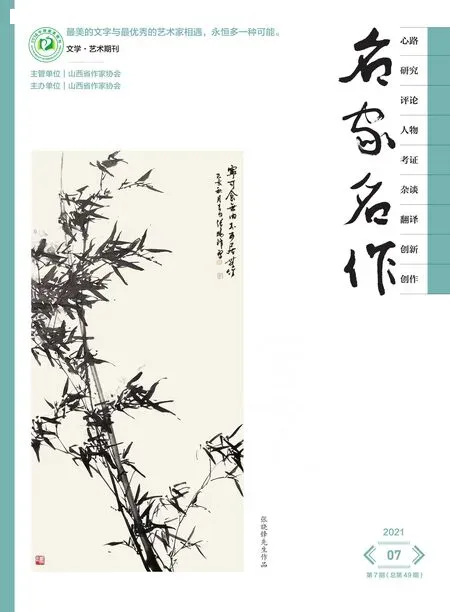苏轼黄州山水闲适诗中的审美超越
李若辰
宋神宗熙宁二年,旨在改善北宋积贫积弱现状的“王安石变法”开始施行,北宋朝内围绕变法分化为矛盾重重的新旧两党,苏轼因与“新党”观点不一,被划归为“旧党”。彼时因屡受“新党”排挤、无法于朝中立足而自请外任杭州的苏轼,几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地方任职八年之久,更认识到了新法施行中的诸多弊端。在“旧党”政治斗争失败之时,“新党”纷纷上奏弹劾苏轼,认为其某些诗文“愚弄朝廷”“指斥乘舆”,“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应“大明诛赏,以示天下”。刚在湖州任知州不久的苏轼因此被逮捕,这场文字狱以其被贬黄州作结。
苏轼于黄州,是政治失意者的无奈修行,也是文学家的精神遨游。对于年已四十五岁、前途渺茫寻不到光亮的苏轼来说,黄州是他人生大起大落之后贬谪生涯的重要节点、文学创作的重要驿站。从元丰三年启程赶赴黄州,到元丰七年离开黄州,苏轼在此次贬谪后共创作了近140首诗,这些诗句充分承载了诗人这一程的行迹与心境,成为黄州词与散文的侧面体现。尤其是其中近30首山水闲适诗,更是诗人一步一步创作轨迹、性格心态、价值观念的记录。山水在诗句中拥有性格与灵魂,“好山水把逐臣变作了一个完全的诗人,而诗人也把这好山水带进了文化史”。
一、苏轼贬黄山水闲适诗的题材特征
(一)漫步山野田圃,“便为齐安民”
黄州古称齐安,东坡居士到达黄州,已经做好了成为普通“齐安民”的准备,“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他的山水闲适诗最重要的抒写对象便是黄州常见的行旅山水与生活中常见的田圃。
元丰三年,苏轼与弟同游武昌县寒溪西山,诗人落寞的心情与山水碰撞,作《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暂时将失意流落的情绪寄托于山水之中,以求获得片刻的肆意与解脱。山水之间草木层层,寒溪泠泠,诗人在这样清幽自然的山水中欣喜于与弟弟的重逢,又思及子由受到自己牵连而内疚,“行逢山水辄羞叹”,深切感情萦绕心中,也借此安慰子由“自坐迂阔非人挤”。既喜悦又落寞苦痛,心情复杂的诗人将精神轨迹留在了寒溪西山的自然中,喟叹不已。
为缓解没有俸禄的困窘境地,苏轼于黄州东面的“东坡”亲自耕种。《东坡八首》真切记录着苏轼田圃耕种的日常生活状态与心情。废弃的营垒无人照顾,“颓垣满蓬蒿”,荆棘遍布崎岖不平的坡地,再加上天旱,开垦工作格外辛苦。“下隰种粳稌,东原莳枣栗”“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诗人真正接触着农民的生活现实,他的这些山水闲适诗更加切实,令人感同身受地剖析着某个时代某个阶层最朴实的状态,既是真实的记录,更是精神文化的厚重颗粒于落地一瞬的升华。
(二)停驻寺观亭台,“更须携被留僧榻”
苏轼抵达黄州,无官舍可住,先是寓居定惠院,随僧蔬食,后妻儿到来迁居临皋亭,“甚清旷,风晨月夕,杖履野步,酌江水饮之”。东坡与寺观亭台的不解之缘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山水闲适诗之中,诗人思想中“归诚佛僧”的佛禅渊源逐渐饱满。
在寓居定惠院之时,苏轼曾写下《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与《次韵前篇》两首诗。睡至夜晚方出门漫步,此时清诗只能“独吟”,却兴致来了自和一二,杯中的酒已饮尽亦无好友借添,在自我慰藉中也警戒莫要“醉里狂言”,这月夜的落寞与心有余悸的痛感暗暗浮现。独自往来的幽人如今只拥有孤寂的清月夜,与去年在徐州对月酣歌、令人怀恋的夜晚遥遥相对。诗人在《次韵前篇》中寄予了浓厚的人生感想,面对着滚滚东流的长江水,诗人感叹自己白发徒生,想要归隐却舍不下“致君尧舜”的愿望。
苏轼平常生活中常常交游佛寺僧人,默坐学佛,“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诗人的失意暂且在佛禅中得到了解脱。安国寺的住持继连是苏轼在黄州结交的第一位僧友,于安国寺,诗人写下了《安国寺浴》《安国寺寻春》,好兴致的诗人卧闻春意,遂起而寻,诗人照旧“叹老忆年少”“思家愁老翁”一番。同月一日冒雨登四望亭,诗人感叹人生如梦与年将迟暮,海棠花落尽,如同一场来去匆匆的梦,诗人的这种虚无缥缈的恍惚感在黄州的作品中格外明显。“暮色千山入,春风百草香”,天已晚而春天亦已晚,苍苍竹木更添萧瑟之感,突然不知何处而来的鹳鹤鸣叫声铺满天际,声音响彻更反衬了环境孤寂,以动衬静,夕阳作结,整个画面的氛围才得以完整。
寺观伴随东坡走过黄州的贬谪岁月,佛禅思想伴随东坡一次又一次的失意与豁然。清扫默坐的佛禅生活给予了诗人精神暂时停靠的港湾,打击与绝望也许并不能完全消解,却也为东坡旷达胸怀中融入更多慰藉,无论安闲还是落寞,或许都并不矛盾,东坡的精神意念并未停歇,亟待不断重新超越。
(三)赏花有感,“尚余孤瘦雪霜姿”
元丰三年一月,在苏轼前往黄州贬所的路途中,度关山、春风岭,作《梅花二首》,将自己的心情抒发为对草棘间梅花姿态的描写。又曾在满山的杂花中得见一树名贵的海棠,在这幽幽空谷,是谁将遥远的海棠花迁来至此,使其“天涯流落”?
黄州若隐若现的细雨中,那几株牡丹轻轻笼罩着水雾,美丽得如同雪色肌肤的美人;岐亭道上“一点芳心雀啅开”的梅花与印象中“尚余孤瘦雪霜姿”那不变的梅格所同。“安居”黄州的诗人行过山川田野,捕捉到了开阔环境中一角一处的风景,在山水闲适诗中也极爱抒写所赏的这些明媚的亮色与生命绽放的姿态。赏花有感,以花入诗,这些长在山野的花朵也就不仅仅是植物,而是被赋予了文化精神,拥有了更久远的生命意义与审美价值。
二、苏轼贬黄山水闲适诗的审美特征
(一)借物喻人:自然人化倾向
“乌台诗案”作为苏轼人生中与死亡相近的磨难,使得他的诗句中愈来愈饱含厚重的人生感慨。眼前所见之花不仅仅是沉默的静物,更倾注了丰富的思想意识,成为诗人此时情感的寄托,再独立于情感牵连之外,成为独一无二的定格的精神个体。
从创作的艺术角度来看,诗人从植物本身联想到了自己主体生命的遭遇,托物言志,借物喻人,具有有迹可循的自然人化倾向。
在黄州的山水闲适诗中,梅花是苏轼偏爱抒写的植物。从诗人赶赴黄州的路途中春风岭上之梅,到岐亭道上所遇梅花,再到有感而发的红梅,梅的品格正是诗人赞扬并努力坚持的品格。“一夜东风吹石裂”,深幽孤寂的山谷里,水流清冷,烘托了鲜艳梅花生长环境的恶劣。偏又一夜东风飞雪袭来,裹挟着寒梅“渡关山”。苏轼此时又何尝不是要渡人生的关山呢?“乌台诗案”刚过,劫后余生又前途渺茫,虽然诗人已经开始考虑安闲人生、安身立命,却也无法就此完全不问政治而消解人生的苦痛。关山难渡,诗人的心境也早已“细雨梅花正断魂”了。所以此时,开在幽谷草棘间“无聊”又“落更愁”的寂寞寒梅,被诗人大笔一挥进行了人格化,成为诗人沦落天涯的好友,飘落清溪,随流水潺潺,相送我直到黄州。苏轼所认同的“梅格”,是哪怕“故作小红桃杏色”也能“尚余孤瘦雪霜姿”的孤傲姿态,是冰清玉洁不流于世俗的坚持,又何尝不是诗人自身的傲骨与高格?
海棠在苏轼眼中的意义与寒梅相近但有些许区别。在他寓居的定惠院附近,满山杂花相映中,诗人漫步一株海棠树下,借海棠树的遭遇暗喻自身流落的境遇。海棠流落在寂静无人的幽深山谷,对与海棠类似的“朱唇”“翠袖”的描写,更是直接拟人化。此时的诗人正逍遥而行,见此高贵的“佳人”,就好像被海棠的绝艳反衬出自身的衰朽,只好“叹息无言揩病目”,海棠是如何流落至此?“天涯流落俱可念”,这种深切沉重的流落之感,精神的苦闷难以排遣,不如一樽酒来与这同样苦闷的海棠相对,甚至是与友人惺惺相惜、对酒当歌精神观念复杂交织又自然真挚,显示出难以复制的超然格调与理想人格。
诗是苏轼思想的化身,诗中的这些不同姿态的与诗人有缘的植物,或许是他沦落天涯的写照,或许是他孤独落寞之时的知交好友。思想是灵活生动的,植物便是生机勃勃的、拥有灵魂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反映出自然人化的审美特征。托花寓意,诗人含蓄蕴藉、不露不张的语言里,饱含着大起大落的思想历程与不断发展的人文主义精神。
(二)烘托手法的运用
如何将所见山水景色最为形象逼真地融入语言与诗句之中,以及如何在自然描写中避开生硬转化而获得情感的升华,或许可以从苏轼此时的山水闲适诗中窥得一二,尤其部分诗句中,烘托、映衬的表现手法给予人的感官与思维理解的途径。《海棠》中“香雾空蒙月转廊”,东风轻柔吹拂着光华,诗人置身于朦胧缥缈的氛围之中,欲趁月光赏花,月却偏偏“转廊”而去,在空蒙的意向群中,诗人用“月转廊”的消失来烘托自己心切的“烧高烛”。当时自然现象夜晚已深、月光角度的变化,却被诗人如此解读,恰恰烘托出了“恐”赏不到海棠花与“烧高烛”的行为。
读者对风景的重新认知,不仅仅依靠想象与理解,更在于诗人最直接想要传达的是怎样的画面。雪后“门外山光”侧面用“马亦惊”来烘托漫山的雪色,“写山光,真写得出”,起笔即精妙;牡丹在“清寒入花骨”的挫折环境烘托中,反而更加“肃肃初自持”,在傍晚的暮色里也更显萧瑟。环境的烘托正是描写对象时的催化剂,在常见的烘托手法中自然而然地增强了表达效果,丰富了语言艺术的审美意义。
(三)动词运用得出神入化
静态的自然景物在精准生动的动词修饰下更具表现性与审美活力,在苏轼贬黄的这些山水闲适诗中,即可捕捉到动词带来的美感与充满自然张力的想象性。苏轼往岐亭访好友陈慥时所记录下“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初春时节,大自然一派春意,江边柳树欣欣向荣,这里所使用的动词“摇”,首先把江柳人格化,摇曳生动而非暮气沉沉,再将整个早春的萌动感作一点睛,正好符合水流的动感。
《雨中看牡丹三首》中雨滴落在牡丹花瓣上的美妙画面,“的皪走明珠”一个“走”字,雨滴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一般,牡丹自身的国色天香依赖“秀色‘洗’红粉”“暗香‘生’雪肤”,正如眼前一位佳人晨起对镜梳洗,肤如凝脂。在人格化之中,利用精准的动词增强画面感与想象力,《海棠》中“东风袅袅‘泛’崇光”呈现出温熏氛围的腾起。炼字正体现了诗人严谨的创作态度与深厚的文学素养,也令我们从中触摸到一位文学家遨游世界的想象力与运筹帷幄的能力。
在这近三十首山水闲适诗中,除了诗人常见的审美特征之外,也可以较为明显地感受到一些写诗的手法与特色。例如苏轼手到拈来的诗歌理趣、人生哲理成为山水访游中精心调制的颜料,而令苏轼不断感到人生如梦的黄州,无论是相似的慨叹“万事如花不可期”,大梦黄粱一枕的虚无感,还是“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中,命运就像大磨中的渺小的蚂蚁,挣扎其中却无法逃脱。这些苏轼曾感慨过的理趣,均是其流落黄州、遭遇人生濒死挫折之后,超越人生普通悲欢喜乐的生命思索,继而在理性的角度趋向统一。苏轼后来离开黄州之后,对这段贬谪生涯进行回顾,这种深刻的哲理性思索尽在《谢量移汝州表》中:“只影自怜,寄命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
三、结语
山水闲适的诗歌对苏轼来说,是诗人们走进自然又重新超越的情感载体。“苏轼的山水诗不再把山水当作体道之物、媚道之形,他既不像魏晋六朝的人那样站在自然之外,也不像唐人那样站在自然之中,而是站在了自然之上,艺术地把握了自然,使之成为自己求诸内心的工具。”也就是说,当山水自然与情感同一所归之时,山水自然的审美性便随之达到了文化意义层面的高峰。这不仅仅是命运轨迹的真实映射,更是精神园地与审美艺术触碰并融合世间万物的理想追求。
而从之后一贬再贬直到儋州海岛的境遇来看,黄州并不算人生最荒芜的低谷。但刚刚从“乌台诗案”劫后逢生的苏轼,当下却正是对政治绝望并心有余悸。旷达的胸怀使得他多次乐观以待,流落的不遇之悲又带来数次的苦痛。这时的苏轼做不到完全摒弃政治而不被世俗拖累,但仍然可以在山水自然中找寻灵魂的栖息地,并且物我为一,在自然之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黄州时期的山水闲适诗,在诗人寓居的寺观缓缓踱步,在逍遥的山水间悄然生长,它是诗人暂时停歇的驿站,是理想思索的隐性挣扎,更是走向其人生澄澈的精神超越中,从情感宣泄到情感升华中极其重要的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