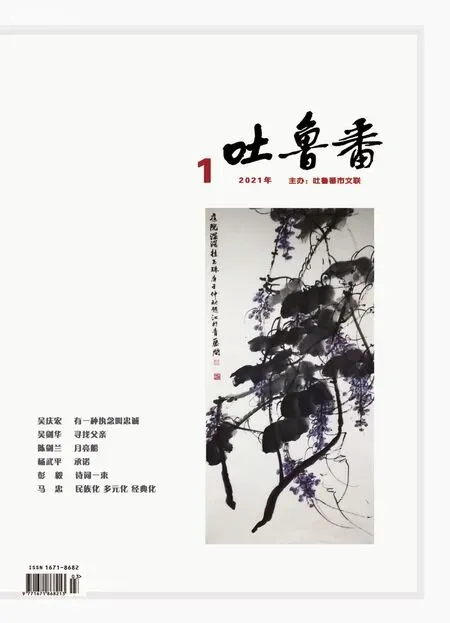送别
马乾
“……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朱自清《背影》
在我四十年光景的人生旅途中,有四次刻骨铭心的送别。前两次,都是我作为懵懂的少年,被父亲送别。他从我身旁离去的渐行渐远的身影,使我从心底升腾起丝丝缕缕的牵挂。后两次,是我为人之父后分别对一双儿女和妻子的送别。我依依不舍地挥手,让流淌在血液里的那份牵挂数度燃起,更感动于三代人之间亲情的代际流动和血脉的香火延续。
父亲第一次送我,是我考上新疆大学去报到。那是1997年8月末的酷暑,父亲背着我的行李,从五十公里外乌鲁木齐的乡下家里一路送来。下了区间大巴车,再倒两次市区公交,跌跌撞撞,一脸的疲惫,但他浑身上下透着执着和满足。那时的父亲,已经六十岁,却不让十八岁的我扛行李,只让我拎着几个零碎的包裹。一路上,父亲一改往日的少言寡语,总是和我没话找话,还主动和邻座的阿姨话聊,说我是我们村里最早也是唯一考上大学的村里娃,还是211工程的大学呢。我就纳闷,他竟然也用“211工程”来炫耀啊!几次与他的目光碰撞,我都读出他的欣慰和骄傲。
进入市区,换乘的公交车在高楼间穿行。父亲睁大眼睛,像未见世面的孩子,对城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到学校注册时,父亲主动走近班主任王老师,热情地握住那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毛头小伙子的双手,那么的谦卑,又那么认真地说:“给老师添麻烦了。”王老师明显被他融化了,没有了年轻教师的故作矜持,对我也热情有加。简单的注册后,我们先领了分配到的宿舍钥匙,我把行李和已经很劳累的父亲安顿在我402宿舍里,然后去领书、充饭卡……一路下来竟是一个多小时。再回来时,父亲已经和早到的几个室友混熟了。在我们离开宿舍时,父亲叮嘱我:“那个戴眼镜的大个子,是吐鲁番人。他英语好,你要多向他学习;那个残疾的孩子,是巴州(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你平时多照顾着点他,打开水时,多拎个暖瓶嘛……”说这话时,父亲的一只手抚在我的肩头,伴着深情的凝望,眼神里透着满满的关爱和嘱托。
正值午饭时间,父亲特意要求和我一起去食堂体验一把大学的伙食。在长长的打饭队伍里,沧桑的父亲在孩子堆里,显得那么耀眼。大伙儿都知道,这是大老远送孩子上学来的家长。“老爷子,你放心,我们这里伙食好着呢。”父亲对橱窗里的阿姨,报以憨憨的微笑。吃饭时,父亲显得十分小心,不时擦拭嘴角,撸掉胡须上的饭粒,平时吧唧吧唧的吃饭声也没有了。我在内心笑他的憨态可掬。“饭菜不错,花样也多。你平时注意搭配,别像在家里那样偏食,不吃蔬菜……”我只是点头,回应他的唠叨。
直到送父亲到返程的大巴车站,父亲都是兴奋的。临了上车时,父亲回首丢下一句:“跟你来,我也算是上了回大学。”然后蹿上车,他的身影扎进一车的人堆里,和渐行渐远的大巴车消失在街市柏油马路的尽头。
父亲第二次送我,是我大学毕业到一千六百公里外的喀什地区人民银行工作。我一生都将深刻记忆着的那个时刻:2001年8月6日15点,父亲陪我从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启程。绿皮火车在广袤的大漠绿洲间走了个“之”字,终于在8月8日下午13点10分到达喀什火车站。两天两夜的旅途,父亲很少离开硬卧下铺和那间隔档,他时时凝望着车窗外旷野里的沙丘、芨芨,还有伴随我们大半个旅程时隐时现的天山雪峰。他的眼神里,多是忧郁。不时闯入眼帘的骆驼、马匹和牛羊,才会解锁他的眉头,才会让他短暂地小小兴奋一下,才会断断续续地对我微笑着说,“看,那是一群双峰驼。”“今年的草好,牛羊多肥呀……”
到喀什地区人民银行报到时,父亲像个羞怯的孩子,向接待我们的领导点头哈腰。“辛苦你们了,孩子给你们添麻烦了。”“给他多安排工作,好让他快快进步。”……人民银行的门口正好有家昌吉人开的餐厅,我和父亲吃过两顿饭。期间,他不止一次向餐馆老板兼老乡嘱托,请他帮忙照顾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恐怕是白托。而且我这么大了,难道不能照料自己?现在想想,我那时真是太自作多情了。
8月10日父亲就要离开回家了,单位派车载着我和他到火车站。快分手时,他木讷讷地重复着已经说过多次的那几句话:“你要勤快些,每天早到办公室打扫好卫生。”“多干活,少说话。”“有空了给家里打个电话。”……他的脸上有深深的忧伤,尽管他用勉强的微笑来遮掩,可我依然洞悉他内心的深深伤感。他的心里一定不好受,他是怕我难过而努力掩饰自己的真情。火车启动了,我追着车厢向他挥手。他从狭窄的床边站起,隔着玻璃窗也伸手挥动着。此时,我看到他突然转过脸去,缩回手抹眼泪。我也瞬间一股暖流从眼眶喷薄而出。
父亲给我仅有的两次送别,正好镶嵌在我大学四年生活的两端。前后间隔四年的两次送别,父亲都特别得动感情。前一次是骄傲和兴奋,一如我开启大学生活的激动;后一次更多的是伤感,就像我无限留恋这段青葱岁月的忧伤。
我明白,我上次离家是上学,还是个孩子。距离家也只有五十多公里,周末几乎都可以回家,更何况一年有两次寒暑长假。再加上考大学是我们这个家结出的沉甸甸的硕果,其中有父亲无私奉献、苦尽甘来的回报,他自然是打心眼里高兴的。而这次则是离家三千里路云和月,一年也就回一趟家。甚至几年回不了一次,也是有可能的。更重要的是,这次是来工作,意味着有可能要定居安家,从此和父母远隔千山万水。六十四岁的父亲显然已经预知,他和我这个最小的儿子就是从此见一面少一面,怎么不伤感呢!
好在,这次送别后的2006年,我因考取新疆大学硕士研究生而回到乌鲁木齐,算是再次回到家,回到父亲身边。即使之后重新工作直到父亲谢世,我都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再无分离。
2009年2月24日,女儿出生了,我也成了一位父亲。因为母亲已于前一年离世,父亲也是疾病缠身。加之妻子生产了六个小时无果,又被迫剖腹产并大出血痊愈,身体相当虚弱。我和父亲商量,同意妻子的月子在岳父岳母家坐。
3月2日那天,我抱着出生一周的女儿,和妻子一起从医院出来,来到岳父岳母家精心布置的月子房。那时没有丈夫陪护假的说法,我得回三十公里外的家和工作单位。所以,这是我第一次以一位父亲的身份,送别女儿。在匆忙的送别间隙里,我殷勤地给她喂了几次奶粉。小家伙似乎感应到了我将要离开,在特意给她换尿不湿时,竟然趁我不防,突然一股子尿飙起,呲在了我的脸和手上。这应该是她使足了吃奶的劲,表达对我的热情。我也分明尝到了她的尿的咸味,却是满脸的嗔怪和幸福。我没有急着去洗脸、洗手,坚持用浸了她尿液的双手,给她换完尿不湿,也一任她的尿液在我下巴上挂成水滴。我的这一副狼狈样,引来妻子和岳父岳母哈哈的笑声,也成了我们家多年来茶余饭后的谈资。我深知,这热乎乎的尿液,是女儿传递给我的第一份特别问候,算是她给即将离开的父亲一份重重的饯行礼物。从此,我的肩头有了沉甸甸的责任和绵稠深厚的牵肠挂肚。
接下来,在离开女儿二十一天零七小时三十五分钟的时间里,女儿的小脸庞,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徘徊;电话那头咿咿呀呀的婴儿呓语声,就是我思念的解药。
2021年1月10日,是我告别一双儿女和妻子到离家一百公里外的哈萨克族小村子,参加访惠聚工作的日子。在单位安排送我下乡的疾驰的帕萨特轿车上,我推送出这样的朋友圈:
晨曦未露,严寒正浓,脚步已匆匆。拖着行李箱,走在灯影稀疏的街巷,一轮下弦月正挂在家的上方……儿子从正酣的晨梦中醒来,催促妈妈打来电话,说手机充电器忘带了……
开启一段新征程,总是心里纷乱又踌躇满志的;告别朝十晚八的日常,还是有些留恋。车行了半小时,窗外还是冬雾弥漫……
一时间,我被点赞和网间送别的亲友感动了。但更让我扯心扯肺的还是一双儿女和重任在肩的妻子。
其实,在我整装出门经过女儿房间时,探进半个身子,听到她沉沉的鼻息声。女儿马上十二岁了,俨然一个大姑娘,还是别吵醒了。爱在心里嘛!但要特意去逗逗儿子。我把一张热乎乎的笑脸,凑近他的小胸脯,屏住呼吸,慢慢地嗅到他的小脸蛋,直到耳朵边,再轻轻地咬他的耳朵。小家伙终于从睡梦中惊醒,先是睁开一双涩涩的单眼皮,又立即一个侧翻,“你的胡子扎死人啦”,撒气地滚到一边佯装又睡着了。我丢下一句,“你个坏儿子,爸爸这一去就是一年呢,也不送送爸爸。”他调皮地伸出一只手挥一挥,嘴里蹦出“Bye-Bye”两个英语单词。
可谁知十分钟后,也就是在妻子送我下楼再回到家中时,我分明听到妻子在电话那头清清楚楚地说:“儿子看见你的手机充电器在沙发上,忘带了……”显然,小家伙在我离开时,也睡不着了。用牵挂的心灵和稚嫩的目光,在房间里到处搜寻我昔日的身影。手机充电器,就是他的战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