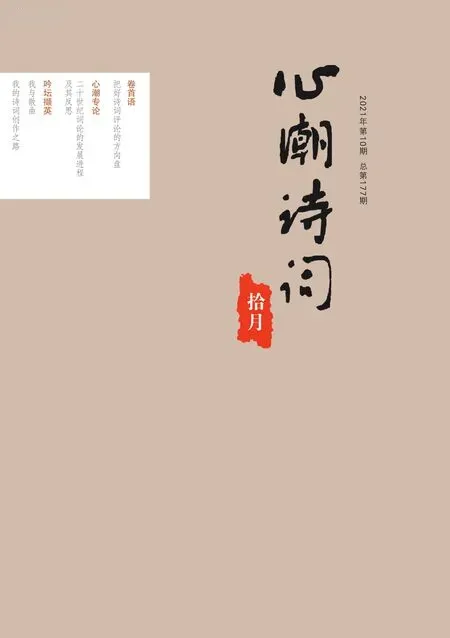以易传之事 为绝妙之词
——论曾缄歌行
周啸天
不知道曾缄(1892—1968)的人,总该知道仓央嘉措吧。曾缄就是将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歌译为七绝体,而又被公认成就最高的那个人。且看夫子自道:“民国十八年(1929),余重至西康,网罗康藏文献,求所谓情歌者,久而未获,顷始从友人处借得于道泉译本读之,于译敷以平话,余深病其不文,辄广为七言,施以润色。”
译诗六十六首,略举四例:
心头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
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
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密意难为父母陈,暗中私说与情人。
情人更向情人说,直到仇家听得真。
美人不是母胎生,应是桃花树长成。
已恨桃花容易落,落花比汝尚多情。
直是落花流水,香草美人,情辞悱丽,兴象高华,自然协律,余韵欲流。深合风人之旨,足见天机清妙。其为汉译经典,上可与北朝民歌汉译《敕勒歌》并肩,下可与姚茫父五言绝句版《飞鸟集》媲美,诚译诗之有滋味者。使人恍想藏中男女,于雪域晨昏,高歌一曲,将使万里寒光,融为暖气,化高山之积雪,回大地之春光。虽属译文,实等再造。至其为论,亦有石破天惊之语:“故仓央嘉措者,佛教之罪人,词坛之功臣,卫道者之所疾首,而言情者之所归命也。西极苦寒,人歆寂灭,千佛出世,不如一诗圣诞生。”(曾缄《仓央嘉措略传》)六世达赖泉下有知,闻此数语,亦当滴泪谢曾缄。
作诗者欲成大器,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条是天机清妙,或谓“多于情”;一条是学识渊博,或谓“深于诗”。天机清妙者,不学而能。学识渊博者,肚里有货,因看到份上,而写到份上。如曾缄者,可谓一身双兼。曾缄,字慎言(一作圣言),四川叙永人,早年游学北大,为黄侃高足。黄先生教学研究之余,喜携学生游山玩水,而经常侍坐的两人中,即有曾缄。无役不与,宴谈常至深夜。故人戏称“黄门侍郎”。今存《西郊禊游诗》,其序作于1940年,时黄先生已下世:
西郊者,在燕京西直门外,都人所谓三贝子花园者也。易代而后,更名万牲,槛兽笼禽,此焉罗列。鸟兽咸若,草木鬯然。公以戊午(1918)上巳之辰,与缄修禊于此,憩豳风之馆,升畅观之楼,遂仿柏梁,赓为此作。属咏未巳,时已入暮,司阍逐客,踉跄而归。其后思之,未尝不笑乐也。良辰赏心,忽逾一纪;昔游在目,遂阻重泉。而缄忝厕门墙,获陪游衍。学射吕梁,曾惊掉臂;抚弦海上,粗解移情。乃奉手未终,招魂已断。池台犹昔,而觞咏全非;翰墨如新,而墓木已拱。抚今怀昔,良以怆悢,故述其由来,追为此序。嗟乎!子期吊旧,悲麦秀于殷墟;叔夜云亡,聆琴音于静室。即斯短制,悼念生平,固将历千载而常新,怀三年而不灭。第摩挲断简,腹痛如何!
含英咀华,锦心绣口,备见才情。程千帆赞不绝口,说:“真是文情并茂。今日读来,当时情景犹在目前。”其古文造诣之深,非同凡响。诗可以玩,须思路开阔,腹笥广大,熟能生巧,始能兴之所至,达到信笔为之,亦精彩纷呈,举重若轻的境界。
曾缄北大毕业后,曾就职于蒙藏委员会,接触许多藏文化。对仓央嘉措其人,产生了浓厚兴趣,始有意搜集、整理、重译情歌。曾缄重译情歌既毕,六世达赖的形象已在眼前活动起来,于是兴不可遏,又仿元白诗体,创作了一首长篇歌行——《布达拉宫词》:
拉萨高峙西极天,布拉宫内多金仙,黄教一花开五叶,第六僧王最少年。僧王生长寞湖里,父名吉祥母天女,云是先王转世来,庄严色相娇无比。玉雪肌肤襁褓中,侍臣迎养入深宫,当头玉佛金冠丽,窣地袈裟氆氇红。高僧额尔传经戒,十五坐床称达赖,诸天时雨曼陀罗,万人伏地争膜拜。花开结果自然成,佛说无情种不生,只说出家堪悟道,谁知成佛更多情?浮图恩爱生三宿,肯向寒崖倚枯木,偶逢天上散花人,有时邀入维摩屋。禅修欢喜日忘忧,秘戏宫中乐事稠,僧院木鱼常比目,佛国莲花多并头。犹嫌生小居深殿,人间佳丽无由见,自辟离门出后宫,微行夜绕拉萨遍。行到拉萨卖酒家,当垆女子颜如花,远山眉黛消魂极,不遇相如深自嗟。此际小姑方独处,何来公子甚豪华?留髠一石莫辞醉,长夜欲阑星斗斜。银河相望无多路,从今便许双星度,浪作寻常侠少看,岂知身受君王顾。柳梢月上订佳期,去时破晓来昏暮,今日黄衣殿上人,昨宵有梦花间住。花间梦醒眼朦胧,一路归来逐晓风,悔不行空学天马,翻教踏雪比飞鸿。指爪分明留雪上,有人窥破秘密藏,共言昌邑果无行,上书请废劳丞相。由来尊位等轻尘,懒着田衣转法轮,还我本来其面目,依然天下有情人。生时凤举雪山下,死复龙归青海滨,十载风流悲教主,一生恩怨误权臣。剩有情歌六十章,可怜字字吐光芒,写来昔日兜绵手,断尽拉萨士女肠。国内伤心思故主,宫中何意立新王,求君别自薰丹穴,访旧居然到里塘。相传幼主回銮日,耆旧僧伽同警跸,俱道法王自有真,今时达赖当年佛。始知圣主多遗爱,能使人心为向背,罗什吞针不讳淫,阿难戒体终无碍。只今有客过拉萨,宫殿曾瞻布达拉,遗像百年犹挂壁,像前拜倒拉萨娃。买丝不绣阿底峡,有酒不酹宗喀巴,尽回大地花千万,供养情天一喇嘛。
这是曾缄代表作,重中之重。盖七言歌行入唐,吸收《西洲曲》及近体诗之韵度,在四杰手中造成一气贯注而又缠绵往复的诗体,特征是四句为节、节自为韵、韵有平仄、换韵处必用逗韵,仿佛是由若干绝句组成;于修辞则多取顶真、回文、对仗、复迭,以增其缠绵。中唐元白,则更多地融入叙事成分,一变而为以《长恨歌》《连昌宫词》为代表的元和体。至晚唐有韦庄之《秦妇吟》,至清初有吴伟业《圆圆曲》。曾缄的《布达拉宫词》,正处在元、白、韦、吴的延长线上。
作者就希代之事加以润色,沉郁顿挫,哀感顽艳,妙语连珠,天花乱坠,如“黄教一花开五叶,第六僧王最少年”,如“只说出家堪悟道,谁知成佛更多情”,如“偶逢天上散花人,有时邀入维摩屋”,如“僧院木鱼常比目,佛国莲花多并头”,如“浪作寻常侠少看,岂知身受君王顾”,如“悔不行空学天马,翻教踏雪比飞鸿”,等等,散行之中,杂以骈语,直令人目不暇接,口舌生香。前人赞美白居易与《长恨歌》之语,如“多于情,深于诗”(王质夫称白居易),如“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赵翼称《长恨歌》),移诸曾缄及《布达拉宫词》,恰似量身定做,无不得体。
曾缄以惺惺相惜的态度写仓央嘉措、译仓央嘉措——本着一种我即仓央嘉措,仓央嘉措即我的态度,信息对称,物我两忘,始臻形象思维之妙境,宜有超越同侪的成就。于是我们可以说,在仓央嘉措成就曾缄的同时,曾缄也成就了仓央嘉措及其情歌。
好事成双,创作亦如之。一如白居易于《长恨歌》外有《琵琶行》,吴伟业于《圆圆曲》外有《楚两生行》,曾缄于《布达拉宫词》之外则有《双雷引》,这也是一篇叙事体的歌行。这首诗写的是上世纪中叶社会巨变的背景下,所发生的一个人琴相殉的悲剧。主人公原型为成都琴家裴铁侠(1879-1950),别号蓝桥生,派宗虞山(此派肇自明清之际,裴氏师承张瑞山弟子程馥)。曾诗有序,颇见史才如传奇文。序云:“蓝桥生者,家素封,居成都支机石附近,耿介拔俗,喜鼓琴,能为《高山流水》《春山杜鹃》《万壑松风》《天风海涛》之曲,声名藉甚。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致厚币征为教授,谢不往,人以此益高之。家藏唐代蜀工雷威所斫古琴,甚宝之。后从沈氏复得一琴,比前差小,龙池内隐隐有雷霄题字,因目前者为大雷,后者为小雷。先是,成都有沈翁者,精鉴古物,蓄小雷,极珍秘。育一女,将殁,谓女曰:若志之,有能操是琴者,若婿也。生适鳏,闻之心动,往女家,请观琴,为鼓一再。归,遣媒妁通聘,故琴与女同归生。生于是挟两琴,拥少艾,隐居自乐,若不知此生犹在人间世也。改革后,家中落,鬻所有衣物自给,将及琴,则大恸。谓女曰:吾与卿倚双雷为性命,今若此,何生为。遂出两琴,夫妇相与捶碎而焚之,同仰催眠药死。死后,家人于案上发见遗书一纸,又金徽数十枚,书云:二琴同归天上,金徽留作葬费。乃以金徽易棺衾而殡诸沙堰。沙堰者,生之别业,生著有《沙堰琴编》一书,此其执笔处也。……余偶适西郊,道经沙堰(在今成都西郊茶店子附近),见一抔宛在而人琴已亡,作《双雷引》以哀之。”诗曰:
何人捶碎鸳鸯弦,大雷小雷飞上天。已恨广陵成绝调,更堪锦瑟忆华年。朝来喧动成都市,焚琴煮鹤真奇事。少城西角有幽人,卜居近在君平肆。不逐纷华好雅音,虽栖廛市等山林。晚为天女云英婿,家有唐时雷氏琴。双琴制出霄威手,玉轸金徽光不朽。断漆斑斑蛇附纹,题名隐隐龙池后。此似干将与莫邪,双龙会合在君家。朱弦巧绾同心结,枯木长开并蒂花。秋月春花朝复暮,手挥目送何曾住。万壑松风指下生,三峡流泉弦上鸣。换羽移宫随手变,冰丝迸出长门怨。歘然急滚声嗷嘈,天风浪浪翻海涛。问君何处得此曲,使我魂动心魄摇。双雷捧出人人爱,自倚蜀琴开蜀派。峨眉山高巫峡长,天回地转归清籁。操缦何如长卿好,知音况有文君在。片云终古傍琴台,远山依归横眉黛。海客乘槎万里来,得闻古调亦徘徊。远人知爱阳春曲,海外争传大小雷。可怜中外同倾倒,名手名琴俱国宝。绝代销魂惜此才,愿人长寿花常好。那知春色易阑姗,花蕊飘零柳絮残。岂必交通房次律,偶然误挂董庭兰。负郭田空家业尽,萧条一室如悬磬。随身唯剩两张琴,周鼎重轻来楚问。归来惆怅语妻子,幸与斯琴作知己。忍将神物付他人,我固蒙羞琴亦耻。何如撒手向虚空,人与两琴俱善终。不遣双雷污俗指,长教万古仰清风。支机石畔深深院,铜漏声声催晓箭。夫妻相对悄无言,玉绳低共回肠转。已过三更又五更,丝桐切切吐悲声。清商变徵千般响,死离生别万种情。最后哀弦增惨烈,鬼神夜哭天雨血。共工头触不周山,划然一声天地裂。双雷阅世已千春,为感相知岂顾身。不复瓦全宁玉碎,焚琴原是鼓琴人。一般风流资结束,人生何似长眠乐。后羿轻抛彃日弓,嫦娥懒窃长生药。郎殉瑶琴妾殉郎,人琴一夕竟同亡。流水落花春去也,人间天上两茫茫。刘安拔宅腾鸡犬,秦女吹箫跨凤凰。但使有情成眷属,不应含恨为沧桑。我闻此事三叹息,天有风云人不测。毅豹养身均一死,木雁有时还两失。嵇康毕命尚弹琴,向秀何心听邻笛。询君身后竟何有,绝笔空馀数行墨。玉轸相随地下眠,金徽留作买棺钱。昔时沙堰弹琴处,高冢峨峨起墓田。从此九京埋玉树,更谁三叠舞胎仙。声声犹似当年曲,只有空山啼杜鹃。
这首诗一度被批为毒草,作者生前亦讳莫如深,如《秦妇吟》秀才。时过境迁,读者应该站在诗的立场上,予以更通达的解读:“此希代之事,非遇无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唐王质夫语)刘君惠曰:“此正诗人之责也。”而不宜鲁莽地、武断地定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或简单地定性为破坏文物案。而应看作是一出命运悲剧,其悲剧性与霸王别姬、杜十娘沉百宝箱等悲剧,从骨子里一脉相通——好景不长,尤物不坚,人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前选择“玉碎”的同时,往往必须搭上自己的最爱,甚至亲手毁掉她。不管用什么托辞,当事者都难逃深深的负疚之感。诗云:“不复瓦全宁玉碎,焚琴原是鼓琴人。……郎殉瑶琴妾殉郎,人琴一夕竟同亡。”诗亦善写音乐,颉颃《琵琶行》:“已过三更又五更,丝桐切切吐悲声。清商变徵千般响,死离生别万种情。最后哀弦增惨烈,鬼神夜哭天雨血。共工头触不周山,划然一声天地裂。”诗人对笔下人物抱有极大同情,方能感人至深,可歌可泣。至如“询君身后竟何有,绝笔空馀数行墨”二语,则简直是作者的诗谶(曾缄在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害致死)。
白居易曾带着复杂心情说,读者喜欢他的感伤诗,即《长恨歌》《琵琶行》,超过喜欢他的讽喻诗,是“时之所重,仆之所轻”。《布达拉宫词》《双雷引》即曾缄之感伤诗也,而亦长于讽喻,有《丰泽园歌为袁世凯作》,诗序杂取佚闻,亦饶文采。如:“袁世凯任中华民国总统,以清丰泽园为总统府,署其门曰新华。国史馆长王闿运过之,阳为不识曰:此‘新莽门’耶?盖讥其有异志也。”“安徽督军倪嗣冲先期献龙袍,以尺寸不合发还。倪大恚,移赠名伶刘鸿升。鸿升一日演《斩黄袍》一剧,所斩者即此袍,识者以此知其不终。”“四川督军陈宦,世凯倚为心腹,至是亦通电宣布独立。世凯知大势已去,中夜仰药自杀。时陕西督军陈树藩、湖南督军汤芗铭亦同反帝制,故时人语云:‘杀世凯者,二陈汤也。’”等等,令人读之掩口胡卢,亦史笔也,不但可助谈资。诗云:
昔日公路(袁术)之子孙,不爱总统希至尊。六人巧立筹安会,一老戏呼新莽门。丰泽园中郁佳气,及时药物能为帝。储贰(黎元洪。自注:元洪任副总统,其秘书长饶汉祥为通电,文有“元洪备位储贰”之言,览者笑之)移封异姓王,旧君(溥仪)翻作乘龙婿。金鳌玉蝀(桥名)变陈桥,诸将承恩意气骄。补衮无功贻笑柄,刘伶先唱斩黄袍。义不帝秦矜爪嘴,书生起作鲁连子。护国滇南举义帜,西南半壁皆风靡。绕室旁皇夜未央,送终一剂二陈汤。怀玺未登保和殿,陈尸已在怀仁堂。当时幽禁先皇处,今日为君歌薤露。挥斧还劳帐下儿,盖棺权借东陵树。草草弥天戢一棺,岂同漆纻锢南山。桓温遗臭非虚语,董卓燃脐一例看。化家为国由儿辈,何意人亡家亦败。皇子流离化乞儿,诸姬织履人间卖。重向修门蹑屩来,我登琼岛望渐台(怀仁堂)。园中池馆长如旧,鹭尾猴头(自注:世凯喜着戎装,以鹭尾饰帽,章太炎戏改杜诗嘲之:“云移鹭尾看军帽,日绕猴头识圣颜。”)安在哉!一代奸雄存秽史,八旬(八十日)天子等优俳。园鸟犹呼奈何帝,日暮啾啾空自哀。
作者以诗存史,材料丰富,叙事纡徐。写出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窃国大盗,所必然遭遇的众叛亲离、祸及身家的可悲下场。堂堂正论,出以滑稽突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极富喜剧性,非大手笔不办。
曾缄性情中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尝为诗讥同僚之治《文心雕龙》者,云:“文心雕尽未成龙。”其恃才傲物,可见一斑,宜其贾祸。平素遇事入咏,无论何种题材,信手拈来,皆成妙谛。使读者于忍俊不禁中,深长思之。如:
想是张王爱鬼才,故将措大付蒿莱。
千秋怨气冲霄汉,一片书声出夜台。
汉殿儒冠成溺器,秦庭经笈化寒灰。
人间不少攒眉事,唱彻秋坟君莫哀。
(《张献忠屠应试秀才丛葬一处名曰秀才坟又曰酸冢偶过其下戏作一诗》)
闲时拄杖过东津,野老相逢意转亲。
亦拟杀鸡共一饭,可怜鸡更瘦于人。
(《野老》)
在我看来,诗有两种好,有一种叫想得到的好,有一种叫想不到的好。想得到的好,是锦上添花。想不到的好,是雪中送炭——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诗词作者,都应该追求想不到的好。如曾缄这两首诗,前诗的“一片书声出夜台”,寓沉痛于调侃;后诗的“可怜鸡更瘦于人”,于自嘲中有悲悯。是含着泪的笑,都有想不到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