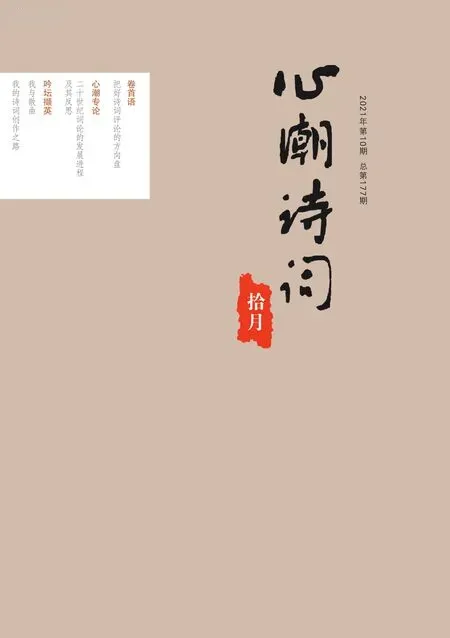二十世纪词论的发展进程及其反思
朱惠国 付 优
词论作为词的“批评之学”,与词的创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从宏观的层面评价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可以发现:词的创作几乎未能产生影响持久而深远的作品,但词论却经历了其发展史上变化最大,且绝不缺乏亮点的特殊时期。究其原因,除这百年间产生了《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等重要词论成果之外,更重要的是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末,中国词论在词学观念、成果形态、传播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直观地看,从南宋王灼《碧鸡漫志》以来,以随笔型、笔记体、印象式、漫谈式为特征的词话批评逐渐让位于新兴的专题式词学论述,简言之,就是主流词论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回顾二十世纪词论的发展进程,展现每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其发展演变的内在轨迹,有益于我们正确把握与评价二十世纪词学,为当下的词学批评提供可靠借鉴,这是一项具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
一
二十世纪词论的起点是晚清常州词学。一般认为,中国词论有两个高峰:南宋和晚清。如果说南宋词论主要是在自唐五代至两宋词学高度繁荣的基础上,对词的艺术特点进行总结,那么晚清词论则是在词的创作经历最后辉煌之后,在更大时段的基础上进行总体性的观照,后者在晚清动荡的社会背景中融入对时代因素的思考,因此更加全面,也更加强调词的社会功能。从社会性、文艺性兼顾的角度看,晚清无疑是中国传统词论最为繁荣的时期。百年词论以此为起点,经历了民国和共和国时期,以二十世纪末的新时期为终点,相比于两宋以来的千年,时间跨度并不大,但形式与内涵变化巨大。在此期间,传统词学不断式微,现代词学逐步建立,基本完成了词论史上最重要的转变。这是中国词论史中最值得关注与总结的百年。
对于二十世纪词学衍变进程的分期,学术界异说纷纭。概而言之,以传统词学的终结和现代词学的建立为主线,大致可划 分 出1900—1949、1949—1979、1979—2000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其中1908年《人间词话》发表、1931年朱祖谋去世、1933年《词学季刊》创刊等标志性事件又可作为关键节点标识词学发展的里程。词论作为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世纪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从庚子事变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00—1949),是传统词学的最后繁荣期和现代词学的创立期。从词论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繁荣发展主要展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词坛名家辈出。这一时期词学家众多,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群体。其一,“由内而内”的词学家,即传统的词学家。1904年王鹏运去世后,以朱祖谋为首的传统词学家继续主盟词坛。他们的词学思想变化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表达“黍离麦秀”与“荆棘铜驼”的遗民之感,这在他们的创作及借助词集序跋表达的词学评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后一阶段,他们关注的重心逐渐向词集校勘和声律研究转移,更加强调词的技法。龙榆生曾将之总结为:“一时词流,如郑大鹤(文焯)、况夔笙、张沚莼(上龢)、曹君直(元忠)、吴伯宛(昌绶)诸君,咸集吴下,而新建夏吷庵(敬观)、钱塘张盂劬(尔田),稍稍后起,亦各以倚声之学,互相切摩,或参究源流,或比勘声律,或致力于清真之探讨,或从事梦窗之宣扬,而大鹤之于清真,弘扬尤力,批校之本,至再至三,一时有‘清真教’之雅谑焉。”其二,“由外而内”的词学家,即所谓体制外词学家,以王国维、梁启超为代表。这类新型的词学家吸纳西方哲学、美学和社会学观念,从纯文学和社会文艺学两个方向渗透、影响中国传统词学,其本质是西学东渐背景下,传统词学理论面对西方文艺理论挑战的应激反应。两人开创了新的词学风气,但所获的理论回应比较微弱,因而,有学者提出此时期词学未能如小说、戏剧、诗歌般形成规模化的“文学革命”。直至1927年,胡适出版《词选》,批判晦涩难懂的梦窗词,提倡清新刚健的词风,同时以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来观照词的发展演变,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多采用分析、实证的方法,在词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三,内外兼修的词学家,即新生代词学家,以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为代表。这类新生代词学家既吸收传统词学精华,又能借助现代的分析方法和实证方法进行词学研究,全面促进了词坛文学观念、研究视角、研究手段、成果形式和词学传播媒体的更新,最终完成了中国现代词学的建构。与他们同声嘤鸣的,还有南北各高校主持讲席的词学教授,如中央大学汪东、陈匪石、王易,北京大学赵万里、刘毓盘,武汉大学刘永济,河南大学邵瑞彭、蔡桢、卢冀野,中山大学詹安泰,重庆大学周岸登,暨南大学易孺等。从地理分布来看,这些词学家又先后形成了沪宁词学圈、京津词学圈、广州词学圈和成都词学圈,共同推动倚声之学的繁荣。
其二,词社活动频繁。从庚子事变到五四运动期间,承接湘社、鸥隐词社、咫村词社、寒碧词社遗风,以柳亚子主持南社、朱祖谋主盟舂音词社为中心,北京有著涒吟社;上海有丽则吟社、春晖社;厦门有碧山词社;成都有锦江词社、春禅词社;台北有巧社。这些社团不全是专门性的词社,但词的创作与讨论占据着其社集活动的重要位置。由于南社体兼诗词文,此阶段词社应属舂音词社影响最大,王蕴章称“海上词社,以民初舂音为最盛”(《舂音余响》)。从五四运动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出现了白雪词社、瓯社、甲子词社、潜社、聊园词社、趣园词社、须社、六一消夏社、沤社、鸣社、蓼辛词社、蛰园词社、梅社、如社、声社、寿香社等词学社团。其中以潜社、须社、沤社影响较大,活动较多,辑有《烟沽渔唱》《沤社词钞》等。抗战爆发后,神州满地疮痍中,词人弦歌不辍,组织有瓶花簃词社、午社、雍园词社、玉澜词社、绮社、瓶社、梦碧词社等。中国词社素来有立派的传统,往往在词社中崇尚、倡导某种词学倾向。民国词社情况则稍有不同,应酬、社交的成分多一些,不尽以立派为宗旨,但以上各类大小词社的社约、宣言、纲领、章程以及社集序跋等文献材料中,均不同程度体现词社的创作倾向和美学崇尚,保留着丰富的词论材料。
其三,词学刊物兴盛。《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是民国时期两种专业性词学刊物,为这一时期的词学研究和词学评论提供了发表园地,极大影响了这一时期的词学传播。1933年4月,《词学季刊》由龙榆生等人创办于上海,以约集同好研究词学为宗旨,主要作者为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赵尊岳、张尔田、夏敬观、吴梅、叶恭绰、邵瑞彭、周泳先十人。这是近代贡献最大的词学专刊,1936年因抗战爆发而停刊,历时三年,共12期。每期主要内容包括论述、专著、遗著、辑佚、词话、近人词录、近代女子词录、词林文苑、通讯、杂缀等。《同声月刊》是龙榆生1940年创建于南京的词学刊物,前后历时近五年,共出版39期。此外,陈赣一于1932年创刊的《青鹤》杂志也刊登了大量诗词作品和评论文章。除了这三家刊物,刊登词学研究文章的期刊杂志还有《妇女时报》《小说新报》《小说海》《民权素》《礼拜花》《红玫瑰》《紫罗兰》《先施乐园日报》《天韵报》《永安月刊》《中华邮工》等百余种。其中,《民国日报》《中华编译社社刊》《北平晨报》等刊物都曾设有词论专栏。
其四,词学著述大量出版。词学创作与研究的繁荣,加上民国时期机器印刷的推广,书籍出版更加便利,共同推动着词学著作的大量出版。1926年,胡云翼出版第一部专门的词史著作《宋词研究》,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探讨宋词的发展、变迁和整体情况,下篇评述两宋主要词人作品。1931年,刘毓盘《词史》付梓,是为第一部略具规模的通代词史。全书共十一章,除第一章论词的起源外,后十章依次详细论述隋唐五代至明清的词人群体和流派。1932年,王易出版《词曲史》,分为明义、溯源、具体、衍流、析派、构律、启变、入病、振衰、测运十个部分,探究词曲的体制源流、宫调格律和词曲二体之异同。次年,吴梅出版《词学通论》,全书九章,前五章论平仄四声、词韵、音律和作词法;后三章标举评述历代词家得失。四十年代,薛砺若三次修订出版《宋词通论》,分七编探索宋词风貌和词人嬗替的轨迹。此外,谢无量《词学指南》、王蕴章《词学》、徐敬修《词学常识》、徐珂《清代词学概论》、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摄影》、胡云翼《词学ABC》《中国词史略》《中国词史大纲》、梁启勋《词学》《词概论》、谭正璧《女性词话》、卢前《词曲研究》、伊碪《花间词人研究》、缪钺《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龙榆生《词曲概论》、余毅恒《词筌》、刘尧民《词与音乐》、孙人和《词学通论》、刘永济《词论》、任中敏《词学研究法》等著作均为此时段较有代表性的词史词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七十年代末,是现代词论的潜伏期。1949年7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确立为文艺发展的新方向。从“十七年”到“文革”期间,在困顿的境遇中,一方面,张伯驹、夏承焘、黄君坦、寇梦碧、孙正刚、陈机峰、沈祖棻、唐圭璋、丁宁、朱庸斋等词人百折不挠,默默坚持创作,留下了不少情感炽烈的诗词作品;另一方面,唐圭璋《全宋词》、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邓广铭《辛稼轩年谱》等词集和年谱的出版,为词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献支撑。更为重要的是,夏承焘《唐宋词叙说》(1955)、龙榆生《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1957)等词学论文的发表,彰显着前辈学者志怀霜雪、不辞辛劳地推动词学研究向前进展的艰苦努力。但由于时代的限制,词学研究也受到大环境的干扰,偏离了正常学术研究的轨道。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将宋词“豪放派”称颂为“现实主义支流”,将“婉约派”贬低为“反现实主义逆流”,甚至强行将“豪放派”又划分为“儒法”二派,把苏轼和其门下词人当作“保守儒家”的靶子来攻击,又将王安石、辛弃疾等人不恰当地理解为“法家词人”。对当时盛行的词学议题,我们应该在对历史背景的理解中批判式继承。
从八十年代初至世纪末,是现代词论的新兴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文艺界的创作和评论环境逐渐恢复繁荣局面。
首先,随着词学的复兴,词学专业刊物重新创办。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联合夏承焘、唐圭璋、马兴荣等创办《词学》集刊。集刊专攻古典文学中词学一块,旨在为海内外专业词学研究者提供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以利大家“互相商榷,互相切磋,互通信息,互为补益”,共同推动研究,繁荣词学。刊物的主要栏目有论述、年谱、文献、词苑、丛谈、图版等。从刊物的办刊宗旨、编辑思想,甚至主要栏目设置来看,均有遥接三十年代《词学季刊》的意图。该刊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的词学研究专业集刊,对新时期词学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除此之外,八十年代初,广东创办有《当代诗词》、《诗词集刊》、《诗词》报等报刊。九十年代,中华诗词学会创办《中华诗词》,东南大学词学研究所创办《中华词学》刊物,这些刊物均促进了词学的繁荣,也为新时期词论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其次,词论文献整理取得重要成果。八十年代在词论文献整理与出版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修订再版了《词话丛编》。唐圭璋《词话丛编》编纂于三十年代,是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词论文献之一。1933年8月出版的《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在“词坛消息”中最早报道编纂《词话丛编》的消息,作者透露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汇刻词话的想法最初由郑振铎提出,唐圭璋先生是“重申斯旨”;其二,唐先生已编出初步目录,计由词话八十种。此后《词学季刊》多次发文,跟踪报道。综合这些报道,《词话丛编》收录词话的数量不断变化,经历了由少(80种)到多(90种),再由多(90种)到少(65种)的过程。事实上,《词话丛编》刊印时,最终的词话数是60种,说明唐圭璋先生也经历了广搜词话到严选词话的过程。八十年代,唐先生的修订本在原来所辑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词话丛编》的重新修订出版,是唐圭璋先生对词学文献整理工作的重大贡献,也是八十年代词学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除了《词话丛编》,这一时期还有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金启华《唐宋词集序跋汇编》等词论文献资料出版,为词论研究走向深入和精进奠定了基础。需要说明的是,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其实编纂于“文革”前,但由于其处境艰难,一直无法出版,能够在此时面世,正说明词学研究的环境已发生改变。
再次,各类词学研究论著陆续出版。晚清以来,各类词学研究著作不少,但专门的词论研究著作,尤其是专门的词学批评史著作十分鲜见,因此,1994年出版的《中国词学批评史》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意义。此书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四位中青年教师方智范、邓乔彬、周圣伟、高建中合著,由施蛰存参订。作者以时间为线索,将中国词学批评的发展分为两大阶段:从唐五代到明末为第一阶段,主要论述以“本色”论为核心的传统词学观和苏轼的诗化理论,对其特点和影响均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清代至民国初为第二阶段,主要介绍、评价相继而起的各种词派。全书以王国维《人间词话》为终结,以为由此开启了“西学东渐”背景下词学批评的新变。两个阶段前后连贯,在介绍词学家、词派以及各种观点的同时,勾勒出中国古代词学批评史的发展轨迹。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编的《词学研究论文集(1949—1979)》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1949年以来词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也可视为重要的当代词学文献,引起学界广泛关注。除了著作外,这一阶段单篇词学论文,如施蛰存致周楞伽以《词的“派”与“体”之争》为题的几封书信,吴世昌《有关宋词的若干问题》《宋词的“婉约派”和“豪放派”》等,也对词学研究走向“百家争鸣”“千帆竞发”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纵观百年词坛,在波折中蜿蜒前进,词的批评之学薪尽火传,生机不绝,在传统词学的基础上成功孕育了现代词学学科。
二
在二十世纪波澜起伏的词学发展中,词学理论的演进堪称重中之重。学者们不辞辛劳,爬梳文献,研习声律,力求准确把握住理论演进、形式嬗递的脉络,创造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有三个方面在词学发展中影响较大,尤其值得关注与探讨:
第一,记录词坛争鸣的“声响”。现代“词学”体系的建构、作词是否严守四声的争议和词体如何解放的命题,是二十世纪前半期词坛关注的核心话题。一百年中,绝大部分词人都曾或主动或被动参与过相关话题的讨论。然而,在此前的研究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各个时期代表词人的观点,极大程度上忽略了词坛上广泛存在的“低音”。以词体解放问题为例,梁启超、胡适提倡完全解放词体,用白话作词,“推翻词调词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胡云翼等青年学者受胡适影响,形成了“词体并不是一种有多大意义和价值的文体,它的生命是早已在几百年前的终结,成为文学史上的陈物了”之类的激烈主张;1916—1921年间,陈柱与友人冯振也提出“自由词”创作理念,倡导打破词谱约束。三十年代,曾今可、柳亚子与赵景深等人以《新时代月刊》“词的解放运动”专号为阵地,掀起了广为人知的“词的解放运动”。大致上说,曾今可、董每戡、柳亚子等人主张不分别阴平、阳平与上去入,以白话或现代浅近的文言入词,但要求保存平仄和韵脚;张双红、张凤等人主张完全废弃词谱、词牌,创制新谱自度腔填词。然而,细细考究,在“词的解放运动”中还存在更多的议题。例如董每戡大体赞成曾今可的观点,但又提出“不使事(绝对的)”“不讲对仗(相对的)”“要以新事物、新情感入词”“活用死律”“不凑韵”“自由选用现代语”六条建议;翁漫栖更加激进,提出“我的改善很不像曾今可先生那样只解放小部份的一小部份(只把阴阳的平仄解放而已)。我以为这种解放脚而不解放乳的解放,似乎太于无聊。所以我自己的改善却是把词谱完全解放”;而叶恭绰则干脆指出文体沿革,诗之后有词,词之后有曲,“曲之流变应产生一种可以合乐与咏唱之物,其名曰歌”,提出“鄙意应不必仍袭词之名,盖词继诗,曲继词,皆实近而名殊。犹行楷、篆隶,每创一格,定有一专名与之,以明界限,而新耳目”。
与此同时,仍有大量词人持保守立场,主张严守词谱、师法梦窗、辨明四声。例如,陈匪石主张严守四声,“若既不知五音,又不辨四声,则不必填词可也”;向迪琮亦提出“今虽音律失传,而词格俱在,自未可畏难苟安,自放律外,蹈伯时所谓‘不协则成长短诗’之讥”;刘富槐则深信坚守词体的价值,提出“西方学者知有此体,殆将播诸管弦,列于美术,宁有屏而不御乎”;蔡嵩云更跳出两派,主张“近年社集,恒见守律派词人,与反对守律者互相非难,其实皆为多事。词在宋代,早分为音律家之词与文学家之词”。可见,在“词体解放”的旗帜下,词人群体的具体思想实则各不相同,而这些细节的差距、微弱的“低音”正是我们深入理解词学衍变的重要资料。
第二,还原词论竞议的“现场”。二十世纪的词论著述中,保存着海量有关当时词人交游、词社活动、词作评论的材料,详细考索,不难还原出众声喧嚣的词论“现场”。若论辑录词人词作,汇辑词坛轶事,可观陈锐《袌碧斋词话》、碧痕《竹雨绿窗词话》、夏敬观《忍古楼词话》、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张尔田《近代词人逸事》、高毓浵《词话》、程善之《与臞禅论词书》等材料。其中,如蔡突灵在《红叶山房词话》中假托寻芳倦客评述自己的词稿兼解释词作所隐射政治事件,又如吴梅《与龙榆生言彊村逸事书》谈论朱祖谋故事,周焯《倚琴楼词话》辑录李劼人、毕倚虹词事,陈去病《病倩词话》抄录友人题《征献论词图》词作,均有存人存词之效。若论评骘词人,甲乙词作,可观闻野鹤《怬簃词话》、黄濬《花随人圣庵词话》、朱庸斋《分春馆词话》等材料。如陈声聪《读词枝语》点评近代女词人丁宁、沈祖棻、陈家庆、寿香馆弟子、龙榆生弟子张珍怀、王筱婧;或如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借说部狡狯之笔,为记室评品之文;或如方廷楷《习静斋词话》论“鹓雏长于写艳,亚子工于言愁;鹓雏秣丽似梦窗,亚子俊逸似稼轩”;再如沈轶刘在《繁霜榭词札》中提出“民初四词家外,尚有三大名家,窃准汉末成例,拟为一龙。以夏承焘为龙头,钱仲联为龙腹,龙沐勋为龙尾”等,均堪称点睛妙笔。若论记录词人交游、词社活动始末,可观王蕴章《秋云平室词话》、蒋兆兰《词说》、陈声聪《读词枝语》、陈洵《致朱孝臧书札》(十通)等材料。如陈曾寿《听水斋词序》记录须社梗概;陈声聪《读词枝语》历数燕京自庚子词社、聊园词社、趣园词社到须社的社集活动与中心任务,又记录南方沤社、午社、如社参与人员;徐沅《瀼溪渔唱序》记录“余于庚子之秋与刘语石、金蔗畦、左迦厂诸君结词社于西泠”;蒋兆兰《乐府补题后集甲编序》记载“去年庚申岁暮,焕琪宴集程子蛰庵、储子映波、徐子倩仲及不佞共五人结词社,名曰白雪,纪时也,亦著洁也”;王蕴章《梅魂菊影室词话》记录舂音词社创社和第一次社集情况,云“近与虞山庞檗子、秣陵陈倦鹤有词社之举,请归安朱古微先生为社长”;庞树柏《袌香簃词话》记录舂音词社社员和第二次社集情况,都是研究近代词社词学思想的宝贵资料。
第三,追溯词学评论的“脉络”。考索二十世纪的词论著述,不难发现,其中保存有大量谈论学词法、作词法、选词法、评词法的内容,足以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传统词学的现代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如陈世宜《珏庵词序》记录了跟随朱祖谋从《绝妙好词》入手学词的经历;陈柱《答学生萧莫寒论诗词书》详细谈论了学词的步骤、对象和要点。又如翁麟声提出“填词之苦,千态万状”,“句之长短,字之多寡,声之平上去入,韵之清浊阴阳,皆有一定之严格”;王瀣主张“窃谓词难于诗,全在会意尚巧,选言贵妍,固不可歇后做韵,尤不可满纸词语,竟无一句是词”;欧阳渐认为“作苏辛词,第一要胆大,俯视一切,敢发大言;第二挂书袋子,开口闭口总是吃现成;第三情挚,一肚子不合时宜,不堪久郁,不管是非,滂薄而出之”;谭觉园主张“清、轻、新、雅、灵、脆、婉、转、留、托、澹、空、皱、韵、超、浑为词之十六字要诀”,又提出“初学者,以《白香词谱》或《填词图谱》,较为适用。《白香词谱》,尤以天虚我生之考正本为妥善”;吴东园则认为“今之学词者,如以空灵为主,但学其空灵,而笔不转深,则其意浅,非入于滑,即入于粗矣。以婉丽为宗,但学其婉丽,而句不炼精,则其音卑,非近于弱,即近于靡矣”。又如汪兆铭在致龙榆生书札中批评古今选家之弊端,提出“选一代之词,宜以落落十数大家为主,于此十数大家,务取其菁华,使其特色所在,烂然具陈……于此落落十数大家之外,如有佳作,亦择其尤精者选之,为之以辅,如此或可兼收众长而去其弊”。值得关注的是,《沤庵词话》中保存有较多对王国维“境界说”的反思和修正。一方面,沤庵认为,王氏标举的“无我之境”实际并不存在。“物境者,景也;心境者,情也;情景交融,则构成词之境界”,境界即为外在物境与内在心境的化合为一。历代词人“以词心造词境,以词境写词心,固处处着我,初无‘无我之境’也”。另一方面,沤庵又反对王氏“隔”与“不隔”的区分方式,提出“凡词之融化物境、心境以写出者,皆为‘不隔’,了无境界,仅搬弄字面以取巧者为‘隔’,‘隔’与‘不隔’之分野,惟在此耳”。
总体上看,二十世纪是词学与国族同风雨,在裂变中涅槃的一百年,催生了许多启人深思的词学议题,在众声喧哗中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学科史,时至今日,二十世纪词论著述依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文献价值。
二十世纪伊始,梁任公作《少年中国说》,引用西谚云“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词论作为一种与词的创作密切相关的专门之学,发展到今天,也积累了千年有余的历史,而二十世纪这一段,在西学东渐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蜕变,成为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学问。作为词学研究共同体的一分子,我们诚挚地期待它能穿越千年的风霜,渡过百年的奔流,仍能承《大学》“日新又新”之诫,秉《大雅》“旧邦维新”之命,在变动不居的时光长河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