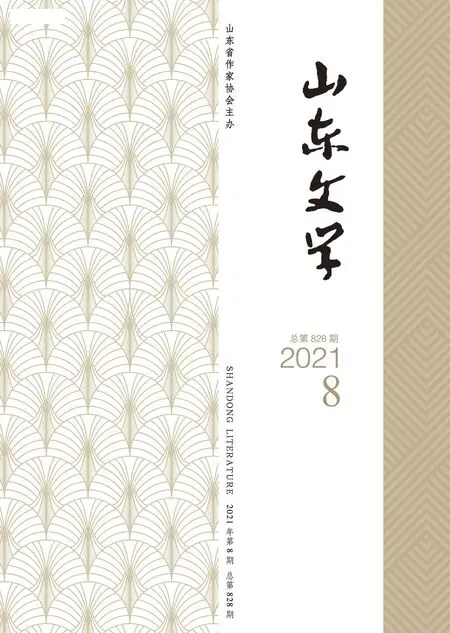龙 骨
吴 苹
七月的阳光生满了芒刺,白马的每一寸皮肤都在喊疼。汗水从它头上滚落,在长睫毛上稍作停留,落进了泥土里。旁边娥姬赶着的那头老青牛,也是同样的汗湿如洗。白马抬起头,目光掠过近处的黄土地,落向远方的天际。天边灰暗迷蒙,似有烟尘扬起。硝烟……硝烟……号角……战鼓……后背上骤然疼了一下,生刍又给了它一鞭子,它只得将思绪拉回。泥土松软,木犁沉重,每走一步,四蹄都要深陷进去。
新翻的田地泛着熟悉的腥味。混合着茎秆、尸体、汗水、羊水以及胞衣的气息。
林平原推着自行车走出仓库大门,恍惚中似乎一脚踏入了秋天。昨夜下了一场春雨,今晨大叶榕很慷慨地将落叶铺了一地。这个东南沿海城市一年到头温差不大,即便是秋冬季节室外也是一片郁郁葱葱。在此地打工二十多年,林平原常生出遗失四季的感觉。只有到了春天树木萌生新叶时,才算捕捉到一丝季节的影子。
林平原骑上自行车,边走边想该怎么安排今天的二十四小时。仓库的工作是两班倒,每半个月白班和夜班调换一次,只有在换班那日才可以休息,昨晚是这一轮的最后一个夜班了。洗衣服、打扫卫生、给老家的老婆孩子打电话,诸如此类的事情是每次调休时都要做的。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再去老关诊所里让他给看看。这一阵子林平原的身体出了点问题,主要是睡眠质量差导致的咽干口苦四肢乏力。老员工都说长期上夜班的人难得有几个睡觉好的。“拨乱反正”这个词用在人类的生物钟上是靠不住的,一旦乱了就很难反正。这个状况也增加了林平原对衰老的恐惧,到底四十八岁了,衰老的脚步是任谁也拽不住的。
林平原经过公司宿舍门口时,见卖凉皮的杨老太太已将凉皮车推了出来,车上的“正宗北方凉皮”几个大字很是醒目。老太太看见林平原,笑说:“下夜班了?”林平原笑着点点头。老太太说:“带份凉皮吧。”林平原说:“谢谢嫂子,你干个生意也不容易,哪能老是白吃你的凉皮呢?”林平原、杨老太太,还有开诊所的老关,三家倒是常来常往的。林平原是山东人,杨老太太是河南的,老关是河北的。在这个北方人稀缺的东南沿海城市,三个相邻省份的人倒有了亲如一家的感觉。盛华电器公司的宿舍和公寓离得很近,一路上林平原看到了不少穿灰蓝厂服的年轻人,那些人手里大多拿着面包或油条,边啃边匆匆走着。公司宿舍每间房内八个床位,住的大都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公寓则是为大学生提供的,每间房内有一个或两个床位。林平原是初中学历,达不到住公寓的资格,他又嫌住宿舍做饭不方便,为此在离公司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民房。好在有自行车,来回上班也挺方便。
上夜班和白班的感觉确实不同,不止是身体累,还头昏脑涨。吃过早饭坚持着将脏衣服洗完就到了十一点。人躺在床上眼睛也闭上了,但是睡意却迟迟不来。尽管嘴里念着静心静心,抵不住有些事情总是蹦出来骚扰,骚扰几次之后心里的防线便土崩瓦解。
这几年兴盛电器公司的效益不错,连仓管员都细分成了两批,一批负责发货,另一批负责进仓。去年公司新增了一个仓库,原来在飞跃仓负责进仓的组长调去了新仓库,林平原暂时做了飞跃仓的组长,不过是代理的。做了十二年仓管员,才当了三个月的代理组长,就撞上了来势汹汹的传染病。这么看来,似乎一切皆有定数的样子。元宵节之后公司虽然复工了,但仓库平均日中转的产品数量只有去年的一半。长此以往,前景堪忧啊!仓库里有这种担忧的不止林平原一个。毕竟是关乎前途和饭碗的问题,难得有几个能做到气定神闲的。
林平原在床上翻腾了一阵子,该来的没等来,尿却等来了。他只得起床去放水,完事后重又躺回床上翻看微信。将各个省的传染病新增人数看了个遍,今天又有一个省被涂成了红色,看来病毒没打算放过一个省份。
白马决定离开。它的出逃计划定在黎明。为了这个计划,它准备了多日。上半夜它睡得很踏实,几乎没有听到老青牛因疲劳而发出的呻吟声。天快亮时它做了一个梦,梦中出现的仍然是硝烟和战场。它在战场上纵横驰骋,英勇无比。醒来时它原想和那头老青牛辞行的,可是老青牛却没了踪影。眼看东方泛白,它决定不等青牛了。它拼出全力挣断了缰绳,回望了一眼这所院落,而后走出了大门。到了官道,白马撒开四蹄,风一样地奔跑。逢溪涧和沟壑,纵身一跃便轻松跨过。这大路、这驿站,虽然从没来过却多次在梦中出现,今日一见犹如故人重逢。给白马惊喜的不仅是梦想成真,还有自己的奔跑速度,迅疾如闪电流星的速度是它从未想到的。
战鼓声逐渐清晰,硝烟味越发浓重。死于沙场还是屠场,相信每一匹马都会如它这般选择。
正午时白马到了一条河边。大河宽阔,风高浪急,河水在太阳下闪着刀刃般的亮光。河上无船无桥,白马决定跳过河。它后退了百步有余,开始做起跳的准备。它向着蓝天发出一声长嘶,回声在山谷里久久不散。而后,它运足丹田之气向着前方奔跑,接近河边时,强健的后蹄蹬着黄土,身体顺势腾空而起。河水就在身下,迎面的风越来越猛,身体越发沉重。眼看岸在近前,狂风却吞噬了它的最后一丝力气。它落了下去。
河水混着泥沙灌进它的鼻孔里,脚下的淤泥合力往暗处拖拽着它。在河水灌入肺里前,它最后望了一眼头顶的蓝天。
既不是沙场也不是屠场,是第三种死法。
退出微信时已是十二点半了。原想着起床先对付一下午饭,怎奈一点胃口也没有。林平原决定去诊所找老关聊聊,这个点诊所应该不忙的。
果然,诊所里只有一个输液的病号,老关则坐在桌前看医书。看到林平原进来,老关笑说:“哥,看来当组长后很辛苦啊,累得人都瘦了。”林平原摇头说:“可别提了。”老关说:“咋了?”林平原说:“形势严峻呢,能不能保住饭碗都难说。”老关说:“别人这么想还罢了,你可别这么想,你的能力是整个仓库的人有目共睹的,十几年了,在工作上你可是一次错也没有出过。”林平原摇摇头说:“目前啥都不好说。”
此时,输液计时器响起,老关过去给病号拔了针。送走病号后,老关坐到林平原跟前说“哥呀,你看你面色晦暗眼窝青灰,这一阵子肯定没睡好觉。”林平原点点头:“这不来找你了嘛。” “你放宽心,不要想那么多,别搞得代理组长转正后,人再病倒了,那样可不值了。”老关拉着林平原坐到桌前:“来,我给你把把脉。”
老关将手指从林平原腕上拿下来:“典型的阴虚火旺肝阳上亢。人的脏腑和四季是对应的,春季属木,肝脏也属木,所以春天是人肝火最旺的季节。本来就肝火旺再加上你又各种焦虑,不失眠才怪呢。”老关开了药方后,在桌上铺开几张大纸,开始抓药。林平原盯着药方的内容逐一看过去:栀子、淡豆豉、菊花、生地、茯神、丹参、珍珠母、炒蔓荆子、龙骨……“龙骨,龙骨是什么呀?”老关拿起一块生石灰状的东西给他看:“这就是龙骨。”他说:“真是龙的骨头?”老关笑说:“名字叫龙骨而已,哪是什么龙的骨头?是古代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它的功效是平肝潜阳、镇心安神的。用深埋在地下几千年的东西把人上蹿的肝火降下来,中药就是这么神奇。”老关将生龙骨倒在黄铜药臼里准备捣碎,林平原忙拦住说:“先别砸,留下两块。”老关笑说:“怎么,你要做研究啊?”林平原说:“感觉挺有意思。”老关将两个整块的龙骨递到他手里,又将桌上的药包一一包好。老关说:“吃了药后什么都别想,好好睡觉。啥也没身体重要,平山就是个例子。”他愣了一下,接过药包说:“行,我听你的,啥也不想,好好睡觉。”
林平原将中药泡上之后,拿出那两块龙骨把玩了一会,而后放在一张干净的白纸上。他盯着那两块龙骨,越看越觉它神奇。这是什么动物的骨骼化石呢?牛?马?羊?他不想它是牛,牛是隐忍的动物,像他林平原,他更愿意它是奔放的马。如果它真是马,那应该是一匹纤尘不染的白马。他找出一支铅笔,在白纸上画了一匹奔腾的骏马,感觉不太满意,又用铅笔顶端的橡皮擦修改了几次。画好后,他拿着白纸细细端详:马头高扬,四蹄腾空,颈项上的鬃毛被风吹起,如同斗篷般俊美。马尾飘散开来,很是潇洒不羁的样子。是他想象中的理想白马了。林平原将一块龙骨放在画上的马头中间,另一块龙骨则放在心脏的位置。感觉还少点什么,他起身走到院子里,折了几枝嫩叶放在了白马的唇边。
尽管吃了中药,林平原心里还是惴惴不安,但愿这药能起点作用。听说温度较低的环境使人入睡快,开了电扇是否能好点呢?是摇头扇,呼啦一下转了过来,又呼啦一下转了过去。风是有了,噪音也随之而来,烦躁又开始蠢蠢欲动。“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平山就是个例子。”“砰——”好不容易睡着了,又被骤然响起的声音惊醒,声音是从楼上传来的。“咣当——”应该是椅子倒地的声音,接着,女人的哭声响起。“你他×的神经病啊!大半夜的你闹什么?”男人的声音很大。
女人在哭,男人在咆哮,赶上电影热闹了。
凌晨的时候,楼上的那对终于消停了。林平原也算小睡了一会儿,只是醒得比较早,起床时还不到五点钟,尽管脑袋昏沉沉的,他也不想再躺了。八点钟上班,六点多就到了仓库。仓库大得像个操场,人走在这一头,脚步声响在那一头。产品如同三军仪仗队分立在通道两旁,看到他到来,齐刷刷地向他行注目礼。这里是他的疆土,它们都是他的臣子。只有在它们面前,他才可以发号施令调兵遣将,他才有被拥护被尊重的感觉。哪怕是在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面前,他也没有过也不敢有这种感觉。
林平原走到一个角落里,拿出昨天下班前放好的油漆桶和刷子,开始在地面上漆白线。原来仓库地面上有黄线,只是线与线之间是等距的,小型号的产品和大体格的产品占了同等宽的位置。那样既破坏了视角上的美感,又造成了空间上的浪费。他根据产品包装箱的尺寸重新做了规划,又买来刷子和白油漆,钱是自己掏的腰包,毕竟一桶油漆也花不了大钱,自己拿就自己拿吧。他决定将仓库当自家田地一样开垦,让产品规规矩矩地在各自的垄里生长,井然有序地呼吸。
“林工,这么早啊。”搬运工老朱走过来。他笑着说:“醒早了,干脆来仓库里干点活。”“林工,还没上班呢,你这是忙的什么呀?来,过来喝瓶水。”老朱扔过来一瓶冰糖雪梨。他接过来,说:“下回我请你。”老朱说:“我们请,我们请,别说一瓶水,请你吃饭都是应该的。”老朱他们几个有湖南的,也有云南的,工资都是计件的。他代理组长这三个月,每天让仓管员及时登记仓库里的剩余空间,尽可能地给他们多争取搬运的机会。他曾经也是握了十年叉车把手的搬运工,但凡有一点办法谁也不会干这种出苦力的活。他对老朱说:“等我将白线漆好后,仓库又能多放不少产品,到时候你们可就闲不住了。”老朱笑着向他挑了一下大拇指:“林工,我们哥几个早就盼着你能当这个仓库的组长,这不,被我们盼成真的了。”他笑说:“现在还不算是。”老朱说:“怎么不算?整个仓库大事小情哪件不归你管,换成别人谁也干不了这个活啊。”他笑说:“那倒是。”
他现在带的徒弟是个大专刚毕业的女孩子,午休时他在仓库里加班漆白线时让那孩子去休息了。毕竟属于义务劳动,自己干就是了不好每次都拉着人家。好在白线工程已完成了大半,这几天进入了收尾工作。他正在低头忙活时,老朱走进来说;“林工,你快去看看吧,仓储主任李丁来了。”他问:“办公室里有其他人吗?”老朱说:“仓管员们和另一个组长在陪着他喝茶呢,就差你了。”他说:“既然有人陪他,我就不去了。”
每天晚上下班后,他都不忘给他画的白马捎一束青草。他觉得那是一匹好马——仁义。即便是死了埋在地下几千年,仍能治病救人,可见,有时候动物比人更仁义。吃了几服药后,他的失眠焦躁明显减轻,尽管那个配方里有十几味中药,他还是认为龙骨在起主要作用。毕竟其他的都是草木,而龙骨的前身却是有血有肉有灵气之物。
这个中午林平原从仓库里出来,脸上还带着如释重负般的微笑。他的白线工程已经竣工,这对他来说是个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仓管员走过来说:“林工,李主任来了,要开会了。”那个仓管员说完,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顿时,一种不祥的预感从他心里升腾起来。
仓库里的人都到齐了,看来就差他一个了。李丁坐在办公桌正中的椅子上,旁边的椅子上是一个陌生男人,三十来岁的样子,留着板寸、小眼睛、皮肤黝黑。看到那人时,林平原心里咯噔一下。李丁说:“既然人都到齐了,那就开会吧。我先来介绍一下,这是阿荣,即日起由他担任我们飞跃仓的组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阿荣的工作……”
李丁说完,似乎向他这边瞟了一下,又迅速地将目光收走了。李丁的话很干脆很利落,没有任何余音,不给人任何幻想。其实这个事情自始至终就是这样,犹如北方的冰雕,你看着晶莹剔透、光彩炫目,你以为它是春天的花朵,你以为它是暗夜的灯笼,你想把它捧在掌心,抱在怀里,注定你是要伤心要失望的。不怪别人,要怪就怪你自己!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走出童年,在成人的世界哪有不跌跤的道理?
林平原感觉自己的脸成了马路,任由全仓库人的目光扫过来扫过去。他知道他们是在同情他,只是这种同情的目光就像砂纸,每抚慰一遍他的心就哆嗦一下。此时尤其不能怂,得做出无所谓的样子,他向每个人都回报以微笑,在收回笑意时他的上嘴唇总是粘在牙齿上,得费点劲才能将两片嘴唇合拢。这个小细节出卖了他,就像一个蹩脚的演员拼尽了全力却屡屡露出破绽。
好不容易挨到了下班,他向仓库里的人笑着点点头,推着自行车往外走。老朱和几个搬运工都在门口,看到他出来立即将他围住了。老朱揽着他的肩膀说:“林工,去喝一杯。”他笑说:“不了,改天吧。”其他几个搬运工说:“走吧,早就说过要请你吃饭的。”他说:“今天真不行,家里还有事。”老朱拍拍他的肩膀说:“那好吧,路上你慢点啊,改天一定请你吃饭啊。”
他从饭店里要了两个炒菜。一个木须肉,一个红烧鲅鱼,又买了一瓶白酒。平时不舍得买这些,今天都这样了,还节省啥呀?他给自己斟上酒,一杯接一杯地喝起来。喝到半截,他猛地想起了什么,拿出一个酒杯放在白马的旁边,往杯里斟满酒说:“伙计,今天咱俩一醉方休。”瓶里的酒见了底,他将空瓶子扔到了桌子底下。他对着桌子上白马说:“你好赖是一匹马,我呢?我他×的就是一只猴啊!” 酒灌到了肚里,火却蹿了上来,蛇一样吐着信子在他身体里到处撕咬。得做点什么,必须得做点什么。他在房里巡睃了一下,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东西,抽屉里有一把老式的手电筒,白铁皮外壳依然锃亮。是哥哥平山的手电筒。他将那把手电筒揣进了衣兜里。
他摸着手电筒就像摸着平山冰冷的皮肤。当时平山的脸就是这种感觉,每次一想起那种感觉他的手都会从指尖迅速凉到手腕。那几年他们弟兄两个都在兴盛电器公司做搬运工,只是不在一个仓库,两人也不住在一起,倒是隔三岔五地能见个面。那天,他搬完一车货正准备喘口气时接到了那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应该是太惊慌了,说得语无伦次。他听过后连手机都想不起往兜里放了,随手一把扔在了地上,接着拔腿就往平山那边的仓库跑。两个仓库只隔着一条马路,跑步也就五六分钟的事。可是,平山连这五六分钟都不等他。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那里时,见平山倒在叉车旁,呼吸已经停止了,眼睛却睁着,两只眼珠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平山的一只手垂下来,另一只手保持着前伸的姿势。似乎是临死前的挣扎,又似乎心有不甘。几个年轻的仓管员惊慌失措,哭成一团。他抱着平山,牛一样地大放悲声。一个老搬运工说:“你别只顾难过,你哥的眼睛还没闭上呢。”一句话提醒了他,他轻抚了一下平山的脸,将那对半睁的眼睛合上了。
他去找的仓储主任李丁。他刚进去,李丁立即将办公室虚掩的门从里面锁上了。他说:“我哥死得冤。”李丁说:“发生这样的事我也很难过。”他说:“有件事别人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只有我知道!”李丁抬头看了一紧锁的门,说:“别激动,慢点说,慢点说。”他说:“我哥之前告诉过我,他说他身体不舒服,向公司请了两次病假,可是你们却……却一次也没有批准。就因为是公司的旺季为了赶着出货……这可是病假啊……呜呜……我哥原本……原本可以不死的。”他捂着脸哭起来。看他哭,李丁也掉了几滴眼泪。“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很难过。可是,人已经走了,再难过也不能使他复生。咱们可以坐下来谈谈,谈谈活人的事情。”他止住哭声,看着李丁。李丁说:“其实我早就发现了你的能力,知道你干工作既脚踏实地又认真细心。我也多次向经理推荐你,让他破格提拔你为仓管员。这次,经理终于同意了。你也知道公司向来都是招聘仓管员,从搬运工里提拔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尤其现在又逢金融危机,很多部门都在减磅瘦身。整个仓储部门上上下下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关键时刻你可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凡事一定要顾全大局,用实际行动堵大家的嘴。你也一定知道自己该怎么说,该怎么做吧!”
顾全大局……实际行动……
这么些年来,他不仅是猴,还是驴。人家在车前面吊了一捆干草,为了那捆草,他拉着车子拼命地跑,结果呢?现在人家将草拿走直接扔掉了。
晚上的凉皮生意不错,被一群顾客围着的杨老太太正忙得团团转。林平原担心老太太看到他,特意从离她摊位很远的地方绕了过去。公寓门前有一棵老榕树,下垂的气根成了天然的屏障,林平原躲在榕树的暗影里,眼睛却紧盯着门口。晚饭后是个热闹时刻,公寓门口一直人来人往。有人提着电脑包走进去,有人双双对对地从里面走出来。眼看时间已到了九点钟,还没见那个人的影子。林平原伸进衣兜里的那只手出了汗,手电筒也被浸得滑腻腻的。他用纸擦了擦手掌,刚把纸团扔进垃圾桶,就看见那人走了出来。
只有他一个人。
公寓门口是一条小河,河边是一条小道,道两边长着棕榈树。那人顺着小道往前走,林平原躲在树影里悄悄跟着他。往前越发偏僻,灯光和人语都被远远地抛在后头了。小路尽头是一片树林,各种各样的亚热带树木挨挨挤挤地长在一起,黑乎乎地如同宣纸上的墨团。四周一片死寂,只有风吹树叶的窸窣之声。林平原距那人仅几步之遥,几乎能听到那人的呼吸声。林平原又向他走了两步,那个脑袋就在眼前了。他对准那个后脑勺,将手电筒高高举了起来……
倏地,那人的手机骤然响起。
林平原忙闪到树后。
他接通电话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
他说:“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
他又说:“你看我容易吗?为了挣那点钱,为了仓储主任这个饭碗,我活得像驴!像猴!像狗!像风箱里的老鼠!就是他妈的不像个人!”林平原高举的手电筒缓缓垂了下来,他竟然会这么想?
他又说:“你知道我在仓库里怎么过的吗?上面的人天天不给好脸色,下面的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心里恨不得把我撕了吃了。今天我得罪了一个老仓管员,估计他杀了我的心都有……”
林平原不想再待下去了,慢慢往后撤。走出树林,远处的万家灯火如星子一般闪烁,他迎着那片灯火走去。
受传染病的影响,附近几家小企业已经关门大吉了。兴盛公司有多年的底子撑着,虽不至于倒下,但每天发货和进仓的数量依旧不容乐观。公司高层已出来了文件,要对公司上下进行减磅瘦身,个别执行力强的部门已经开始了行动。现在整个仓库里的人都成了惊弓之鸟,搞得人人自危的。产品少了,仓管员们就聚在一起聊天,聊到最后总绕不开两个话题,一个是传染病,一个是裁员。这是两条死胡同,聊天的人每次都是以叹气作为终结。林平原听到后也加入了他们的话题。林平原说:“如果我被裁掉就去捡破烂,怎么着不是活一辈子?”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林工你不会的!”“我怎么就不会呢?现在想想也无所谓了,刀在头上,迟早有落下来的那一天,爱咋咋地吧。”
调班的那天,林平原和老关一起喝酒。老关说:“哥呀,听说有的公司已开始裁员了。你们公司不会吧?”林平原笑说:“估计正在行动呢。”老关说:“还没到山穷水尽的那一步,都还有挽回的余地。”林平原说:“有办法?”老关说:“当然有。裁谁不裁谁你的领导说了算,你完全可以利用这几天和他多联络多沟通,然后……然后,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当然明白。”林平原摇头说,“兄弟,还是算了吧。我是想通了,大不了回家种地或是捡破烂。这个事吧,你把它想复杂了它就复杂,你把它想简单了它就简单,就像迈出去一步再退回来那么简单。”老关笑说:“哥,你能这样想我就放心了。”
林平原出了老关家,在兴盛公寓门前的大榕树下坐了一会。榕树的树冠浓密如盖,新生的叶子肥厚硕大。前面的小河静静地流淌,小路两边的棕榈树如同两条平行线,笔直地伸向夜的深处。他想起数天前的那个夜晚,他跟踪那个人走向小道的尽头。他笑着擂了自己一拳:“他×的。”
他从河边拔了一把青草,折身往家里走。
白马正等着他和青草。他将昨天剩下的草丢进垃圾桶,将新的青草递到它的唇边说:“吃吧,吃吧,每天都少不了你的。”他坐在灯光下望着纸上的白马,经过这些天的悉心喂养,白马似乎真的壮硕了不少。隐隐约约地,他感觉白马的鬃毛在微微拂动,他以为是风吹纸动,他凑到近前细细观看:天啊!不仅是鬃毛,全身都在动呢。白马像在摆脱某个束缚,一直在挣扎,四蹄踏在桌上“哒哒”有声。
终于,白马跳到了地面上,两只前腿跪地,脖项亲昵地贴在他的脸上,口中呼出的气流吹得他的耳朵直发痒。他对白马说:“你起来吧。”白马说:“谢谢,谢谢你救了我。”白马站直身体后,他发现这真是一匹好马!身量高大壮硕,两只眼睛清亮如水,鬃毛光滑如缎,四蹄健壮有力。他环视了一下出租屋,犯起了愁:“这么大点地方,我该怎么养你啊?”白马说:“我还真不能久待,我得回去救一个朋友。”他说:“需要我做什么?”“需要你跟着我回去一趟。”他回身找了件衣服。白马说:“你得拿点武器之类的东西。”看了一圈,没有什么武器可拿的,他的脑子里灵光一闪:手电筒!
他握着手电翻身上了马背,白马一声长嘶,撒开四蹄开始驰骋。身前身后一直有薄雾萦绕,分不清是凌晨还是黄昏。雾霭中,路两边的田地里似乎有农人在劳作。他无意中回转身,发现随着白马的奔跑,道路一直像卷轴一样跟着向内回卷。跑着跑着,柏油路变成了石子路,后来石子路又变成了黄土路。随着周遭的薄雾变淡,林平原打开了手电,手电光束中是更震惊的一幕:田里的农人的头发、衣服,还有身边的农具也变个不停。先是由现在时兴的毛寸变成了盘在头顶的辫子,又从辫子变成束发挽髻的样子。发型改变的同时,他们的农具也由全自动变成半自动,由半自动变成手扶铁犁,再由铁犁变成了铜犁。
后来薄雾散去,视野之下一片明朗。白马说:“到了。”林平原便关了手电的光束。远处,是一片低矮的茅屋草舍,近处的黄土地里,一群着短衣短裙扎裹腿的人在扶犁耕田。有人在河边用一种奇怪的东西灌溉庄稼,林平原想起来了,那是一种叫“桔槔”的工具,他上学时曾在一本历史书上看到过。白马回头对林平原示意:“这是生刍,我以前就在他家。你看,他现在又换了新的马和牛。”林平原看了那个耕田的男人一眼,那人又黑又瘦,实在不起眼得很。林平原问:“你的朋友呢?”白马说:“可能在张屠夫家,咱们得赶紧过去,千万别晚了。”
张屠夫正霍霍地磨着手中的青铜尖刀,院内的柱子上拴着一头觳觫不止的青牛。白马回头和林平原交换了一下眼神,两个皆心照不宣。白马纵身闯进院子,没等张屠夫反应过来,林平原从肉案上抄起一把青铜刀,抬手斩断了青牛的绳索。张屠夫大吼一声挥刀冲了上来,林平原左手牵着青牛,右手将手电筒掷了出去。张屠夫不识此物,哇哇大叫着向后逃去。
林平原骑着白马,牵着青牛,向着前方奔去。身后,黄沙弥漫,烟尘滚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