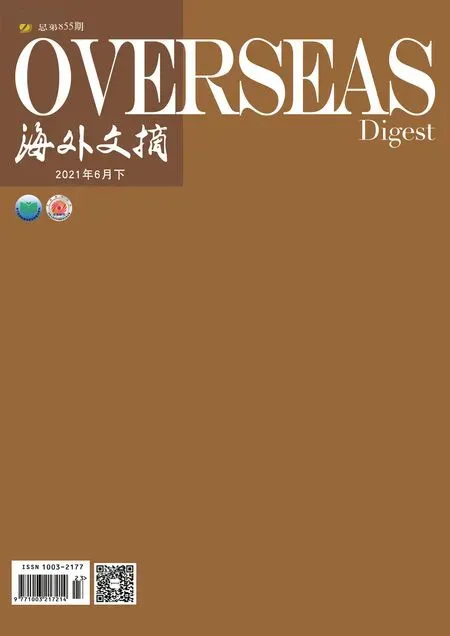浅析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缺陷
王定忠
(广东国律律师事务所,广东东莞 523000)
1 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立法背景
2021 年1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开始正式实施,原本的《婚姻法》相继废除。与废除的旧版《婚姻法》不同,《民法典》第1077 条在办理离婚登记中增加了“离婚冷静期”的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并领取离婚证;未申请领取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随之,民政部发布了《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有关婚姻登记规定的通知》。其中对离婚登记程序进行了调整。即2021 年1月1 日起登记离婚需要经过“申请─受理─冷静期─审查─登记(发证)”五个环节。自此,离婚冷静期作为离婚的一项程序性的制度,调节功能开始启动。
诉讼离婚中不设置离婚冷静期制度。我国的离婚程序性制度规定了两种,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离婚冷静期作为离婚的前置程序,只适用于协议离婚。该程序性制度的调节功能,通过赋予夫妻双方单方撤回权来实现──在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申请之日起的30 天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申请,即需要积极作为、主动申请;在上述期限届满后的第二个30 天内,夫妻任何一方未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则视为撤回申请,即消极不作为的单方撤回。由此可见,“离婚冷静期”实则为60 日,且任何一方都可以单方撤回离婚申请。
2 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缺陷
2.1 民事基本原则的冲突
离婚冷静期制度的设立,与婚姻自由原则存在直接的冲突。婚姻自由不仅是我国婚姻法之基础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人权制度。婚姻自由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包括结婚自由权和离婚自由权。就婚姻当事人一方来说,该项权利有其相对性的一面。但是,当婚姻当事人双方均同时实施该项权利时,其权利的相对性就不再彰显。此种情形的婚姻关系解除,当事人双方享有绝对的权利。如若再科以婚姻冷静期的前置程序,就是对婚姻双方当事人离婚自由的干涉,而不是针对相对权利的限制,更不是对离婚自由制度的补充。可见,当婚姻关系双方当事人同时享有并实施离婚权,并就此竞合一致时,离婚冷静期制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以契约角度论,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实施违反了民事契约制度下的合意原则。婚姻关系的实质就是特殊身份的契约关系。契约的成立与解除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即一方与契约相对方达成意思表达一致。当然,这种合意也有其相对性的法律属性。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就解除婚姻这一点,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在不违背社会等公共利益和第三人权益的情形下,即可离婚。设置离婚冷静期制度无疑是对契约合意精神的破坏。
同理,该制度的设置与实施,也是对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挑战。作为民事行为规范的灵魂原则,意思自治有其相对性的一面,那只是在有碍于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的情形下,所受到的限制。但是,在合意离婚的情形下,无论是婚姻关系的哪一方,所作出的离婚意思表示,均符合相对方的利益,在没有关涉到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方自由的情形下,就没有对这样的意思自治进行干预的实践基础。就此角度论,离婚冷静期的程序性前置措施,无疑是挑战了意思自治精神的正当性。
2.2 混淆离婚实践的评判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9 条规定,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节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诉讼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由此可见,离婚的界定标准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而没有其他。这也是评判离婚的唯一标准。即使是协议离婚,也是如此。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任何一件协议离婚案件,在登记时均科以离婚冷静期的前置程序,“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离婚实践评判标准就容易被混淆。由此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当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在离婚冷静期届满继续主张离婚的,离婚冷静期究竟是用来判断“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程序性证明,还是离婚与否的直接评判标准。假如离婚冷静期届满双方仍然继续离婚的,该冷静期制度的设立就会形同具文。同时,人们往往会混淆离婚的界定究竟是“感情确已破裂”还是“离婚冷静期”。实践中必然会出现以“离婚冷静期”,来错误的替代“感情确已破裂”的离婚评判标准。
2.3 增加离婚成本
婚姻关系双方当事人处于自愿协议离婚的,在登记时设置离婚冷静期前置程序,无疑会徒增个人离婚成本和司法诉讼成本。当诉求离婚的双方在登记时,由于离婚冷静期程序的牵制,往往会在冷静期届满后,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外地出差、学习等其他客观事由不能继续办理登记手续的,当然也不排除恶意报复等,协议离婚就会必然失效。当事人的时间成本、自由成本以及物质成本等就必然会增大。当事人继而选择诉讼离婚的,无形中就会导致人民法院离婚诉讼大幅度上升。这给当下本身就司法资源紧缺的国情,造成更加大的压力。浪费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增加了离婚成本。
2.4 影响婚姻家庭质量
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双方自愿登记解除婚姻,这本身就说明了他们之间的婚姻存在问题。如果已经达到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由于离婚冷静期的设置,导致双方因时间等种种原因,放弃离婚。势必会在将来的生活中,矛盾不断,在斗争中过日子。不和谐地继续着“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婚姻。其婚姻质量与包办等违背自愿的婚姻,在本质上没有区别。由此可见,离婚冷静期的设置,往往会影响到当事人之间的婚姻质量。同时,作为家庭成员的子女,无形中成为受害者。双方长辈的晚年幸福又何尝不受影响。
3 离婚冷静期制度设缺陷的成因。
离婚冷静期制度设置的理由缺乏逻辑的正当性。离婚冷静期制度设置的初衷是为了缓解离婚潮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立法提案认为目前社会离婚率持续增高,源自于激情式冲动离婚现象严重。80 后、90 后缺乏家庭责任感,遇到鸡毛蒜皮的家庭生活小事就离婚。所以,设置离婚冷静期制度来温和地干预离婚,给冲动离婚者一个缓冲的机会。
对此,笔者认为该立法理由缺乏生活逻辑。生活当中确实存在所谓“冲动型离婚”的情形。但是,这种归纳推理命题不真。以个案情形归纳推理出一般社会现象,需要个案情形具备一定的社会代表性,否则,结论不准确。再者,即便是一时冲动就协议登记解除婚姻,如果夫妻感情基础存在,复婚的选项无疑是一条康庄大道。冲动型离婚的本身,也就说明了其婚姻感情基础存在问题。以离婚冷静期来缓冲,矛盾并没有解决,而是压制了。而且离婚的诉求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表述,属于主观命题。主观意思领域的表述,仅靠外界制度的阻却,不是解决问题的逻辑手段。因此,离婚冷静期制度设置的前述理由,缺乏逻辑的正当性。
同理,离婚冷静期制度设置的借鉴理由也是缺乏逻辑的可比性。支持者意见的另一理由,就是借鉴国外的立法,来支持我国离婚冷静期制度设置的合理性。他们认为,韩国为遏制不断上升的离婚率,在2005 年推出了“熟虑期”和义务调解制度。规定申请离婚的夫妇如有子女,必须经过3 个月的“熟虑期”,如无子女,则“熟虑期”为1 个月。从2010 年6 月起,韩国大法院推出了“离婚熟虑制”。实践表明,这种“离婚熟虑制”效果显著。京畿道水原地方法院试行该制度半年后,协议离婚取消率从6%上升到了23%。 加拿大法律规定,婚姻破裂而且分居达一年者,才准许办理离婚手续,除非已有通奸或虐待的证据;美国的普通离婚程序中,需要经过6 个月的等候期之后,离婚手续才会办理完成,夫妻关系才可以终止;英国法律规定,婚姻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作出离婚声明后,须经过9 个月的反省与考虑期后,如果离婚申请人和当事人都认为婚姻无法维持,则准许离婚。
国外的制度是否科学、文明,须由其本土的社会实践来决定的,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不讲国情不加任何变革直接移植。前述国家设立离婚冷静期制度,或许有其存在的社会合理性。
我国则不然,仅仅从我国离婚制度的逻辑演变来看,我国设立离婚冷静期制度,必然导致该方面的法治倒退。综观我国离婚制度的立法,曾经也有类似离婚冷静期的规定与演变。1994 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此法律现已失效)第十六条规定,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当事人的离婚申请进行审查,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对符合离婚条件的,应当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注销结婚证。当事人从取得离婚证起,解除夫妻关系。可见我国在离婚制度的立法初期中曾规定了“离婚冷静期”。2003 年修改后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取消了审批期的规定,改为当场发证。离婚冷静期被取消。可是到了2020 年5 月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 年1 月1 日起施行。第一千零七十七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很明显,我国的法治建设,在这方面是倒退的。如果借鉴国外制度一说逻辑符合我国国情,可以起到抑制离婚率高涨的社会问题,不如直接引进实施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关于离婚的制度,直接剥夺配偶一方的离婚权即可,何必借鉴韩国等“离婚冷静期制度”。可见,借鉴一说同样缺乏正当性。
社会离婚率高涨,根本原由不是冲动离婚所带来的结果。而是由社会诸多因素造成,如住房、工资、就医、子女教育等现象所致。要解决离婚率居高不下的社会问题,只有在社会各个领域配置科学制度,体现充分公平的社会体制,减少夫妻、家庭矛盾,而不是依靠离婚冷静期这一冰冷的制度。
4 结语
协议离婚奉行的是登记主义原则,取消“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程序性限制,更好地彰显社会主义的自愿、效率、公平、自由的精神。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7 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2)《婚姻登记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当事人的离婚申请进行审查,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对符合离婚条件的,应当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注销结婚证。当事人从取得离婚证起,解除夫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