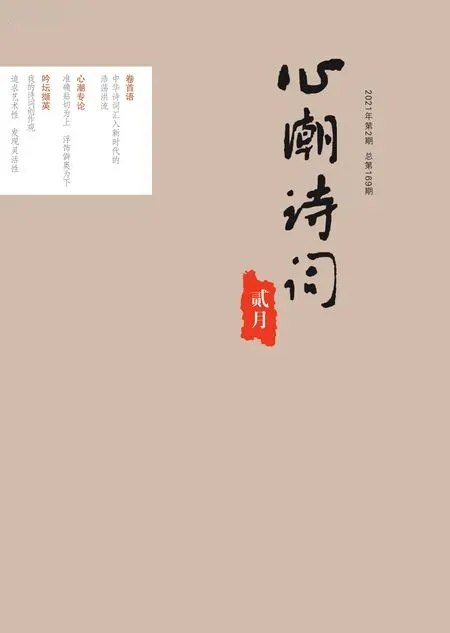浅谈当代诗词发展
乔 乔
诗词创作从古至今都是文人墨客的一大标志性特点。不一定是学者,文学爱好者也写;不一定能写好,合辙押韵的就成;不一定有意义,表情达意了便是。这并非是否定,而是一种客观事实。但写诗词者众,真正叫得上姓名留得下经典的却不多,大部分都沉默在了时间这无涯的荒野之中。大抵有的诗是千古绝唱,便成就了诗人;有的人为帝王将相,便留下了诗文。
在近几年的当代诗词研究中,已有学者提出了诗词中应有现代性,而后又出现了关于“既要有现代性,也不能牺牲其古典性”的讨论。在当代进行诗词创作已经不再只是一种传承,更是一种挑战。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有三点是一定要去关注的,那就是其作者、作品和受众。
一、“诗人”和“学者”
当代诗词创作者较之古时,数量更多,两极分化也更为明显。而在诗词的研究和创作过程中,首先要区别“诗人”和“学者”。并非是鉴别诗词作品的好坏,也无褒贬之意,而是对其作者身份进行区分。
“诗人”和“学者”从字面上就有着明显的分别。“诗人”是写诗的人,而“学者”意为做研究的人,这里仅指做诗词研究的人。在古代,能够识文断字的人非常有限,读书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年代越久远,越奢侈。但也正因为这样反而将诗人词人的范围控制在了真正有学识的人当中。同时也产生了“诗人”即“学者”的情况。当然,这里不排除依然有大部分的诗人由于不那么出众,其诗文并未能流传至后世。而当代社会在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下,大部分人都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这对于诗词本身的推广自然是有益的,读者的鉴赏水平理论上也应有所提高。对于诗词创作来说,却是降低了门槛。人人都知道律诗、绝句,人人都懂得词牌名和押韵。因此“诗人”和“学者”之别就显现出来了。
“诗人”以诗词创作为主。当代“诗人”早已不只是某一个特定的群体。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写,都可以被称为诗人。有人偶尔灵感乍现写出了好句子,有人始终写得随意,连平仄也不循。龚刚教授在对当代新性灵主义书写进行释义时表示:诗是先有被闪电抓住的瞬间,然后再于沉静中回味而得(华兹华斯《我好似一朵云独自漫游》)。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古体诗词的创作。当代诗人写诗词有着不可避免的问题,比如没有灵感却有指标时如何写?没有感悟却有任务时怎么办?又或者只有情绪没有经历的人写什么?浮于表面的诗写多了,也会有惯性。太多不可抗力摆在当代诗人的面前时,一首好诗就尤为难得了。何况好的表达、好的意象就那么多,前人早就写烂了,想要写出足以流传的诗句就更难。
“学者”以诗词研究为主。这一群体就更为特殊。有的学者只做研究,而有的学者同时也进行诗词创作。做诗词研究的人会在研究过程中学习到更多的理论知识,并对理论进行深挖。诚然,理论会使创作的进步更加迅速,却也会为灵感戴上枷锁。知道越多顾虑越多,学者在创作诗词时更容易瞻前顾后。尽管早在清代的《随园诗话》中就已有:“不过一时兴到语,不可以词害意。”而《红楼梦》里在香菱学诗一段中,也出现了“不以词害意”的说法。但知易行难,这也是各行各业“学院派”和“野路子”之间最大的差别。也有人说,这都是初学者犯的毛病,一个成熟的学者会知道如何用好理论,写出好诗。
即使有了不拘于外物的诗人和成熟的学者,也并不意味着当代诗词就能有更好的发展。作者固然重要,读者却也必不可少。
二、“读者”和“作者”
与古代诗词相比,当代诗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读者少而作者多。前一章提到了当代诗人较之古代诗人应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群体。尽管质量参差不齐,但数量甚多。若是写诗的便叫诗人,那除了各地诗词学会成员外,还有多少不被大家所知道的小圈子、小范围的诗人存在?
可读者不是。古代由于娱乐活动少,书籍纸张贵,因而诗词成了成本最低的娱乐活动。官方的诗词有专人编纂成册,民间诗词也有机会在坊间传唱。反观当代,各样的娱乐活动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如果不是圈内人,能接触到古典诗词的机会实在不多,又何来传唱。而诗人自己,扪心自问有多少当代诗人会去研读当代诗人的古典诗词?即使有研读,却也甚少,更多的时间也是放在了那些经历过时间的洗刷所留下的精品上。因而当代诗词真正的读者群体,几乎就只有各期刊的编辑,或做当代诗词研究的学者。
这并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鉴赏诗歌对于读者的要求是高过小说、歌词等更加通俗的艺术形式的,而读古体诗词对于读者的要求又要大过于现代诗。从鉴赏能力和阅读时间上就拦住了大部分当代人。但这大部分当代人,却正是当代社会最大的读者群体。
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写诗是闭门造车,一群人也是。现在有一个词很有趣,叫“火出圈”,指的是某句话、某件事、某个梗的热度已经从自己的固定圈子传播出去,成了圈外路人也熟知的事。诗词创作也一样,只有群里人知道这首诗,只有朋友圈的人点了赞,过几个月再没有人记得。那诗词创作的意义有多大?尽管大部分诗词的宿命注定是淹没在时间里,但至少,应该想办法使它们留下。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古代诗词、现代诗歌被谱出曲、唱成歌,却鲜有当代古体诗词能“获此殊荣”。其一,众口难调,每个人的欣赏角度和评判标准不同。其二,与古人相比,部分当代诗人的诗词韵味确实不足。古代文人自小所习便是文言,而当代人并不人人熟通白话,何况文言。其三,在资本占领市场的大环境中,另辟蹊径并非明智之举,风险甚大。这就涉及当代古体诗词的传播要不要造星,该不该造星的问题,这里不做深入探讨。
被唱成歌的当代诗词并不是没有。《大宋提刑官》的主题曲《满江红》其歌词就改编自当代诗人王凯娟的词《满江红·狂风沙》。其改编也仅仅是在副歌部分将词的上下阕相结合重新唱了一遍,并无太大改动。尽管学界对这首词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它依然是一首火出圈的当代词。自2008年《满江红》之后,并无新的当代古体诗词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大众的视线之中。但2007年前后却涌现出一批古风原创歌手,有团队也有个人。他们也均是以古代诗词或当代古风诗入歌,并未进行古体诗词的创作。
但无论是“诗人”“学者”之别还是“作者”“读者”之量,都是限制当代诗词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因素。最重要的还是当代诗词应该有属于自己的风格,学习前人固然重要,但一味的模仿,却也会失掉了当代的特色。
三、“古代诗词”和“当代诗词”
诗,志也,从言寺声。意为表达内心之志向,抒发心中之情感。词,意内而言外,从司从言。本意是对于内在意义的外在表达,而词作为诗歌的一种表现形式,与诗一样,有着表情达意之意。诗词最初的意义,便是用来表达心之所想、心之所感、心之所愿。历经千年,诗词早已成为独立的文体,而不是时代的附属品。
时代在发展,人们的生活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诗词发展报告2018》中提到当年的讨论焦点之一便是“现代性”。古体诗是否、怎样具有“现代性”以及如何让当代诗词接地气。诚然,古人今人都是人,有着相同的七情六欲,但表现形式定然有所不同。而这不同也使得诗人们在进行诗词创作时有着不同的特点。
从创作角度上来说,差别最大的是边塞诗。古代的边塞诗偏重“我见”,而当代的边塞诗偏重“我闻”。古代的边塞诗人一般分为两类:为建功或心之所向行至边塞的文人,因战事或戍守边关后有感而发的武将。但这两类诗人都是自己来到了边塞经历了战争,或在前线或在后方,但都亲身经历过、亲眼见过、亲自指挥过战争。因此他们对于战争的理解与感悟应是更为直观也更为透彻的。而当代诗人,擅写边塞的就已不多。在当代中国数十年来相对和平的大背景下,战争离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个人都十分遥远。因此创作出的边塞诗只得以塞外风光为主。塞外风光是什么?对今人而言它是沉淀的文化,是厚重的历史,是掩埋的鲜血,是原始的风貌,它并不以单纯的皮相之美而美,更多的是因其背后所承载的一切。但这只能被记得,无法被看见。能写出“我见”的,永远只有那些已经被尘封在历史洪流中的人们。如今再写,也只得用“忆当年”“忆往昔”“遥想”“遥记”等诸如此类的词来回溯历史。那些“金戈铁马”“烽烟四起”“血染山河”于今早已不复存在,“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词二首·其一》)也不再是如今诗人们所能体会的了。
从意象使用上来说,变化最明显的也是生活气息最浓厚的,就是闺怨诗。闺怨诗是女性视角下的产物,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背景下,应是最能反映古时日常生活起居的诗文。而日常生活起居也正是古代与当代差别最大的地方。“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其中提到的“锦书”为书信,一般指夫妻间互传的书信。在古诗词中非常常见,但若是放在如今就显得奇怪。有哪个夫妻会将一条微信一个电话能解决的事,非得写信呢?哪怕是有这个生活情趣也并非常态,更不会因为等不到信而着急致使分隔两地的二人思念倍增。可若是将“微信”“电话”等词放进诗词之中,却又破坏了诗词的古雅和含蓄。同样被日常生活所淘汰的意象除了书信还有蜡烛。“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夜雨寄北》)中虽是以剪烛形容深夜秉烛长谈,其意并不在烛,但放在今日却也不再合适。幸而“灯”之一字倒还古今通用不显得过分违和。
和“古代诗词”相比,“当代诗词”应该有更多当代的气息。如今的读者可以从诗词中了解和学习历史与文化,看见曾经的人文风貌。毕竟诗本身就是用来记录民风民俗表达思想观念的。可当21世纪成为“古代”的那一天,后人是否还能从诗词中了解今时今日的一切?还是说只能通过其它的材料,如影视作品、小说、散文去了解?可喜的是已经有学者开始实践并在大学的课堂上将此种尝试延续了下去。
结语
诗、词作为文学体裁,自古以来就不是少数人的娱乐,而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珍宝。为了推动其发展和传承,今天的诗人们要做的,不只是写好诗,还需要以开放的态度去接纳更多元的融合。文化没有圈,人人都可写诗词,都应该被鼓励。读者没有界,人人都该读诗词,诗人更要阅读。诗词没有代,代代都得有特色,融合古典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