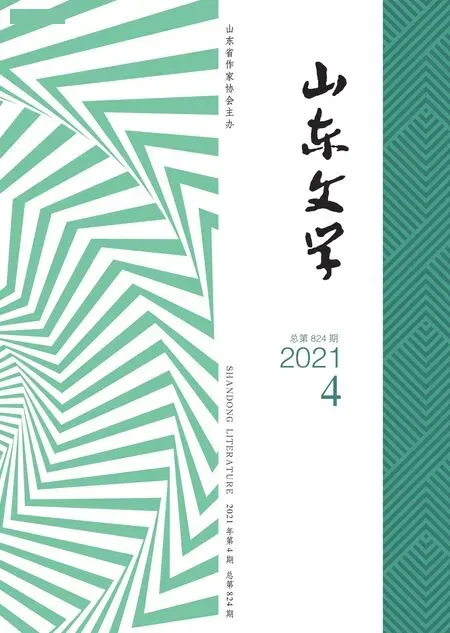域外作家小记
梅里美
梅里美的小说之美是狂放的美,就像他笔下的吉普赛女郎,有一种野性、放纵和原始。他的笔触也有曼妙轻柔,有不能避开的残忍,无法自拔的冷艳,练达世故的冷漠。梅里美画出了十九世纪法国上流社会的风俗画,充盈的浪漫主义情调和那种理智的批判向度,让人感受到一种冰层下面涌动的力量。
《卡门》在世界文学版图上一直星光璀璨,自从比才的四幕歌剧1982年由中国歌剧院第一次搬上汉语舞台后,在国内更是备受推崇,经久不衰。梅里美将一个悲剧写得风情万种,在有限的文学空间里,展现了卡门的无畏、泼辣,当然也带着无奈和反叛。沉浮于声色犬马的漩涡里,卡门无法随心所欲,我行我素,只好随波逐流,红尘翻滚。她酷爱自由,奔放不羁,但始终步步惊心,身不由己,处于弱者地位,缺乏安全感。卡门是一个贪婪的惊叹号,是一曲夜店挽歌,折射出一种扭曲的世相人生,映照出浮华社会的虚伪、无情和颓废。
梅里美笔下这种狂放之美,掩盖不住一种深入骨髓的惨淡,像罂粟之花让人不寒而栗,看似美好的事物潜伏着腥风血雨,残酷的美,实际是无法抗拒的痛。
吉田兼好
吉田兼好是一个法师,他用一只法眼,看这个红尘世界,总带着俏皮的善意,带着入世的警觉,睿智、机敏和乖巧,有一种只可意会的禅味。
禅境是一种修行,是一种气度,也是一种生活姿态。徒然并不是无聊,它是一种闲逸。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处处留痕。这些随手记下的点滴,是本真的写意,是自然的情状,是旷达的流泻,犹如浮在心头的明月,有一抹“云深不知处”的邈然。
兼好法师说:“保留某种不完善会使事物显得有趣,并使人感觉到还有一点发展空间。”这个意思就是,有转身的地方,才有回旋的余地。法师用三只眼睛看世界,我们只能用两只耳朵来体味。世上有一些不易体察的事情,发觉的秘密就在于你开了慧眼。其实,所谓慧眼,大概就是比别人多一分细心、细腻、细致的考量。这“徒然”也就显得不那么空洞而有了一些实际的意思。
任何事情,包括幸福的弓箭,都不宜拉得太满。储备下力量,才能保持勇往直前。《徒然草》就是让你“徒然”的时候,放松下来不再“徒然”。
三岛由纪夫
爱,也会饥渴,过分的饥渴就是畸形。畸恋充满危险,步步惊心,是颓废的土壤上一朵恶之花。三岛由纪夫是一个冷静、固执、细腻的作家,他用扭曲的视角写出人间现实的悲苦。
《爱的饥渴》是一本寂寞的小书,写一对夫妇感情不和,女人两次要自杀,丈夫死后又被公公霸占,但内心里又狂恋着自家的仆人,最后反而杀死了他。全书十二万字,在越写越长的年代,这只能是一部小长篇。三岛写得很节制,很冷静,却很见分寸,很有质感,甚至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一丝丝锐利的寒气。小说的骨骼棱角分明,语言的肌肉充满弹性,放射着苍白的人性之光。
家庭需要经营,爱情经营不善,就会危及婚姻殿堂,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三岛由纪夫的小说,写的是不常见的悲剧,其实是虚幻的枝繁叶茂遮蔽下的一枚精神恶果。这是长期隐藏的一角阴暗之处,却最能体现世间的爱恨情仇。当纯净和明丽不再眷顾人生,惨淡的结局已经预示着唯美的毁灭。缠绵、暴力和血腥只隔着一层遮羞布,一旦揭开,所谓的爱就是咫尺天涯。一切爱都有根源,真爱不可出轨,原罪不可饶恕,变态不可同情。只有痛惜和叹惋,像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为灰色的饥渴爱痕打上时间的烙印。
普鲁斯特
好书是有气场的,好作家就是气功师。感受大师气场,亲近的过程就是心灵震撼的过程,也是精神升华的过程。可惜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亲近大师,这是多么贵族化的精神之旅啊。普鲁斯特就是这样的大师。有时候你要睡了,昏昏欲睡的那种,这时候天昏地暗,就要合上双眼,正像普鲁斯特的小说一开头营造的那股气氛,心里说“我就要睡了”,但实际上反而清醒了,在气场的作用下,你仿佛谛听到了普鲁斯特的娓娓恳谈。
《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长河小说,它适合在任何情况下阅读,每读一页就有一页的收获,它的奇特也许就在那漫长的絮语里。
在斯万家那边,夜幕低垂的时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烛光一直在梦里,在普鲁斯特不倦的思绪里摇荡。一群鲜活的少女舞蹈着,“斯万夫人在钢琴前坐下,她从粉红色或白色的,总之色彩鲜艳的双绉丝的便袍的袖中,伸出那双娇美的手,张开手指抚弹琴键,依然是那种存在于她的目光中却不存在于她心中的忧郁。”
“对某个形象的回忆只不过是对某一片刻的遗憾之情”,普鲁斯特用夜色和水一样清澈柔和的语调向你倾诉,透明的不加任何粉饰的意境雨雾般曼妙。即使是寂寞和忧伤,普鲁斯特也那么诗意,那么淡然,就像是清风拂过琴弦,有一种沉醉的优雅。
有人说“理想使痛苦光辉”,的确,这个自幼就与病魔抗争,只活了五十一岁的气功大师,就是用痛苦而光辉的身影,在世界文学高原上“占有一个无限度延续的位置”。
写作需要一气呵成,长河小说也有一个“气”,作家就是靠这股“气”来形成气场,去感应别人。所谓写作意义上的“心平气和”,就是情绪饱满,酝酿清楚,下笔如有神。普鲁斯特就是这样,他“在时间之中”,缓慢而有力地影响着读者,让人感受到气场十足的喜悦,感受到一片史诗光芒的照耀。
茨威格
奥地利是艺术之邦,蓝色的多瑙河水缓缓流淌,不舍昼夜,不仅滋育了伟大的音乐奇才莫扎特、施特劳斯,著名的精神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更有杰出的小说家茨威格。
作家张炜说“他的作品太吸引人,太漂亮也太巧妙,好得让人嫉妒。他的小说都可以被读者记住,都有极为用心的设计,但绝不是市面上的读物。”这是小说家的真知灼见,是伟大艺术心灵的沟通。读茨威格,你内心一定会很纯洁,没有一丝杂欲。《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象棋的故事》……这些耳熟能详的篇什充满了美妙情趣,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一如吸足了汁液的海绵,饱满、松软,富有柔韧的弹性。细节在平静中像刀锋一样锐利,睿智与机敏忽隐忽现,体现出古典的优雅。那些如月色一般沉静的倾诉,好似静谧的大海,柔和、亲切,涌动着温情。充满多瑙河气息的文字,搭起了一个斑斓的舞台,舞蹈的幻影展示出华彩的技艺,一切都那么湿润,那么清澈,诗肠鼓吹,引人入胜。茨威格真是语言的魔术师,这些平凡的文字到了他的笔下,就生动起来、明媚起来,灵性起来,于是你会感到文字在暗夜里燃起的光亮是如此美丽,你会感受到阅读茨威格就是阅读一次多瑙河的蓝色风景。
清少纳言
《枕草子》是一部多趣的书,有些琐细、顽皮、多情,更是一些呢喃、絮语、片段。它写“扫兴的事”“可憎的事”也写“愉快的事”“担心的事”“无可比喻的事”甚至写 “人家看不起的事”“可怜相的事”“想早点知道的事”。它写了很多事,一枝一叶,举手投足,都是人生的观察和经验,虽然是小女子的眼光和情味,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忧郁和无奈,却自有它的甘醇和妩媚。
你看它写“秋天的傍晚”:“夕阳很辉煌的照着,到了很接近山边的时候,乌鸦都要归巢去了,便三只一起,四只或两只一起的飞着,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它写“不大可靠的事”:“厌旧喜新,容易忘记别人的人。……善于说谎的人,装出帮助别人的人,把大事情承受了下来。”
它写“男人”:“男人这东西,想起来实在是世上少有的。有难以了解的心情的东西。舍弃了很是整齐的女人,却娶了丑女做妻子,这是不可了解的事情。”
其实,《枕草子》更像是一部日记,是一个人心灵的书写。它的有趣就在有意无意之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的是情调悠然。带着一份好奇亲近周围的事物,世界原来这么奇妙。
博尔赫斯
1986年6月14日,87岁的阿根廷著名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日内瓦逝世。他从六岁开始写作,以杰出的小说和诗歌赢得读者,与乔伊斯、卡夫卡、萨特、福克纳齐名。1967年,68岁的博尔赫斯双目失明,此后坚持口授写作,毅力惊人。他一生出版了三十多部作品,但他在1961年才开始获得国际声誉,那时他已经62岁。他曾先后获得阿根廷国家文学奖、法国国际出版家奖、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数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虽因种种原因失之交臂,但这并不能动摇他世界级文豪的地位。
博尔赫斯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将理智与抒情、叙事与辩证有机地剪辑到了一起。他的小说,以人生和命运的神秘为主题,开辟了小说写作的先锋文本。他的小说大都不长,都很精粹,是标准的短篇小说。他喜欢简洁,他认为20世纪的小说,应该越短越好。这对我们今天网络时代的写作很有启迪,现代人沉浸在纸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多媒体的冲击和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不再迷恋琐碎的长篇了。博尔赫斯的小说之所以受到欢迎,一方面是简短精致,另一方面是“融进了智力深奥的远见,洞悉人性的见解”,处处闪烁着机智的光芒,像《彼埃尔·梅纳德》《虚构》《手工艺品》《小径分岔的花园》等,都是传世经典。《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很喜欢博尔赫斯,称其作品是他书房的永久性藏书。
博尔赫斯还是个特别爱书的人,他的《私人藏书》也是经典之作,他自豪地说:“让别人去夸耀写出的书好了,我则要为我读过的书而自诩。”好书真是个魔术师,它的气场和温度,使人感受到一次新鲜的重逢。沐浴经典,这是黄金时代脆弱、奢侈而又幸福的事情。就像风中的爱情,燕子带走了它们的呢喃,却留下一串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