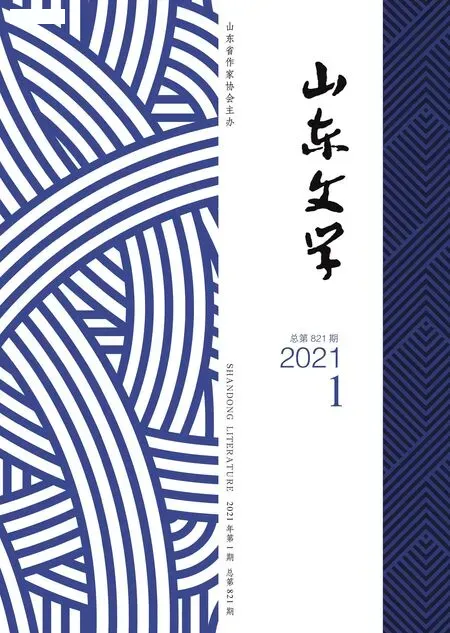皂角树下
卢金地
皂角树是一棵次生树,原先的那棵曾祖母去世时伐了打棺材了。第二年春天,在伐过的树根上又长出了一棵小苗。这棵小苗,如今成了我们村最老的树。
由于乡民的实用观念,除了寺庙、官府,很难落下成百上千年的老树。宅院外不能种树,宅院内没地方种树。当初,先祖们建家都是在山坡上,平地好种庄稼。山坡上能整平的地方受限,除去后滴水前出口占下的边角,院子就非常有限了。为了造土杂肥(老俗语:家土换野土,一亩顶二亩),家家户户院子里是必须挖出一个土坑积肥攒粪的,名曰粪坑。院内的落叶尘土、牲灵的粪便全入坑沤肥。粪坑的大小取决于院子的大小,院子大粪坑则大,院子小粪坑则小;粪坑当然越大越好,可也总得给人留下出入挪步的地方。堂屋门的左侧每家又必须设一个香台子供神。能生长一棵树的地方只有两处,一处是香台子旁边,多半是石榴树,另一处便是粪坑崖。我家这棵皂角树就是长在粪坑崖上,没人知道最初的那棵是人栽的还是自然生长的。
二十年前,我们兄弟子继父业招工进了百里之外的煤矿工作。父亲退休后回了老家和母亲一起生活;上年纪的人,五十六十还能自理,七十八十就难了。父母七十岁那年,我们决定接他们来煤矿生活。那时父母就住在皂角树旁边的瓦房里,人走后没有顾家的,怕小孩子打皂角打坏了房瓦。房瓦坏了房顶就漏雨,房顶漏雨房子就坏得快。为了保住房子,决定砍掉皂角树的“树头”。
那时的孩子,包适我自己,生活困难,食品缺乏,哪里有什么吃头。能打发嘴头子的只有野食,桃、李、杏、桑、楮不说,荚角里的种子只要能吃也在其内。这皂荚里的种子,除去外壳的硬皮,里面有一层透明的“肉”,最里面才是种芽。我们就吃那一层透明的“肉”。初时是剥离下来直接进嘴吃掉,后来生出一法,找一小瓶,里面倒适量凉开水,把“肉”放进瓶里,再放少许盐末,三四天后食之,弹牙咸甜,真是好吃。我近水楼台,吃得最多(也许这一吃法就是我发明的),也拿皂角发送给相好的小朋友,得不到的趁家里没人时就拿石块偷打。那时候,不光吃嘴的东西缺,生活用品也缺,买肥皂得用票。国家的利润是从下往上收,福利是从上往下放。票们分到生产队还能有多少?不跟生产队长相好的社员,除了按人头归定的布票外,其它票证很难得到一张。过年的时候也许会给一张肥皂票,但也买不到好肥皂,洗黑领子发灰,洗白领子发黄,打上的肥皂越多洗出的白领子就越黄。年轻人爱美,看着黄领子撅着嘴生气,打听着用什么东西才能洗白了领子,这就想到了皂角。
到我家找皂角的人可真不少。那时候的人没有卖的念头,都是找。去年秋天,一个收皂角的人到我家看皂角,说皂角开花时没打药都长了虫子眼了,原本能卖三百元的,给我五十块钱收走吧。我叫他收走了。那是自从有皂角树至今唯一挣到的五十块钱。
我记事的时候皂角树可能正是旺年吧,挂果很多,谁找给谁。冬天,皂角叶落净,光溜溜的树枝上满满地挂着皂角,乌紫发光,长如镰刀,亮如弯月。有一天,一个外村的老太太赶集路过我们村,七弯八拐地摸到了我家。响午头上,我母亲正在烧锅,头上搭块青头巾,不紧不慢地拉着风箱,听见大门一响,进来一个人,高声说:赶饭时的来了。我母亲听出是个老太太的声音,摘下头巾抽打着身上的草木灰走出来,一看,还真是个老太太,胳膊上挎着个菜篮子,正站在皂角树下仰望皂角树冠。见了我母亲说:大妹子收拾得这么利索,看你这院子扫的,都能照出皂角来了。我母亲一听就知道八成是来找皂角的,便开玩笑说:你这一夸准是来给俺儿说媳妇的,可俺儿还小着呢。老太太说:可不,您儿要是当娶的年龄我非得和你做亲家不可。俺那闺女这两天就去相对象,白领子洗不出个白来,我跟你找皂角来了。我母亲说:皂角现成就有,只是落地的都叫人找去了,得现够,我灶里还着着火,墙角间有竿子你自己够吧。正说着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放学回来了,母亲就转向了我,说:来的正好,你把书包放下,给您大娘够几个皂角。老太太看了看我,扭头对着我母亲说:大嫂,看你家学生多精神,赶明儿我给你说个好儿媳妇,你快回去看火吧,别烧到灶外来了。我把书包放到屋里,出来看见我母亲进锅屋了,老太太咕嘟着嘴直看我。我从墙角间拿出来一根长竿子,竿子的一头拴着铁钩,铁钩下罩着布袋子,既能勾皂角也能钩柿子。夏天解下钩子还能翻地瓜秧子。
有十多年,皂角树没挂果;砍掉了老树头,新抽出的枝条开不出花挂不上果。我以为皂角树再也不能结果了。那年春天,我正在皂角树下面的石桌上喝茶(石磨拆解后,两扇磨盘一个摞到一个上面成了喝茶的石桌),听到有蜜蜂的叫声,抬头看见树叶间有飞动的蜜蜂。有蜜蜂便有花,我站起身细细地找,终于在向南伸展的一根枝条上看到了一两串花穗。
我把茶壶茶碗放到石桌上,沏上茶,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耳朵里马上出现了声音:风声、鸟叫声,还有蜜蜂的嗡嗡声。可刹时作怪,竟然出现了推磨声。我把两扇石磨摞到一起,时间成了推手,石磨突突地转了起来。
在我们村没有电,没有打面机之前,老辈人都是用石磨推粮食制干头(粮)的。有牲口的人家还好说,把毛驴或者牛牵到磨道里,戴上眼罩,嘿哈一声毛驴或者牛就慢腾腾地走起来,石磨也就跟着呜呜地转起来;隔一会,两扇石盘的合口处就吐出粮食糊来了。没有牲口的人家就要人推了,往往都是全家人齐上阵,劳力多的还好,劳力少的,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唯一的男劳力我父亲在百里之外的煤矿上班,三个姐姐大一个出嫁一个,再说女劳力的力气也有限,这就得孩子“出战”了。照母亲的说法叫“有牛使牛,没牛使犊”。
我小的时候,村里已经有了电,也有了打面机,只是停电是家常事,一年到头送电的日子没有停电的日子多。那时的电线也差,刮风下雨打雷打闪肯定停电,就是有人在电线杆上尿泡尿,有人在电线下大着嗓子喊一声都有可能停电。这一停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送。你问大队电工什么时候能来电?大队电工说:这个咱不当家,得问公社。你问公社电工:什么时候能给俺大队送电?你是哪个大队的?尖山大队?尖山大队线路没问题,找你们大队去。直到上面有了新精神,大队革委会主任想用大喇叭头子喊喊,一开扩音器,没电;对着话筒吹吹气,没声。这才叫来电工去排查。
我最怕停电的时候家里没有了煎饼,这就得推磨。
往往天还黑着,屋里黑着,屋外也黑着。从黑地里传来了哧哧地刷磨盘声,哗哗地倒粮食声,我就知道要推磨了。我装着没听见,蒙头大睡。突然一股凉风把被子掠走了,上面传来慈母的吼声:起来推磨去。
我迷迷糊糊穿上衣裳,走出屋子,磨已经推了好大会子了,母亲正在接磨下来的粮食糊。清凉的晨光里突噜噜地推磨声响满了院子。石磨就盘在锅屋的北山墙下,两根磨棍插在磨眼里,一根三姐在推,另一根空着(母亲离开磨根去接糊子了)。我一边擦眼泪打哈哈,一边走到磨道里,把那根空磨棍顶到胸脯上;一边瞌睡,一边推磨。推完磨,天也亮了。东边的房顶刚有了一点红意思,生产队长的上工哨子就响了。姐姐们喝碗开水,一边吃着煎饼一边上工去了。母亲请了假在家烙煎饼,把我留下来烧鏊子。
今天的年轻人哪里见过鏊子,见过的也是那种直径二三十公分的小家伙,还是烧电的。我小时候烙煎饼用的铁鏊子直径有一米多长,想把偌大个鏊子均匀地烧热,让煎饼顺利地烙上顺利地揭起,可不是件容易事。火候是很难掌控的。除烧火的技巧外鏊子的支法也很重要。支鏊子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地鏊子,什么时候烙煎饼什么时候支,找块平地,用砖头或土坯支起十到二十公分的高度,底下只能烧柴火。另一种是灶鏊子,和锅灶一样是固定的,比锅灶稍底,却比锅灶宽大,灶里用煤箅子烧煤。那时正封山造林,没有木柴,禾柴不撑烧,多半都是烧煤。可烧煤的难度要比烧柴火大的多,煤箅子有限,为了把火散布到鏊子周边,煤火上面须要盖一块圆型的泥饼子。泥饼子盖在煤火上,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煤多了,泥饼子压上去就压死了,只出烟不出火。又不能加太少,煤少了,泥饼子把火势敛住了,火生发不出来。这两种都会造成鏊子热凉不均,热的地方煎饼煳了,凉的地方煎饼还没熟,揭不起来。那时我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还没有足够的烧火经验和技巧,每一回烧鏊子都要有这么两三回热凉不等的情况发生。母亲好性子的时候就帮我搂搂火,加减加减煤;碰到不高兴的时候,正在急头上,不但不帮我搂火,反而是煎饼劈子(削薄的竹片,约有半米长短,为抹平煎饼用的)劈头打来,打得我眼放金星,泪水流面。母亲打完,一手把我扯开,重新把炉火调整好,再交给我烧。我拉动风箱,炉火确是旺了,火苗呼突突蹿出了灶口,烤得我脸上发烧,泪也烤干了。
一只鸟在鸟窝上鸣叫。一缕阳光从鸟窝上照下来,正好照在我的脸上。我醒了,似乎就没睡,哪里有醒?可当年的老景确是来过的,我鼻子里还有烧鏊子吸进去的煤烟味。这会子那些老景一下子又不见了,北屋还是只存着半截屋框子,西边的锅屋没有了,上面皂角树的树杈上却多了只鸟窝,好像皂角树伸出一只手把锅屋提上去当成了鸟窝。不知那里面还有没有鏊子和烧鏊子的我。
皂角树上搭起了鸟窝,上面住满了鸟。各种各样的鸟,斑鸠、鹡鸰、白头鹟、小凤、水燕子,还有不少说不上名儿来的。为此,我不敢用没有盖的茶杯在皂角树下面喝茶,怕的是那些在我头顶上的鸟,一时急上来干出不人道的事来。
去年这树冠上还来过一对野鸭子,通体麻色,只在脖子上围了根蓝宝石一样的围巾。它们可能是以为树冠是一坑水了,想临时来这里洗个澡顺便看看有没有能吃的小鱼虾。它们落下来才觉得不对了,脚没站稳,又扑棱棱地飞起去了。野鸭子的这一荒唐行为,把皂角树吓了一跳,众枝条一起纷纷颤动。等看清了是两只野鸭子,皂角树宽厚地笑了。它早已成了老树,经历了不少世代,什么洋咕咕没见过?日本人在街上走的时候,它见过;还乡团抓二祖父的时候,它见过。那天去赎回二祖父的牛临走时就拴在它身上,另一头牛也是在它身上拴过后入社的。
皂角树还见过我祖父、祖母的离世。祖父去世时我还没生人呢,我只模糊记着祖母的丧事,朦朦胧胧觉得院里院外一片白晃晃地热闹。后来翻过“礼簿”,祖母去世于1966年。
皂角树还见过六个闺女的出嫁。我大姑、二姑、三姑;大姐、二姐、三姐。她们都是在皂角树下出嫁的。六次出嫁我只记得三姐的出嫁。嫁妆已经装上了车,拉三姐的地排车上一领红席围成了弧棚。三姐上车了。三姐哭,母亲也哭。有人说:驾着车把送送您姐。开始我没明白是说我的,等明白过来,一个堂叔已经去驾车把了。我只好跟在后面,一直送出胡同。那是1976年。
时间刮得眼生花,黑夜白天不分家。我伸手把石桌上的茶杯端过来,茶还是热的,就喝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