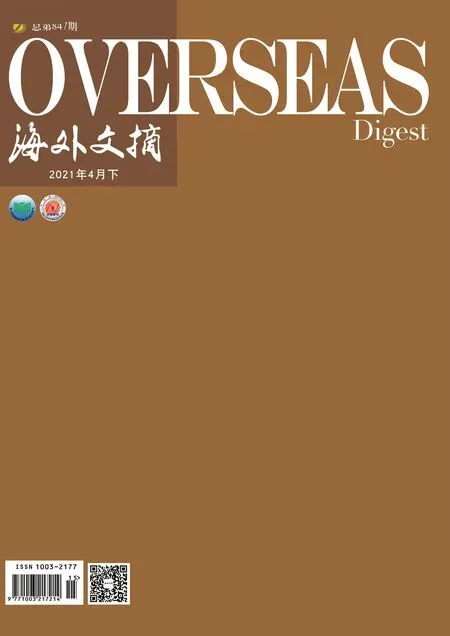后现代文化中的“失语症”危机——析《后现代主义及文化理论》
赵建宇 李卓群
(郑州小小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河南郑州 450007)
0 引言
《后现代主义及文化理论》是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费雷德里克·杰姆逊(Fedric Jamson)于1985年应北京大学之请来华讲学所开设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课的翻译记录,聚焦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文化特征。时值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转型时期,学术界整体上承接“五四”时期以来的启蒙思想,还停留在对“现代性”的仰望之中,因此,杰姆逊教授对于后现代理论的引入在当时可谓掀起巨浪,引来学界广泛的关注及讨论。
书中,杰姆逊曾多次提及“语言”这个承载文化、且与其不可分割的概念。在正式迈入现代性之前,传统语言学一直认为人类是语言的中心,而语言不过是用来表情达意、传递思想的工具;直到19至20世纪“语言学革命”以来对于语言与人类思维关系的研究面目一新,加上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跨领域带来的补充、解构,语言在现代社会工业化生产的萌芽与发展过程中,于日常用语贬值、陈词滥调肆意横行的普遍情状下逐步走向失控。本文籍此现象为参考,从现代语言学对语言本质研究的流变出发,探讨语言遭后现代工业生产及形象文化侵掠、腐化现象所造成的“失语症”危机。
1 语言本质研究的历史流变
杰姆逊在书中提出,现代语言学也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现代语言学穿过种种现象,对语言本质做出反思。
洪堡特被誉为“19世纪语言科学界最著名的四大学者”之一,他认为语言是人类的天赋属物,语言使人成其为人,语言与人类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赫尔德观点的基础上,他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世界观,认为语言决定了思维,人和事物受到语言的制约。
杰姆逊提出,在不同语言系统使人们看待事物产生差异的过程中,涉及语言的功能及语言给我们的认识所造成的障碍或帮助的问题。而当代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萨丕尔也认为语言决定了人的感知,并提出了著名的“沃尔夫-萨丕尔假设”:语言在存在之前,决定了存在,而不是存在决定语言,因为我们的思维和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是由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的语法结构塑造而成的。
20世纪,“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整理出版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奠定了人类言语科学的理论基础,并且对语言本质的问题做出了具有里程碑式的开拓。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复杂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一套孤立、自足并可以独自运行的符号系统,而主体只不过是这个系统之中的一个成分。因此,人必须栖居在语言这个系统内,才能够表达自己的观念。
杰姆逊认为,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问题,乃是当代哲学和理论的核心,贯穿了20世纪的哲学思辨。一直以来,人们理所当然地把语言作为“工具”来看待,自认为语言受自己主导和掌控。现代语言学则认为:人类是由语言塑造而来的,受语言制约,一切意义和经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以容纳它们。
或许,学者们对于语言本体论的观点在不同程度上夸大了语言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但这一发现确实值得我们反思、怀疑,并且重新衡量语言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2 后现代社会的语言现象
2.1 “语言贬值”现象
语言是人们日常交流、表情达意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文学的物质媒介,在工业化社会中自然难以幸免。杰姆逊认为,在工业城市,“语言不再是有机的、活跃而富有生命力的,语言也可以成批地生产,就像机器一样,出现工业化语言。”进入后现代语境,社会上确实充斥着五花八门的程式化的、趋同化的陈词滥调,它们来自报纸、电视广告、宣传标语、网络媒体等。这一现象则涉及了后现代文化的基本主题——复制。
杰姆逊引用了米歇尔·福柯的理论对此进行阐释,他首先将“摹本”(copy)和“类象”(simulatcrum)做一个简单的区分。所谓的“摹本”指的是对原作的模仿,被永远标记为摹本。原作具有真正的价值,而摹本的价值只是从属性的。“类象”则有所不同,指那些没有原作的摹本;在其诞生之初,就存在大量几乎一模一样的复制体。
简而言之,商品式的大规模生产和复制就是所谓的类象,当这种“复制”出现在语言中,就成了以电视及广告为核心的“形象文化”。它们霸道地占有了语词,使人们在消费这种形象的同时,将语言原本的指涉物抛在脑后。此外,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也遭受腐化,“复制”成了对个人主义的抨击。在文学生产中,作家不再是“中心化的主体”,因为自我已经被彻底打散、抽离;写作“没有笔锋、笔触,只有绝对的相似性”,个人的创造风格丧失,仅仅对一切进行机械化的复制。
2.2 精神文化的危机:“失语症”
语言在工业化社会中受到商品形式的入侵,被商业利益集团大批地运用及生产、大众无限度地消费,最终使语词的内涵不断遭到贬损,大量的陈词滥调充斥着整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思想被语言垃圾所充塞、占据,精神空虚的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已无法再表达任何情感。人们虽然能感觉得到,但就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就形成了后现代社会一种普遍的“失语症”危机。
杰姆逊提到了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的结构研究。后者在评论精神分析时,将索绪尔在其结构语言学中“能指”和“所指”的概念套用到萨满教之中,提出了“能指的剩余”这个概念。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萨满教的巫师和精神分析专家所采用的方式是一样的,所做的就是给病人提供丰富的能指。病人之所以痛苦,正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语词来描述这种无名目的痛苦,所以不能够抵抗、把握它们。而巫师的作用就在于给病人们提供“能指的剩余”,在祭祀当中使它们把自己的痛苦与这些能指组织、联系起来,一旦痛苦便变得有意义了,能够被表达,便减轻了一些。
然而在后现代语境中,人们之所以陷入一种无法表达的痛苦,并不是因为找不到特定的语词去描述它,而是因为一切所指的多向性、未定性,都被某个单一的能指所固定化,暴力地强占了。在形象的世界里,甚至字词都可以变成“形象”(image)。在广告界最常用的一个词叫“logo”,泛指一些具有传播性、辨识性的商标。它的文字形式体现在某种特定的标语、口号,当他们随着时间推移,在大众群体之间广泛传播,并且深入人心,就逐渐替代了其原有的指涉对象。可以想象,当海子的诗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被房地产公司作为宣传标语反复利用,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便丧失了原本的美和诗意。
在后现代社会,人们不需要象征性的倾诉,因为一切都变成了象征:成千上万的品牌、商标、称谓、口号漂浮在整张偌大的语言网络,粘附并且取代了其他原有的所指。各式各样粗制滥造的文化垃圾借助语言媒介批量化生产,在市面上肆意横行,只为了满足大众快餐式、趋同式的审美趣味,使人们跟随时尚滥用语词,一旦热度减退,又弃之如敝履。语言如果确如本体论所言,塑造了人们的思想,那么在后现代,由于无法表达,人们宛若无根浮萍,找不到一个落脚点,在能指的泥沼里挣扎,害怕词不达意,于是彻底丧失了真实感,只能像罹患“失语症”一般,永远保持缄默。
3 结语
纵观古今,语言学的发展经历了语言工具论、语言符号论、语言本体论三个重大的革命。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论述的正是语言本体论这个阶段,他认为20世纪以来现代语言学的意义,在于颠覆人们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认识,使人们重新意识到语言在感知、认识及理解方面的重要性。而在后现代语境下,人们正面临着一场精神危机:后工业社会商业化、机械化的生产使语言不断遭到贬损,以电视、广告为核心的形象文化又进一步吞没了语词,使人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焦虑感,如同罹患“失语症”,最后彻底失去声音。相较于西方,中国的消费社会与后现代尚有一段距离,但在多国化的影响下,后现代主义文化已向全球扩张。当我们揆诸现实,不难发现有相同的“语言贬值”现象,不断腐蚀、掠夺原本纯粹且具有活力的日常用语,值得引发我们对相关社会问题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