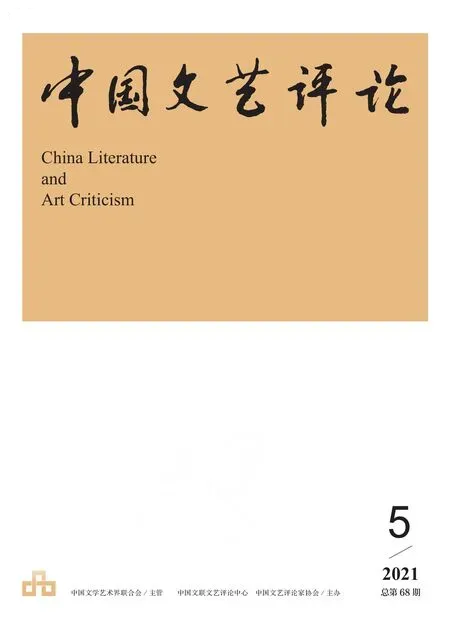全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及其学理思考
甘 元 谢 春
全媒体在新时代文化建设层面肩负着建设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责任和使命。1948年,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发表了题为《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的文章,并在其中明确提出传播具有三个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检测环境、协调关系、传承文化。传播与文化天然具备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内隐的文化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传播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传播内在的对话性与平等性对中华优秀文化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完成自身的当代书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全球化背景下对于非遗的传播与保护不仅是对传统文化传承的人文关怀,而且也体现了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包容。遗憾的是,目前非遗由于受到历史、经济、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复杂影响,濒临消亡,对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工作日臻迫切。因此,本文从全媒体时代的媒介背景切入,尝试探讨非遗在当前传播的特点、优势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对非遗的创新传播与保护提出一些建议。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全媒体环境
随着传播技术不断进步,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都已经明确意识到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但是,全媒体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仍存在很多模糊地带。不同研究者在使用时也多有分歧。中国人民大学的彭兰认为,“全媒体是指一种新闻业务运作的整体模式与策略,即运用所有媒体手段和平台来构建大的报道体系”。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的周洋则认为,“全媒体的概念来自于传媒界的应用层面,是媒体走向融合后跨媒介的产物”。显然,前者侧重认为全媒体是一种运作模式,后者更倾向于全媒体是一种新的传播形态。但无论侧重于何种认识,全媒体传播领域首先涉及的就是媒介融合。这种传播学范畴之下的融合是对媒体形态、媒介生产和传播的整合性应用。
媒介环境的巨大变化打破了原本的传播模式,尤其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人们已经转向通过移动终端获取信息,传播环节中传者与受者的关系已经不同于以往。实时、互动、巨体量成为当前传播过程中的突出特点,并由此衍生出了新的社会关系,构建了全新的文化传播体系。这种有别于传统媒体传播模式的新媒介形态,以其特有的开放性、平等性、交互性、全民性不断影响传统文化静态自律的存在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既有赖于文化本身的内在活力,也受到传播过程的巨大影响。因此,在传统媒体与各种层出不穷的新媒体融合的全媒体时代,在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活力的基础上,探索传统文化在全媒体背景下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全媒体时代非遗传播的媒介优势
传统的非遗传播主要依靠口传心授式的人际传播,影响范围较小,无法有效利用新的传播技术,从而也很难保证传播效果。而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给非遗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与方式。借助新的传播手段,非遗能够打破原本时空的限制,以视觉、听觉甚至触觉、味觉等多种方式完成自身的呈现,并且随着记录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些瞬间性的非遗文化能够被完整地记录保存,以便更好地传播与学习。显然,全媒体所带来的技术和传播理念的提升在非遗传播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
1.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与综合化
全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是基于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介与语言、视频、AR、VR等新媒体的“协调”传播。受众接受信息的渠道,也不再仅仅停留在某一媒介层面,而是一种立体式和综合性的信息感官体验。传播主体的多元与传播手段的协同并存,为非遗传播提供了更多的渠道选择和展示空间,呈现出一种多元化与综合化的发展态势。
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媒体传播模式,具有即时、开放、分众性与低成本等特征,符合人们信息需求个性化、娱乐时间碎片化的需求。传播者积极推进非遗网站、APP应用平台建设,拓宽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渠道。如2017年,光明网、斗鱼直播团队深入浙江、安徽、湖北等14个省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源地,走访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推出移动直播三十余场,向网友展示了包括台州乱弹、芜湖铁画在内的多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直播观看人数近3000万。通过互联网平台让大规模受众群体跨越时空与精彩纷呈的非遗面对面,开启非遗文化传播新的历程。
诚然,在积极利用新媒体传播非遗的同时,以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介,凭借着强大的内容生产力、专业化的传播理念和运作机制,以及在社会公众心目中较高的权威性与信誉度优势,在信息传播模式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我们应充分利用传统传播媒介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加大对非遗本真价值的宣传和普及力度,以主流声音引导社会舆论,促进民众对非遗价值的认可,扩大其生存空间。如北京卫视录制的《传承者》、湖南卫视制作的《舞动奇迹》等电视节目,以多元的视觉、深入浅出的解读方式,吸引了大量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观赏与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
融合,就意味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相反,二者的整合与链接,能够催生出新颖的传统文化表现方式,更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达到更理想的传播效果。
2.传播模式的交互性与大众化
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过程中以往的角色都已经不再成立,尤其是对于接受者而言,主体性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从被动接受一跃成为与传播者交互信息的主体,信息传受也从单一传送转变为双向动态回转。同时,媒介技术拉近了信息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信息的制作和传播已变得更为便利与日常生活化,人人都可发声,人人都是传播者。传播者可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和直播、短视频等视频终端,与受众展开交流互动;受众对信息的选择也充满了自主性与随意性,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定,同时借助关注、回复、留言、转发、点赞等方式直接快速表达自己的意见。如由腾讯与中国手艺网联合开发的“年画重回春节”手机APP游戏,玩家可以在游戏中画年画、识年画,还可以出售自己的年画作品以换取相应礼品。再如,湖南岳阳楼文化创意园通过UGC(用户生产内容)短视频,将洞庭湖区非遗打倡巫舞低回婉转的唱词、古朴诙谐的舞姿以及蕴含的民间传说制作成为小游戏和表情包,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推送。此外,很多传播者在直播中设置大量传统文化类的问题,吸引大量用户参与其中,充满趣味性的互动方式冲淡了文化本身的厚重与严肃,增强了传播效果。
新媒体的交互性特征促进了传统文化的群体传播,也改变了以往单向灌输的传播方式以及受众被动接受文化信息的局面。原本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具备相当主动性的参与者,成为传统文化建设的有生力量,更利于非遗资源的创新发展。
3.丰富传播内容的超文本性
大部分的非遗都不是静态呈现,其活态性特征导致传播内容的复杂性。超文本以计算机所储存的大量数据为基础,使原来线性的文本变成可以通向任何数据库中所包含的、受众所感兴趣的文本。新媒体的这种超文本性的信息组织方式,极大地增加了传播内容的综合性、可选择性和自主性。受众接受非遗信息时,可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思路随意查看,关于所查对象相关的各种报道、新闻动态、历史背景等,均能通过互联网呈现,让非遗的传播不止停留在对其表面的介绍,还囊括其产生背景、历史演进、文化内涵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内容,从而让受众真正认同非遗文化的传播价值。同时,新媒体传播的超文本性也同样有助于全面完善非遗相关资料的储存。
此外,更加前沿的例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混合现实(MR)等技术的应用,为非遗传播提供了一个宏大的第二世界,不仅能让受众在身临其境的沉浸感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洗礼,同时也给予受众超图像、超文本的信息传递与想象空间。
三、全媒体时代非遗传播的困境与思考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充满了机遇与挑战。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忧的那样,新的媒介技术确实给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但是也让人们更容易迷失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对于非遗传播也是如此,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通融合成为非遗重要的传播环境,其传播效果有利有弊。一方面,媒介融合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由此就能够推出更多创新的传播方式,扩大了非遗传播的影响和范围;另一方面,在瞬时、快捷获取文化信息的同时,也被其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困扰。如何在实现从传播形式到传播内容层面的深度融合的同时,规避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突破目前传播困境,也是学者必须正视的问题。
第一,碎片化传播方式削弱了对非遗内涵的深层次解读。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德国的一些研究均指出,人们在浏览网页时,人均耗时不到10秒钟。而当今的信息传播早已越过了早年单纯网页的形式,图片、声音、动图、短视频每一项都在不断打破人们注意力的下限,并在快速的信息变化中提供更多选择。碎片化的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获取信息并完成初步的加工利用。但这种“快餐式”的阅读方式对具有完整性、逻辑性的传统文化文本进行了解构,不能引导受众深刻、全面、系统地对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和丰富文化内涵的非遗文化进行准确认知。在全媒体时代,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是避免碎片化阅读方式对非遗进行解构的有效途径。如借助新媒体技术手段,制作生动有趣的非遗纪录片、影视剧等,将非遗文化熔铸其中,这样,既传播了非遗文化,也提升了影视剧的文化底蕴。
第二,媒介结构的转换引发对文化信息的误读与曲解。全媒体时代,文化传播过程实现了信息交互的瞬时性和高效性,但人们在虚拟的传播空间里,媒体传播所具有的虚拟性和隐匿性也接踵而至。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微博、微信、抖音等便捷的自媒体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在自编、自导、自撰的全媒体传播环境中,很容易造成对非遗文化内涵的误读、扭曲等。另外,全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新媒体、新技术和新渠道的融合,必将对其原生态的表现形式进行跨媒介结构性的转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将被打破,信息的总体性和语境化会不同程度地被解构。如为适应抖音和快手等新媒介娱乐、时尚化的传播特征,传播者将非遗文化与时尚文化融合,以增强其个性化体验感,力求引起年轻群体对其产生兴趣。在此过程中,不少信息传播者为了追求点击率和 “眼球经济”,走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象化”“娱乐化”的传播道路,从而削弱、消解了非遗原生态结构,使受众对非遗的认知只读其表而不识其质。再如电影《雪花秘扇》,影片为了获取商业利益,将湖南江永国家级非遗项目女书的文化内涵演绎成同性恋文化,误导、扭曲了受众对女书文化的认知。江永女书实则是用于记录当地妇女生活、婚姻家庭、社会交往、幽怨私情等的独特文字,是女性心灵世界的投影,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地域文化特色。全媒体时代,为了避免非遗传播过程中的信息误读和信息曲解,信息传播者在改编、演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应力求忠实于文本原叙述,确保文化本身的严肃性不被瓦解,这是全媒体时代非遗传播的立足之本。
四、全媒体时代非遗传播体系的构建:路径与建议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我们应在整合传统媒体资源的基础上,融合文化与科技,大力发展非遗数字化传承与保护工作,以拓展信息接收渠道,创新受众体验传统文化的方式和空间,实现信息的全方位覆盖,加深人们对非遗内容的理解,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实现信息共享,建设优秀的非遗文化体系。
第一,文化与科技融合促进非遗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媒介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形式多元的相关信息,同一时间点上能够完成多形式的呈现使得文学、艺术、传媒、科技等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有利于宣传推介非遗文化资源。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文体广新局在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文字版本基础上,利用新媒介技术制作了“江格尔”动漫,剧中融入了新疆民族歌舞、风土人情等传统文化,让受众在轻松愉快的视听享受中认知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被称为非物质,就是强调这种文化的精神核心,这里包含了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发展中一以贯之的生态意识、人文情怀、孝亲伦理等,通过积极创作文化创意产品,借助全媒体传播媒介打造文化品牌,能够让精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与实际结合并持续发挥作用。例如在上海世博会上推出的《清明上河图》电子动画版就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这件作品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完成了电脑动画创意技术与中国文化精品相融合的尝试,更重要的是它十分恰切地将北宋时期浓厚的民俗生活意味以一种可知可感的方式传递给了每一位观众。《清明上河图》电子动画版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也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科技与文化是可以融合发展、互利共赢的,非遗也会伴随这种融合进入良性循环的传播模式。
第二,运用大数据提升非遗存储、检索及传播效率,形成非遗信息传播的“数字共同体”。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7%。其中,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9.2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2%。另据艾瑞咨询《2019年非遗新经济消费报告》显示,网购平台、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消费者了解全国非遗产品的重要渠道。以上数据显示,不管是信息传播者还是信息接受者,其文化信息传播和接受路径大多基于互联网及大数据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建设是一个包括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等多维度、多层面的综合工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府管理部门,应协调不同层面的非遗保护力量,建立体系完整的中国非遗数据库,著录、整合、检索、备份协同,在此基础上构建非遗数字博物馆体系,以高、清、真的4K直播、VR漫游、5G全息投影秀等数字技术传播非遗文化。传播媒介的技术进步,使得非遗数字化传播过程呈现出普遍性与多样性特征。全媒体语境下,我们应着力整合新媒体资源,利用AI、VR等技术,提升非遗数字展示效果,将受众带入到场景体验式传播模式,从而扩大非遗传播范围。据统计,截至2019年4月,在抖音平台上有关非遗的视频超过2400万个,积累播放量达1065次。显然,短视频平台已成为非遗数字传播的重要渠道。数据资源是智能媒体的基础,丰富的非遗大数据只有通过科学的存储和智能应用才能实现其价值。非遗数字化建设,能使人们快速获取、处理、分析并从中提取海量的、多样化的有用数据,从而提高研究者和保护者查询相关数据的效率,延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和研究的水平。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传承、弘扬和发展需借助媒介。在全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想要获得更好的传承与发展,必须要充分了解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在此基础上借助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新兴传播方式,让非遗传播更具生命力,使非遗文化传播能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提升人们的文化素养搭建更广阔的平台,发挥传统文化应有的精神引领作用,进而增强中华民族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以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