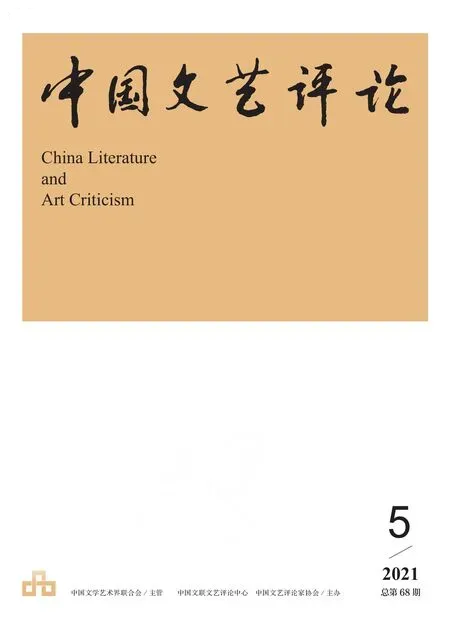论“审美现代性”视野下音乐的释义对歧义的宽容
杜 鹃
音乐,以一种特定的符号传达意义,在此过程中同时传递着社会价值观念。在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人们对音乐意义的解读产生了深刻转变。总体来说,随着音乐进入现代性的审美进程,人们对音乐释义的实践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对歧义的宽容,甚至是鼓励歧义的存在。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与音乐的创作、演奏以及理论发展有密切的关联,更与西方社会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对“美的艺术”态度的转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审美现代性”与音乐文化
“审美现代性”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概念。从哲学观念来看,现代性代表着启蒙思想的开始,意味着人们开始抛弃宗教的统治地位,转而相信人的主体力量。冷静客观的理性逻辑,成为了改变世界的主要动力。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在现代性的进程中,渐渐被忽视、遗忘。然而,审美作为一种超越现实的活动常常否定甚至对抗逻辑理性带来的冰冷。因此,审美现代性常以自由和超越的品格拒绝现代性的理性分析。在审美现代性领域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审美现代性的感性形式:“大众审美文化”和“精英审美文化”。前者迎合消费主义潮流,在不自觉中沦为现代性的战利品,丧失了自由而超越的审美品格。后者则是一种超感性的审美形式,以精英知识阶层为主体,具有超世俗性、反叛性、精英化和非理性主义的特点。在我看来,精英审美文化代表了人本主义的审美现代性,它具有深厚的审美意蕴和形而上思考,抗议人的异化,强调自由的品格,追求个体性,趋向精致化,承担起了唤起生存自觉和保持自由精神的任务。
从这一立足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自18世纪开始,西方音乐世界经历了审美现代性的转型。18世纪是浪漫主义萌发的时期,也是世俗社会取代神性的现代化转折时期。人类本来视为权威的东西此刻正在消解。人的主体最终取代神的位置。尽管大量文献表明,音乐现代性的转型和裂变在 20 世纪前期表现得极为剧烈,但事实上,音乐审美现代性的萌芽自18世纪“美的艺术”的确立就已经开始。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如此定义“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促使包括音乐在内的“美的艺术”导向自律性和去功能性。在这个过程中,作曲家对音乐的掌控力日益增长。比如,莫扎特和海顿的音乐在宗教和世俗目的的委约之外,开始关注人自身的意义。尽管这种意义并非来自作曲家自身的情感,但他们的音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部分音乐已经走下神坛,降临人间。清唱剧原本是以基督教教义为主要内容的大型声乐体裁,但海顿的清唱剧《四季》却采用了英国诗人汤姆逊的同名世俗诗歌改编的脚本写成。这首清唱剧并不是为了满足宗教目的,转而采用具有浓郁乡村气息的音乐主题。全剧分为四个乐章,分别以“春”“夏”“秋”“冬”为标题,剧中人物老牧人西蒙、牧人的女儿哈娜,以及哈娜的爱人卢卡斯都像是温暖的、生机勃勃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戏剧情节,也基于发生在当时的人们身边的事件。如第一乐章《春》中,作曲家用混乱的音响与和弦描绘可怕的风浪,用半音阶进行到凄惨动人的旋律来再现旅客的惊呼、海洋的咆哮和狂风的呼啸等,直到音乐回归美好,象征着风浪归于平静……在18世纪海顿的手中,用音乐的戏剧性来反映现实社会和自然场景,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同样,阿多诺认为,在贝多芬晚期的大多数音乐作品中,客观地展示了19世纪前期作曲家对现实不可和解的主观精神。
音乐释义的历史回望与现代性解读
自18世纪起音乐从神坛下降,不仅体现在音乐的创作形态上,更深层的体现是音乐意义及其释义的转变。对音乐的释义一旦离开唯一的神,被赋予了人的特质,释义便不再如18世纪前那样具有明确且唯一的指向。对音乐的释义变得复杂且多元,歧义不再被视为对音乐的不恭。
释义学作为一门旨在对文本之意义进行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学科,深刻地受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深刻制约。在西方音乐世界,自古希腊至20 世纪再到 20 世纪中下叶以来的后现代,总体来说,对音乐的释义呈现出一种由中心主义向多元主义转变的趋势。于润洋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中对西方音乐释义学的历史作了梳理和研究。中世纪音乐哲学思想的发展趋势同当时神学释义学的方向基本一致。经院神学家们对音乐意义具有绝对的解释权。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倾向的音乐家们对音乐的本质和意义作出了新的解释,要求音乐摆脱浓厚的经院哲学色彩,同世俗社会的现实生活和个人的情感生活联系起来的观念开始萌芽。古希腊的“模仿论”在此时盛行,并被赋予了新的内容。17世纪时,笛卡尔倡导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文化现象。这种科学主义的倾向遭到了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反对。维柯在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中提出了历史主义的释义学。在他看来,不能将一个事物放置在一个真空环境中去理解,而应把它放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解释。但维柯也认为在此过程中不应加入阐释者的主观因素。上述种种思想使18世纪欧洲音乐哲学一步步地摆脱了经院哲学的束缚,开启了理性精神的大门。到了18世纪下半叶,启蒙思想家们更愿意将历史看作是一个理性发展的过程。19 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继承了维柯的观点,强调要重建产生作品的那个世界。
此后,近代释义学提出“视域融合”的观点,认为对文本的释义过程是一个“同化”的过程。不仅作者的精神世界无法回避,读者的精神世界也应当与之产生共振。在此过程中,文本产生的历史得以重建。宋瑾曾对18世纪以来的音乐阐释学进行归纳和梳理。他认为,从18世纪到20世纪下半叶,艺术文本释义的中心从作者、作品过渡到读者。艺术作品的意义也从确定过渡到未知,从单一演变到开放。笔者则认为,18世纪最终摆脱经院神学束缚,走下神坛的西方音乐就已经具有了对歧义的宽容。宋瑾也认为,18世纪维柯的历史释义学中已然预知未来——释义的中心逐渐向读者转移。尽管无词的器乐音乐在18世纪前的一个半世纪就已经获得解放,但这并非意味着器乐音乐早已作为绝对音乐为人所接受。尽管脱离了语词,在18世纪以前器乐音乐仍然有着具体而明确的含义,如穿插在弥撒仪式各段落之间的教堂奏鸣曲,对仪式的进行起着连接的作用。再如,由一首众赞歌的第一句改写成的赋格主题,然后用它写成的众赞歌赋格曲,在宗教仪式中可作为会众演唱众赞歌的前奏,由管风琴奏出。尽管也有一些器乐作品并非为仪式活动而创作,但绝大多数的器乐作品由宗教声乐作品改编,其旋律仍具有深刻的宗教含义。器乐作品在意义的阐释上尚且如此——它明确地指向对神的赞颂,更不用提用语言明确表达意义的声音作品了。脱离了宗教的束缚,器乐音乐既不能“诉说”,也不能“体现”事物的特质,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乐音艺术。
在18世纪以前,艺术家们通常假定一首音乐总是表达同样的效果。如果有人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会借用古老的四种性格气质学说来解释例外的情况:如果谁没有辨别出快乐的音乐,那么他一定是忧郁型气质,这种人会将所听到的一切都吸入自己的悲哀定式中。但另一种声音也在此刻获得越来越多的赞同:纯音乐不仅仅是实用音乐的一件外衣,不是实用音乐的抽象,它能够升华到诗意的境界。从前被视为“机械手工”的器乐音乐,现在开始具有了“诗意”。那些有文字表达精准含义的声乐音乐却被视为粗俗。文字变成了音乐达成诗意境界的拖累。到了19世纪,代表绝对音乐的器乐音乐已占据半壁江山。如E.T.A.霍夫曼等德国早期浪漫派文人,出于自身对纯粹艺术审美的追求,高举器乐的形而上学旗帜,强调器乐音乐的至高无上。正是由于器乐音乐在此时具有了绝对崇高的艺术品格,它所体现的绝对音乐观念触及到的诸多音乐哲学、美学的基础问题。正是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分析和辩驳,推动了音乐美学思想史的发展。
如果说在19世纪,对音乐意义歧义的存在还令人大伤脑筋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人们已接受这种歧义的存在,甚至到了刻意彰显的地步。20 世纪中下叶,不仅对音乐意义的多解性的宽容已深入人心,就连传统意义上的音乐“作品”概念也被解构了。对音乐意义的追问被视为是“永不在场之物”。如施托克豪森的《来自七天》中的一个乐章《金粉》,演员的表演并不参照传统的乐谱,作曲家创作文字谱代替乐谱,它不规定演员演奏的音乐的内容,而是提示演员应怎样生活。就这样的音乐而言,不仅最终确定的意义已然消解,就连表演过程也极度开放。音乐作品的意义对每一位听众来说都是一种新的可能。
从20世纪兴起的接受美学角度来看,音乐释义有赖于欣赏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音乐本体出发对旋律和篇章进行解构重组,从而创造出契合社会接受与个人接受的主观体验,在精神区间实现音乐的审美感应价值。音乐作品释义的不确定性则在艺术接受的宏观框架内整合各种歧义,继而通过欣赏者的审美经验宽容歧义,发掘音乐所承载的情感依托,从而对音乐形成更为多元开放的全新认知。
以上概述了音乐的意义从明确唯一到宽容歧义的历史过程。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对歧义的宽容,甚至纵容歧义的产生正是现代艺术的基本取向。从接受美学强调批评对文本的建构作用,到现象学对艺术作品意向性存在的论证,再到释义学美学对“意义”和“意味”的区分,所有这些都确证了审美现代性相对于传统审美的特征所在。与此同时,传统的音乐文本也是一种“及物的”“可读文本”,它把确定的意义和场面交代给听众;而现代音乐文本是一种“不及物的”“可写文本”。所谓“可写性”,强调的是那种垄断文本意义的权威的“作者之死”之后,听众方才“诞生”。艺术文本的欣赏者化身为了艺术文本的生产者,他们既是读者也是作者。
对歧义的宽容引发的反思
进一步来说,审美思维呈现为多元性和多义性的包容。音乐审美现代性的特征之一也正是审美思维对歧义或差异的宽容。音乐自摆脱了“机械手工”的划分进入纯艺术领域,它那种追求唯一意义的解答便转化为容许多种解释的存在。
尽管西方音乐发展到20世纪前后,对音乐释义的宽容才在理论界受到广泛的重视。但我认为,在音乐的实践领域,这种宽容自音乐走下神坛便已开始。走下神坛的音乐所带来的对歧义的宽容,更深层的是对人的精神多样性的宽容。这深深地体现了启蒙运动对人自身的关照。18 世纪无词的器乐音乐获得独立意义所引发的关于音乐意义的思考和争论,恰能说明音乐在意义层面的特殊性在此时已初露锋芒。这种特殊性就在于音乐意义的不唯一和多解性。因此,应当说音乐审美现代性释义中对歧义的宽容在18世纪就已然呈现出来,但它仅是若隐若现地体现在音乐的理论和实践中,鲜有上升到反思的层面。直至20 世纪前后,这种思想才成为一种思潮凸显出来。这一思潮所带来的音乐理论上和创作、表演、欣赏上的转变,使现代音乐几乎走到了传统音乐的反面。在过分关注个人体验的现代社会中,作曲家和理论家不仅宽容歧义的存在,他们鼓励甚至刻意追求歧义的存在。
美国当代作曲家约翰•凯奇创作了著名的“无声”的《4'33"》(1952),从而名声大噪。事实上,凯奇对东方哲学的兴趣深深地影响着他的音乐创作。如他在1950年至1951年创作的《预制钢琴和室内管弦乐协奏曲》采用投掷硬币的方法来确定音乐的写作方案。凯奇从第二乐章开始,将乐队与强奏或阳性的乐思相联系,而钢琴则与弱奏或阴性的乐思相联系,并为乐队和钢琴分别列出表格,将每一次随机投掷硬币阴阳两面的顺序与演奏的顺序填入表格,最终形成音乐演奏的效果。凯奇认为,他的创作深受《易经》中哲学思想的影响。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凯奇这源于《易经》的偶然程序向创作者和欣赏者都敞开了意义的大门。如何诠释这样的作品,不仅成为一种解放自我的手段,更要求建立一种新的诠释规则。
笔者认为,在对肖邦钢琴曲《马祖卡三首》的多样演绎中,帕德雷夫斯基、埃德温•费舍尔、利帕蒂、科尔托等的弹奏,都匠心独运、各具风采,或冷隽精密,或圆融贯通;或激越热烈,极富个人色彩,或细致琢磨专注于华美音色;有的被赋予了宗教意味,有的自我释放如醉如痴,每位钢琴家都有权利去诠释自己心目中的肖邦。而华裔钢琴家傅聪对肖邦的再现同样出神入化,德国著名作家赫尔曼•黑塞曾对他的演奏赞许有加。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里,中国人向来以刻苦勤练及技巧娴熟见称。以完美技术为根基,东方音乐家的作品中浸透着化解哲学观之对抗属性的平和与宁谧,是一种在多维音域空间中平直的线性流淌,是一种不羁于来由、不穷究去向的灵动气息,从而营造出典型的艺术沙龙氛围。我们陶醉其中,有如感受到阿维尼翁鸢尾花的清香、马卡略岛普降的甘霖。这种精神意象在“道”的指引下幻化为沉着稳健、从容不迫的演奏,琴声淡雅、如梦如幻,音乐本体的微妙韵律及充盈其间的活力,尽皆表露无遗。不论演奏者还是聆听者,现当代语境下肖邦曲目的审美品鉴,都应从内心深处领悟当时波兰以及巴黎文化中所蕴含的怀疑主义。而每一场演奏,都应是一次次在细节上崭新独特的视听体验,绝不能是“老调重弹”。
总之,我认为在对音乐意义的理解过程中,尽管听众自身的精神世界是意义重建过程中极其重要也无法消除的一环,但对歧义的宽容仍限定在有限范围之内。这个范围应以作曲家为轴心,以听众的精神世界为外延。20 世纪下半叶以来那些过分地把音乐的意义交代给听众,甚至为了获得多义性而放弃了轴心的音乐作品,在我看来却丧失了音乐意义歧义存在最初所具有的那种精致和诗意的内涵,而流于形式的表层。当代中国的音乐创作应收放兼备,牢固把握音乐的核心释义,在塑造民族音乐基因之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引导欣赏者在轴心释义的合理边界内,对音乐本体进行更加有利于优秀审美传统传承的再创造,从而优化作品外延,让更多的中国音乐与历史审美经验融会贯通,顺应日新月异的时代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