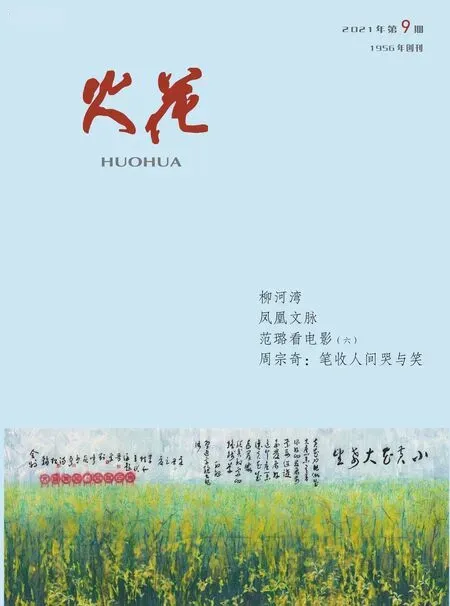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三)
鲁顺民 陈克海
第三章贫困记
一、刘大叔
工作队2016年春天驻村,转眼到了2017年。
山里的生活节奏慢,也真是慢。按照县城的生活节奏,上班,去处理一宗一宗杂事,不知不觉间一抬头,已经是该吃午饭辰光了。而在村里不一样,早晨起来做过一宗一宗事情,待歇下来,太阳泼水一样照亮田野,山间的雾也散去了,变淡了,以为快中午,一看表,才不过上午九点。露水正在褪去,庄户人忙罢田里的活,才准备出去放羊。
“山中方三日,世上已千年”,这话说得有些过,可能仅仅是个感觉,但这个感觉很准确。
可是,日子过得也真是快,在这样的生活节奏下,一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另一个一年也不知不觉过去了。几个工作队员很忙,核实村里的各种情况,还要回单位处理必要的事务,回乡里回县里参加各种各样的会。生活节奏显得有些乱,时间过得真是不知不觉。
曹元庆是工作队长,过罢年回到村里,刘福有说:老曹啊,鬓角上有白头发啦。
可不是,不独老曹有了,回头看老周周胜贤,也有了。
陈福庆年轻,但也经不住岁月磨损,赵家洼村的山风和霜雪将他送过不惑之年。
都是农家子弟,村里6户人家13人一天一天打发着日子,开始还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正常,有什么不妥,可是,过了一年,再过一年,工作队的压力就来了。
主要是心里不安。
尤其2017年,陈福庆从工作队员“荣升”为赵家洼第一书记,压力伴着不安,越来越厉害。也正因为是农家子弟,看着眼前的父老生存状况,这种压力与不安来得更甚。
陈福庆的家虽然在岢岚北川的三井镇,农业立地条件比赵家洼好一些,平地多,交通方便,但农家院里进行着的生活其实与赵家洼区别并不大,苦,穷,都一般模样。
当年上初中,跟姐姐一起住校,一日三餐说供不上就是供不上,好长一段时间,姐弟用一张饭票,吃一份饭。陈福庆是家里的独苗,上头三个姐姐,下头一个妹妹,父亲母亲真是倾其所有来供几个孩子读书,终是有报偿。陈福庆差强人意考上当时的忻州商业学校,妹妹则考上山东济宁贸易职业学院。
兄妹二人被“供”出来,父母亲也就老了。
他看到刘大叔刘福有,会想起自己的父母亲。或者说,看到刘大叔,就更惦念父母亲。老人们都不容易。一个县份,地域不同,但情景并未因物理空间不同而有什么区别,简直太雷同了。
有一段时间,记者来采访陈福庆,陈福庆跟记者们说起村里的人,总是大爷大娘大叔大哥这样来称呼,记者们看陈福庆的《民情日记》,日记说起某一个人,也是这样来称呼。大家很感动。
事实上,陈福庆他们在村里的工作能够顺利展开,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这种姿态起着很大作用,拉近距离,黏合情感,融入其中。
而在陈福庆那里,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特别,有什么可值得称赞的。
乡村社会,本来就是靠血缘、亲缘、族缘、地缘关系形成的秩序聚落。尽管赵家洼村是一个“乱家百姓”村,“赵,‘照’不到一起,刘,也‘流’不到一块”,血缘、亲缘、族缘在村落中的影响并不太大,倒是地缘关系让三个自然村的村民很“抱团”。
远亲莫若近邻,赵家洼的村民可能体会更深一些。即便到第四代马龙飞这一代人,说起周围邻里长辈,也是叔叔大爷这样来称呼,即使称同辈一茬,也免姓只呼名字。乡村社会里,儿童从小就被教育,“大名小字”直接称呼某一个人,是极端不礼貌没有教养的行为,甚至可视为乡村禁忌之一种,被坚决呵禁。
陈福庆担任过阳坪乡的人大主任。一进村,一见到村民,见了比父亲大的一定叫大爷、大娘,比父亲小的一定叫叔叔、婶婶,同一辈,那就是哥哥嫂子来称呼了,一切来得如此自然,并不刻意,毫无矫饰,身份转换流畅到天衣无缝。这一切,都来自乡村的教育,来自童年的训练,或者说,这是土地赋予人的基本教养。
有什么样的训练,就有什么样的文化。
人,一旦进入乡村,山水田野,农舍炊烟,林坡草地,长云低巡,鸟儿鸣叫过后,村巷里恍然听见有人在呼唤你的小名。
刘大叔,就是刘福有。他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陈福庆的《民情日记》里。因为留在小赵家洼的老人中,就数他的年龄大,2017年,刘大叔年过七旬,跟陈福庆父亲一样,生有四女一男,也跟陈福庆的父亲一样,老汉为培养子女那是竭心尽力。
刘福有在赵家洼是一个每天都很快乐的人,无论是手里有营生做,还是坐下来抽烟跟大家说话,盐咸醋酸,根根由由,一件事情,在他的嘴里会很快理出头绪。
他没有理由不快乐。
老伴叫杨娥子,也勤快。刘大婶比刘大叔小一岁,都是过了70岁的人。但两个人不能闲下来。为什么?刘福有说:“任务没完成呵!”
“没完成任务”,恰恰是刘福有快乐和舒心的原因。
育有五个儿女,儿女娶的娶,嫁的嫁,一个个从赵家洼老屋走了出去。儿女们走得有心劲,前面说过,2016年,孙儿考取南昌航空大学,外甥女考取汾阳医学院,“都是好大学”!
老人为儿为女操劳一辈子,那份辛劳陈福庆哪里能不知道?
老人的儿子叫刘永兵,现在家搬到了城里住,只身在神木打工。老人说,他这一支,就是单苗苗往下传,1993年,永兵结婚,那时候刘福有还不到50岁,三间正房让出来给儿子做了新房,自己又在南边搭了三间南房,就住在那里。旁边就是牛圈,方便起来招呼喂牛。
儿娶女嫁,才算完成“任务”之半。刘福有还有91岁的老娘在堂。高堂老母健在,算起来就是四世同堂。四世同堂啊!在传统的农耕村落,这样的家庭构成还不是最理想的吗?家有一老,强如一宝。子孙繁衍,福寿无边。
刘福有的老娘现在躺在炕上,妻子杨娥子笑着,像喊一个孩子,大声大气跟她说话才听得见。喊她起来换洗衣服,喊她起来吃饭。七十出头的妻子,在婆婆面前仍然像个闺女。
两口子对老娘孝顺,村里人都看在眼里。
老娘年轻时候的相片装框子,放在柜子显眼处。年轻时候的老娘也是一个美人胚子,眉是眉,眼是眼,俊俏得很。老娘当年也不容易,人家走了两处,先在宋木沟白家,过得不顺心,这才跟了刘福有的大。父亲呢,更是一个俊后生。老父亲去世将近20年,相片就摆在老娘相片的旁边。70岁的大白眉白鬓,老了老了,那一双眼睛还炯炯有神哩。
老娘在炕,自己就不能算老。
在村上,刘福有是好受苦人。当年,坡梁地,沟塌地,总共种着90亩地(陈福庆核实过,共89.7亩),这90亩地1982年分过一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又重分过一回,包括人畜口粮地、轮荒地、油料地、开荒地。1982年分地,村上按地亩的产量来分配,刘福有家人口多,加上自己开荒的地,90亩绰绰有余。
到2017年这一年,他不能不“认怂”,但还种了些地,其它的退耕的退耕,流转的流转,这点地还得种。
种些什么?“庄户人家不用问,人家种甚你种甚”,左不过玉米、胡麻、莜麦、红芸豆、土豆、谷子、糜子、黍子,中间还间作黑豆、牙豆、大豌豆、小豌豆,只比别人种得更多。刘福有谦虚,其实他在种地上花的心思比别人更多些,前些年养一头牛,现在是养着两头牛,牲口的青贮饲料和精饲料都需要地里出产解决,买饲料喂养,“算不过账来”。
除了牛,前些年他还养羊,也不多,20多只。那时候骆驼场张拦全喜放羊,20几只羊就托给张拦全喜放。乡村经济互助合作行为中,这种合伙放羊的方式叫作“捎羊”,把自己的羊交给羊倌出坡散放,到夜影降临,再交回到各自的圈里。羊群回村,乱蹄踏得雾气腾腾,羊倌用鞭子一拦,谁谁家的羊会自动分开,一个娘领几个孩子纹丝不乱一个不少,熟门熟路赶回到自家羊栏里去。
每年,主家会付给羊倌若干报酬,报酬也不太多。
羊的青贮饲料和精饲料也需要地里出产来解决,若去买,还是个“算不过账来”。
还养猪,有力气那些年,刘福有有时候养一头,有时候两头,冬天岚漪河冰封,是“卧猪”(注:杀猪)时候。杀了猪,猪肉大部分要储存起来,给儿子拉一块,给女儿拉一块,都给孩子们准备下过年用,剩下的可以交易,换几个钱。
老刘说,是不算账,养一头猪,不说人的辛苦,每天一日三餐都得给做熟侍候,一顿不吃也不行。光算一下一年的饲料,青饲料不算,仅是玉米,就得七八百斤,算不过账来。
老刘家的日子这样来过,家家户户的日子也这样过。寒来暑往,四季不同,农家生活的旋律似乎一成不变,岁月就这样一年一年打发过去了。农家院落里的生活,如同一张弓,儿女们则是一支一支箭,“会挽雕弓如满月”,长弓一次一次拉满,儿女们一次一次被射到山外。现而今,弓疲弦弛,“任务”过半,刘福有势不可挡变成一位结结实实的老翁。
在乡村朴素的观念里,儿孙满堂,多子多福,这种观念被抽象出来,乡间民居的砖雕、木雕、石雕拿来做题材一再强调。但老百姓又讲,“儿多女多罪过多”,前者是愿望,后者则是现实。为儿为女奋斗一辈子,家无长余。
工作队给留守的老人们做过体检,刘福有倒没什么大毛病,就是老年性关节疼,“气不够用”,活儿重了就喘不上气来,身体各部位都招惹不得,稍不慎重就感冒。
老刘因年老逐渐失能,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说起贫,说起困,说儿女,老刘说:“他们也是娃娃蛇蛋(注:孩子多),念书的念书,打工的打工,负担好重,咱不给他们添累赘就够好了!”
老刘是个开朗的人,什么事都想得开,说自己该享受的还要享受。
平常进阳坪乡,到县城采买办事,别看刘福有70多岁的人,还骑着一辆二手摩托车,摩托车的车况比老刘的身体更差,浑身稀里哗啦响。陈福庆不止一次说过他,要老刘轻易不要骑车上路,要多危险有多危险。刘福有却笑笑:自家的东西自家知道。尽管知道,但车子还是三天两头就坏了。
领陈福庆进家,他又指着电视机说,看看,咱这电视。
1993年,刘福有记得清楚,买了第一台电视机,花了整整2000元,本来就是给儿子结婚预备的,就给了儿子。再后来,儿子搬到城里去,他才又添了一台康佳电视机,花了1420元。
下来,还有一个小冰箱,这是仅有的“奢侈品”。
二、杨大叔
杨大叔,就是杨玉才。
杨玉才不是建档立卡户。在赵家洼村留守人口中,他还年轻,1963年生人,55岁。妻子50岁,生有二女一男三个孩子,大女儿读了一个中专,太原会计学校,现在在家里带孩子。
一个儿子,杨云飞,28岁,就是马龙飞笑眉笑眼提到过的同龄人,也是“都不爱念书”,在太原打工,给酒店配货。结婚成家,在太原租房子住,租的是一个城中村。具体在太原哪个城区哪一块,杨玉才也说不大清。他只去过一回,下了东客站,车来车去,绕得头晕,下了车,还需要走个十来分钟,他也没记清到底是什么地方。
“大城市,娃娃们也难!”老杨感慨说,“现在的娃娃们就不愿意种地,谁还回这村村里?不爱念书,还不爱种地,都时兴在外头打工。”
老杨是一个好“受苦人”,身上“有苦”,杨玉才把自己的日子扑腾得红红火火。虽然不能跟城里那些富人相比,但在赵家洼村,老杨家的日子堪称富足。
杨家比起其他家族,来赵家洼相对晚一些,到杨玉才这一代,才不过两代。
父亲杨亮孩,保德县杨家湾村人,15岁就“娶过老婆”,男儿十五夺父志,一个15岁的孩子就开始为一家人吃喝“刨闹”。但本籍保德县,地狭人稠,“过不了”,就来到赵家洼。推究起来,杨亮孩就是1943年或者1944年响应边区政府号召,前来保德开荒种田的那一批保德人。
杨玉才1963年生人,父母生他生得晚,是因为父母亲连生了三个闺女,养下儿子半道夭折。没有办法,按乡俗,从外头抱养了一个儿子,这就是杨玉才的哥哥杨旺财。抱回哥哥,果然应验,杨玉才、杨聚财两兄弟相继出生,无病无灾,现在都是年过半百,遥望花甲。
哥哥杨旺财也是“好苦水”,早就搬离赵家洼在县城里安家,年望六旬,仍然在外头打工,现在在东胜(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那边给人帮忙。老三杨聚财,在1982年,“分开地”当年就回到原籍保德县东关镇打工,户口仍在赵家洼。保德县乃晋西北能源大县,赖此地利,老三杨聚财过得也不坏,而且两个儿子都安排了工作。老杨感慨说:我兄弟可闹了个好,过去是保德不如岢岚县,现在倒是保德县强过岢岚县,风水轮流转啊!
哥哥、弟弟离开村,后来妹妹也离开村,丢下的地亩全部由老杨一个人来种。老杨说:
村里就剩了五六户。有钱的早在县城买下房,没钱的也出门打工,早把村里地撂下了。我妹也进城多年了,在超市给人干活,一个月1500元,妹夫在河曲下窑。我把几家人的地给种上,还给人出上包地款。包一亩给人50元,前前后后,他们三家是18亩地。也不给人活钱,我种上山药,他们过来拿几袋子就顶了。
我种的地多,我妹妹的,我哥的,我兄弟的,我的,总共四家的地。山梁地都不种了,光产权证上的地,怕也有四十好几亩。种些甚?玉米、红芸豆、谷子、山药、扁黑豆。玉米哪年还不种个二十来亩,种多种少,净喂了羊了。莜麦后来都不种了,坡梁地上种些,一亩打不下几十斤,不顶事。后来牲灵(注:牲畜)也不养了,价钱上不来,养上泼烦得不行。这二年种甚都用上机器了,旋耕机又快,无非就是多花它两个钱。好年头,一亩玉米能产个千二三,年头不好产个千数八百,均下来,一亩产个一千斤没问题。谷子也不种了,全种上草。红芸豆种不多,种上个三二亩,产不多,一亩就能摘个三几袋袋,遇多也就二百斤,也就够买个油盐酱醋。山药种上个三二亩,黑豆也种个一二亩,反正就是够个自己吃就行。
养了一百五六十个羊。卖上十来个羯羊,二十几个老母羊,一年出栏也就三十来个。卖个三十个,一年也就三万来块。那几年行情好的时候,一斤卖个十四五块,一个羊平平常常也要卖一千四五。前二年羊不抵(注:不值钱)了,一斤才卖个十块钱。我们在村的时候,养了几年,也没挣下个钱。
四十多亩地,一百五六十只羊,怎么可能“没挣下钱”?
陈福庆他们给老杨一项一项算账。
收入:
种植:玉米,20亩,1100斤 /亩,计22000斤,按每斤0.8元计,毛收入17600元。
红芸豆,3亩,200斤/亩,计600斤,按2016年价格每斤3.4元计,毛收入2040元。
谷子,轮作。种多种少,自用。
土豆,3亩,2000斤/亩,计6000斤。以2016年价格每斤0.7元计,毛收入4200元。
黑豆,2亩,400斤/亩,计800斤。以2016年价格每斤3.5元计,毛收入2800元。
养殖:羊160多只,一年出栏30多只。每只出栏均值1400—1500元,以1400元计,毛收入42000元。
羊绒,年收入12000元。
几项收入相加,毛收入76800元。
支出:
机耕,每亩80元,40亩地共3200元。
铺膜,每亩50元,有30亩地需要覆膜种植,计1500元。
化肥,每亩80元,也有30亩地需要施肥种植,计2400元。
种子,主要是购买玉米种,其他种子自留。每斤12元,每亩需要5斤,20亩就是100斤,计1200元。
礼金支出:以3000元计。
平时衣服、米、面、油、肉、调味品等生活必需品购置,以10000元计。
共计21300元。
收支相抵,年纯收入55500元。
陈福庆他们哪里能不知道,在农村算账,一项一项,就是把犄角旮旯里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呈现出来的也仅仅是一户农家生存经济的大致轮廓,若用会计核算标准去计算,注定是一笔糊涂账。
赵家洼过去“养懒人”“养穷汉”,能够收留接纳众多生存无计的逃荒者安顿下来,实在是因为乡村和田野有太多公开的秘密,比如开荒,比如林地经济,还比如田边地头以及庭院种植,这些“秘密”不必进入会计视野。
此外,帮老杨计算的账目中,人工并不算在内。老杨说:咱就是个受苦人,受苦还能计算进去?再说,要算起来,贴进去的人工那真是无法计算。不独老杨,也不独赵家洼,贴进去人工无数而不算账,恰恰是传统农耕经济的一个特点,即“以不计成本的劳力投入来弥补资本不足”,在传统农耕经济中,劳力本身有着浓烈的生产资料意味,乡村伦理中“多子多福”观念根深蒂固,其原因正在这里。
老杨这笔账还仅仅是一个固态账目,在具体生活中,这笔账又显得非常可疑。比方,子女未成人之前,在城里读书所费,平时头疼脑热购置药品花销,都没有体现出来。老杨说,那几年娃娃们念书,“紧着个供”,一年下来就是“打个平手”,与日月相搏,收支勉强平衡。
1982年“分开地”,赵家洼村有七八群羊,每群羊一百多只,老杨一直养羊,这是收入中的大项,如果仔细分析,老杨种40多亩地,有一多半其实也是围绕养殖展开,比方玉米,一年收获两万多斤,有多一半充作饲料,地亩收获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转化为货币现金收益。
岢岚县是一个农业传统县份,直到2013年,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占县域经济的21.8%,第一产业占比如此之高,并不是因为岢岚县农业有什么特殊之处,而在于第二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只占到县域经济的23.9%,第三产业却占到54.3%,经济总量与周边县份相比,显然要弱小得多。为什么说岢岚县第一产业在县域经济中占比高呢?因为,同一时期,山西省第一产业占比为5.6%左右,最高的2016年,也只占到6.2%。第一产业占比越来越低,山西一省如此,全国各地皆然,中国如此,全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如此。
绝对贫困触目惊心的地区,相对贫困也是顽疾,相对贫困区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农业过度依赖,或者说,农业占比的高低,与贫困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因此,岢岚县历届县委县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养殖业,以绒山羊养殖为龙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2013年的统计,全县绒山羊养殖达到46万只,年出栏17万只,此举成为岢岚县农民增收的突破点。
老杨的生存经济,也大致上与全县养殖业发展速度相合拍,经济收入的构成,也与全县其他乡村农民相差无几。
但应该看到,以养殖来补充农业收入之不足,农民首先要面对波动的市场价格。正如进城之后“一夜搬了两次家”的张二縻所言,有些年份,羊肉价格一直上不来,出栏一头羊只有100多元,价格上扬起来,也是近年的事情。所以老百姓说,“家有千万,张嘴的不算”,传统养殖业,要面对波动的市场价格,还要对付来势汹汹的各种瘟疫、灾害与兽疾,这个产业来得并不保险,显得甚为脆弱。
除此之外,绒山羊散养放坡,吃草是连根拔起,犄角要蹭破树皮,对草坡、林地破坏甚大,46万头绒山羊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一旦超过生态承载能力,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将是灾难性的。
不管怎么说,老杨是养殖能手,也是种田能手,但“紧够忙乱”。
放羊一年到头就是能闹个4万,刨掉欠债,也剩不多,这还不算耕坡挖地受的那煎熬。放羊挣上4万块钱,你贴的还有两个人哩,一个人放羊,一个人忙家里那一摊,早上五点起来就得去地里头,紧锄赶锄,还锄不完,锄完地,回来吃了饭,赶上羊上山,晚上八点多九点才回来,可受够了。
老杨辛苦如此,尚只能“打个平手”,其他对农业高度依赖的农户,其生存经济就等而下之了。像种90亩地的老刘,像带着两个孩子、寡居多年仍然种着10亩地的王三女王大娘。
三、王大娘
“生产队”那会儿,队里打了一口井,是利用山泉渗水打的一口渗水井,井倒不深,也就五六米的样子,全村的人畜饮水全靠它了。但是,当初修井的时候,没有修井栏,就在井沿上砌了几块大石头,夏天还好说,冬天一结冰,井沿上洒一滴水不要紧,两滴水也不要紧,再多就结成一个冰片,擦擦滑滑,很危险。
刘福有说:当年修的时候,大家都年轻力壮,就没有修井栏,谁估摸咱还有老的那一天?
2016年,工作队进村,他们就发现这口井实在是成问题。其时春寒料峭,岚漪河里坚冰未化,气温还没有回升,井沿上的冰结得滑滑溜溜。人来担水,一根绳结一只桶,抖下去,一回能舀半桶,两回能舀一桶,然后担回家里去。刘福有那样担,王三女一个老太太也需要自己来担。
老曹曹元庆说:这可不是小事情,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万一滑倒摔断一半件那可不得了。他们发现,不仅小赵家洼是这样子,大赵家洼也是这样子。几个人商议,报请县人大,由机关出钱买了两台水泵,自来水入户是大工程,不现实,但安装好水泵,至少上水的时候,人不用靠近井沿,一合闸就可以用水管子接。
安装了水泵,虽然消除了一些隐患,可是他们还“不歇心”(注:不放心),刘福有年近70岁,王三女也过了66岁,两位老人每天早晨出来担水,陈福庆看着就难受。说起来,刘福有跟自己的父亲年纪相仿,王三女跟自己的母亲也差不多年纪,两人担一担水回家,老天爷都看着难受。扶贫工作队三个人商量,干脆每个人“轮流值日”,把小赵家洼刘福有、王三女,还有大赵家洼独门户李虎仁的担水“营生”负担起来。
刘福有刘大叔死活不愿意,理由是:我不缺胳膊不少腿,庄户人家嘛,不担水还像个庄户人?最后,刘大叔跟他们打起了游击,趁工作队有事不在,就早早把自己的水缸担得满满当当,有时候在井沿上碰到,实在拗不过,才让陈福庆担一担回去。
王三女王大娘更是惶然,连连念叨:不当人子,不当人子。
不当人子,是一句很古的南方方言,却意外地在晋方言中保留下来,意为不敢当,相当于“罪过啊罪过啊”的祈告。陈福庆不善跟人寒暄辞令,听王大娘念叨,心里难受,但脸上现着笑,也不多言语,自己收拾水桶直奔井沿而去。
陈福庆每天早上起来,就到王大娘的墙外喊几声。喊几声当然是要给她担水,更重要的是,上回给贫困户体检,王大娘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早晨过来看看,怕的是半夜睡过去有什么差池。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老太太也实在是一个苦命人。
王三女先在下寨那边,丈夫对她不好,离婚之后带儿子嫁到赵家洼曹家。儿子长大,家境贫寒,好不容易在神池县“问”下一桩婚姻,只是,“问”下的媳妇是一个智障,同时还伴有间歇性精神病。很快,儿媳妇生下一儿一女,一双孙儿也同样是残障。
陈福庆进村之前整理村民资料,已经知道王三女的具体情况,但进村入户,扑入眼帘的情景仍然让他大吃一惊。2016年,两个孙儿一个11岁,一个10岁,外表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甚至还不失伶俐,缠在老太太身边,亲得寸步不离。后来,工作队要送两个孩子到忻州读特殊福利学校,事前做鉴定,一为残障三级,一为残障二级。
陈福庆描述他第一次到王大娘家里家访的心情:那真是心在哭啊!
这还是其次,2004年,老伴曹继存患病去世,2014年,儿子患癌去世。十年之间,梁柱摧折,把一个风雨飘摇的破家扔给这位65岁的老太太。紧接着,智障儿媳妇也不愿意在家里待下去,某一天,不辞而别,弃家出走。
想想未来的日子,王大娘一边抹泪,一边说:我倒没些甚,愁的是两个娃娃。将来我老得爬不动了,就是领上两个娃娃讨吃要饭也走不了多远!
2016年的春天,这位被贫穷和厄运一路穷追猛打的老太太出现在工作队的面前。
精准扶贫真是及时,如果不是精准到人,精准到户,这样的老太太怎么能进入扶贫视野?曹元庆老曹,周继平小周,还有陈福庆,三个人一边整理资料,一边这样感叹。
农户的贫困,经济维度上的考量是一个方面,贫困,常常是很复杂的社会问题。
王三女当然是极端贫困中的贫困极端,在赵家洼,类似王三女这样的情况还不是孤例,只不过贫困方式不同罢了,所谓穷有千种,困则百样。极端贫困的直接体现,就是青壮男子到了婚育年龄却无力完成婚姻大事,以至单身,最后成为五保户。
光棍多,是极端贫困地区、尤其是山庄窝铺的普遍现象,其严重程度每每让人吃惊。
在乡村表述里,凡涉婚姻大事,都有一个“过”字,未婚称为“没娶过”,结婚称为“娶过了”,光棍一人则称“娶不过”,婚姻是多么陡峭的一道大坎!婚姻又直接考验着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直接考验一个男儿的谋生能力。老乡们说,“男儿无妻财无主”,一个没有妻室的男子,就像没有主人的财富一样不能发挥其正常功能,派不上正经用场。
在赵家洼,截止到2018年,全村2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有7户属于这种情况。未列入贫困户中,“光棍”还有几个。相对于单身五保户,等而下之残破不堪的婚姻状态怕更糟糕。不必往远说,王三女这一代,跟丈夫已经是半路夫妻,两好未必合一好,贫困状况没有因此而稍有改变,到下一代,只能退而求其次,明知对方有精神疾患,但也只能向严酷的现实低头,进而把残障延续到下一代。
民间歌咏,多关乎爱情。爱情路经贫苦大地,像一阵风,来了,又走掉。“梦里拉住妹妹的手,醒来攥个空袖袖”“小剪子开花六瓣瓣黄,为眊(注:看)妹妹上了个房”“大河流凌冰驮冰,什么人留下个人想人”“山不遮云彩树不挡风,神仙也拦不住人爱人”。
咏歌所及,大抵悲情。落回现实,云愁雾惨。
不必说一村,先来说一家。
王三女夫家老曹家,是爷爷那一代从宁武逃荒到赵家洼安家,第二代曹贵根两兄弟,兄长后来迁出赵家洼到岢岚县西豹峪安家。第三代生有五子二女,这老大就是王三女王大娘的丈夫曹继存;下来老二曹继银,后到了五寨县韩岭庄安家;老三曹纯银,娶了老婆之后,先迁到岢岚县的皮后沟,现迁到神池县安家;老四上头有两个女儿,跟着女儿排序,叫曹六仁,是留村户,因学致贫;老五跟着叫曹七仁。
老弟兄五个,零落四散,只剩下曹六仁一家和寡嫂王三女一家还住在村里。
所谓“没儿愁断肠,有儿气破肚”,饶是父辈如何“刨闹”,让五个儿子都顺顺利利婚娶成家,也真是一桩不可想象的大工程。曹六仁说起父辈,也不能怨我老子,一个老汉,拉扯七个娃娃,不让大家挨饿已经相当不易,扶贫先扶志,扶不起志来,说成个天也不行。
问题出在老五曹七仁身上。
曹七仁是老小,是兄弟五人中长得最精干的一个,还有木匠手艺,但到了三十大几岁迟迟不能完成婚姻,后来经人撮合,娶回大滩沟一个女人来,女人新近离婚,还带着三个孩子。村里老一辈,小一辈,这种情况也多,大家也见惯不惊,不费什么事就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反而是一桩相当“合算”的事情。三个孩子,来的时候都“不大大”,小的七八岁,大的十来岁,七仁都亲,视同己出。外出打工,四处游走“耍手艺”,三个孩子娶的娶,嫁的嫁。谁想到了51岁,妻子突然不辞而别,跟神池县一个下井煤矿工人跑了个没踪影。三个孩子,虽然视同己出,究竟不是己出,娘拍屁股一走,也不认这个后老子。
总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七仁也有七仁的毛病,脾气臭,两口子这十几年夫妻过得也不和谐,更主要的,是挣钱难,挣不下钱。而那个女人,不是二婚,跟定曹七仁已经是三婚,先前跟一个甘肃人勾挂在一起,结果让这个男人卷包了财产给骗了,这才来到赵家洼。现在,儿女成人,煤矿工人有退休金有劳保,人家想着自己的后半辈子找个依靠。“穿男人,吃男人,死了男人嫁男人”,离婚已成习惯,三婚可以,四婚有何不可以?
女性地位低下的乡村社会,女性突然以这样一种方式高贵起来,让人猝不及防。
经过这样一场变故,七仁可能也有些后悔自己的脾气,开始四处寻找妻子———茫茫人海,一个落魄的农民,出门处处难,哪里能找得见?最后,自己都走得没有名姓,自己把自己给搞丢了。哥哥曹六仁记得,那一年是2008年,到2017年,走失正好十个年头。哥哥听到弟弟最后一个消息,是有人在五寨县城关,见到弟弟一个人孤零零地摆着一个炒瓜子摊子叫卖。此后,就再没有了他的消息。
四、曹大叔与张秀清
陈福庆嘴里的“曹大叔”,就是王三女王大娘的小叔子曹六仁。
曹大叔有四个孩子,三男一女,负担很重,但一个一个全“培养”出来了。老大曹利军,39岁,山西省粮食贸易学校毕业,现在榆次一家私企做饲料加工,在当地成家;老二晓军,36岁,当年因为哥哥在外读书,“送不起”学校,报名参军,服役两年复员,学会电焊手艺,在外打工,天津、北京、包头,哪里有活往哪里跑;老三进军,30岁,也在北京做焊工;女儿红艳,21岁,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就读,学会计专业,孩子上进,在学校准备“专升本”考试。
陈福庆对曹大叔非常敬重。因为曹大叔曹六仁家里只有他一个劳力,而且,妻子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视力弱化,鉴定为二级残疾。老曹说自己的妻子,“家里油瓶跌倒也晓不得扶”,说白了就是一个病人。要说妻子也是“苦命人”,几岁上就死了娘,由老子一手拉扯大。曹大叔一人种40多亩地,回到家里还得操持家务,包括做饭。孩子们一个一个长大成人,曹大叔一个大男人,打里照外,是如何熬过这漫长岁月的?
但就是这样的光景,从2016年工作队进村,两年间,工作队逐户走访,曹大叔没有向工作队提过任何哪怕一点点个人要求。
毕竟男人持家,再仔细也会粗疏,何况还有很重的庄稼活要作务。新上任的县人大领导第一次到赵家洼慰问贫困户,一进老曹的家,院里是院里的乱,家里是家里的脏,人大一行人的脚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从此之后,人大的同志每到村里,工作队总要帮老曹收拾归置一下院子里的杂物,这才显得整洁了一些。陈福庆跟曹大叔聊天,也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这种漫无边际的闲谈,也是工作队进村了解贫困户具体困难,制定精准帮扶措施的工作方法之一。
陈福庆发现,曹大叔尽管言语不多,但他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他回到家,待一切收拾停当,总要拿出一个小本本写写画画,这些小本本都是儿女们读书时候留下来的笔记本或者作业本。
陈福庆要看,曹大叔的脸腾一下就红起来,但还是拿给他看。
上面的内容都是曹大叔自己没事“憋出来的”,或是四六句,或是一句话,谈不上名言警句,基本上有感而发。
比方一句:
没有永远的贫穷,只有永远的勤劳。
比方一句:
扶贫先扶志,有志无难事。
比方一句:
只有用自己的双手才能垒起更高的墙。
等等等等,总是这样自我励志的话。工作队做了些什么,老曹心里很清楚,他嘴上不说,其实都写在这些本本上面。
忆起当年养育四个子女的艰难,曹大叔自己“憋”出一个四六句:
子孙无钱难更难,养育四子苦难堪。
(若)干年已把钱花尽,梦想求人不敢谈。
从大儿子在县城读高中,到2016年女儿曹红艳考上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曹大叔家里没有断过念书娃娃。老曹说:“供了四个娃娃,没有向政府提过任何要求,咱没有因为自己娃娃上学去求人的想法。四个娃娃念书,找东家,求西家,借了个遍,反正没过过一天宽裕日子。”说到刚刚在天津上学的闺女,曹大叔说,“这一年学杂费、生活费加起来,总共要26800元,春天开学走,给拿了9000元,又争取到助学贷款6000元。这不,中途打电话过来,只说没钱了。我能咋?我就是再作难,也不能叫你个女娃娃在外头作难啊,这就又打在卡上1000元。”
“女娃娃比男娃娃操心大,人说富养闺女穷养男,闺女就给她宽裕一些,现在外头的世界乱哄哄的,怕一时受了憋屈,怕学坏。”
曹大叔里里外外一个忙,负担重,情况特殊,生存经济就显得颠三倒四,根本算不起账来。名下有50.5亩地,几轮退耕还林下来,到2017年,仍然种着26亩地。地之出即庐之入,再无长余。陈福庆发现,凡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农业收入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像曹大叔这种情况,一个人打里照外,根本无法分身外出打工,所以种的地也就多。
在先种个四五十亩地,也就是个广种薄收。除掉化肥种子之类成本,最多的时候,一年也就能收入个6000来块钱。净坡梁地,平地不多,一口人就七分地,一家人就是个三四亩。沟塌地,土壤子不厚,净石茬地。莜麦一亩地也产不多,一亩就那么一袋袋。能卖的也不多,那些年净种些葵花,七八亩,碰上下雨,全长霉,臭了。种地就是个碰运气。没分地以前,国家还有收胡麻油料任务,1982年刚下户,我们还得给完成那任务。1983年以后就不用了。
没养过羊,就喂了一个牛。一个人根本照顾不过来。至2013年,耕地才用人家的旋耕机。以前净是雇上牛工,雇一个牛工一天100元。旋耕机连旋带点播一天100元。机器还是速度快,也方便。现在种地可是投资大了,我种上十来亩地,旋拼、地膜、种子、化肥,乱七八糟下来,一年咋也得5000来块。
再过二年,娃娃毕业了,好是好了,好也是她好了——咱为的就是个娃娃们好。
我“憋”了两句话:闺女欢喜她娘愁,老子闹成了个灰骷髅。
曹大叔喜欢写这样一些顺口溜,是心声,是感触,其实更像是自言自语,甚或,还是贫困艰难生活的一个段落分割符号。这个少言寡语的汉子,在这样的自言自语中,其实是在与世界与生活本身对话。一句写罢,四句连缀,心理会缓释不少吧。因为他为儿为女一辈子操劳,现实正在慢慢地与梦想一一对应过来。
赵家洼村老一辈人,像曹家五男二女七个子女的家庭并不在少数,到曹六仁这一辈逐渐递减,但仍然是四个子女,下来,马贵明三个儿子,比曹六仁年轻将近十岁的张秀清,则还是四个子女,只不过,他是三女一男,三个女儿大,一个儿子小。
三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时代昌明,手心手背,不同过去重男轻女,一样培养。张秀清在年轻一茬人中,两口子负担同样重。
张秀清两口子很上进,也吃得苦耐得劳,2017年,秀清50岁,妻子赵改兰则49岁。49岁还不算大,但岁月将一个俊俏的媳妇磨成一个地道农妇,头发花白,甚至牙都缺了两颗,乍一看,60岁都有。
说起当年生孩子,赵改兰说:
我21岁上嫁到赵家洼,家在中寨那边。四个娃娃,三个闺女,一个小子。那会儿人们也封建,就想传宗接代。要是这会儿,送个娃娃念书这么难,叫我要也不要了,要上两个决不要了。
超生咋不罚款?咋也把五六千给罚走了。那会儿你辛苦一年,也挣不下个五六千。老二还有准生证,老三和老四都挨了罚款,老三一直罚到12岁,老四罚了二年,最后做了绝育手术,一次性交清罚款2000还是多少,再没罚过。
罚款再多,也难抵“人们封建,就想传宗接代”的老观念前来抗衡,更何况,在基础建设严重落后的山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劳力参与方可展开,过去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实行起来特别艰难。在取消农业税之前,乡村干部四大难,“催粮催款,刮宫流产”,此“四大难”工作,部分地方推进过程中的简单粗暴,正是导致乡村治理恶化的重要诱因。然而,在善于把一切宏大叙事消解并喜剧化的乡村社会,会莫名其妙出现“王五千”“李八百”这样的孩子小名,细问之下,原来这些孩子的名字,就是当年超生罚款的数目。
张秀清4个孩子,罚款达五六千元。现在看来,罚款虽多,但也值得。
大闺女28岁,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在太原打工。二闺女26岁,也是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先前在太原打工,成家生孩子后回岢岚“哄娃娃”(注:抚养孩子)。被罚款最多的是老三,一连罚了12年,出息最大的也是老三,叫张艳霞,正就读于山西师范大学。老四,儿子张艳阳,也正就读于郑州工业学校。
一家四个孩子,全部“供养”出来,全部通过高考离开村庄,这在赵家洼绝无仅有,两口子被大家视为榜样,每每提及。
但他们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致贫原因,当然是因子女就学。但谈及“供养”四个孩子上学,秀清两口子虽然感到苦,感到累,但舒心。此贫非彼贫,贫与贫不一样。赵改兰说:
不是不想离开村子,是出来了找不下营生,不知道咋供四个娃娃念书。
前10年,秀清在外头打工,我在家里种地。前些年我种了30来亩地,养的3个猪,还喂一头骡子。秀清下窑,宁武也在过,内蒙也在过,哪里给的价钱高就往哪里走。
下窑一天能挣个一百四五。前些年,一天挣个几十的也有,这几年工资高一点。他们不是正式工,也不是合同工,就是人家揽上活儿,再雇他们。满打满算,一个月有个四千多,平平常常一个月两千大几。娃娃还在念书,辛苦也得再坚持一下下。
我们都没什么文化,好工作也找不下,秀清可能是个初中,我就念了个小学。
那会儿种地甚也有。葵花呀,黑豆呀,糜子、莜麦、豌豆那些,都有。那会儿种庄户,甚也种,先不说卖钱,得刨闹点吃的。前年种的就不多了,梁地都退了耕,就12亩沟塌地,种了六七亩玉茭子,二亩山药(注:土豆),种了些草。支出也就是买点化肥、地膜,加上别的,乱七八糟,一年下来就是个两千多。
后来秀清不再外出打工,回来养羊,大羊有80来个,连上羊羔子,养了一百四五十个。
庄户人家,就是个这,早上种完地,赶中午再把羊放出去。娃娃们当时从阳坪开始,就住校。念高中时候,在城里给赁了个家,姊妹四个,大的照应小的,大的和二的错的两岁,二的和三的错的四岁,三的和四的错的两岁。那会儿赁房不多,一个月就70元。
算上学费,支出就多了。前头两个闺女花了多少钱,咱也不记,反正那会儿秀清打工,我养羊,怎么也不够,一到娃娃们上学就发愁,把亲戚们借了个遍。三闺女上学那会儿好点了,可以助学贷款,四年都是从银行贷的,一年贷5600,贷了4年。
现在国家政策好,四年内给还清,不收一分利息。就管个生活费,闺女用不多,一个月600块管够。三闺女周末啊国庆啊,就出去给带个家教,暑假也不回家,给人打工,管住不管吃,一个月还能挣2000元。闺女也懂事,不想再给家里添负担。她学习好,同学们都说让她考研究生。研究生这又得三年,她想想就算了。她说她小时候咋还没咋(注:没做什么事),就给家里塌下那么多饥荒,现在念到大学了,快不要念了,给家里存点钱,让弟弟娶媳妇吧。
小子费钱,郑州那地方饭也贵,他又能吃,一个月1000也不好说,有时候够,有时候就不够。
好在,后年这两个也毕业了。现在想的就是好好再刨闹上两年,把孩子们的贷款给还了。咱也一年比一年老了,好多地方做营生,一到五十五,就不用你了。
几个娃娃念书都没赶上“雨露计划”,后边两个娃娃是2015年上的大学,扶贫上的“雨露计划”2016年才开始。
娃娃们肯念书,咱也有盼头。你看咱种地受一辈子苦,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太阳晒着,熬煎得,咱辛苦辛苦,可不要娃娃们再受二茬苦。咱受下苦,一辈子也完了,娃娃们还年轻呢。
咱这样的人家,在赵家洼也不多。人家最多叫娃娃念个初中高中就不叫念了,回家赶快去给挣钱哇。我们家四个,六仁家一个,永兵家一个,算是念成书了。
咱不是勤快,坐不住,实在是娃娃们要用钱的地方多,天天催着你要钱,你想坐也坐不住。
一番访谈,感动涌上来,感慨也涌上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