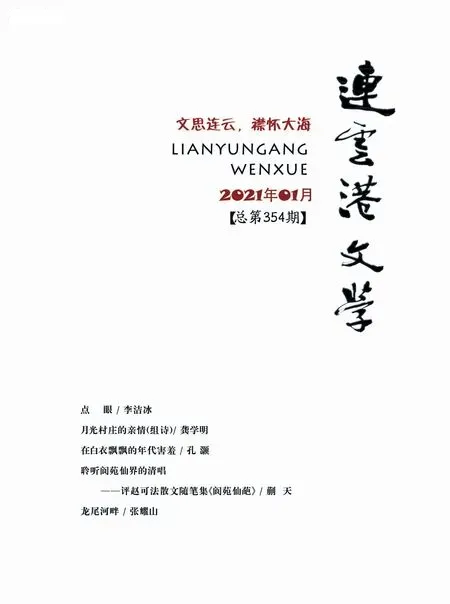点 眼
李洁冰
一
云彩起了。风动,云走,月亮把半个脸从鱼鳞云的背后静静地探出来。一团团云絮就这样在月光底下游弋着,时走时停,偶有风过,便倏地飞逝了。穹庐之上,只剩下一轮满月,圆圆白白地挂在那里,衬着周边几颗晃眼的星辰,打谷场变得清凛凛的,显出一派空旷。一忽儿,云彩又一堆堆地涌过来,是被风驮来的,适才还通透着的满月,此时又渐显渐隐,直至消失了,周边幽幽暗暗,再度陷入一片阒寂。
“天狗吞月了……”不知谁在嘴巴里嘟囔了一句。半天并无人回应。河堤草丛里的虫鸣却潮水一般涌起来了,是亘古不变的、举凡有翅膀的蠓虫的声音;钻土打洞的蝼蛄的声音,还有某种不知名的小魔怪拉锯的声音。一波才歇,一波又起。中间裹着一串搅天杠地的咳嗽,少顷,有个声音慢慢地,由混浊终至清亮起来。“是说龙呢……”仿佛,那声音是从遥远的河对岸传过的,嘁嘁喳喳,伴着蝉鸣,蛙鼓,还有夏夜潮漉漉的气息,在乘凉人的耳边交织着。
“哪儿的天狗?说的是盘古开天地,龙涎河里有一条通身泼漆的龙,落生时,也就筷子般粗细,倒是个见风长的货色,喝风屙雨随走随长,端的是一条好龙。后来让玉皇那老儿听说了……”“怎么了?”有人惺忪着睡眼问。“还能怎的,就召了去,管些个云雨的事情。”“是说狮子楼武松杀嫂,还是潘巧媳密会小沙弥?又该到几分光了……”有人无厘头地跟了一句。“尔壶,你且记得几分光?”旁边有人拿话勾他。“没说嘛,西门庆宽袍大袖子一搭,一双龙凤筷子轱辘辘就落到那嫂嫂的绣鞋上。”叫尔壶的亦不示弱,搭嘴就续上了。众人大乐。正嘈乱着,一叱声又起了——“熊孩子多话,且听慢慢道来。”
雁窝荡的鳏夫刘老爹,平日里搭个棚子在打谷场边住着。一俟夏凉,挨不过夜深难熬,就摆龙门阵,通常是荤素一锅乱炖,亦不管驴头搭到马嘴上,招惹得雁窝荡人饭后掮了席卷儿,只奔打谷场的方向走。
“接着说龙的故事。转眼间,漆龙长大了,每天跑到龙涎河里去喝水,然后在河滩上作法,立时云飞星走,扫帚般的尾巴挤出一串喷嚏,苏鲁交界方圆数百里,举凡龙飞过的地方都降甘霖了……”“原来这档子事”,有人泄气地跟了一句,“有甚嚼头!”刘老爹只是不理,紧接着讲,“玉皇大帝由不得随意布施的,就派天兵去捉漆龙,想把它收归到天上。满世界霎时起了黑云头,唏哩夯啷,箭矢如雨,漆龙终是不敌,最后一头从云彩里栽下来。”
“掉哪儿了?”谷雨子懵懵懂懂地问。弄不清刘老爹怎么跟龙缠磨上了,从前总讲些玉兔、蟾桂、柳毅传书,今夏却夜夜讲龙,蛮龙归正、龙马负图、龙女盗神鞭……都快葫芦似的拎串了。就说这龙窑的故事,入戏慢,闲篇多,中间插科打诨的亦不少。讲着,听着,谷雨晃眼看云彩,一会卷,一会走,就像龙尾巴在忽闪,月亮明明灭灭的,又听得满耳龙飞,龙舞,龙闹腾,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待醒来时,一场子人都走光了,端午摇她,左右只是不起,就把灯草席子一轱辘拽了。谷雨咿呀一声,打个滚从地上跳起来。月光把地面映得益发疏朗了。谷雨手被攥着,一径踉跄地朝前小跑。“到底掉哪儿了?”没头没脑的,又追一句。“钻山了,打洞了,跑南北老海喂狗鱼了。”端午不耐烦地说。谷雨知道不是真话。漆龙总归是投胎了,至于去了哪里,刘老爹说了,且听下回分解。
夕阳从篱笆墙上打过来,筛下满地的散金碎银,端午的脑袋顶着草须子,围着柴禾垛子左搭搭,右撩撩,抽冷子从柴禾洞里掏出个东西。谷雨眼尖,一下在旁边逮个正着,俩人围着柴禾堆腾闪几个来回,谷雨方弄清手里的宝贝。黄巴扎娑的毛边纸,用线绳锥的补丁,封面上有行花体字:小布头奇遇记。再看,一对狸猫眼,咧嘴虎头的绣花帽子,圆头、阔面,真真爱煞个人!“哪来的?”谷雨问。“管哪的!”端午说,“天黑就得还,半页都未看。”谷雨说:“你躲在这里,豆不磨,草不剁。”端午说:“鸡轰上树了,草剁在锅里跟豆渣煨着,还要哪样?”谷雨没词了,只好咕咕鸡似的嚷嚷:“哪个先看,剪子包子锤。”端午挡不住央告,连说西村等着要,太阳落山前就得还了。
“鼠老五,鼠老五,溜出洞来散散步,最好找块甜点心,外加一个烤白薯。”《小布头奇遇记》看完,谷雨嘴巴里就唱上了。“别唱!”端午发话了,“谷雨,你去找些碎花布。”谷雨翻翻白眼,又支使人。端午伸出仨指头——“猜三样,猜中就不让你添磨了。”添磨,指的是在磨坊里推磨的时候,掌着勺子朝磨眼里添豆子。转几圈,啪地扣下半勺头,须得手眼身法步,样样跟上,速度得快,定盘星要准,白色的浆汁才能扑扑簌簌,从辗盘缝里不停地淌下来。谷雨每逢推磨,抱着根棍儿转得晕天杠地的,云也不见,日头也不见,像个打眼罩的驴子,哪里有心思摸勺头。这回自然兴冲冲,脱口而出道:“粘谷子,做鞋垫。”端午将脑袋晃得跟摇头茧似的。“孙歪媳妇生大胖了。”端午还是摇摇头。谷雨眼睛倏地放了亮:“花书包。”“说你傻,你就傻。”端午拍拍手,嘤声唱道:“这就做个小布头。”
二
桂树底下放着笸萝,孙歪媳妇正坐在那里纳鞋底。锥子在刘海里抿抿,然后用长指尖抵住锥子朝鞋底一扎,细细的线绳便拽出了,那线绳有红有绿,丝丝缕缕,远远看上去就像织云彩。谷雨躲在槐花树后面,丢块鹅卵石,孙歪媳妇呃一声,四下里看看。只有风,还有邻居家的花公鸭甩着屁股,脑袋一歪一歪,从喉咙里挤出一串奇怪的求偶声。孙歪媳妇将脑袋低下来,再扎,“哧哧哧”,又朝外面拽彩线。谷雨忍不住了,蹑手蹑脚地挪过去,这才看到没织云,是在绣喜鹊蹬枝。一对狸花鹊子蹲在枝头,口对口衔着梅枝子。只是梅花瓣还未绣好,鹊子的爪子半悬空着,让谷雨担心,不知何时会啪的一下掉下来。
“鬼丫头捣鼓甚?”孙歪媳妇笑笑,鼻翼的蝴蝶斑看上去益发重了。谷雨不应,低着脑袋去针线笸箩里一通扒拉。顶针轱辘辘打个滚,蹦着跳着走远了,绣针盒倒着口,撒了满天满地银光。孙歪媳妇拽个鞋底子抡个半圆:“八岁的大丫头还淘气!”谷雨左手拈张画报纸,右手攥几块碎布头:“七岁半,这好看,那好看?”孙歪媳妇脸一绷:“都好看……还得粘布做谷子。”孙歪在东北老林里伐木头,每逢年后上路,腰里总是裹爿锅盔饼,一串千层底。媳妇熬更打点,将碎布做了鞋底衬,左右供不上男人穿。谷雨如何晓得大人心,只管攥了花布头。孙歪媳妇招招手:“谷雨丫过来。”然后凑上去嘁嘁嘈嘈。谷雨只觉得耳根子痒痒的,回转身,笸箩里的碎花布不见了。“这胖婶婆,像你啵?”孙歪媳妇笑吟吟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八度。谷雨打开画报纸,果然有个皱皱巴巴的美人头。齐眉的刘海,月牙的眉,两团腮红赛牡丹。“磁婶呀,想做个小布头。”谷雨嗫喏着,把端午的话又挤出来。孙歪媳妇是雁窝荡的小抠,外号磁婶。谷雨说漏了嘴,那边早把脸挂下来。“熊孩子玩家家,撒尿砌墙盖房子去!”说话间把笸箩拾掇了,变戏法似的捂个严实。
正午的太阳有些毒热。谷雨怏怏地溜达着,中间碰到一位丢了菜瓜的农妇拍天打地的骂街,主人家的土狗在旁边气咻咻地叫着助阵。谷雨懒得看,又串了杂货铺,裁缝店,都被当成小把戏哄了出来。谷雨急得两眼冒金星,鼻头上沁出了几粒汗珠子。端午画书看魔障了,非得仿着做娃娃。大人都觉得他吃饱了撑的。可这俩心有灵犀,巴掌一拍就约定了,那几日,进出都晃着脑袋念经,唧唧唧,唧唧唧,这就做个小布头。实则,谷雨早想要布玩偶了。你看电影里演的,玻璃橱里摆的,把眼神晃晕了,有的还满地打鼓转圈儿。如今自己动手做了,忍不住在心里描了千回,画了万遍。不过左右得备齐碎布角、棉花、针线、刀剪什么的。端午给谷雨的任务,就是找布头。
转到太阳落山,谷雨空着两手回到家里。“巴克夏”又拱开围栏跑了。这家伙细软的红毛茸沓沓地贴在皮肉上,两腮陷得深,嘴巴却尖得像根毛笋,吃食时“唧溜唧溜”的。每每提起,妈妈总是叹息:“这老大哥还真不好伺候啊!”小姊妹俩的猪食是白烀的意思了。烀,就是将青草麦糠放到锅里用柴火煮烂,然后舀到食槽里喂猪。谷雨割草,端午烧锅,姊妹俩放学后整天忙得陀螺般疯转,“巴克夏”半年没上膘。这家伙待得腻烦,时常一头拱开围栏就跑了。一蹿就是几条巷子,搅得端午兄妹几个围、追、堵、截,再加上在县里开会匆匆赶回的母亲抄起一根棍兜头敲上去,才勉强吆回来。眼下围栏又空了,只有葵盘似的蜂窝挂在屋檐上。端午交代的事没着落,顾不上巴克夏了。谷雨将围栏门关上,晃眼看到葵盘里的蜂子排着长趟,飞三匝,钻进去,旋即又爬出来,嗡嗡叫着飞走了。也是好奇心重,便折了根槐枝子戳戳捣捣的,想钻过去看个究竟。忽听一声大喝,“哎呀,找死!”随即被一股力牵着,从围栏里呼的跌了出来。
“鬼灵精,要闯祸了!”梅子妈端着个笸箩,站在围栏外吆喝着,谷雨定神看时,辫梢子正在对方手里抻着,头顶上的太阳倒是益发毒了。“形影不离的,咋分开了?”梅子妈耳朵上戴俩吊坠儿,头发用银簪子松松地绾起,是村里有名的巧媳妇。谷雨惊魂未定,只觉得心跳得急,脸红得紧。“嘿,端午……”不知怎样搭话,一眼瞥见梅子妈手里的笸箩,讷讷地说,“就要做个小布头。”“跟我来,到姨家挑去。”巧媳妇仿佛知晓谷雨的心事,扯着丫头风踩水皮一溜疾走。
谷雨心里美滋滋的。今天终于访着正主了。
梅子妈跟谷雨家是邻居,一道篱笆墙隔开了两户人家,一年四季轮回,墙头上开着长须探日的丝瓜花,咧着嘴巴的石榴枝,垂挂着滴哩耷拉的吊瓜儿。梅子爸在部队当连长,长着一脸劲疙瘩,人却和善。探家回来,系白毛巾的茶缸别在黄挎包上,屁股后总是跟满鼻涕小子。梅子妈在村里开裁缝铺,雁窝荡能踩缝纫机的人家,算是上等的富户了。加上人勤,活精,自是好人缘。每天早晨太阳升起来,谷雨听到篱笆障子西边,就传出“哒哒哒”的脚踏缝纫机的声音,那是梅子妈在做衣服。
现在,谷雨看到梅子妈将蓝花布摊在案子上,拿起绿色的圆粉饼,上下描描,左右画画,然后抄起银光闪闪的大剪子“哧溜”几下,衣领,大襟,前后摆就都有模样了。却是瘦瘦的,麻雀样的紧凑。“梅姨呀,这是给哪个?”“刚才谁跟磁婶磕牙来?”梅子妈笑笑,“没看人家大肚子。”谷雨“噢”了声,这才明白孙歪媳妇脸上的蝴蝶斑是怎么回事。一溜看过去,几案上摆满了小八件,有王字脸的虎头鞋、睡帽、打横系带的睡衣、楦满棉花的紧身袄裤,又都是松松窄窄,包月子孩的那种。正看得入神,却见梅子妈眯起眼睛吹吹,将剪剩的边角天女散花似的呼啦推到地上。“谷雨丫,姨忙着,你自个拣去玩。”言毕,梅子妈将剪好的蓝花布塞到针孔底下,两脚一踩,“哒哒哒”的声音又起了。
“天呐,果然是魔幻的世界!”谷雨一声欢呼,随即拱到了桌子底下。就觉得万紫千红一齐开,眼睛很快被映花了,心咚咚乱撞个不停,随即挑了干枝梅的、斜纹杠的,眼见得虎头龙脑、凤飞蝶舞、哪吒闹海……各式碎花布头鼓鼓囊囊裹了一大包。朝桌外钻的时候,脑袋被桌角磕了一下,竟是浑然不觉。
三
端午拿把剪子左眯眯,右照照,有点生疏地比画着,然后“哧啦”一下,剪子剪下去了。就听“哎哟”一声,谷雨急慌慌近前来看,端午面露苦相,将手指头塞到口中不停地吮着。“咋的?”谷雨问。端午咧了咧嘴巴,低头,又剪。谷雨掌着煤油灯,灯光晃晃悠悠的,端午的脑袋映在墙壁上,变得出奇的大。谷雨心疼地看到她挑来的花布头被一块块地做着试验,东割西剪,柳败花残,心疼得口中“咻咻”抽着冷气,半天不见对方有歇手的意思。直熬到夜阑时分,灯花“噼噼啪啪”炸了满屋子,煤油灯瓶子熬裂了两个。鸡叫头遍的时候,桌子上的东西总算显了形,谷雨举煤油灯的膀子累得胀胀的,心里还真佩服端午了。这是一件蓝花的小衣裳,有领口、袖洞、前后襟。菊花瓣的白,湖水样的蓝,看上去清清爽爽,却又不一般的韵致。剪好了,端午像个大人似的,在飞针走线的时候,头也不抬地吩咐道:“去,把小布孩拿来。”谷雨应了,赶紧打开墙洞搁板上的纸盒子,从里面取出俩布偶。一律圆乎乎的脑袋,半拃长的身体,手脚齐整,用彩线系着,看上去有模有样。这是端午做的,用的是高支棉,本地不多见的斗纹布,不知从哪儿淘来的。接下去,端午变戏法一般,很快给布偶套上衣服,鞋子,竟然还有粉嫩的绒线袜。一切穿扎停当,端午说:“谷雨,好好看看,还缺什么?”谷雨左瞧瞧,右摸摸,心像要飞出嗓子眼儿,手心很快变得汗津津的了。
戴着绒球憨蛋帽,穿着团团花酱色小棉袄的,自然是男孩了。端午想得周全,脖子上竟然围了花格巾。另一个,两条辫子搭在肩上,紫平绒的斜对襟小褂,蓝花花的兜兜裙,头上还顶着金银线绣的布帕子。谷雨看得呆了,看得傻了,就觉得端午的巧心,端午的身手,端午的心思真不是白费的。听见那边嘤声道:“一把伞?小篮小铲小锅碗,外带件一件绿风衣?布娃娃出门也得看风景。”端午笑了:“再看看,这回猜不中不给玩了。”谷雨有点急,拼命搜罗着连环画里的情节,那布孩儿飞来飞去,被误装到运煤车上,后来从人口袋里漏了出来。接下去遇到谁……噢,好像滚到老鼠洞里,有只老鼠对着它唱,“吱吱吱,吱吱吱,俺得把牙齿来磨磨。”“要不做个花匣子?”谷雨觉得只有装到盒子里,里外三层裹上,才算进了保险箱。
“眉眼在哪里?”端午问。谷雨凝神细瞅,大脸盘上白光光的,还没顾得上画鼻眼。端午这回却沉着得很,老练得很。显然早有准备的,说话间搬出了一堆新物什。
月色从窗棂外泄进来,影影绰绰的,打在屋子里的蚊帐上。煤油灯瓶子里的灯油快熬干了。槐树梢上挑着浅浅的一抹月牙儿,旁边有颗星星却亮得晃眼。
桌子上的砚台有点方,有点笨,边沿上蹲踞着吐着虬须的龙,是很老派的老种。谷雨跟母亲去在县城大楼里工作的父亲那里玩,曾经见识过。父亲喜欢文墨上的事,从前不忙的时候,偶尔会抡开膀子写几笔。诸如“我见黄河水,凡经几度清,水流如激箭,人世若浮萍……”啥的。与人交谈时,偶尔夹杂着“张妙于肥,藏真妙于瘦”的句子,半文半白,只是听得懵懂。后来父亲越来越忙碌,渐渐练得少了,偶尔再去,谷雨发现砚台夹在一堆马恩列斯毛本本里,上面落满了灰尘。现在,谷雨看到端午将砚台摆好,嘴里又发话了:“谷雨,弄点水浸下,把墨磨好。”谷雨不情愿了,“这画鼻子画眼的,磨墨做什么?”就翻翻弄弄的,去书包里找大字笔。端午很快猜透了谷雨的心思,从桌腿底下将墨水瓶掏出来,直直地抵到谷雨鼻子上,“好闻吧?”一股子刺鼻的异味,直冲到谷雨的脑门上。说来也怪,这些年凡在雁窝荡联营店买的墨汁,一律臭得不能近前,听说是用河沟里的臭苘沤的,未辨真假。“你说说,这臭墨子能画布孩?”端午振振有词地问。谷雨不吱声了,就磨。实则困得磕头虫似的,早想睡了。无奈妈妈去城里开会,哥哥姐姐都在县城上学,眼下是端午当家,只有听她的了。更重要的,是小布孩的模样快出来了,哪个不想先睹为快呢。
墨磨好了,端午把团团袄的男娃拿过去,屏着气息开始绘眉毛。先是拤了比例,一边各戳一个点,然后拿毛笔勾着,细线拉成了柳叶眉,再慢慢朝两边拓着,越描粗,谷雨越呼吸得紧。“甭画了,再画粗不好看了,没听刘老爹说许仙是柳眉凤目。”端午笑了,“许仙是这样的?”还是可着劲涂,转眼就涂成了两条黑黑的卧蚕眉。再画眼睛,又是铜铃似的大,睫毛倒是描得根根清爽,酷似画书里的小布头。接下去是鼻子、嘴巴。谷雨心下急得不行,端午没有一样听自己的,却又眼看着那男孩眉目生动地站在了桌子上,仿佛一抬腿能跳起来。心想这就是小布孩,我也能做呀。当下心里有了主意。
扎翘翘辫的小布孩,是谷雨自己画的。端午先是不允,挡不住谷雨苦苦哀求。那是谷雨生平以来首次画布偶,手颤心抖,几次将墨汁溅到桌子上,甚至在画鼻子的时候,由于笔尖划了一下,鼻线有点歪。端午赶紧握住谷雨的手,往左添了一下,往右添了一下,然后说:“这是个笑模样,太直线就不像真的了。”谷雨哪敢怠慢,连心跳也放缓了,喘气也不敢大声了,捏着笔尖点点抹抹的,终于把想象中的柳叶眉、丹凤眼画好了。要想笑,嘴角弯弯唇上翘。端午在旁边小声咕哝着,不时做着提醒。生怕妹妹画砸了。谷雨很争气,除去提笔时那道眉线,再没出过别的庇漏。就这么描呵画的,当两只玩偶搭着膀子立在煤油灯底下的时候,灯花又噼噼啪啪响了,屋子里顿时亮了许多。
灯火爆,喜事到。端午长长地抻个懒腰说:“好啦,赶快让小布孩入洞房。”谷雨的瞌睡虫早飞九霄云外了。嘴巴里“咚咚呛呛”地做着伴奏,将小布孩一路送进早已布置好的墙洞里。蓝花的布幔,龙凤配的桌椅,小床小帐小枕头,几乎将所有能想到的都摆弄好了。桌上甚至搁了酒盅作小碗,摆了红枣、大米、红纸裹的筷子。然后端午将蓝花布帘子一拉,“快来看,成亲喽,正月里来是新年,吹吹打打结南瓜……”唱了又唱,讲了又讲。“端午,终于有洋娃娃了。”谷雨总是直呼其名,母亲说了几次都不改口。“谷雨,也像画书里那样了。”看露天电影的时候,里面的孩子穿着公主裙,坐大飞船抱洋娃娃……“谷雨,一样样来。”端午允诺着,“小布头有了,飞船会有的,还会有火车,呜呜叫着开跑了。”桌面上丁零当啷,旋即拾掇净了。回头再喊谷雨,那边早已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唇角弯弯的,还挂着刚才的笑模样。
四
“哇呀,漆龙遁啦!许多年后,葬土的土堆上出现了洞口,人们发现,洞里竟然空着,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地道……”恍惚间,谷雨耳朵里又飘过一句话,随着河堤林间的风,若隐若现地送过来,中间有些词,固然听得不清楚,心下却明白着,又在说龙的事情了。漆龙从那么高的天上栽下来,笃定死了。可掉哪儿了,看到后又是怎么埋的,一概不晓。刘老爹讲古,谷雨又来晚了,打谷场上覆满了像蚂蚱似的席地乘凉的人。开始时,照例扯闲篇,几个顽劣后生,净逗着刘老倌子朝男女之事上引,“卖油郎怎地独占了花魁来?”尔壶搔搔脑袋,“谁晓得,莫不是七分光……”众人哄地笑开了。“不消七分的,三分就够了,吉小玉跟着郭排军,去河边寻了人家过日子了。”几个人驴唇不搭马嘴地显摆着,刘老爹目光沉沉的,只是不语。一袋烟毕,抻个悠悠颤颤的懒腰,挤出排山倒海的一通大咳嗽,人们就知道,龙门阵又摆上了,接的是上回书“……有些年岁了,打柴的、采药的顺着蚯蚓般的洞子钻进去,前不见日头,后不见光,一径走下来,什么都没碰到。就知道漆龙遁了,连骨头都化了,只留下了肠子般的巷道子。”
电要来了,谁见过?雁窝荡自打从水库底下搬出来,家家墙上都悬着豆粒大的煤油灯瓶子。现在,有人又扯开新话头。“那东西看不见,摸不着,跟无影巴掌似的,能将人瞬间掴倒呢。”刘老爹的话,总是透着权威性。谷雨听着既神秘,又好奇。但有桩事却是明白的,电通了,满村就大亮了,再也不用点豆粒大的煤油灯了。那日谷雨风车般乱转,给“巴克夏”梳了毛,草剁了半箩筐,连过年包汤圆的糯米,都跟端午从大瓦缸里翻出来,将虫子筛了,然后放到秫秸匾里晒着。等晚上直奔打谷场上,已经挤不到老爹边上了。
“就叫了乌龙窑,也是鬼灵精啊!人们从此就用洞子做了烧窑的去处,举凡陶器投进去,烧得又透、又省柴,忙去附近耗子似的钻土打洞,仿着造了许多孔窑,养活了更多的人家。不消说,皇帝使的碗盏,都是那洞子里的土烧的,自然是上等的货色了,用手指头能弹出铜音来……”嘁嘁嘈嘈的声音,又起了。谷雨只听得满耳的“不消说”,中间既无回应,也无人掰文,随着月亮时明时暗,周围再次陷入沉寂。
“遁,就是不见了。”谷雨心里只有一念,“总归遁了。”“玉皇那里不收,没准去了人间吧。有一位雇身子的后生,遇到姓崔的姑娘……”仿佛为了回应,刘老爹的声音又起了。谷雨听得昏沉,全然辨不清来龙去脉。谷雨总是这样,每逢关键段落,就被瞌睡虫缠上了。掐也不行,拧也不行,虫子叮也不行。说也奇怪,那月亮、那虫唧,还有舒风缓云,刘老爹胸腔里轰轰隆隆的大咳嗽,时而徐、时而急的情节推进,都成了入眠最好的伴奏,听着,梦着。满脑袋满眼,就都是龙了。这不,总算撩开眼皮,又赶上了龙王大战,“是年大旱,早已在人间成家的漆龙显形,给旱地下了一场透雨,惹得皇上又动怒了,复派天兵天将下来。一通雷鸣,轰了个满天满地鳞……”“这回掉哪儿了?”谷雨又提起老话茬。端午在旁边掐了她一下,“懒谷雨子,瞌睡虫,没听着片甲不存了,漆龙真的殁了!”谷雨耳谷雨轰然大响。急抬头看天,一块大云彩不见了踪影。
“听说是去南北朝了。”刘老爹慢吞吞的,撂了一句话,“话说梁武帝命令张僧繇在金陵的安乐寺墙壁上画龙,那龙画得,嘿嘿,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只待雷霆冲云霄……”
转眼到了夏历九月初九。端午说:“谷雨,赶集去。”这天是苏北鲁南交界有名的马场庙会。往年每到此时,雁窝荡的男女老少,都要带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赶到六十里外的马场,一则撂地摊,二则瞧热闹。马场会的习俗未知哪朝哪代传下的,总之方圆几百里,都跑去赶场子。第一日,是请蒙阴山上的法师剪幡。长得竹竿子似的老法师一袭长袍,披挂穿戴的时候,旁边就开始唱歌。那是端午姊妹俩百听不厌的一串曲子,气不喘、音不颤,亮刷刷通透透,直唱得歌者两嘴夹沫,围观的众人嗷地叫起好来。穿戴完了,法师就开始拈香作法了,四下里招一招,南北向划一划,口中咿呀出调子来,《莲花曲》唱毕是《灵神曲》,随后仰天叩地,谢天恩。第二日是踏七星,三日烧纸送钱粮,祈求十里八乡四季吉祥。此外还有耍刀枪的、变戏法的、耍猴戏的,说大鼓书的。三天里人喊马嘶,鼓乐笙箫,紫色的雾霭能遮去半个天空。
谷雨牵挂着的,不唯是瞧热闹,更多还是卖米粉、炸丸子和糖果的游贩担子。顶着毒日头,就这样走一路,看一处,只是饱了个眼福。待挤到卖玩具的地方,就见满眼的风筝在槐树梢上一路挂过去,接着又看到卖鬼脸谱、竹木刀枪的,卖滑石猴、泥响、哗啦棒的。谷雨拽着端午的手,饿得满眼金星子乱跳,肚子里“咕噜噜”大响,“姐,买呜哇。”摊主拣起一只泥青蛙,放在嘴巴上捂着,两手像翅膀忽闪了两下,倏地就流出一段天音来。呜哩哩,呼噜噜,一缕青烟转了几道弯儿,然后幽幽咽咽,直钻到漫天云里去了。听得耳顺,看着眼熟,谷雨口中蓦地蹦出仨字:“尔壶叔?”对面一拍大腿,“是你俩鬼灵精!”随手指了指,原来槐树周遭都是雁窝荡的人。梅子妈、孙歪媳妇、刘老爹,都来了。这边挤挤眼,那边笑笑,小姊妹俩就看到树上挂的、地上摆的,满天满地的十字绣、虎头鞋、小裤褂、柳编篮……正愣神呢,忽听端午说:“有了!”便低了头,拽了妹妹一径急急地朝前走。
“谷雨,把小布孩拿来。”回到家,端午又发话了。谷雨赶紧去墙洞里寻布偶。自从上次吹吹打打送进洞房,谷雨悄悄看过几回。每次都好好的,小布孩们勾肩搭背,亲昵得不行,谷雨就放心地搁了回去。有太阳的时候拿出来晒晒,复又裹了塑料兜去搁板上放着。现在,谷雨踩着凳子,将布偶提着心掏出来,觉得手心怎么潮乎乎的?心内“咯噔”一下。小布孩看上去模样完整着,但眼睛洇了,墨描的眼线都化开了,仿佛刚哭过。原来前几日落雨,让潮气侵着了。俩人心下沉沉的,都知道明天不能拿到庙会上去了,谁喜欢哭泣的布娃娃呢!端午思忖了半晌,拽过谷雨,神秘地咕噜了几句。谷雨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下午,趁着母亲带人通电,姊妹俩将箱笼抽屉翻了个底朝天。最后搜罗出断帮胶鞋底两只,蝉蜕10 个,锈蚀的胶轱辘皮半块。然后循着货郎担子的吆喝声,换回两截蜡烛棒。货郎子管它叫洋腊的。端午不要彩绘,执意要了本色的。然后一路疾走,趁着太阳落山前赶回家里。
“谷雨,拿火柴来。”饭后拾掇了,端午说,谷雨好奇地看着端午,先是抽出一根火柴棒,去盒沿上蹭蹭,就听“哧啦”一声,眼前亮起了一簇椭圆的小火苗。接下去,端午手捏火柴杆,凑到烛尖上耐心地烤着,少顷,半空里倏地腾起一团烈焰,又慢慢小下去,小下去……最终,缩成了黄豆大的一粒烛火。端午就这样举着洋腊,轻轻地倒扣过来,让那火苗渐渐变形,拉长。谷雨正诧异呢,忽见一滴烛泪,晶晶莹莹地掉了下来,端午赶紧拿碟子去接,就听邦的一响,烛泪滚了几滚,像一粒珍珠似的,定格在盘子中央,不动了。
那烛珠儿说也奇怪,圆圆的,中间有个凹窝,看上去玲珑剔透。端午摁住烛尖,稳稳地对准碟心,一滴滴烛珠儿就这样扑簌簌地落下来,顷刻间,大珠小珠落玉盘,谷雨的眼睛瞬间被映花了!“端午?”谷雨好奇地问,“想怎弄的?”“点眼。”端午诡秘地笑了笑,随即从匣子里捻出一枚穿银线的绣花针。她此时的神情,就是妈妈平时缝衣服的样子。将针尖去刘海里抿了抿,然后对准盘子中间稳稳地一挑,烛珠儿便亮亮地顶在针尖上了。
端午翘着兰花指,捻了捻手里的银针,朝布偶的大脸盘挪过来。谷雨看着,渐渐有点明白了,激动得心里颤颤的,嘿,这鬼端午,主意就是多!接下去,谷雨看到孪生姐姐将针鼻上穿过的丝线打个绕花儿,像绣十字绣似的,手指飞快地舞动着,左扎扎,右拽拽,一根银针捻上捻下,在指缝间闪挪腾跃,眼看着烛珠儿就飞到布偶们脸上去了,眼看着小布孩就栩栩如生了。清澈澈的月光这时候从窗外打进来,映在小布孩的脸上,晃眼看上去,两个调皮鬼手拉着手,像是随时要拔腿跑掉。
谷雨急慌慌的,将小布孩一把搂住。那对布偶双目炯炯,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精气神凝视着她。端午说:“谷雨,动作要轻,烛珠儿还没干透呢。”
五
这是秋天的月亮,清冽,幽远,将世间的一切尽收眼底。农忙才过,田间到处都是散落的花生藤和地瓜秧、黄豆荚儿。农人的牛车拖着山包似的稻垛子,踢踢槖槖地在路上穿梭着,白天喧闹的打谷场复又于沉寂。
刘老爹的龙门阵,已经摆到南北朝了,说的是梁朝,有一位出名的大画家叫张僧繇,画像的手艺在方圆数百里都很有名啊,就被皇帝老儿叫了去,画龙。
又是龙,这刘老倌子八成前世是龙脱托生的了。谷雨在打谷场上盘腿坐着,脑袋像磕头虫似的,左右转筋。本来明天要去庙会看踏七星的,可端午忙完点眼的事,拽着谷雨,说好久没去打谷场啦,不知刘老爹讲到哪儿了。姊妹俩脚不点地地赶过去,果不其然,又在说龙。
“那一年,梁武帝派张画师为金陵府的安乐寺作画,高堂大屋的庙宇啊,只有四壁空着,然后画师来了,画了三天三夜,四条龙就腾云驾雾了。端的是长须绕梁,口衔金珠,仿佛真龙模子铸的……”“这回是漆龙?”谷雨脱口喊道。听讲的人都笑了,“是呀,漆龙转世了,谷雨丫哪天顶着花布帕子去捥青,没准路上遇见个俊后生。”刘老爹接着讲:“大师画好后,十里八乡的人都跑去看。齐刷刷的,都看出其中的端倪来。”“猜着了嘛。”谷雨又跟了一句。端午在旁边戳戳她,甭多嘴。
“几条龙全都没眼睛啊!”刘老爹说,“论年古辈,这画龙哪有不点眼的?莫说皇帝老儿,看的人都看不过了,就央求他,赶紧把龙眼点上。大师却不慌,笑笑说:这不难,点了你们就后悔了。众人听不懂他卖的关子,就催着赶紧点眼。画师被催无奈,说好,好,我点,先点两条。这天庙宇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那个叫张僧繇的,当着众人的面,就撩起宽袍大袖,去龙头上轻轻一点……”刘老爹低了脑袋,吭哧吭哧地忙着磕火石。众人不敢吱声,皆屏了气息,听下文。“嘿嘿,忽然间狂风大作,一道闪电将天空豁刺刺撕了道口子,果见两条龙腾空而起,一爪子蹬倒了墙壁,驾着云头飞走了……”听到这里,谷雨突然心如擂鼓,耳里轰轰隆隆,像有一列火车急速驶过。“天呐,龙飞走了,是点眼才飞的……”再不敢往下想了。
月光从帐子外面打进来,照在熟睡的端午脸上,这天晚上,谷雨老觉得蠓虫在枕边嘤嘤的,音调粗粗细细,有独唱、有合唱。钻到被子里不行,用衣服将脑袋包起来也不行。胳膊上,脸上麻酥酥的,忽痒忽疼,又抓摸不着痒疙瘩在哪里。急得谷雨牙根痒痒的,真想拿柴火棒去撩她。这家伙蒙头进了黑甜乡,哪晓得妹妹的苦心思?谷雨躺在那里,盼着瞌睡虫赶紧上来,说来也怪,那晚瞌睡虫都跑光了,屋子里倒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囫囵咽点口水,动静亦是惊人的大。心下却明白着,有桩心事必得做的。索性一轱辘爬起来,鞋也不穿,蹑着脚,鬼鬼祟祟地蹩到墙洞处,将里面的东西探手掏了出来。端午说过,见了风,就不好了,太阳升起前动不得的。依旧忍不住,借了月光揭开外层的油粘纸,又拽了塑料布,第三层,是缠裹的蓝花兜。一径抖开,俩布偶嘟噜噜滚了出来。谷雨通身打个激灵,端在掌心上,那两只小布孩笑吟吟的,正眼对眼瞅着自己。谷雨理理蝴蝶结,捏捏鼻头,再拧拧胳膊腿,都好好的。说也奇怪,接下去,搁前置后,打开,包上,线绳绕了花儿,横竖只是不适。索性扯块蓝花帕子重新裹了,塞到贴身穿的小褂夹层口袋里,然后摸到床沿歪着,大气不敢出,慢慢将身体放下了。
一堆堆的云彩在天边翻卷着,时聚时散,猛然间撕帛裂绢,虹霓千道,漆龙显形了!那龙吐着两跟长长的须子,像鱼似的拍打着尾巴,在云端做着各种奇怪的姿势,水花随着它抡圆的尾巴,像甘霖似的喷下了,每洒一次,就有无数稀奇的动物,兔子、獾子、狐狸、猴子纷纷在漆龙的翅膀上跳着、蹦着,其中有两只,看上去怎么有些面熟?谷雨揉眼睛,再瞅,脑袋訇然一炸,天呐!小布孩也在上面……比画着,还没看清鼻子眼,就双双脚踏彩云,一路唱着歌子飞走了。谷雨想唤,不出音,想追,亦身不能动,脚不能移的,仿佛被无数根蛛丝般的玻璃绳捆住了手脚,只好用脚使劲蹬着,直挣得通身虚汗淋淋……正挣扎着,被人一把拽醒了。“谷雨子,魔障了?”端午晃着她的肩臂,一迭声地问。谷雨嘤嘤哭了,“点眼了,小布头飞走了!”边说边下意识地捂住身侧的布兜兜,左右不肯松开。端午满脸狐疑,伸出指头去她胳肢窝里捅了一下,小姊妹俩旋即在床上滚成一团。正嚷闹间,屋外传来母亲匆匆赶回的脚步声,“鬼丫头吵啥,都不上学了?”
正欲回话,屋子里訇然大亮,原来是通电了!
灯光下,端午将布偶拿在手里,口中不期然咦了一声。谷雨偱声望去,发现它们的眼睛,竟然像水滴似的掉了下来。这才明白,原来是一场梦!小布孩哭了,该是舍不得离开吧?想到这里,谷雨将布偶一把搂在怀里,眼泪唰唰落了下来。端午笑嘻嘻地,说:“谷雨呀,你整天蹙个眉,想啥呢?”转身端出针线匣,很快又将烛珠儿穿缀好了。
谷雨瞪大眼睛,看到两只小布孩通身鲜活地站在那里,眼珠子水灵灵的,像是随时要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