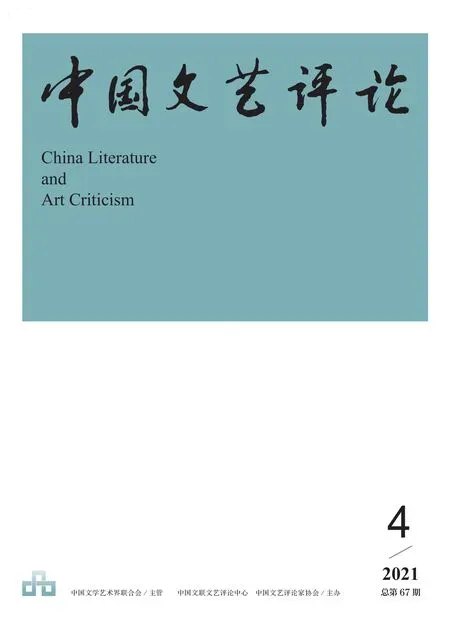镜与灯:从三部戏剧新作出发的反思
傅 谨
美国知名文学批评家艾布拉姆斯的名著《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形象地用“镜”与“灯”比喻两大类型的文艺作品,所揭示的就是文艺作品与所表现对象的两种关系。无论是处理历史题材或者现实题材,文艺作品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借用这两个比喻。本文不是试图阐释艾布拉姆斯的精彩比喻,只想借用这两个词汇,讨论最近接触的三部戏剧新作。
京剧《文明太后》的历史改写
京剧《文明太后》表现北魏时期实际执政达二十多年的冯氏太后的政治与社会贡献,在这位身后被谥称“文明太后”的历史上少见的女性政治强人执政时期,北魏社会发展迅速,为此后的隋王朝乃至大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当然是可以通过戏曲形式表现得很有开掘价值的历史人物。
其实,这位文明太后人生经历之丰富复杂,为戏剧家提供了与她的政绩同样丰富、甚至更为丰富的材料。北魏是鲜卑人入主中原后建立的政权,冯氏太后出身于北燕王室,北燕亡于北魏后,其父因故被杀,她被没入掖庭,无意中成为太子青梅竹马的童年玩伴。在她12岁那年,太子拓跋濬登基,是为北魏文成帝,她立刻被新帝选为贵人,三年后更被立为皇后。但他们的婚姻生活并不长久,文成帝25岁就英年早逝,此时冯氏皇后只有24岁。史载她与文成帝拓跋濬感情十分和睦,在按北魏习俗举行文成帝遗物焚化仪式时,她突然纵身火海自焚,幸好被左右救出。她做了将近10年的皇后,在此期间并不限于关注后宫事务,相反,她早早就开始逐渐参与政事,发挥她的执政能量,而皇后期间的历练,对她此后的政治生涯产生深刻影响。文成帝之后拓跋弘继位,世称献文帝,尊冯氏为太后。拓跋弘虽然并非冯氏所出,却是由冯氏抚养长大。这位少年皇帝此时只有12岁,实际大权难免落入前朝留下的亲贵们手中。这对孤儿寡母看似懦弱无助,然而冯太后很快便显示出她超人的政治智慧与对北魏最高权力强大的操控能力。史载,她运筹帷幄,设计诛杀了在朝中权势熏天的丞相乙浑,并临朝亲政。尽管冯氏太后一年半后就归政于献文帝,但她既然有能力从权臣手里抢夺回江山,就不会真的完全放手让这位少年皇帝掌控国家权力。所以母子关系逐渐趋于紧张,但冲突的触发点却不在国事而在家事。拓跋弘对冯太后拥有众多宠臣男侍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尤其是太后经常让男宠中的杰出者进入政坛,这更激起他的反感。拓跋弘执政五年后,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诛杀了冯太后最亲近的男宠李弈,并残忍地灭了他全族,且故意重用告发李弈的大臣,母子之间的冲突因此激化。他们这次剧烈冲突的结果,是献文帝借口欲潜心修道宣布退位,让还不足五岁的太子拓跋宏即位,是为孝文帝。《魏书》中称“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当非空穴来风,只有18岁的拓跋弘成了太上皇,他大概是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18岁的太上皇自然不甘寂寞,皇帝年幼,拓跋弘虽然名义上退了位,却依然手握着部分权力,尤其是兵权。他率领大军四处征战,一点都不像是个修道的人,当然也不会真的完全放弃行政权力。数年后,母子间的矛盾再度爆发,冯氏设计在献文帝前来请谒时将他拿下,几天后传出献文帝暴毙于宫中的消息,他究竟是自杀还是被冯氏毒杀,已经无可考证,历史进程中可见的结果就是冯氏再度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这一次她再不肯放权了,而且她对这位当皇帝的小孙子也非常严苛,直到她49岁那年生命终结。
京剧《文明太后》当然不是这样写的。京剧《文明太后》从禁田之争开始,拓跋弘按祖例将平城一带划作禁田赏给功臣,正在众位将领驱逐百姓时,中书令弈冲挺身而出,力阻皇帝将田地分封给诸贵族,一下就把摄政太后与献文帝母子间的分歧推到了前台。这场冲突因宫中小皇子诞生之喜而中止,弈冲侥幸逃脱未被诛杀,而拓跋弘在朝中奸臣的唆使下,矫令解除禁田,骗取冯氏太后的信任,归政罢朝。搬开太后这座大山后,他得以独揽朝政。弈冲在相州实施均田,风波再起,终于被下狱诛杀,他的冤死促使冯氏太后下决心再度临朝摄政并继续推动均田。太上皇拓跋弘则被外派抗击刘宋大军的进攻,等到他打了胜仗归来,正欲率兵兴师问太后之罪,却被太后骗进宫中,一番母子情深的回忆之后,太后骗拓跋弘饮下毒酒身亡。从此,北魏开始全面实施均田之策,全剧的冲突亦因拓跋弘之死而终结。
京剧《文明太后》把禁田与均田之争作为全剧贯穿始终的有关执政方针的核心冲突,并因此引出冯氏太后(编剧为她取了名字“冯雁”)和拓跋弘之间的尖锐矛盾。这是为了将文明太后和拓跋弘之间的矛盾描写成一方“心在民间不在朝堂”,一方“一心只为权贵想”,两相对立,谁是谁非一清二楚。冯太后的形象因此显得高大伟岸,她的对立面则显得既坏又蠢。国家最高权力于她如囊中之物,她想临朝摄政就可以临朝摄政,而气势汹汹前来兴师问罪的太上皇,被她轻而易举地骗到宫里,还事先被他的幼子收了宝剑。
京剧《文明太后》除了冯太后之外,还塑造了一位为国为民而勇于和权贵豪门斗争的二号英雄人物弈冲,其历史原型差不多就是历史中的冯太后平生第一重要的男宠李弈。第一场皇帝要划禁田时,只听一声“住手!”中书令弈冲凛然上场,力阻皇帝分封之举,营造了该剧第一个冲突;第三场,已经被贬为相州刺史的弈冲,前来力劝太后重新摄政。有关他们的私事,《文明太后》显然是要回避的,弈冲盼太后重新摄政遭拒后声称要归隐,太后摒退同行的御史中尉,对他情真意切地唱道:“你忍心离我去天涯遁隐,全不念二十载君臣们心意相通暖意融融……”算是一点含蓄的表示,但也仅是一点暧昧,点到即止。他为报太后之恩,立誓要实施均田之策(然而他此时只是地方官),壮志未酬,刚离开太后宫邸即被关入大牢。太后独自夤夜探监,弈冲通过此时的大段唱腔,简直成为胸怀大志、为国为民、公而忘私的道德圣人。即便太后已经还政,国家大事早由儿子掌管,她愁的还是“国有疑难问谁人……扶社稷不靠弈冲靠何人?”这无非还是为了衬托弈冲之重要,北魏朝所有良臣的善举似乎都被浓缩于他一身,尽管他在剧中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作为。
我不会指责编剧是在“篡改”历史,历史只是戏剧的素材,戏剧家有权按自己的想象与理解重构历史。如果要让古代题材戏剧作品完全按史著编撰(即使是所谓“大事不虚”),那就必然导致戏剧的窒息;戏剧始终是戏剧家体现其主体动机的自觉创作,而正由于编剧可以用历史作为材料,充分发挥其想象力,因此当编剧有意识地改写历史时,就可以从中发现戏剧家的思想情感取向。我相信《文明太后》的编剧对史书如何描写冯氏太后比任何人都熟悉,因此真正需要讨论的是编剧改写历史的动机,比如说作者有意识地改变了冯氏太后一生的时间线,将她前一次执政仅一年半的摄政改为十多年的时间,这当然是为了照应剧中拓跋弘的年龄;将她两次亲政的时间间隔从五年改为八年,是为了让新皇不至于显得太年幼;但是把冯氏太后和那位显然是按她的男宠们的经历浓缩而成的弈冲,写得如此完美与高大,尤其是把文明太后和弈冲描写成政治与道德两大领域的两朵“白莲花”,徒有爱国爱民的满腔热情,却善良得对宫廷斗争的血雨腥风没有丝毫警觉,则在根本上破坏了这一题材最有可能生发的历史与人性内涵。
文明太后充满争议的一生原本是极佳的戏剧题材。冯氏前后执政时间超过20年,有关她一生的功过,如果仅以简单的是非加以评价,简直是对这一难得的好题材的糟践。她执政能力极强,却也留下杀戮无度的残暴名声;她与文成帝感情甚笃,但寡居之后男宠不断,且多位美貌男子因她的宠幸而获高官厚禄,远远超出了私德的范畴。冯氏太后在魏国推行的均田制,对北魏的发展虽然并不像剧中所写那么重要,但也不失为一项固本安邦的良策。可惜的是,京剧《文明太后》的人物设置,就这样简单地分为“好”和“坏”两端,一面是文明太后、弈冲等,他们洁白无暇,所言所行始终大义凛然;另一面是拓跋弘、京兆王,他们祸乱朝纲,所言所行件件祸国殃民。
在写出文明太后历史上原本就有的复杂性和将她写成一位单纯的“好太后”这两种创作取向中,作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正是这样的选择让该剧的主人公变成了政治上的低能儿,冯氏太后如此,顺便也贬低了她的对手——拓跋弘也是如此。冯太后既然两度亲政,必然经历过与权贵们九死一生的恶斗,如何不知道放弃权力后将遭到反噬,怎么会那么容易就被拓跋弘一句“解除禁田”蒙住了(剧中冯太后还大大夸赞了拓跋弘一阵,真是讽刺);归政后的数年,她对天下大事居然毫不知晓,还需要弈冲前来告知她皇帝允诺解除的禁田实际上又恢复了(全剧的前半段,她和弈冲忧虑的似乎唯有“禁田”这一件事),而且面对弈冲给她提出的重新摄政之劝告,她还十分忌惮于皇帝的“羽翼已丰,骄悍成性”。当拓跋弘亲政后,弈冲立刻被贬为相州刺史,仅此一桩,英明的太后难道还不明白危机四伏吗?至于太后最后决意重新摄政,居然是因为一个在门后偷听的狱卒去联络八王;那时的太上皇拓跋弘在前线率军和刘宋打仗,后方的太皇太后居然在这样的时机下,强行没收前方将领的禁田,毫无政治家的审时度势之策,反倒怪罪他们“以怨报德”;而为了废太后而杀回平城的拓跋弘,居然就轻轻松松地被太后骗进了宫。
京剧《文明太后》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设置并不难找到其渊源,在故事情节上,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20世纪60年代最为流行的历史叙事模式,在政治理念上有“遵循祖制”和“变法改制”的冲突,在施政实践中则是支持豪强兼并土地与将田地分给农民之间的分歧;在人物设置上,它深受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且在“样板戏”模式中达到顶峰的区分“正”“反”两类人物形象的理论影响。尽管文明太后有历史原型,而且史书中有关她的叙述褒贬兼具,但在编剧眼里所有那些有可能损及冯氏太后作为“正面人物”的历史事件和细节都被舍弃或修改了,剩下的就只有一个“好太后”。这样写历史真的有意思吗?
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的人物纸片化再造
郁达夫是现代文学领域中关注度很高的作家之一,他在东京留学期间开始涉猎文学创作,1921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沉沦》,让他一步踏入著名作家行列。郁达夫的小说、散文一直深受读者喜爱,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创作中最有成就的大家之一;而他作品题材与内容的独特性,他对自己生活以及情感中的阴暗面惊人的坦诚,则构成了其作品之魅力的重要部分。有关郁达夫的文学风格,他的生活包括情爱,还有他的政治立场等,在现代文学领域早有大量研究,除了他最终在南洋不幸身亡的原因还留有诸多疑点,他生活及文学中的大部分问题都有定论。而且更由于他的文学写作深受日本“私小说”流派的影响,他的情感世界乃至心理空间对读者而言基本上是敞开的,所以认识与理解郁达夫,并不算太困难。
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写了一位令人感到陌生的郁达夫。这部话剧从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展开,通过日本“宪政之神”尾崎行雄教授用“清国”指称中国留学生引出争议,更由于他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激起郁达夫反驳并逼其当面向众学生道歉。《郁达夫•天真之笔》这个“战狼”式的开头,为这位文学青年在该剧中的舞台表现打下了底色。从戏剧结构的角度看,这个开头和其后的大量描写之间形成有机的呼应,确实,这部话剧新作所描写和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和日本激烈的民族冲突中,始终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抗日英雄郁达夫。
我丝毫不怀疑编导有权按自己的理解表现郁达夫,话剧不满足于此前文学研究界的学者们将郁达夫的文学形象定格为感伤、颓废的基调,更不满足于历史材料以及后人的研究揭示的郁达夫的浪子形象,它要让我们看到这个全新的、激情昂扬的、正气凛然的、永远带着满满“正能量”的郁达夫。如果说他还有什么缺点,那就是显得“天真”了一点,不,难道这不正是难能可贵的优点吗?
我相信编导对有关郁达夫的材料有足够多的掌握,对文学史家的研究与评价完全了解,这些材料用来完成一部两小时的戏剧作品当然是绰绰有余的。当我们在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里看到的戏剧主人公与现代史上那位著名作家的形象反差如此之大时,我并不认为这是因为编导在把“郁达夫”这三个字作为一个符号,仅仅将现代史上曾经有过的“郁达夫”这位著名作家作为其创作的灵感来源,在此前提上构筑一部完全游离于其人物原型的戏剧作品;而且我相信作者的意图并不只是为写一篇翻案文章,她大约是希望通过与学者们的严肃对话,提出有关郁达夫的文学和人生的另一种描述和评价。我想编导是希望通过对这个现代作家人生的重新梳理,让我们看到郁达夫生命中的一个特殊侧面,那就是平常并不为人们所关注,甚至多数场合都被人们所忽视的侧面,编导并不希望观众将这位郁达夫看成是纯粹的戏剧人物,更希望人们通过这部作品恍然大悟——哦,原来郁达夫似乎早已定型了的形象中,还有不为人知的这个立面。所以,《郁达夫•天真之笔》是对郁达夫这位著名作家人生的重新书写与对他个性的重新阐释,是在努力揭示并强化郁达夫人生的这个侧面;为了更清晰地展现这样的目标,仿佛是为借助历史资料佐证并支撑该剧所描写的郁达夫的真实可信,剧本刻意抄录了郁达夫本人许多回忆他过往的文字,使该剧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接近于文献剧的面貌。
但是从这部话剧的呈现看,文献剧只是风格化的外壳,作者显然无意用文献剧的方式表现郁达夫的人生本色,相反,该剧更重要的努力,是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将郁达夫描写成一位抗日爱国的英雄。而有了“革命烈士”这样的定位,整部戏就成为努力按照有关“革命烈士”的定义来表现郁达夫的一场艰难跋涉。编导显然是熟悉郁达夫的,所以他们比外人更知道要将现代史记忆中有关郁达夫的那些灰暗的记忆抹去,但要让郁达夫在观众面前只展开他如此单一的向度是如此困难,以致该剧用了绝大部分篇幅帮他“洗白”,剧中把鲁迅、郁达夫、沈从文这样三个截然有别的人凑在一起,专门用一场戏演绎他们之间亲如异姓兄弟般的相互理解与接济。而这煽情的桥段只是一个开端,从这里开始,《郁达夫•天真之笔》娓娓道来,渐次叙述了他是一个多么负责任的儿子、丈夫和父亲,尤其是一位至情至性的恋人;郁达夫和他日本房东的女儿隆子的关系,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他处处留情的风流浪子形象被赋予许多堂而皇之的理由,他独自抛下在北平的妻儿出走,并且在和孙荃的婚姻存续期间疯狂追求王映霞,这在剧中被披上一层追求幸福和浪漫的温情的纱幕;他每一段感情和婚姻都是如此美好,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一笔,那就是必须指出亲人们和世人们对他的那些责难是多么的不近情理,等等。
郁达夫是一位作家。作为一位著名作家,尤其是以坦荡地抒发青春时期的灰暗心理为标识的作家,郁达夫一生写了很多作品。然而在《郁达夫•天真之笔》里,用剧中郁达夫第一位恋人隆子的话说,他是一直把笔当作“武器”的,如剧中的鲁迅所说,他“拿起笔冲上去”了,连他去南洋也变成了因准确判断了“战火迟早要烧出国门”而“提早占领海外文艺阵地”,似乎他从未写下那些以宣泄苦闷为主要内容、颓废而感伤、有时甚至充溢着略显夸张的厌世情调的作品——而郁达夫之所以成名并广受欢迎,正是由于他这些与该剧所表现的内容格格不入的作品及其风格。
我相信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和京剧《文明太后》的编剧一样熟悉其所表现的对象,然而又都在“塑造正面人物”这一动机的引导下,有意识地改变戏剧人物。区别在于《文明太后》的作者用的是虚构,而《郁达夫•天真之笔》的作者用的是辩白。在真实的郁达夫的一生中切割出和该剧主题相关的部分,并通过寻找各种从勉强到牵强的理由——包括“天真”这个被用到剧名中的暧昧词汇——为主人公的行为和情感辩护,郁达夫终于被这所有的矫饰压成了薄如脆纸的一层。忽略舞台表演的声嘶力竭,从动机与结果的吻合度看,经过这样的特殊处理后,观众或许看到了郁达夫“烈士”这扁平的一面,所以编导当然是可以获得剧场反馈的,然而,戏剧真的需要或应该如此处理人物吗?
中国现代戏剧曾经走过一段弯路,在“样板戏”盛行的那个年代,不只是对社会的认识与理解偏狭到了极点,还因为简单机械地将“人”划分为“正面”和“反面”两大类,发展出一整套纯化人物的戏剧手法,将“正面人物”塑造成从道德、情感,直到日常生活中所有细微末节都无比完美的“高大全”式的人物。而依托改革开放,用更像“人”的方式表现戏剧人物的丰富性,才不再是禁忌。值得玩味的是,郁达夫之所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正是由于他的文字突破了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他运用他的笔触,真诚地暴露出自己内心深处诸多与世俗观念相冲突却又十分真实的一面,用自己的社会声誉为祭品,将中国文学带入一个新的境界。而郁达夫自己,唯其真实,所以并不高大,更决非所谓的道德圣人。遗憾的是,《郁达夫•天真之笔》选择了一条和作品主人公的原型截然相反的创作路径,我想郁达夫在天之灵如果看到这部话剧,他一定会感慨时光倒流,不仅倒流回到改革开放之前,而且倒流回到新文化运动之前,他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完全白费,他的牺牲突然显得如此可笑。
湘剧《云阳壮歌》的贞洁观
湘剧《云阳壮歌》改编自歌剧《玉姑》,因无缘欣赏《玉姑》的歌剧版,所以无从得知湘剧文本与歌剧间的异同,因此,这里所讨论的内容仅限于湘剧版。
在20世纪30年代,中央红军撤离湘赣边界时大批当地青年加入红军,湘剧《云阳壮歌》的女主人公玉姑就是当时参军的云阳青年春牛留在家乡的妻子。玉姑还有位与她相映衬的好姐妹霞姑,她的丈夫秋林和春牛一起参军,从春牛和秋林离开云阳直到1949年解放的15年里,她们相互陪伴着经历了漫长的等待。苦难以不同的方式降临到她们身上,作为红军家属,霞姑在白匪军追捕过程中被残忍地熏瞎了双眼,而玉姑经历的苦难更具精神性,春牛离开时玉姑已有身孕,她为躲避白匪军逃到外乡,然而她又回到云阳,只不过她带回了一个男人,还有个女儿。他们三人在家乡组成一个新的家庭,于是在这15年里,她备受村民的嘲弄、奚落和疏远。
在这15年里,玉姑和霞姑都因身为红军家属经历苦难,但村民给予她们的是截然不同的评价,正是这种强烈反差构成这部湘剧新作的核心内容。该剧从第二场就开始渲染她们殊异的情境——村民们为霞姑送来“光荣军属”的大红牌匾,而秋林也将要衣锦还乡;玉姑则无缘享受这份荣光,因为她既已改嫁,在村民眼里她完全不配“光荣军属”的称号。
湘剧《云阳壮歌》不是写两位红军家属在长达15年的艰困环境下矢志不移的等待,玉姑和霞姑15年的等待只是其铺垫或前戏,该剧主要情节是新中国成立后,她们15年的等待终于盼来光明,却因此陷入更暗黑的夜。诚然,她们的痛苦并不一样,霞姑的痛苦,是因为秋林回乡之前顺路参加了剿匪,他外出15年身经百战安然无恙,却在家门口剿匪时意外牺牲;玉姑的痛苦在于,她等待了15年的刘春牛确实从部队请假回来和她团圆了,她却无法安顿已经在一起生活了15年的男人铁保。预期中的幸福突然发生逆转,这是戏剧性表达教科书式的范例,但是这里更令人关注的不是戏剧技巧,而是其情感内容。
当春牛满怀喜悦地回到家乡,终于和分离15年的妻子重逢时,玉姑却不让他进家门。原本应该因亲人回乡而兴奋莫名的玉姑,却因春牛回乡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她很难在铁保和春牛之间做出抉择。因为在15年前,春牛参加红军离乡后,在白匪军抓捕红军家属的关键时刻,铁保挺身而出舍命救了她们母女,并且在此后的日子里,为她们提供了生活的支撑。按照剧情的发展,她当年之所以要从江西回云阳老家,就是由于曾经有过要等春牛回来的这份承诺,但是15年后,当这份期盼果然可以变为现实时,她却突然意识到,物是人非,既有铁保在,当年的承诺竟然无法轻易和简单地兑现。
既然春牛杳无音信地离家15年,归来后发现玉姑已经组成新家庭,并且有了女儿,他纵然心有失落,实际上他并没有太多的权力责怪玉姑,更不能因为自己成了打下江山的胜利者,就可以让孤身留在家乡的妻子一直为他守节,更何况在这漫长的等待过程中,后者实际上是看不到希望的。但是春牛并不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之所以不能接受,是因为在春牛的预期中,曾经给了他承诺的玉姑原本应该为他独守的,该剧始终着力渲染的村民们对玉姑的冷言冷语,只不过是春牛此时心声的放大与回响。戏里春牛与玉姑矛盾的焦点,是在他们分离的这15年里,玉姑是否已经“变心”了。春牛试图相信玉姑并没有“变心”,即便看到她已经“改嫁”,却还在为她设想种种不得已的理由,然而在现实面前,他的这一信念还是不可阻挡地动摇了,而他的情感反应又成为加剧玉姑之痛苦的动力。
那么,湘剧《云阳壮歌》为什么要编织这样一个故事呢?我相信作者是有意识地赋予玉姑姓名中这个“玉”字以内涵的,其意就是为了突出主人公与“玉”一样洁白无瑕的品质;春牛临走之前和玉姑的约定以他们各自手里的玉镯为见证,又进一步强化了剧中“玉”的内涵。“玉”是该剧之主题的物化象征,其中含义并不难解读。《云阳壮歌》的编剧很擅长运用互文,在他的笔下秋林和春牛不仅在姓名上是相互对应的,行为模式也具有强烈的相互映衬的效果。秋林参军15年,始终把临走前霞姑给他做的一双布鞋带在身边舍不得穿,这就是春牛15年一直带在身边的玉姑送给他的那只玉镯的对应物。它们的戏剧功能简单明了,秋林是把这双鞋子看成与霞姑间承诺之象征的,尽管不如玉镯那样具有信物的质地。作者通过这两件信物表达了两位男人对爱情诺言的信守,就是为了借以反衬玉姑之不能“守”。在玉姑的生活空间里同样如此,无论春牛还是村民,即便是戏里对玉姑最为关爱的元婆,都认为她并没有“守”住,“变”了心,而无法接受她。春牛的痛苦以及村民的嘲讽,尽管是出于误解,但在本质上是对玉姑和另外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变相谴责。假如这些都不是误会,那么,在他们眼里丧失了贞节的玉姑岂非命定要落入万劫不复之境地?
而玉姑和铁保的关系,用另一种特殊的方式渲染了“守”的价值。在《云阳壮歌》的情节设置里,构成解放后玉姑和春牛面对的特殊情境的前史,是玉姑在逃避白狗子对红军家属的追捕时铁保这位好心男人舍命救了她,铁保如何救她的情节是一笔带过的,这不是该剧重心,重心是她和铁保回到云阳后的奇异关系。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铁保和玉姑以及她和春牛的女儿盼盼共同生活,虽似夫妻一样生活并共同抚育盼盼,却并无夫妻之实。重点在于这15年里,玉姑对铁保只有感激之情,且从未有两性之间的那种情愫,玉姑等待春牛回来的诺言,则成为阻挠他们组成真正家庭、成为一对“真”夫妻的理由。正因为他们之间保持这样特殊的关系,玉姑还阻止了唯一知道真相的霞姑,不让她为之辩白与解释,宁愿生活在村民们的误解之中,“白天掩面避人走,深夜里偷偷把泪淌”。既然事实不为人们所知,而且当事人还在有力地阻止人们知晓真相,仿佛一切都是等着春牛回来撕开这层尴尬的帷幕,让玉姑陷入更进一步的道德困境。
这个故事一点也没有新意,湘剧《云阳壮歌》的文本,只是传统戏《武家坡》《汾河湾》的翻版,只不过作者把女主人公放到了一个比王宝钏或柳迎春更极端与残酷的环境里。她不只是在苦苦“守”着那个前途未卜的丈夫,她的身边还有一位一起生活的男人。她一面接受铁保的帮助,一面又盼着春牛回来,而铁保则成为她备受熬煎的另一把柴火。
诚然,如何设置戏剧情节是编剧的权力,但我们细读一部戏剧作品,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努力从剧本的情节安排设置中发现编剧的动机,包括其情感动机。如果不是如此痴迷于要确保女主人公的冰清玉洁,玉姑未必不可以和铁保做真正的夫妻。假如故事是这样的,那么,春牛回来后玉姑同样是纠结的,然而此时的纠结,就与她在《云阳壮歌》里的心理活动截然不同,因为这样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就不会只是一个有关贞洁的故事。
我并不想简单化地批评《云阳壮歌》情节设置的人为和刻意,让主人公的悲惨和内心挣扎丧失了可信度;这里真正重要的,是作者完全无意于站在玉姑一边去控诉村民们对她的精神凌辱;他所想表达的情感取向恰恰与之相反,那些村民——包括声称最心疼玉姑的元婆在内都是作者的工具;而作者还不满足于通过这些村民表达对玉姑的谴责,他还让玉姑自己也与那些凌辱她的村民站在一起,她隐瞒真相的行为就像是一种自虐。这些村民如此苛刻地对待一位弱女子,直到发现“误解”了她之后,却只有轻飘飘地说一声“错怪”。他们从未因为对这位弱女子缺乏起码的同情心而感到歉疚,只是遗憾于对她的“错怪”,假如他们并没有“错怪”,这些歧视性的行为和语言暴力,就有足够正当性了吗?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能把湘剧《云阳壮歌》看成是一部红色题材戏剧作品,它只有一个红色题材的外壳,其戏剧内核是在革命胜利后主人公面临的人伦困境。而导致这一人伦困境的,并不是、或主要不是铁保对玉姑以及对她和春牛的女儿的救助,而是玉姑要在这15年里“守”住贞洁。所以,编剧不会让这个故事里的玉姑和铁保在这15年共同生活中成为真正的夫妻,似乎这样玉姑在道德上就有了污点,就意味着她对诺言的背叛。湘剧《云阳壮歌》营造了一个近乎真空的戏剧情境,只是为了培育、彰显和维护一种迂腐的贞洁观。我并不反对弘扬忠孝节义这些传统美德,无论在哪个时代,一个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坚守贞节(而非贞洁)都是一种令人敬仰的操守。不过弘扬贞洁观念有个重要前提,那就是要把道德对人性的挑战约束在一定限度内,否则,效果就会适得其反——落入迂腐之道。
所谓“贞洁”,自古以来就是男权的宣言书。或许编剧会辩解,《云阳壮歌》里贞洁的要求不仅针对女性,作者对男性——春牛和铁保都具有同等重要的规范性。即便如此,也不会改变“贞洁”观念作为对人的身体强制性的占有和束缚这一特点。像这样一部以20世纪的革命者为主人公的戏剧,却在努力渲染和传递这样的价值观念,实在令人遗憾。然而这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作者在描写和表现《云阳壮歌》的众多正面人物形象时,正由于要高度注重于其形象的“纯净”,这些人的戏剧言行中不能有任何“有损于”其正面形象的成分——前提是在作者看来,村民们对玉姑的嘲讽不仅不是缺点,恰恰是“革命立场坚定”的爱憎分明。通过对正面人物的纯净化处理来塑造道德完人,这是四十多年前我们极为熟悉的理论话语,今天居然又找到了合适的土壤。这才是应该由《云阳壮歌》引发的思考。
结语
如艾布拉姆斯所说,从浪漫主义时代以来,文艺作品逐渐趋向于更自觉地表达艺术家的主观理念,“镜”与“灯”的关系,也就因此开始向后者倾斜。尽管20世纪中叶以来,从苏俄到中国的左翼文艺批评,在理论层面对现实主义的强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表面看来非常重视文艺作品作为“镜”的价值和意义;但在实际的文艺方针与指向上,更注重其“灯”的作用,总是希望通过艺术对历史和人生的改造实现其教化功能。这种基于主观理念的改造超越一定程度,艺术就不可避免地离现实的历史与人生越来越远。上述这三部戏剧作品,都因艺术家在历史与人生的改造过程中用力过猛导致作品显得虚假。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它们都在提醒戏剧家,文艺创作必须兼顾与平衡“镜”和“灯”的关系,才能让作品真实可信,无论历史题材、红色题材还是当代题材,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