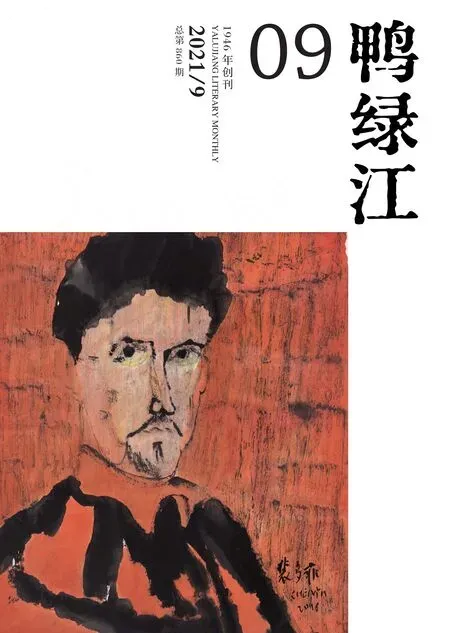用某种方式说出这些事情
——读《自传与公传》随想
赵 勇
2020年岁末的一天,刁斗兄突然加我微信。通过之后,他就连发几条语音,核心意思是他将为《鸭绿江》杂志主持一个栏目,每期推出一个他觉得有话可说的辽宁作家,想约我写稿。他说:这个董学仁吧,搞的是“一本书主义”,早就写出了“长河散文”,却基本上无人知晓,但我特别喜欢。然后,他就给我描述了一番他喜欢的理由:你看过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吗?看过卡内蒂的“自传三部曲”和夏多布里昂的《墓后回忆录》吗?董学仁的《自传与公传》,就类似于这种书。
此前,我对董学仁一无所知,没读过他的任何东西。但刁斗热情洋溢的一番推荐(我联想到了赵本山小品中的“忽悠”),让我拒绝都不好意思。不过,等他发来长达百万字的电子版,我还是被吓住了。写个几千字的文章,却要读这么多东西?而且我的状态,一直就是从头忙到脚,要写的文章排队等候,夹塞儿往往比较困难,这可让我如何是好?但我一跟他诉苦,他就微信道:“明白——但咱,有萨特的面子呀。当然你酌情,我不逼你,你体谅我,方欢喜。”
萨特的面子?此话怎讲?
这里面有故事。
那是2009年9月,《山西文学》主编鲁顺民折腾了一个笔会。那天我赶赴太原,与大部队会合并与聂尔同行。到了晋北河曲,方才发现刁斗也已驾到。聂尔与刁斗早已相熟,我则久闻其大名,却是第一次相见。三个月前,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把我们三个拴在了一起。于是一见面,刁斗就钻进我与聂尔的房间,细细聊起了前因后果。此前聂尔与我通气,让我对刁斗有了种《红灯记》里王连举的印象:叛徒?但听他解释,详述原委,我才明白了他当时的处境和具体的事态。
那天晚上,鲁顺民把聂尔、刁斗、王童和我拽出去喝茶。茶馆是晋北风味,我们好像是盘腿坐在一铺炕上,服务员不断倒茶续水,我们则在那里神吹海聊。聊到尽兴处,不知怎么就说起了萨特。我说前几年我对萨特用过功,萨特的书,写萨特的书,几乎一网打尽,尤其是列维那本《萨特的世纪》,像《存在与虚无》一样能当秤砣使,但我却读得血脉贲张。
听着我讲述,刁斗又坐不住了,他说:“《萨特的世纪》我读过,写得真他妈好!赵勇啊,咱们得为这本书握个手。”说着说着,他已从炕那边蹦跶过来。
这厮居然读过这本砖头厚的书?万里他乡遇故知!于是我也起身,两只手握在一起,像是演电影。因为已经进入剧情,我脑子里立刻蹦出一句台词:“照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啦?”刁斗反应快,立刻朗声答道:“许旅长的饲马副官胡标!”把三位观众看得哈哈大笑。
想起这个握手的梗,我说,啥也别说了,等我写完手头这篇就读。
萨特真有面子!
打开《自传与公传》第一部《迷失之地》,我一口气读将起来,然后是第二部《伤痛之年》。《伤痛之年》读得差不多时也快要“就地过年”了,这时候,我翻出半年前开了个头的东西,准备写成大块文章,而董学仁的书,仿佛也为我的文章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历史语境。我要写的齐大卫先生是195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我必须从头说起;董学仁则是从他在娘肚子里的1954年开始写自己的。这样,我写的人与他说的事就有了奇妙的交集。待这篇《档案内外的齐大卫》尘埃落定,我又打开了《狂乱之心》《深渊之火》《献祭之羊》《大地之门》……我看到的《自传与公传》,写到董学仁大学毕业那年,即1983年,此后则是一片空白。后面的年代他写了吗?他原来计划写到哪年?
应该先介绍一下他的写法。
实际上,读完第一部,我便意识到了董学仁的勃勃野心,也对他的写法基本门儿清。五十岁那年,他“突然决定把自己经历过的、看到听到和想到的事情记录下来,用非虚构文学的方式记录下来,给比我小的人、比我经历少的人、与我不是一个国度或者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来阅读”。但他不想写成小说,因为“当代中国小说的想象力太弱了”“我想来想去,至多可以像诺曼·梅勒《刽子手之歌》那样,写一些非虚构的东西。不同的是,他采访的是别人,我采访的是自己和我经过的时代。”然后他继续写道:
再想来想去,我将要写下的东西,是将我、我的家庭、我的城市、我的国度、我的世界融会在一起的编年史,是自传和公传。
过去,我们在研究汉代法制,乃至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时,往往认为,皇帝拥有最高立法权,皇帝金口玉言,能够用敕令修改法律规定,皇帝拥有最高司法审判权,可以御笔断罪,改变司法机关的案件审判结果。这些结论是否正确呢?笔者认为,汉代皇帝在立法领域和司法领域中的权力是有限而非无限的,有限皇权在汉代法制领域中有着显著表现。
“公传”一词可能在世界上是第一次被使用,只能从与自传相对的字面意义去理解。它们在我的记忆里时而融会,时而分离,它们是自由的,没有任何约束。
这是一种从没有过的文体。记得我对一位比我小了十多岁的外国作家说过,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文体,写的人多了,就成了文体。还有,人是写作的主导,文体是为作家服务的,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文体。让文体束缚的作家,无论如何,都算不上聪明的人。
需要稍做解释。董学仁出生于1955年,五十岁那年是2005年。也就是说从2005年起,他有了这个念头,然后开始了这次写作长旅。用什么文体呢?可以说是无文体或跨文体,也可以叫作非虚构。“非虚构小说”这个说法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此后又逐渐演变成“非虚构”。而国内大张旗鼓倡导“非虚构写作”是2010年,其标志是《人民文学》在当年开设了“非虚构”栏目。也就是说,在许多作家和刊物还没意识到“非虚构”的价值时,董学仁便已得风气之先,“弄潮儿向涛头立”了。然而,与一些因“非虚构”而暴得大名的作家相比,董学仁至今依然默默无闻,或者只是在很小的圈子里被人知晓。
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待遇?答案很简单,因为董学仁写得太真实了,真实到只能在《西湖》这种地方性刊物发表一些。
于是我只好说其写法。
自传都知道,是不需要解释的。在这部非虚构作品中,董学仁的自传应该是一条经线。因为自传的缘故,他才把需要呈现的年头上限定为1954年,而不是1949年或1942年;也是因为自传,才保证了这部作品“我”的存在——“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我”的体验与“我”的思考。然而,自传显然并非董学仁写作的主要目的,他的野心在于要为50年代以来的历史写出公传。于是,每年发生的、经过“我之思考”值得一写的大事小事,便进入了他所谓的公传序列。
公传中写什么呢?比如1955年,他有十三个子题目,其实就是做了十三篇文章。这些文章围绕着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展开。但是,他并不只写“国家大事”,而是记录了许多现在已被人遗忘,或者已被宏大叙事删除的趣事小事,例如,在1961年,他曾写有《战争,让女人与孩子走开》。如此看来,这部大书所谓的“公传”,实际上是重在揭示隐藏在历史皱褶中的细节。说实在话,无论是他写周扬还是胡风,都不可能写到李洁非《长歌沧桑——周扬论》《误读与被误读——透视胡风事件》的份上,但是他写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历史细节。
我就是冲着书里的细节,才读得津津有味的。
我原以为萨特会出现在1955年,因为那一年,萨特与其终身伴侣波伏瓦有过一次中国之行。但实际上,萨特却姗姗来迟。直到1964年,董学仁才专门写了一节《存在主义的萨特》。当然,即便是这一年写萨特,他也依然是从1955年写起的。他说,那一年萨特来访,中国方面派出一男一女两位作家接待他们。那两人“年岁比他们大,长相比他们老”。但因为双方都不熟悉对方的创作,他们只好谈美食,“法国的油封鸭、芝士焗明虾、紫菜酱煎法国鹅肝,中国的红烧肉、葱香鲫鱼脯、美味麻辣小龙虾。萨特的感觉是,不知道中国这一男一女写作水平高低,但谈起美食很有水平,好像不是访问中国著名作家,而是访问著名厨师”。
因为看重细节,我立刻对这一处的叙述产生了兴趣:这两位作家是谁呢?
我想到了赵树理和丁玲,但他们是萨特的同龄人,而且,“方向作家”赵树理后来虽然“失去了方向”,但他是1943年才真正开始文学创作的。我似乎在哪本书里看到过丁玲见过来访的萨特。为了把这个细节落到实处,我请教了年轻的萨特研究专家阎伟教授。他告诉我,从1955年9月起,萨特与波伏瓦来访中国45天,曾访问过沈阳四天,当时由作家陈学昭陪同。罗大冈留学过法国,期间亦曾陪同。但他明确指出,赵树理没见过萨特,我在《赵树理年谱》中也没查到相关记载。
于是,这两个作家是谁依然下落不明。
但在我看来,这一节内容依然重要,因为董学仁谈到了20世纪80年代存在主义给他带来的正面影响:“一是调整了社会观念,知道社会是一张巨大的网,我是其中的一个网结,反抗只能是局部的反抗;二是树立了个人英雄主义,因为存在先于本质,你选择了个人英雄主义,才能成为你个人的英雄。这种影响至今还在延续,我现在的写作,仍然是想要成为个人英雄的一种努力。”
我在前面说过我写出了《档案内外的齐大卫》。在齐大卫的档案里,最触动我的一份材料是《对我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检查与认识》,“个人英雄主义”伴随他走过二十多年的岁月。只是到了萨特和存在主义影响中国的年代,个体才终于从集体中成功剥离,个人英雄主义也才冲破集体英雄主义的重重迷雾,成为“80年代新一辈”的价值观念。可不可以这样说,董学仁写出的这部大书,实际上就是20世纪80年代价值观的重要遗产?
我倾向于这么认为。而且,董学仁不仅得益于萨特带来的价值观,他的写法似乎也高度吻合了萨特倡导的文学观和写作观。众所周知,萨特高举的是“介入文学”的大旗,但他同时在《什么是文学?》中也说过:“人们不是因为选择说出某些事情,而是因为选择用某种方式说出这些事情才成为作家的。”这句话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它甚至可以成为检测作家成色的试金石。而这里所谓的“某种方式”,既可以宽泛地理解为文学形式,也可以理解为某种文体。
很可能这就是董学仁写作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依靠个人英雄主义的支撑,他“介入”并且说出了许多事情,但这只能证明其勇敢;而当他以“非虚构”的方式如此讲究地说出这些事情时,事情的真相所袒露出来的本来面目,才具有了直指人心的效果。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他选择了小说的写作样式,其真实性,则完全可能大打折扣。我没想否认小说的真实性,但小说追求的是另一种真实,而那种意义上的真实,弄不好也容易变成伪饰。
但有趣的是,他在《读书有没有用处》一节的一开篇就写道:
有人说,凡是自传,都有小说的成分。被他这样一说,我一直当成长篇散文来写的这些文字,几乎就变成了长篇小说。
再想一想,他是对的,我的文字,描述了很多奇特、怪诞的事实,如果被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时代的人阅读,很容易被当成想象力丰富的虚构。
于是有必要谈谈真实。
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合招的研究生班中有位叫王玲的作家学员,我正在指导她做硕士学位论文。她的论题是“非虚构”写作中真实感的构建问题,目前已拿出初稿。在她看来,真实感的构建有三条途径:一,口述实录的倾诉;二,历史资料的打捞;三,现场介入的凸现。由此来看《自传与公传》的构建方式,我以为它主要是以第二种为主,却也有一和三相辅佐。当然,除此之外,它还有个人回忆开道或为其保驾护航。于是,这部作品中的真实感就呈交叉重叠之貌:历史资料是主角,口述实录、现场介入和个人回忆则陪伴其左右,它们相互指涉,相互印证,层层叠叠,密密麻麻。这样一来,真实感也就具有了厚度和力度。
但真实感只是一种主观感受,它能够成立,其前提是有真实这碗酒垫底。
那么,什么又是真实呢?这个问题说起来恐怕比较麻烦。以前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告诉我们,有两种真实,生活真实是其一,艺术真实为其二。按夏之放主编的《文学理论百题》的说法:“所谓生活真实,是指实际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人和事,即生活事实。而艺术真实则是指文学作品通过具体形象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的本质意义。艺术真实来源于生活真实,然而生活不等于艺术,生活真实也不就是艺术真实。”为了说明艺术真实优于生活真实,教科书往往会举例道:《白毛女》的“生活真实”原本不过是一个“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但经过周扬指导,特别是经过贺敬之等同志的再创作,立刻就揭示出了这个传说中所蕴含的生活本质——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其实,艺术真实在我看来并无多大问题,而且确实也存在着一种名为艺术真实的真实。为什么恩格斯认为《人间喜剧》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为什么他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都要多”?原因在于巴氏奉行批判现实主义,把艺术真实做到了极致。但问题是,从苏联过来的现实主义根本无法与批判现实主义同日而语。所以在我们的语境里,艺术真实成了“两结合”“三突出”“高大全”和“红光亮”。而此时回到生活真实、历史真实,就是对异化了的艺术真实的深度拒绝。我以为,这才是“非虚构”的主要价值,也应该是董学仁之所以如此打造他笔下真实的原初动机。
我还看到董学仁说,如何挑选合适的叙述语言来写这部《自传与公传》,曾经让他颇费琢磨,因为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情形下,语言里都“充满了矫饰的空洞”,所以,我也确实看到了董学仁在语言层面的努力。汪曾祺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我前面提及的作家聂尔说过:“写散文就是写句子。”他们也都是汉语写作的高手。董学仁的叙述语言舒展中有隐忍与克制,冷峻中又不乏幽他一默或调他一侃的机锋,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在我看来,假如他的语言能再讲究些更精致些,或许会有更好的阅读主要是体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