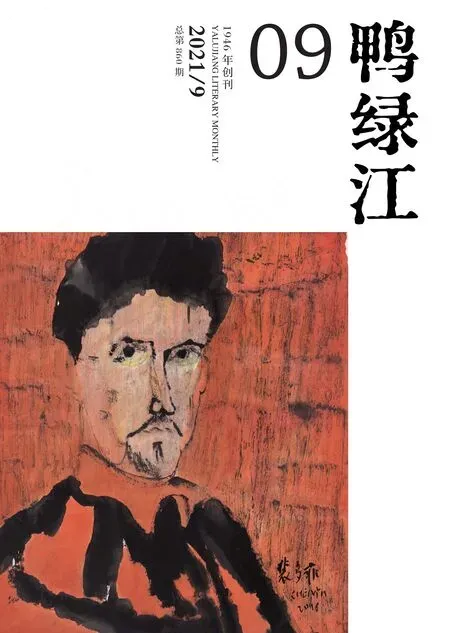邢东洋小小说五题
邢东洋
只说了几句话的房子
一个下着浓雾的早上,它跟我第一次打了声招呼。我是说我的房子——我居住,并在那里写字、读书、办公、会客的房子。
那天早上我起得比平时要早,这可能与前一晚的停电有关,我因此早早睡下。当然,白天也确实把我累坏了。你一定不想听是什么让我那么疲倦。算了吧,工作的事不值一提,总之那一夜恰好停电。起初我还有些不高兴,不停地咒骂供电公司和物业公司等所有我能想到的和停电这码事相关的部门。后来我意识到这样做毫无意义,与其苦等来电,还不如直接上床睡觉来得实在。如此繁忙的一天使我配得上这样的休息,我想,更重要的是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醒来后,我给自己倒了杯温水。我端着水杯站到窗前,发现所有我预想能够看到的景物全都被掩盖在白茫茫的雾气里面。当然,我的房子离公路不远,还能听到汽车奔驰而过的声音,不然我会以为我在梦中迷了路,来到一个我从未来过的地方。
我看看时间,发现比我想象得还要早,就决定出门到院子里转转。这是很少有的。我是说在这个时间。我很少早睡,因此对我来说早起通常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即使偶尔不得不勉为其难,也基本上是为了完成某项工作,在电脑上,在房间里。根本用不着出门。
我围着院子走了走,感觉还不错。我想起小时候我和妈妈在家中小院子里的事。儿时的事情总让人怀念,虽然我告诉自己这怀念并非理智,但总免不了去想想。谁说我们要一直保持理智呢?我打消了突然冒出来的要每天早起到院子里转转的念头。就在这时,我听到了它跟我打招呼的声音。
那声音怪怪的,像从很深的洞穴里传出来,并不空洞,很清晰,但像穿越了时空走了很远的路,我说不清楚。我记不得它是怎么说的。嗨?哈喽?阿牛哈塞哟?还是你好?总之我知道那是一句见面的开场白,客套话。我吓了一跳,既是被这声音的突然出现,也是被这声音古怪的质地。我四下里看,不知所以然,然后它又说话了:“在这儿,我是你的房子。”我听清了,但是不敢相信。我没出声,转过来面对着它。
我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没发现什么异常,或者是朋友跟我恶作剧的迹象。重要的是,我在这儿根本没什么朋友。客户?开玩笑!相信说话的真是我的房子?我有点不知所措了。
“相信我,我知道对你来说有点难以置信。”它又开始说话了,音量不大,但足够听清楚。
“相信你什么?”
“没什么,我只想说说话而已。”
好吧,我假设说话的家伙是我的房子,仅仅是假设,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没听别人说起过类似的事情。
“每所房子都会说话吗?”
“并不是所有,一部分吧。需要一定的条件。”
它犹豫了一会儿,并没说那“一定的条件”是什么,想必是不愿意讲出来吧。这可以理解。当然我也没有追问。些许的恐惧和一大堆混乱的问题围绕着我,我的思路不能沿着正确的轨迹行进下去了。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
我怎么说了这么一句,可笑。
有一阵子它没出声。我呆呆地站在那儿好久,有几分钟。我以为结束了,慢慢地往前走了几步,又往左边房子的侧门走了几步,然后才听见它的声音。
“没什么。”
声音的确是从房子传来的,我是说房子本身,而不是房子里的某一点。老实说那时我就已经相信了,说话的的确就是我的房子。
“和你相处很愉快。”
“我也是!”
这是它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后来我有点恍惚,回到房间里又睡了一会儿。接下来的工作我完成得还算可以,我想是忙碌帮我安稳度过了那一天。那天我没继续早睡,之后也再没有早睡。我尽量让自己保持之前的作息,然后那件事也再没发生。我承认我有点恐惧,但又不尽然。我曾想跟别人说一说,又觉得它应该不会愿意。一周之后这件事慢慢冷却下来,我也可以冷静地想想了。我试着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它,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我没有答案。也可以说我得出了很多答案,但并没有谁可以告诉我哪个答案是正确的。我把房子整个儿打理了一遍。我擦了每一扇窗户,修理了房顶漏水的地方,更换了室内破损的设施。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做这些时是怎么想的。是希望它感谢我还是仅仅不要恨我?是希望它再次跟说话还是不?有时候我觉得它是我的一匹马,被我驾驭;有时候我又觉得其实我是一个婴儿,被它照料。就是这样。
感觉不到饿的包小姐
感觉不到饿的包小姐并不是一个精瘦的柴火妞,反倒是有些胖。不过只是微胖而已,算不上大块头。就长相来说,她虽然不能被称作美女,但还过得去。“算是好看吧”,她给自己这样的评价。
与那些动辄嚷着减肥的女孩不同,包小姐很少纠结自己的身材,包括前些天坐公交车路过广场,看见那个身材超好的女孩时,她也仅仅羡慕了一下而已。当时那女孩几乎全裸,站在广场中央的雕像下面,惟妙惟肖地模仿雕像的动作。“这就是行为艺术吧?”坐在车厢里的包小姐想。
包小姐从来不知道饿是一种什么感觉,她没有感觉饥饿的能力。因为这种颇为与众不同的特质,别人会觉得,减肥对于包小姐来说,一定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不吃饭就可以了嘛。但事实上她自己心里清楚,那绝不能轻易尝试。
每次看到家里的三花小猫在食盆边奋力吃食的样子,包小姐都在心里暗暗忧虑:不要吃太多,要撑死的。包小姐不仅感觉不到饿,对于饱的感受也相当陌生。所以她对小猫的忧虑一部分是源于她自己的特质,还有另一部分是因为,小猫不完全是她自己的。
严格来说,小猫应该算是公司人事总监程先生寄养在她家里的。
有一次程先生随老总到外地招聘,要出差一周左右时间。下班后程先生找到她,说出差这段时间里,家里刚刚出生不久的一只小猫没人照料,很不放心,希望她可以帮忙。说这话时程先生出现在她家的门口,手里捧着的宠物包里面就装着它。包小姐当然没法拒绝。可是不久程先生出差回来,却一直也没把它取回去。那只小猫很自然就成为程先生接近包小姐的一个理由。
程先生曾对包小姐说,她身上有一种来自深海般的神秘气质。包小姐虽然不解其意,但心中着实暗爽了好几天。她当然看出了程先生对自己的好意。那么她对程先生的感觉呢?“还不错吧。”包小姐想,“虽然有点娘(哎呀,这个好烦人!),但那么整洁的男人还真少见呢!”他们试着交往起来。
可包小姐一直也没告诉程先生自己那个隐秘的特质。程先生每次来包小姐家总要带来很多普通女孩子都会喜欢的糖果零食什么的,这让包小姐很为难。因为身体特殊的原因,她必须严格保持自己饮食的平衡,甚至精细到几颗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都不可以多吃或少吃的程度。这听起来好像很残酷,但对包小姐来说,因为没有克制饥饿感的需要,所以要容易很多。不过平衡一旦打破,再想恢复就难了,搞不好还要像刚毕业时那样反反复复地调整,不是太胖就是太瘦,想想都受不了。
有好多次包小姐都准备好,马上要告诉程先生了,但结果还是没能说出口。她也不知道自己的顾虑是什么。其实不光程先生,所有朋友都不知道她这个秘密。她总是说不出口,就好像一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她所有的勇气就被本来应该属于她的饥饿感吸走,带到遥远的异次元空间。所以当她看见广场的行为艺术女孩时,潜意识里也被女孩的勇气打动。
那天,包小姐正要去太原街的某家西餐厅与程先生约会。交往了小半年,一块儿吃饭还是他们第一次。本来程先生是要去家里接她的,但临时接到老总电话耽误了时间。好在不用取消约会,不过他们只能兵分两路在餐厅会合了。
此刻我们已经知道,包小姐在路上被意外遇见的女孩的勇气所鼓舞。但她并没有注意到,就在她乘坐的公交车刚刚经过广场之后,很快就有管理者过来处理这一事件,驱散了女孩的艺术表演……那么包小姐在约会时到底会不会告诉程先生自己的秘密呢?
我想,还是交给包小姐自己来决定吧。
全世界都很小声
从我掉头发那天开始,我就留起了满脸的络腮胡子。这个样子多少让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尤其当我穿上那件黑色的毛料外套时,整个人简直像是电影里一个用警棍殴打犯人的邪恶的监狱看守。
不过我并不是一个凶神恶煞之人。我一个人安静地生活,从不制造打搅别人的噪声和气味。虽不与邻居来往,但偶尔碰见我也会点头致意。事实上,如果你能看见我每天提着一个精致的搪瓷水壶,在阳台上给那些植物仔细浇水的样子,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柔软的人。
我养花的爱好继承于母亲。两年前她去世,之后,我把她的植物全部搬回我的住处照料。或许是因为种植的天赋,又或许那些植物把我认作某种程度上的兄弟,总之那些原本萎靡的花草,在我这儿释放出惊人的生命力。我相信,在与我的相处中,它们获得了比在我母亲那儿更多的愉悦。
我很享受这种与花草为伴的生活。从它们身上,我学会用安静克制的态度与这喧闹的世界相处。这很像是一种修行。我时常幻想自己也是一株植物,每当这时,我便感觉周遭的世界安静下来,在我的吐纳间明灭。
在头发彻底掉光之前,我剃掉了它们。那一天夜里,红蓝相间的警灯不停地闪烁,窗外人声嘈杂。我在卫生间的镜子中发现,额头位置的发际线彻底失守,我的头顶像是海水被吸干后的海岸。我像除去花盆里的杂草一样处理掉我最后的头发,仿佛进行某种仪式一般。
我很快适应了没有头发的感觉,像在一个重力很小的无人星球漫步。我回到房间,把整个身体浸在沙发里面。这时突然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我确认没有人会来找我,我没理会。但敲门的声音越来越大,还有一个女人的哭喊声:“快给我开门,姓刘的,不然我明天就把你的丑事告诉你们杂志社的领导!”
她应该是搞错了,但是我没有起身开门去阻止她。我坐在沙发上,仿佛陷进柔软的泥土,生出无数须根。敲门的声音没有停止的迹象,我似乎能够隔着墙壁看见她,却越来越模糊。我感觉我的皮肤在一点点开裂,长出绿萝一样柔软的茎和窄小的墨绿色叶片。门外女人的哭喊声和敲门声像一根不停被抻长的细丝牵扯着我。我想如果我能扯断它,就可以安静地开花了吧。
你要哭到消失为止吗
记得昨晚入睡前最后一次看表时间是23:51。我调整闹钟,将响铃的时间定为早上的06:31。
每天调整闹钟时间,根据入睡前最后一次看表的时间来决定早上响铃的时间,是我的一个小习惯。没什么具体的原因,无非要让时间在这个区间里可以感觉上整齐些罢了,好像这样就可以把时间放在箱子里,拎起来。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定在06:31而不是06:51——那才是整整七个小时。又或者为什么不是06:21?0621的六个半小时也比0631的六小时四十分钟让我觉得要更牛些。我不知道是谁支配我最终选择了0631,也许是午夜的某个巨型卡车司机,也许是路灯操纵者,或者是喝闷酒的秃顶园艺师?
但是,其实在06:31我并没有起来。我把空调开得很大,以至于在七月这样的伏天夜里睡觉,我也总感到一阵阵地冷。
我问她:“这样好吗?她不置可否。”
也是,我怎么会问她呢。就在前一天的晚上,她站在窗前,对我说:“你注意到了吗?我们这里好像在缩小。”当时我正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地玩着手机,没搭理她。她转过身,屁股靠在窗台上,对我说:“我总觉得那些路过我们门前的卡车越来越大,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要大,就好像我们在一点点变小一样。”我说:“我怎么没注意到?”她说:“因为你没仔细观察过呗。也不明显啦,估计半个月能大个几厘米吧。”我问:“你怎么知道得那么具体?”她说:“那就是个比喻啦,就是说变化很小,但一直在持续。”
我想说,要是她的胸脯也能像那些卡车那样,一直变大就好了。不过我觉得她可能不愿意开这种玩笑,所以就没说。我说,我希望咱们能有一颗越来越大的冰镇西瓜……
然后她就哭了。
她哭得很小声,只是默默地流泪。可是她的眼泪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多得快把她自己流干了。我有些担忧,说:“别哭了,你看你都干成什么样了。”她继续哭。我说:“别哭了,你看你看,你越来越小了,连骨头都快没有了。”她还是继续哭。我把她扶起来,捧在手里,说:“你要哭到消失为止吗?”
关于死人的话题
有一个人死了。
老夏跟他说起这个人的死时,两个人正在按摩店里做足疗,脚泡在大木桶里。
他特别吃惊,问啥时候事?老夏说:“老长时间了,七八年了。”他问:“怎么死的?”老夏说:“脑出血,我听说。”他说:“多年轻啊,怎么脑袋还出血了呢。”
他叹了口气,接着说:“七八年,那也就三十出头呗。”老夏说:“可不是嘛。”他问:“你咋知道的呢?”老夏说:“他家一直住我妈家那院儿,我妈告诉我的。”他问:“有孩子没?结婚没?”老夏说:“没结婚。”他又叹了口气:“那还行,那还行。”
松过了肩膀,擦完脚,俩人躺在按摩床上,按照技师的要求调整了下位置,“这儿行不?”“再往下点。行不?”“好,好,这样就行。”然后俩人接着聊起来。
“他是咱们同学里第二个死掉的了。”
“第二个?还有谁没了?”
“那谁,那个……想不起来叫什么了,就初中跟刘洋处对象那个。”
“跟刘洋处对象?谁啊?”
“啊对,忘了,你初三就不念了,你不知道。”
“我也没听刘洋提过啊。”
“他俩就处一段,初中毕业就黄了。纯瞎扯,都没好好处。那女的高三没的,我听刘洋说的,高考体检,搁医院里,猝死,没抢救过来。”
“在医院都能没,那就是寿禄到了,命,老天爷定好了,躲不过去。”
“后来我道儿上看见过一回刘洋,个儿长起来了,比以前高不少,聊了一会儿,说起这事。刘洋说当时他没相信,还欠儿登地往人家打电话,结果电话通了,她妈接的,他说姨我找谁谁谁,那边一听哇哇就哭起来,说俺家那谁谁谁没了。”
“刘洋这事办得多少有点缺德。”
“也不能怪他,他说他也挺后悔,主要也真没信啊。这电话打完就信了。”
……以上内容是我听来的。
那天晚上,他去找老夏,把借来开了两天的车还回去。见面后两个人计划找我一块儿出来喝点,但打了好几个电话我都没接着,然后他俩也不想喝了,决定去洗个澡。可是车开半道,老夏突然想起来个事,他第二天还要早起出个白事。一个朋友家属,交通意外,情况比较特殊,得去殡仪馆帮忙抬一下,完事之后还得洗澡啊,所以就跟他商量,当天不去洗了,直接去按个摩得了。他倒是无所谓,咋的都行,然后俩人就改道去按摩了。关于死人的话题,也就是从那儿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