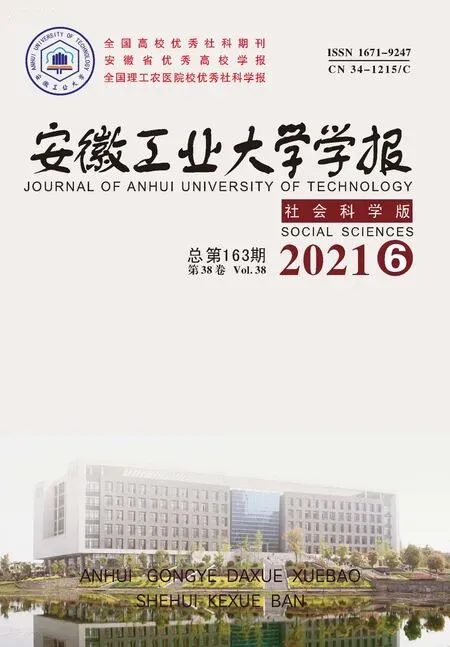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登高》中译者主体性对比分析研究
高红云,李翠翠,张 艳
(安徽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
一、引言
近年来,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新的翻译理论,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生态翻译学理论愈发成熟,研究范围也逐渐扩大。自2008年起,对《登高》英译本的研究从探讨其英译方法逐渐过渡到从多元视角进行译本的对比分析。但近年来,《登高》英译研究视角仍较为有限,主要有:路玉从识解理论视阈下探究杜甫《登高》在辖域与背景、视角、突显和详略度四个维度的英译差异;唐逸男从符号学视角探讨杜甫《登高》诗中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的得失;邓玉华从翻译美学视角对《登高》五种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探究《登高》诗中的叠音对仗美;郭红燕选取宾纳(Witter Bynner)、弗莱彻(W.J.B.Fletcher)、许渊冲三位学者《登高》英译本,从解构主义视角分析《登高》在延异、原文与译文以及多元翻译标准的体现。目前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登高》进行论述的文章较少。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杜甫的《登高》进行英译研究,以期在某种程度上能对中国古诗文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交流与传播。
中国古诗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语言维来看,中国古诗言简意赅,与现代汉语在表达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从文化维来看,中国古诗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浓缩,映射了一个时代的跌宕起伏,因此很难在目的语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来传达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交际维来看,中国古诗晦涩难懂,且蕴含作者的众多思想感情。对于译者而言,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准确传达原作者的思想情感,实现跨文化的交际目的,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因此译者需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维转换方法的基础上,准确传达原文内容信息,并进一步展现中国古诗文化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实现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目的。
随着译学思维的转变,翻译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生态翻译学这一学术研究范式也应运而生。生态翻译学是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的,涉及生态学和翻译学两个学科,是一种跨学科性质的交叉研究。该理论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产生的,利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将翻译环境与生态环境进行类比,以“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为翻译原则,形成三维转换方法,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选择,论证和构建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突出译者主体地位。
杜甫(712-770),字子美,是唐代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一生中经历了唐朝的兴盛与衰落。因此,诗人常借用笔墨来抒发内心情感,创作了大量诗文,悲叹国家动荡不安,哀叹百姓流离凄苦,惋叹个人凄惨遭遇。其《登高》一诗作于在夔州之时。全诗前四句写景,描写江边空旷寂寥的秋景,后四句抒情,感慨个人穷困潦倒、远在异乡以及国家动荡的悲痛之情。全诗在遣词造句、格律等方面极其严格规整,被称为“七律之冠”。
二、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译文质量的评判标准是整合适应选择度的高低,整合适应选择度的高低是译者产生译文时,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等多维度选择性适应的程度之和。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运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方法对翻译做出恰当的适应和选择,而这种翻译过程就是译者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被翻译生态环境因素所左右的选择活动,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文和原文产生冲突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翻译不是字对字、词对词的翻译,而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技术。译者需要在忠实原作内容的基础上,对译文做出恰当的适应与选择。如:当原文的意美、形美、音美或形似、神似等难以抉择时,译者就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避轻就重,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和技巧,使译文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语言习惯。
一部好的作品主要取决于译者的翻译水平,正可谓“成也译者, 败也译者”!但强调译者主体性时,会不会出现译者过度的主观创造呢?答案是并不会。因为成功的翻译取决于译者的能力,译者的能力有赖于译者发展,而译者的发展又基于译者的生存。同时在生态翻译学中,“适者生存”和“事后追惩”的法则无形中对译者的翻译行为产生制约。随着译者的自主权增大,译者的责任也相应增大,会受到自律、他律等多方面的制约。作为一个合格的译者,要想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亟需提高自我责任意识,做到严于律己,并不断提高自身的翻译水平。
三、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唐诗《登高》译者主体性分析
随着各国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世界文化得以发展与繁荣,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也日益增强。译者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交流的媒介,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译文的好坏取决于译者的文化功底和文学素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对译文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将以许渊冲、章学清和Witter Bynner三位学者的英译本为例,从生态翻译学的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方面分析译者主体性在唐诗《登高》中的体现。
(一)语言维的主体再现
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
例: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Living in times so hard, at frosted hair I pine;
Cast down by poverty, I have to give up wine.
(By Xu Yuanchong)
Weighed down in troubled times with care, I hate the growing hoary hair.
A broken heart, for cups I pine; Oh, if my health permitted wine.
(By Zhang Xueqing)
Ill fortune has laid a bitter frost on my temples.
Heart-ache and weariness are a thick dust in my wine.
(By Witter Bynner)
汉语是意合语言,英语是形合语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考虑这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运用增补、转化等方式对语言进行适应性选择与转换,实现两种语言的平衡。《登高》作为七言律诗的佳作,对仗工整而巧妙,字数简短而精炼,语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了更好地传达七言律诗的含义,三位译者都在其译文中加入了主语“I”,以第一人称视角来写,更能让读者身临其境,体会诗人的壮志难酬和孤独无依之感。其中三位译者都将“酒”译为“wine”。据维基百科解释,“wine is an alcoholic beverage”,本义指“葡萄酒”,而在汉语言文化中,诗人所喝的“酒”多为“粮食发酵而成的酒”。但据查证,在西方语言文化中,人们常常将“wine”作为“酒”的统称,而不是特指“葡萄酿制而成的酒”。因此,三位译者将“酒”译为“wine”,符合西方读者的认知习惯和语言表达习惯。
例:渚清沙白鸟飞回 。
Water so clear and beach so white, birds wheel and fly.
(By Xu Yuanchong)
The isle so drear, the sand so pale, the lingering gulls in circles sail.
(By Zhang Xueqing)
Birds are flying homeward over the clear lake and white sand.
(By Witter Bynner)
“渚清沙白鸟飞回”营造了一种孤独、荒凉之感。诗人苦闷忧郁的心情无处排遣,只能寄托给“鸟儿”,以此来表达诗人目前的悲惨处境,象征着诗人对自由、对亲情的渴望。“鸟飞回”一词在诗中释义为“鸟在急风中飞舞盘旋”。许渊冲先生将“鸟飞回”译为“birds wheel and fly”,将“盘旋”和“飞”两个动作并列,让人不禁想起“绕树三匝, 何枝可依”的凄凉感, 悲哀之情油然而生,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章学清先生和Witter Bynner分别译为“lingering gulls in circles sail”和“birds are flying homeward”,但笔者认为,该译法并不是很妥当。章学清先生将鸟译成“gull(鸥)”有待商榷。其次,Witter Bynner将“鸟飞回”译成了“birds are flying homeward”,释义为“飞回家”,但笔者认为鸟儿徘徊低旋,主要是为了表达“鸟”的孤独凄凉之感,且诗人用象征的修辞手法,看似写“鸟”实则写“人”。诗人漂泊在外无法回乡,“鸟儿”自然也无法回到家乡,因此,译文在意义上与原诗相矛盾。
(二)文化维的主体再现
所谓“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就需要译者充分考虑源语言与目标语之间的差异,并准确理解源语言文化的背景、内容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使译文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最大程度上传递原文内容的文化信息。
意象的诠释离不开文化背景的铺衬,“登高”一词,在中国人的意象中,往往代表着“登高望远,漂泊孤独,思念故乡”之意。诗人杜甫以《登高》为题,抒发自己对故乡的思念之情。许渊冲先生将《登高》译为“On the Height”, 章学清先生译为“An Ascent”,Witter Bynner译为 “A Long Climb”。三种译法,笔者更倾向于许渊冲先生的译文。不同的语言环境下,译者需要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需要将中国古诗所传达的涵义以及作者情感尽可能地让外国读者读懂并有所感触,因此“登高”所含的孤寂之感则需要表达出来。章学清先生的“An Ascent”和Witter Bynner的“A Long Climb”读起来都缺少一种“孤独”的韵味,而许渊冲先生的译文“On the Height”则略胜一筹。诗人身在高处之感更加形象,并且也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想进一步了解诗人接下来在高处的所作所为。笔者认为,也可以译成“Climbing the Height Alone”,“Climbing”一词表达了诗人远赴登高的艰辛涵义,而“Alone”一词进一步表达诗人独自登高的孤独寂寞之感。
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By Xu Yuanchong)
All over such a vast expanse, the rustling leaves off branches dance.
The Yangtse River rises yon, and passes raging on and on.
(By Zhang Xueqing)
Leaves are dropping down like the spray of a waterfall,
While I watch the long river always rolling on.
(By Witter Bynner)
地名是人们赋予具体的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一般包括专名和通名两类。在我国早期,专名的拼音通行“威妥玛”或“邮政式”拼音音译,通名则译成外文,如:“长江”(又名“扬子江”)译为“Yangtze River”。诗人当时位于夔州之地,眼前的“渚清沙白”正是长江之景,因此“长江”译为“Yangzi river”可直接被读者理解和接受,了解诗人登高望远之地,因此并未不妥。但笔者认为,相比于直译,许渊冲先生运用意译,其译文略胜一筹。“endless”一词,将“长江水”滔滔不绝之势彰显得淋漓尽致,在气势上更加磅礴壮观。外国学者Witter Bynner根据古诗文的字面含义直译为“the long river”,该译文略显不足。1987年12月2日,中国地名委员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地名标志不得采用“威妥玛式”等旧拼法和外文的通知》,在这一通知中明确指出地名标志上的地名,其专名和通名一律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因此“长江”也译为“changjiang river”。根据CNKI翻译助手,输入“长江”一词,共有1 669个词条,来自21个领域。其中译为“Yangzi river”的有1 250个词条,居于首位;译为“changjiang river”的有188个词条,次之;译为“the long river”的仅3条;此外还有18种翻译词条,应用频次共计228次,但由于其应用频次较低,不再一一列举。从文化维层面来看,“长江”这一概念,在19世纪就以别名“扬子江”为西方人所知。而Witter Bynner将“长江”译为仅有3个词条的“the long river”,没有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语言习惯,忽略了中西文化之间以及源语言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未能最大程度上传递原文信息,致使译文接受者所占比例过少,没有很好地实现文化传播的目的。
(三)交际维的主体再现
所谓“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关注译文是否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以及获取和原文读者类似的阅读感受。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进行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还要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例: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A thousand miles from home, I’m grieved at autumn’s plight;
Ill now and then for years, alone I’m on this height.
(By Xu Yuanchong)
Apart from home so far and so long, with autumn, myriad sorrows throng.
With illness all my life to fight, I now alone ascend this height.
(By Zhang Xueqing)
I have come three thousand miles away.Sad now with autumn and with my hundred years of woe, I climb this height alone.
Ill fortune has laid a bitter frost on my temples.
(By Witter Bynner)
在中国古诗词中,数词可以用来表示距离、时间等,但在文化中数词并不都是确定的概念,更多的是具有模糊性,而诗歌中数词模糊性主要是由语义模糊、固定搭配、文化差异引起的。在译文中,许渊冲先生和Witter Bynner均将数词概念具体化,分别译为“A thousand miles from home”和“ three thousand miles away”,而章学清先生采取意译的方式,译为“Apart from home so far and so long”。这三种译文,笔者更倾向于章学清先生的译法。由于数词具有模糊性,“万里”并不仅仅指“一万里”,而是一种虚指,表示离家距离之远,如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中的“三千尺”,并不是表示具体高度,而是表示虚数,意为“很高的地方”。章学清先生采用意译的方法,既传达了原诗内容,也能让读者感受到诗人在外漂泊孤独无依之感。许渊冲先生和Witter Bynner均将“万里”译为具体的数值“A thousand miles”和“Three thousand miles”,将模糊性数词具体化的确能够让读者更加清楚距离这一概念,但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读,误以为诗人离家距离就是“一千里”或“三千里”,在传达诗人远在异乡、无法归家的漂泊、孤独之感上略显不足。
不管是从语言维、文化维还是交际维,三位译者都对《登高》做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其译文也各有千秋。笔者认为,无论哪一种译文,译者都在生态翻译环境中对其译文字词等进行了筛选,做出了不同程度的适应和选择。而译文进行适应与选择的过程,也是译者主体性体现的过程。总体来说,笔者认为两位中国译者的译文略优于外国译者Witter Bynner的译文,其中许渊冲先生的译文最优。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语言复杂难懂,古诗词等经典文化更是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来阐述其中蕴含的丰富人生哲理。任继愈先生曾说,和其他文化背景下的译者相比,本土翻译者在理解中国文化上能最大程度降低其局限性。相比于外国学者Witter Bynner,许渊冲先生和章学清先生出生于中国,占有一定的语言优势,且对中国古诗词颇有研究,因而在对中国文化理解上更加独到,译文也自然略胜一筹。相较于章学清先生在翻译上追求忠实、通顺,许渊冲先生主张优化论,更加追求译文的“美”,擅用创造性的译法,发挥译者主体性,不断深化译文,使译文在某种程度上优于原文。
四、结语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积极构建国际话语权。唐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经典,其研究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方面,对比分析译者在唐诗《登高》译文中所做出的适应与选择,由此可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具有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