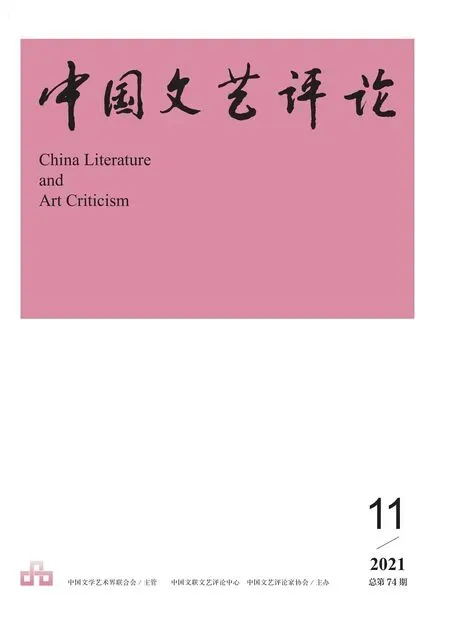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的思想根源、基本方法和话语特征
王廷信
2021年8月,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特别提到,要“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改进评论文风,多出文质兼美的文艺评论”,明确了中国特色的评论话语构建的途径和方法。这其中“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被放在首位,其次才是“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针对前者是“继承创新”,针对后者是“批判借鉴”,旨在强调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的主体地位。
不可否认,西方文艺理论的吸收与借鉴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对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文艺评论话语有着重要贡献。但中国拥有五千余年的文明史,从甲骨文诞生以来的历史也有三千余年。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中,积累了大量文艺评论资源,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批评体系。但自近代以来,这种传统或遭批判、或遭搁置、或被淡化,甚或被遗忘,以致我们当下的文艺评论出现了非西方不言、非西方不会言的尴尬局面。近年来,大量生僻理论、生涩概念、生硬模式的引入,也使文艺评论出现“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的倾向,进而使文艺评论仅仅停留在学术领域,甚至出现创作者不理、同行们不看、老百姓不懂的严重脱离“地气”的情形。为了克服这种倾向,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理清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思想根源、基本方法和话语特征,重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的价值。
一、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思想根源
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思想根源是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基本出发点,体现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价值观。对于这个问题,须回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原初历史语境中来进行考察。
中国古代最早涉及文艺批评的文字记载是《尚书》。《尚书·虞夏书·舜典》云:“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段记载虽然简略,但已透露出中国古代最初文艺批评的基本动机,那就是舜帝让乐官用诗歌和音乐对贵族子弟进行教育时,通过诗歌、音乐所营造的“和”的情境,使人的性格、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达到和谐状态。这说明在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之初,是把文艺与人之间的关系放到重要位置的,从批评的出发点上体现出文艺对人的教化功能。而就文艺自身来说,这段记载把诗歌和音乐结合起来讨论,指出诗歌对于人的情志的表现功能,音乐对诗歌的表达作用。而就诗歌与音乐之间、音乐的“八音”之间的关系而言,都在强调“和”的要旨。从此,文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核心命题,而“和”则成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讨论的核心范畴。
儒家自孔子开始,多祖述尧舜、阐发周礼,援《诗经》《周易》《春秋》等经典文献展开文艺批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在以尧舜等先王为范的讨论中提倡“和”之美德、在阐发周礼的过程中倡导以“仁”为本的和谐社会秩序的,而《诗经》《周易》《春秋》则被作为上述核心思想的主要文献依据。孔子谓《韶》曰:“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曰:“尽美矣,未尽善也。”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用自己所崇尚的西周时期的两部乐舞为范型讨论乐舞的美与善,谴责季氏用乐舞对周礼的僭越,旨在强调乐舞的美、善统一。孔子在论《关雎》时云:“《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旨在强调文艺作品的情感不能因过度而偏于一极。孔子指出:“不学《诗》,无以言。”他提倡“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从《诗经》的价值出发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及其对人们日常修为的滋养作用。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的“艺”泛指做各种事的技艺,具体可指《周礼》所言之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六艺”中,乐、书二艺均属艺术技能,可见包含艺术在内的技艺已被孔子纳入人的重要素养。而这些素养又是建立在对于道的追求、对于德和仁的依赖基础之上的。即孔子不赞成单纯的技艺,而是认为只有在道、德、仁等观念的支撑下,人才能悠游自在地从事技艺,也才能让人在行使技艺的过程中达到自由快乐的境界。孔子在具体谈到诗、礼、乐与人之关系时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意谓人的成长可以从阅读《诗经》开始,进而把礼作为立身的根基,又能用音乐来陶冶情操,从而完善自己的人格,旨在强调文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儒家哲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对于艺术的看法影响深远,其代表人物孔子继承了《尚书》讨论文艺与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核心命题以及文艺作品追求“和”的基本立场,着力思考美、善关系,道德和艺术的关系,并将其作为评判文艺作品的基本标准。这些动机和做法思之精深、传之久远,成为中国古代文艺评论思想的基本品格。如果说孔子在以礼乐关系讨论社会和谐秩序的构建中涉及文艺与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构建中国古代文艺评论提供了主流方向,那么道家和释家也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其文艺评论观。
道家先祖老子的言论是围绕“道”的问题来讨论的,只是在讨论“道”的问题时涉及文艺批评的动机,这种动机也是为阐发其哲学思想服务的。老子的社会理想是清静无为的和平世界,其治理社会的基本理念是绝圣弃智、无为而治。所以他在讨论“道”的问题时强调“有”与“无”的辩证关系。《老子》云:“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认为“道”是“恍惚”而不可捉摸之物,但其中包含着“象”“物”“精”“信”等品质。《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认为,“道”是先于天地万物而生的,支配着天地万物之运行,但因无法名之而“强为之名曰大”,认为道是一种无形无名的强大力量,也是包含天地万物的巨大空间,人仅是其中之一,而“道”之来源则是“自然”。这段论述体现出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道家观察世界的方式就与儒家有了显著区别。孔子也讲“道”,但孔子之“道”是围绕人事而思考的,集中体现在以“仁”为本的人心之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治世思想。孔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老子则把人与万物放在并行的空间里,认为人当以“无为”的态度面对世界,方能体现出“有为”之价值。所以《老子》云:“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提出“致虚极,守静笃”才能“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体察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在观察万物之“道”的动机下产生的,对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学说,运用大量实例体会和阐发“道”之精微,从而使“道”呈现出勃勃生机。庄子所言的庖丁解牛“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庄子用庖丁炉火纯青、游刃有余的宰牛技艺彰显“道”之魅力,让老子所言“道”之“恍惚”落实在现实人生的技艺体验中。庄子借颜回与孔子的对话提出“心斋”的命意。(颜)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认为运用虚静之心方能感受“道”之存在。庄子有心说“道”、无心言“艺”,但在说“道”动机的支配下,把艺术感受的精髓讲明白了。所以徐复观说:“当庄子从观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谓道,而我们也只从观念上去加以把握时,这道便是思辨的形而上的性格。但当庄子把它当作人生的体验而加以陈述,我们应对于这种人生体验而得到了悟时,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
如果说孔子从“有为”视角出发把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思想引向关注社会、关注人性善恶的现实主义批评轨道,那么老、庄则从“无为”视角出发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提供了虚静养心、以观奥妙的理想主义批评轨道。而到了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艺创作的日益发达,人们谈论文艺风气的日盛、对于精神生活境界追求的提升、佛教与魏晋玄学的相遇相结,让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思想出现了“拐点”。这个“拐点”便是直接针对文艺创作本身来思考文艺的价值,其突出表现就是大批文人士大夫针对文艺有了较为专门的思考。扬雄、王充、曹丕、曹植、陆机、左思、钟嵘、刘勰、谢赫、嵇康等一大批诗论、文论、画论、乐论家的出现,让汉魏时期的文艺批评成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第一座高峰。《汉书·礼乐志》云:“(圣人)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继承了儒家的礼乐思想。钟嵘《诗品序》云:“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直接把诗的地位提升到感天动地的崇高地位。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训》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这些论述均在昭示文学的地位与价值。谢赫《古画品录序》云:“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也把绘画上升到高台教化的地位。文艺地位的提升延续了先秦诸子的基本思想,无论是“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的礼乐,还是感天地、泣鬼神的诗歌;无论是“五形之秀”“天地之心”的文学,还是“披图可鉴”的绘画,都从文艺自身出发思考文艺的崇高地位,从另一角度彰显出文艺的社会价值。
从两汉到魏晋,是中国文艺创作骤然崛起的时代,也是中国文艺批评骤然凸起的时代。与文艺以及文艺的自觉相伴相生的还有玄学和禅宗的兴起。玄学源自老、庄和《易经》,是在从大一统的两汉到分裂的魏晋南北朝社会出现剧烈震荡的背景下产生的。动荡时代的士大夫文人选择了避世之路,一时间黄老之学、清谈之风大盛,为玄学奠定了社会基础。《魏书·释老志》记载:“显祖即位,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晋书·陆云传》所云之“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是玄学名称的较早出处。《尚书正义》在解释《老子》所云“玄之又玄”时指出:“‘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谓幽潜’也。”这种解释指出了玄学幽深的本质。玄学把时人的思想引向幽深玄远的境地,竹林七贤正是玄学人格的杰出代表。他们常集于竹林,酣饮纵歌、谈文论道,享受着肆意酣畅的自由生活。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时至魏晋,佛教般若“性空”之说与清谈玄学之风“不谋而合”,在贵族士大夫阶层广为流行,为唐代禅宗思想的形成铺平了道路。时至唐代,禅宗思想大盛,也深刻影响到文艺领域。禅宗可上溯至灵山会上释迦拈花,迦叶微笑传授佛法,后有达摩面壁静坐、寂然无为,直至六祖慧能开创的南派禅宗,主张“教外别传,直指人心,不立文字,顿悟见性”,才让禅宗深入人心,并渗透至文艺领域。这时不仅出现了大量诗僧(如王梵志、寒山、拾得、皎然等)、画僧(如善导、贯休等),而且赢得众多士大夫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兴致(如李白、白居易、王维等)。禅宗的“顿悟”主张不仅从哲学层面为人们认识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而且让文艺创作和批评进入一种新的境界。直到清代刘熙载评价苏轼诗歌时说:“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机括实自禅悟中得来”,也是运用禅宗的“顿悟”学说评价的。葛兆光说:“中国的禅宗便是在印度禅学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一株结着无花果的智慧树,它虽然植根于印度禅学,却融汇了印度佛教其他方面的种种理论,并与中国土生土长的老庄思想及魏晋玄学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既具有精致的世界观理论,又具有与世界观相契合的解脱方式和认识方法的宗教流派。”
从先秦至唐,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思想根源从萌芽到形成,为后世的文艺批评奠定了较为稳固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的特征体现为文艺与社会人生的密切关系,儒家“有为”与道家“无为”的辩证关系,玄学“清谈”与禅宗“顿悟”的互证互补关系。自宋以降,这些特征虽在不同时期表现特征略异,但总体来说,它们都一以贯之地被后世所继承、所阐发、所光大,体现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思想的显著个性。
二、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基本方法
如果说文艺批评的思想代表批评者的基本立场的话,那么文艺批评的方法则是站在这种立场思考、分析文艺现象的具体做法。文艺批评的思想着力解决“为何评”的问题,而文艺批评的方法着力解决“如何评”的问题。中国古代的文艺批评是围绕文艺与社会、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的,是为了实现“和”的理想目标而评的。这种思想也决定着其批评的基本方法。本文认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基本方法可从如下四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知人论世的关联方法。
知人论世是指批评家基于对创作者本身的认识而对其文艺作品进行评价。知人论世的方法较早出自儒家。《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强调对于创作者所处时代、身世、思想、品格的理解是理解其创作动机、创作过程和作品的前提,提倡与品格高尚的艺术家为友。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郭绍虞也曾对此作过专门论述,他认为儒家对文学批评的方法主要是“体会”的方法。他说:“儒家之所谓体会,其方法有二种:一是在本文内体会的,一是在本文外体会的。……其在本文内体会者,更有二种方法:一是论世,一是知人。《易·系辞传》云:‘圣人之情见乎辞’,因为情见乎辞,所以可以知人论世。”知人论世的方法可上溯至《尚书·虞书·舜典》“诗言志”之说。《尚书》较早把诗歌与人的情志联系起来认识。《毛诗序》亦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亨把诗歌看成是人的内心情志的表达,而人的情志与人的身世、际遇都有直接关系。不知其人,难以理解其志,进而难以理解与情志直接关联的诗之含义。司马迁《报任安书》云:“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第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所举之作皆与作者的身世和处境密切关联,司马迁的批评也印证了中国古代文艺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知人论世把创作者与其作品密切关联,不孤立地看待作品,是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最为基本的方法。这种方法贯穿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始终,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了中国文艺批评的优良传统。第二,日常体验的言说方法。
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家自觉让批评渗透在人的日常体验中,渗透在人与人的日常交流过程中,从人的基本情感出发,与人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密切结合,故而充满鲜活的生命力。《论语·八佾》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夏从人的美眸流盼的动人笑容中询问孔子关于“美”的道理,孔子将其与绘画联系起来,说先要有绚白的底子,然后去作画方能有美感。子夏问“礼”是后来才有的吗?孔子从子夏的回答中得到启发,才说可以与其讨论《诗经》了。可见,孔子正是在与学生的日常谈论中,基于对日常生活的体验来理解和评价文艺现象的。
《庄子·达生》记载过一位名叫梓庆的工匠制作的一种名为“鐻”的乐器架的故事,说乐器架子制成后,“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其缘由,梓庆说他为了制作好乐器架,需要斋戒七日,直至达到一种虚静忘我的境界方能进入山林,按天性凝神选材,也才能制作出如此神奇的乐器架来。庄子借助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流,把制作乐器架需凝神静气、进入与物质材料“神交”的境界以理解乐器架所需之材特性的深刻道理生动地讲出来了。
《礼记·乐记》中记载过魏文侯与子夏讨论“郑卫之音”的故事。魏文侯问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糅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乐记》也是通过魏文侯与子夏之间的日常对话道出“音”与“乐”的差异,从而阐发古乐与新乐之别。
钟嵘《诗品序》云:“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钟嵘的这则议论也反映出南北朝时期士大夫们常常借助诗歌讨论时事,说明在南北朝时期,文艺已经渗入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而被评价。
在中国古代,除了较为专门的文艺批评著述,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将文艺批评与生活体验密切结合,让文艺批评成为人们日常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我们从《红楼梦》中贾府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诗歌创作与品评活动即可看出。
第三,以心感物的认知方法。
这种方法源自儒家提倡的“格物致知”(《礼记·大学》),道家提倡的“虚而待物”的“心斋”,后由魏晋玄学与禅宗的“顿悟”方法所承接,在宋明理学中得以光大,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认知方法。成复旺曾说:“翻开中国传统的美学论著,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其中的中心议题,就是心与物。”“无论诗论、画论、乐论,亦无论‘意象’论、‘意境’论,总之都是论心与物。”这种看法十分准确。《礼记·乐记》在谈到音乐的起源时曾云:“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所以“心”与“物”的关系从中国艺术理论的源头开始就是中国文艺的核心命题,以心感物的方法也是中国文艺批评的优良传统之一。《礼记·大学》云:“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儒家为人的成长设置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步骤,让人从“格物”开始以达到可为“平天下”的理想目标服务的基本涵养。这是儒家为实现其社会理想而从人的角度提出的实现途径,让人通过“格物”——体认万物而“致知”——洞明世理,通过“致知”而“诚意”“正心”“修身”,从主观修为上提升自己,进而投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务当中。如果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体”,那么“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用”,“体”“用”结合,是儒家从个体的人的角度所提供的方略。这种方略也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基本方法,其中体认万物以“致知”的方法为认识文艺创作的基本原理、发掘文艺作品的价值、评价文艺作品的基本特征开启了思维之门。
道家以“虚”为特征的“心斋”理念,是借助纯净的“心斋”体认事物奥妙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在后世文艺批评活动中也被广泛采用。如南朝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倡的“澄怀味象”正是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澄怀”要求体验者涤除内心欲念、以超越世俗功利的心境去看待艺术,是“味象”——体味艺术精神的前提。而禅宗从万物自然变化的规律悟出佛理的做法,则是超越世俗迷障,直指事物本性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让以心感物的文艺创作和评论方法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王维“在京师日饭数十名僧,以玄谈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方有其如“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这般空灵自在的诗作。晚唐诗僧皎然遍访名山、精研佛典,他在《诗式》中评价康乐公(谢灵运)诗歌时所说的“但见性情,不睹文字”,就是禅宗思维在诗歌批评中的体现。金元之际的文学家元好问所言的“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赠嵩山隽侍者学诗》)更是生动深刻地道出了禅与诗的密切关系。直至清代刘熙载《艺概·诗概》在讨论杜诗时所云之“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如上都承继了禅宗的批评方法。
由此可见,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禅宗,皆在高扬并涵养主体的“心”的能量,用以心感物的方式处理“心”与“物”之间的关系,借以感受、理解、领会文艺作品之精神,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认知方式。
第四,感通万物的思维方法。
如果说以心感物是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认知方法,旨在让批评主体与批评客体在界限上发生区别和联系,让批评客体在批评主体思维中被对象化的话,那么感通万物的思维则是让这种认知方式具体化,让批评主体面对批评客体得以浸入、感受、化生、提升和完成的更加具体的方式。《周易·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孔颖达疏:“观看其物之会合变通”,是指观看主体对万物之变的一种洞察力,与“感通”同义。而“感通”一词最早出自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中。《周易正义》又称《周易注疏》,是对《周易》的进一步解读。《周易正义》云:“‘咸’感也。此卦明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必须男女共相感应,方成夫妇。既相感应,乃得亨通。若以邪道相通,则凶害斯及,故利在贞正。既感通以正,即是婚媾之善”。“感通”在此是指男女之间的心性感应,孔颖达强调男女之间以合乎法度的方式从内心深处相互感应,才会获得美满婚姻。“感通”源自《周易》,刘勰的《文心雕龙》深受《周易》影响,就文学的思维来说,《文心雕龙》对《周易》“感通”万物的思维作了有益的尝试。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曰:“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刘勰的“神思”正是感通万物的思维,其在时间上可“接千载”,在空间上可“通万里”,让人之“神”与万物相“游”,从而借助神思之枢机,让万物呈现生气。这种思维既是文学创作的思维,又是文艺评论的思维,强调批评者面对作品要“感而通之”,从而发掘深藏于作品中的生机。
到了宋代,以张载、程颐、朱熹等人为代表的儒学家在解释《周易》时,把“感通”思维发挥到极致,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方法提供了思维“中枢”。《周易》咸卦“篆辞”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极言感通之理。”咸卦“篆辞”在此把天、地、人“三才”因感应而通万物之理说得很透彻。朱熹云:“天地间无非气。人之气与天地之气常相接,无间断,人自不见。人心才动,必达于气,便与这屈伸往来者相感通。”朱熹在此指出感通万物的思维形式是以“气”为媒介的,人心之“动”须达于“气”,通过“气”才能使“心”与万物“屈伸往来”之变相通。在宋代理学家看来,思贵虚不贵实。杨万里《诚斋易传》云:“心者,身之镜;思者,镜之翳。镜则虚而照,思则索而照。虚而照,无物也;索而照,有物矣。惟无物者见物,有物矣,安能见物哉?……役思于事物往来屈伸之变,故思未能感通于事物,而事物万绪,朋来从之,而不胜其扰且害矣。”杨万里的思想深受老、庄影响,倡导“虚以待物”,认为“役思于事物往来屈伸之变,故思未能感通于事物”,反对从主观意志上被“思”奴役。苏轼对《周易》也深有研究,并深受其影响。他所言的“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师》)也反对杨万里所言的“役思于事物往来屈伸之变”,倡导以空静之心而“纳万境”。
中国古代哲学之“感通”也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世界的全面体验。这种体验最初是生理上的,而最终被上升至心理层面,升华为精神性的事物。古代哲学常言的“五色”是目之所感,“五音”是耳之所感,“五气”是鼻之所感,“五味”是舌之所感。人在感受这些事物时最初都是生理上的感受。但中国古代哲学往往能自觉地把生理感受上升至心理、精神感受,这种做法正是“感通”思维的体现。所以在从事文艺批评活动时,批评家能把“色”“音”“气”“味”会通,集中以“味”来体现,体味、品味成为批评的方法,意味、滋味等成为批评结果。之所以集中以“味”来体现,当与中国古人把“舌”与“心”连结起来思考有关。《黄帝内经·素问》云:“肝主目……心主舌……脾主口……肺主鼻……肾主耳。”《灵枢经》云:“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可见“舌”与“心”关系之密切。在古人看来,“心”是感受和思考事物的中枢,“舌”是五官最重要的媒介,所以“心主舌”。由此我们便不难体会,为何中国古代文艺批评能将五官所感会通于“味”了,也能体会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何以能将生理之“味”会通为精神之“味”了。
感通思维也是需要训练而养成习惯的。《二程粹言》记载过孔子和客人之间的一段对话:“或问:‘学必穷理。物散万殊,何由而尽穷其理?’子曰:‘诵《诗》《书》,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覆研究而思索之,求止于至善,盖非一端而已也。’又问:‘泛然,其何以会而通之?’子曰:‘求一物而通万殊,虽颜子不敢谓能也。夫亦积习既久,则脱然自有该贯。所以然者,万物一理故也。’”孔子在此强调感而会通非一日之寒,需长期炼心养性,涵育思维习惯,厚积薄发,才能有自然而然的贯通。
感通万物思维方式的价值在于让批评者“浸入”作品的时空情境,以“游”的方式自由感受作品描述的物象,并能“跳出来”将这些物象特征提炼出来化作批评者的“心象”,为批评者评判作品价值提供参照。常有人说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多为感受性较强的经验描述,殊不知这种现象恰恰是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的闪光点所在。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家在评判作品时不刻意把作品切割成可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逻辑元素,而是借助感通思维,从整体上感受作品的特征、把握作品的风貌,并将这种特征和风貌以自由而富有生机的语言表达出来,既能化为批评者自己的精神力量,又能呈现出作品的精神特质,所以带有较强的经验特征。运用感通万物的思维方式进行批评的结果,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价值判断,而更多是富有个性的特征判断。所以,感通万物的思维方法是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重要批评方法,也是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方法的优良传统。
由上可见,知人论世的关联方法让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不被置于孤立状态看待,日常体验的言说方法让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心感物的认知方法让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区分出主体与客体并让二者发生联系,感通万物的思维方法则体现出迥异于西方文艺批评的理性特征,让文艺批评活动成为批评家可浸入、可体验、可化生、可判断、可创造的能动的批评行为。这四种方法互相补充、互相支持,成就了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方法论传统。
三、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话语特征
如果说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思想源于对文艺与人之间关系的讲求,源于对“和”的理想的追求,那么基于这种追求,其独特的批评方法使中国古代文艺批评获得了具体的体认、思维和表达途径。而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话语则是基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思想根源和批评方法而生成的批评模式。所以我们要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思想根源和批评方法出发,思考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话语特征。
“话语”是言说事物过程中所选择的视角、所使用的范畴和概念。这些视角、范畴、概念构成一种言说模式,用以阐发事物之价值、揭示事物之特征。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在长期积累和演变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身较为独特的言说模式和话语特征。如果说视角是人们认识世界的观测点的话,那么范畴则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途径,而概念则是在范畴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次范畴”,用以概括次于“范畴”范围的现象。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视角、范畴、概念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基础上的,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文艺批评领域的延伸和运用。
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建立在天、地、人“三才”的关系基础上,其认识世界的视角也是从这三者的关系入手。最早为这三者建立关系的典籍是《周易》。《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周易·系辞》所言的包牺氏作八卦的思路、方法和目的。包牺氏把天、地、人三者之间的联系用图符形式来表示,旨在“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种做法也是人与天地沟通、用类比而生的象征方式表现世间万物情状的做法。
《周易·系辞上》引孔子语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周易》是儒家倡导人们阅读的“五经”之一,反映出儒家对先民认识世界原初思维方式的认可和尊重。《周易·系辞》有效地解释了这种方式。观象于天、观法于地、体情于人和万物,区分“形而上者”之“道”、“形而下者”之“器”,重视事物之“变”、万物之“通”,让这种道理施于天下百姓而成其“事”。这种做法开辟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话语源头,后被广泛运用于文艺批评话语系统中。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话语源自中国哲学的话语,首先是从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做起,从思考天、地、人之间关系的角度考量,从感物之变、道器辩证、形神兼顾、立象尽意的思想源头渐次展开。儒家、道家沿着这些思想源头展开各自的阐发,魏晋玄学和稍后的禅宗在道家思想基础上开辟了另外的道路。
中国古代的哲学范畴由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所沿用,成为其感受工具和分析工具。但这些范畴也各有轻重和指向。轻重是指主次,可以用层级来划分;指向是指侧重点,如侧重于本体论的范畴、方法论的范畴、价值论的范畴等。为了便于理解,笔者在本文中把范畴按轻重划分为理想性范畴、根源性范畴、支撑性范畴、延伸性范畴四个层级。其中理想性范畴代表中国哲学和文艺批评思想的最高理想和目标,根源性范畴代表中国哲学和文艺批评的思想基础,支撑性范畴是用以分析和展开根源性范畴的支柱,而延伸性范畴则是在支撑性范畴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较为具体的范畴。
“仁”是儒家思想的根源性范畴。“美”与“善”是建立在“仁”这个范畴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支撑性范畴。儒家在处理“美”与“善”这两大范畴之间关系的过程中,用“尽善尽美”来树立社会理想与艺术理想,这种理想的最高境界是“和”。所以“和”便成为儒家认识社会和艺术时的理想性范畴。换句话说,儒家思想在“仁”这个根源性范畴基础上,通过处理“美”与“善”这对支撑性范畴之间的关系,来实现“和”的理想。而儒家在讨论“文”与“质”的关系时,强调“文质彬彬”的“和”的风貌,道家从“阴”与“阳”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对“和”的另解。《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又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可见,“自然”是道家所树立的根源性范畴,是“道”之师,“道”是道家思想的支撑性范畴,而“阴”与“阳”是道家认识“道”的延伸性范畴,“和”仍然是道家的理想性范畴。儒、道两家殊途同归,均以“和”为理想。与“阴”“阳”相对应,道家凝练出“有”“无”两大范畴。《老子》曰:“天下万物生於有,有生於无。”王弼注:“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於无也。”认为“以无为本”,倡导“无中生有”,以“无为而治”的思想实现“和”的社会理想。《老子》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提倡祛除人的欲念,保持内心之“静”,从而使“静”进入道家思想范畴视野。道家从“无中生有”演化出一套可以让“有”生生不息的思想,那就是让人的内心保持“静”的状态,才能让万物涌现生机。庄子继承了这种思想,在阐发“静”的思想时提出“动”以及“虚”与“实”的范畴。《庄子·天道》云:“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也,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则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指出“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在此,庄子以“静”类“阴”、以“动”类“阳”,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所以,正是庄子把道家的阴、阳观和有、无观通过类比的方式转化为“动”与“静”、“虚”与“实”的通用范畴。这四个范畴被广泛运用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活动中。
最为可贵的是道家对“气”的阐发,道家从另一角度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老子认为在阴、阳交互作用的运行过程中,需要“冲气”方能达到“和”的境界。那么何谓“气”?老子并未给予界定,而《庄子·人间世》明确指出:“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庄子的解释与孟子把“气”看作是充满“体”内力量的看法异曲同工。二者都认为“气”是“体”内之物,但孟子主张“以志帅气”,庄子主张“虚而待物”。孟子是运用人之“志”主动把握体之“气”,庄子则以无为的姿态让“气”处在自然状态以便接纳万物。在老庄的学说中,是把自然气候变化之“气”与由此延伸出来的人的精神之“气”并用的。如《庄子·在宥》所云之“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调,四时不节”,是指自然气候之“气”;《庄子·达生》所云之“夫忿滀之气,散而不反”,是指人的情绪之“气”;而《庄子·天地》所云之“汝方将妄汝神气,堕汝形骸”,则指人的精神之“气”。从老庄对于“气”的运用可以看出,道家是把“气”作为连结宇宙万物的纽带来看待的,其与“道”形成一种连带性关系,让“道”有了可以依赖的实体。所以“气”在道家思想中也成为一种与“道”相表里的支撑性范畴。而在中国古代哲学和文艺批评思想中,人们常常赋予“气”以精神特质。那么自然之“气”如何转化为精神之“气”呢?《黄帝内经·素问》云:“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是说“气”是由人的“五脏”化而生成的。《管子·戒》云:“滋味动静,生之养也。好恶喜怒哀乐,生之变。聪明当物,生之德也。是故圣人齐滋味而动静,御正六气之变,禁止声色之淫。”房玄龄注云:“六气,即好、恶、喜、怒、哀、乐。”可见,自然之“气”是通过人之五脏转化为人的体内之“气”,再经过人心对于“滋味”和“动静”的体认而转化为精神之“气”的。而正是基于此,“气”才由自然界域“迁移”至精神界域,也才让“气”有机会进入文艺批评话语范围中,成为一个重要范畴。由这个范畴展开的其他范畴十分丰富,如阴(柔)气、阳(刚)气、气象、气质、气韵、气势、神气、正气、生气、灵气、秀气、壮气等。这些概念在文艺批评活动中被广泛运用,或表状态、或表风格,成为十分活跃的话语方式。
与“气”紧密关联的另一范畴是“味”。前文讲过,“味”是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感通思维的结果。当自然之“气”转化为精神之“气”时,生理之“味”也在感通思维的作用下转化为精神之“味”。基于此,“味”也与“气”生成一个地位相当的重要范畴,由这个范畴延伸出来的范畴也颇多,如品味、体味、玩味等被用于批评活动,意味、滋味、韵味、品味、兴味、趣味等被用于描述批评结果。
魏晋时期,人们崇尚清谈,玄学大兴。士大夫们也在品藻人物的过程中,将其风气引入文艺批评领域,出现不少有价值的范畴。《老子》开篇即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魏晋士大夫继承了老子的学说,认为“玄”开启了体察事物之“妙”的大门。所以,魏晋时期士大夫们的思想是紧紧围绕“玄”“妙”两大范畴展开的。这两大范畴便是他们哲学思想的根源性范畴。而相对于《周易》和老庄而言,这两大范畴又是支撑性范畴,因为魏晋士大夫的玄妙之学多是在解释《周易》《老子》和《庄子》的过程中生发的。《周易》《老子》和《庄子》三部经典时称“三玄”,而《老子》《庄子》被称为“玄宗”。魏晋士大夫们凝练出来的“玄”的范畴实与老庄所言之“道”相通,甚至可以说是“道”的另称。而恰在这时,由东汉时期传入的佛教与老庄之学合流,于是般若之学、谈玄说妙之风大行其道,直到禅宗的出现,由禅宗生发的“顿悟”思想破除了玄学的迷障,开辟出一条哲学认识新路。由禅宗衍生的哲学范畴如“心性”“自在”“清净”“本体”“妙悟”“禅境”“禅趣”等为中国哲学引来一股清风。直到宋明时期,大批理学家把《周易》和儒、道、禅宗思想的阐发引向极致,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这些范畴也被广泛运用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活动中。如南宋时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辨》认为“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乃典型案例。
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话语主要是由认识文艺现象的角度和一系列范畴以及在范畴之上衍生出来的“次范畴”——概念构成的。由《周易》开端的哲学思维为这种话语系统开辟了源头,儒家、道家、魏晋玄学和禅宗的哲学思维沿着《周易》所开辟的源头继续深化,并且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织的思维模式。而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家们在运用这些哲学思维模式的过程中进一步延伸出丰富的话语体系。如果说以《周易》为开端的哲学思维认识世界的角度是从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关系入手,那么儒家、道家、魏晋玄学和禅宗也未脱离这种关系,由此引发的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话语模式也延续了这种关系。这种思想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知人论世”“日常体验”“以心感物”“感通万物”的基本方法即可看出。而在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话语体系特征上,围绕范畴的凝练,概括出理想性范畴(如“和”)、根源性范畴(如“仁”“自然”“心”)、支撑性范畴(如“美”“善”“道”“气”“味”“有”“无”“悟”)、延伸性范畴(如“意”“象”“形”“神”“文”“质”“境”“妙”“雅”“俗”)。在这些范畴基础上,一系列“次范畴”——概念被凝练出来,具体运用于文艺批评活动中。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文艺批评较少讨论“真”的问题。如《论语》《孟子》中从未出现“真”字,《老子》中仅出现三次“真”字,儒、道两家早期典籍中惟有《庄子》较多讨论“真”的问题。《庄子·渔父》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没有给“真”下一个客观的定义,而是把“真”建立在人之“精诚”的认知态度基础上来讨论的。这是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留待哲学家去探讨。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也好,由哲学思想延伸出来的文艺批评思想也好,之所以较少讨论“真”的问题,是因为这些思想从未把“真”当作孤立存在的纯粹客观事物,而是由人之“精诚”与否来感受和判断出来的事物,也是将其置放在特定的语境中来感受和判断出来的事物。这种思想也深刻影响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我们从中国古代文论较少出现有关“真”的典型范畴和概念即可看出。
四、结语
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理论的思想宝库,其对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持续关注,对人与文艺之间关系的持续思考,依然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应当持守的立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方法也是富有生命力的方法,无论是知人论世的关联方法、日常体验的言说方法,还是以心感物的认知方法、感通万物的思维方法,都是生机盎然的有效方法,对当下的文艺批评仍然有效。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话语特征,是在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思想根源、基本方法的基础上,通过批评家们长期而独特的感受、体悟,凝练而产生的,以层次丰富的经典范畴为代表,足以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当代文艺批评应珍惜这种话语模式,进一步发掘其时代价值,并自觉将其运用于文艺批评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