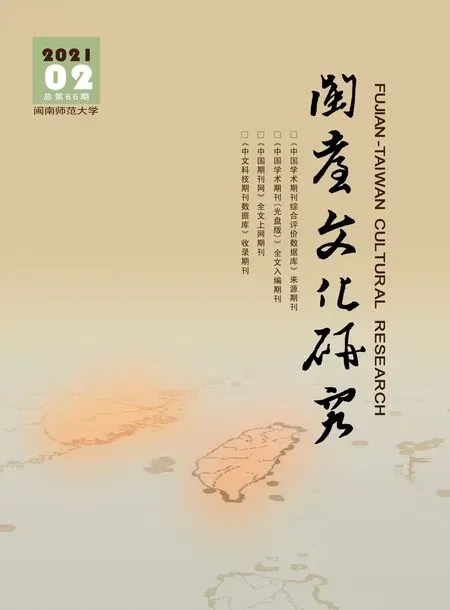翁闹小说中的世纪末情调
钱嘉禾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福建福州 350007)
翁闹作为台湾文学史中早夭的天才作家,曾一度沉寂于历史之中,然而,由于他对时代精准的感知以及对新颖书写形式的开辟,其作品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后再次获得了价值的肯定:“日据时代的台湾小说,可说到了翁闹的手上,才有独树一帜的表现,才开启了另一文学艺术的崭新领域。”在大陆,研究翁闹的学者甚少,张羽的《寻找台湾“幻影之人”翁闹——兼论翁闹与郁达夫的日本叙事》通过对翁闹和郁达夫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两者在日本文化场景下体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创作情态,分析了翁闹作为殖民地作家的创作心理与颓废意识。在台湾,日籍研究生杉森蓝的硕士论文《翁闹生平及新出土作品研究》探讨了翁闹的作品特色,首次理清翁闹的生平以及新出土作品《有港口的街市》,并揭露了当时日本与台湾新感觉派之关系;萧萧与陈宪仁所编“翁闹的世界——翁闹百岁冥诞纪念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翁闹的世界》中翁闹摆脱了“幻影之人”的迷障,以确定的活动空间与精准的生活轨迹重新为世人所认识;黄毓婷在《东京郊外浪人街——翁闹与一九三〇年代的高圆寺界限》中探究了殖民地青年的共同心性,同时追寻翁闹个人史的细节,并在其译著《破晓集》中整理并翻译了翁闹现存的所有作品。
一、19世纪末的颓废情调
翁闹的创作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由于西方理论进入东方社会具有一定的延迟性,此时的台湾文坛正好承接了19世纪末在西方英法等国兴起的,以波德莱尔、王尔德等艺术家为代表的具有近代颓废和唯美主义倾向的“世纪末”文艺思潮。翁闹作品中纯粹的艺术性,实现了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崭新接轨。叶石涛在《台湾文学史纲》中提及:“翁闹已经有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怀疑精神……他的作品影响到龙瑛宗和吕赫若等人,使得这些作家都多少带有苍白的知识分子、世纪末的颓废。”“颓废”在这里摈弃了“精神萎靡”与“意志消沉”等常见内涵,诠释了世纪末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混沌状态产生的惶恐不安的感受力,是向内对生命敏感的体悟,其中包含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以及人类的生存状态。翁闹十分擅长于对内心世界的描摹,其作品中的颓废意识显而易见——在《音乐钟》《残雪》《天亮前的恋爱故事》《罗汉脚》《戆伯仔》《可怜的阿蕊婆》等短篇小说中,主人公时常游走于虚幻与现实之间,或自说自话,或穿梭于梦境,或沉溺在冥想之中。翁闹通过人物无意识的状态展现了这个特殊时期人类特殊的内心世界。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在落入想象与回忆时,往往带有一些明确的情绪,这是他们对过往生活或是想象中的生活的一些感知,如《音乐钟》里“我”对同睡女孩身体的渴望,《可怜的阿蕊婆》中阿婆对昔日生活的喜爱,《戆伯仔》中戆伯在梦中飘离地球时感知到的痛苦,这些或悲或喜的情绪隐匿于他们内心深处,成为逃离当下现实的某种手段,这种逃离是由于对世界末日的恐慌所造成的,因为当主人公抽离回忆或想象再次回到现实,所面对的仍是一个焦虑的、苍凉的、不知所措的世界。
“颓废”在《天亮前的恋爱故事》中表现尤为突出,小说中的“我”至始至终在向某个对象进行情感倾诉(但实际上只是“我”的独白,对象并不一定存在),“我”时而跌入回忆感受青春期懵懂的恋爱心思,享受观看或是拆散正在交配的动物之快感,时而沉入想象拥抱女性的肉体,体验热烈的情欲,可一旦回归当下,“我”便陷入了自怨自艾、难以得志的恋爱状态,无论是回忆、想象或者是与现实中虚构的人物对话,通篇小说中“我”始终沉浸在自己的虚幻的世界中,这实际上是翁闹对无法勾勒的内心世界的一种描摹,它不能被看作是人文知识分子对现实的逃避,而应当认为是当下时代引起的某些心理与精神状态的展现。学者施淑曾对《天亮前的恋爱故事》做过这样评价“这篇带有恶魔味道的小说,它的世纪末色调,它之力图表现思想上无法说明的事物,乃至于叙述上的不稳定、几近消失了轮廓的语言及文体,为台湾文学开展了一个新的面向,使它成为三〇年代台湾小说的‘恶之华’。”施淑将《天亮前的恋爱故事》比作是波德莱尔的《恶之华》,也从侧面肯定了翁闹无论是作品内容或是书写方式上都为三十年代的台湾文坛,开辟了崭新的天地,而这种“新”并非无病呻吟式的宣泄,而是波德莱尔式的从人性的恶中寻求价值,只有正视并承认本身存在的恶,才能从恶中得到宣泄与重生。“这时代的青年作家大都渴望新奇的美和理智的亢奋,我们不能因他们有些偏颇的嗜好和人生如梦的悲叹……将他们完全抹杀。他们绝没有失掉求生的意志与活力,或者反可说只因他们活跃的生命不安于四周沉闷的空气,故发生了好奇与求知等欲望。”所以说,翁闹的颓废实际上是人文知识分子因为彷徨与焦虑对现代社会产生的一种特殊抵抗。但是,引发这种颓废情调的原因也同样值得探讨。张羽将翁闹出现强烈的颓废意识的原因归结于“在殖民地的历史断裂的夹缝中,作家个人很容易更多回归本我”,这实际上强调了翁闹作为殖民地作家的特殊身份,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被殖民的身份,却又不甘低人一等,但在他漂洋过海试图凭借才情打入“中央文坛”的过程中,却又发现自己始终无法融入东京这个现代化的大都会,现实与想象的差距让翁闹出现了“始终像被什么追赶着似的,有踏不着地的感觉”,而作品中看似对无意识世界的侧重以及对现实世界的回避实际上表达的便是这类难以名状的“踏不着地的感觉”,翁闹对现实的疏离并非真正的疏离,而是在疏离的过程中寻求真实的存在于当下的感觉。当然,从殖民地到“帝都”,由乡土社会到现代都市,历史的断裂除了在身份认同方面让翁闹陷入尴尬处境,现代都市携带的新型文明也让翁闹处于难以与现实沟通的状态,这也是翁闹作品中产生颓废情调的重要原因。
二、都市中焦虑的“他者”
19世纪末近代西方社会进入城市化阶段,急速的都市生活渐渐取代原始的乡村生活,高耸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人群、纵横交错的街道以及舞厅、酒吧、咖啡馆、剧场与电影院,世纪末的灯红酒绿代表着新兴的都会文明闯进人们的生活,同时也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反映,这成为了《音乐钟》《残雪》《天亮前的恋爱故事》《有港口的街市》甚至《可怜的阿蕊婆》中的重要场景。由于现代都市时代的到来,人们的个性与创造被否定,加上关东大地震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恶化,一种焦虑、孤独、忧郁甚至绝望的情绪渗透在都市的空气中。值得一提的是,翁闹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常常表现出这种症状,翁闹作品中的人物虽然不能说完全是其生活轨迹的复刻,“然而处身现代都市,面对自我的内心,却隐约浮现存在的不安感、焦躁感,从这个角度而言,翁闹的文学世界可视为他内心的写照。”所以,翁闹对这些都市风光的描摹并非陶醉于都市生活的先进与便捷,而是通过对现代都市的不满与反叛来诉诸自我的颓废,展现出一位焦虑的“他者”。
电车到了有乐町站时林还不想下车,就这么一路搭到了新宿才下。他想到新宿夜里拥挤的人潮就觉得厌烦,于是避开闹街,径直走回了大久保的住处。(《残雪》)
但是,阿蕊婆偏偏是在人为粉饰与虚构组成的都会里长大的,那里连泥土都被覆盖在别的东西底下,没有植物也没有小溪,有的只是电线杆和臭水沟。人类的灵魂实在具有不可思议的属性,对于自己长久居住的地方,就算再脏再丑,也因为是故里而长久回荡在记忆里。(《可怜的阿蕊婆》)
说实在的,比如说当我看到那些花几百圆买来不为保暖,而是挂在肩上给人看的围脖就感到莫名的嫌恶……我简直想吐。还有,比如那个收音机,这东西实在让人受不了……另外,只要一想到那些市区电车、汽车和飞机,我就全身发毛。(《天亮前的恋爱故事》)
“厌烦”“脏”“丑”“嫌恶”“想吐”“全身发毛”……翁闹不断地使用这类带有负面色彩的词语来描述都市环境,以至于文本的夹缝中都弥漫着焦躁不安的情绪。翁闹本人生活在都市里,他作品中的人物也生活在都市里,但他却从来只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身不由己处在都市却从不与都市相容的陌生人,对这种新型文化进行冷酷的讥讽与焦虑的抨击。在《东京郊外浪人街》中翁闹写到“来到东京之后我频频迁徙,也落脚过许多地方……最后还是不得不又沦落到高圆寺这里。仔细想想,这个浪人街的风情毕竟是溶入了自己的调调里,再也逃不掉了吧!”这样看来,翁闹从未真实地融入于东京的“调调”里,反而融入了高圆寺的“调调”里,他无法认同自己是一名都市人(即使他正身处其中),而选择成为都市外的浪人(即被都市所遗弃的流浪汉)。因此,他更善于描写主人公无法跻身于都会,并与现代都会相互吸引、又产生抗拒,出现焦虑症状的过程,如《残雪》中的林春生对东京虽心怀志向却只能在小剧团演出;《天亮前的恋爱故事》中的“我”对都市生活感到极度的焦虑,产生了发疯与自杀的念想;《有港口的街市》中的谷子遭父母遗弃,在都市中闯荡后又被迫离开。而翁闹栖息的高圆寺作为市郊,距离东京咫尺之遥,既拥有低廉的生活消费,同时受到东京大都市文化的辐射,这样的住址选择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翁闹内心的想法,“翁闹将自身偏离都市中心,而不完全离开都市,仿佛就是意识到都会的‘他者’性。”翁闹无法融入都市,又想作为旁观者观看都市人的生活,这种“他者”性强调的是翁闹自身的矛盾,他与都市环境的格格不入、与现实无法达成沟通,更无法获得精神上或是感觉上的共鸣,即“在帝都之中却又相隔遥远的现实”;这种“他者”性也是解释翁闹小说中弥漫着焦虑情绪的原因,正如上文所言,这种与现实相隔遥远的距离感才是翁闹对当下最直观的感受,它们是破碎的强烈的向内出发产生的个人意识,翁闹通过对周遭令人厌恶的现代都市环境的描写,来展现人孤独、忧郁与不安的末日情绪。由于对都市“他者”性的无所适从,翁闹只能回归精神世界来展现自身与众不同的创造力,他作为旁观者从外部描绘都市的面貌时,也同时作为体验者从内部探求自我的内心世界。
二、精神困境与真实人性的探求
黄毓婷曾这样评价翁闹:“永远孤独、永远像未成年般纯真,永远追求不同流俗的精神世界。对于‘别人认不认同他,他是全无兴趣’的自负,翁闹是有的。”由于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排斥,外加这种不可一世的气焰,促使翁闹向内出发,从更加复杂的精神世界中寻求真实的人性。这与同时代的一些五四作家是很相似的,他们的作品中同样充斥着世界末日的混乱情绪,如郁达夫笔下“零余者”们的自卑与焦虑,刘呐鸥对都市中颓靡景象的书写,甚至张爱玲所传达出的城市人的无尽苍凉。翁闹同这些五四作家一样,作为弱小民族的子民,受到资本主义的侵袭,同时置身于都市文化中,对周遭环境的不适感、对世界末日到来的恐慌感让他们的思考把对现代都市的感触提升到反映人类精神困境的哲学高度。他们敏锐地感知到了人类的精神困境——不安、焦虑以及惶恐的世纪末情绪。但正是因为难以突破这种困境,翁闹更追逐于探求真实的人性:“人性本应该更复杂,也应该有更多通融、自由、奔放不羁的面向……但愿你能观照人性的真实。”在他看来,人性自由而流动,如果只从善或恶的单一面向来了解人性并不完整。翁闹绝不否认人性中有光彩熠熠的一面,但他也毫不忌讳地描述了人性中堕落与悲观的一面,正如他写道,“我想啊,如果这地上再次为野兽所虏,该有多好啊!我不是期望人类灭绝,请你别动气,我的意思是希望现在的人类把所有的生活样式和文化全部忘掉,再一次回到野兽的状态”。翁闹渴望回到原始的野兽状态(野兽世界没有机械文明带来的忧郁,只有动物本能所附带的快乐),并强调应该要忘掉现在人所拥有的“所有的生活样式和文化”,也反映了他排斥都市文化,希望通过寻求原始自我来摆脱焦虑与孤独的生存状态。
翁闹对原始人性的追逐可以落实到爱欲和暴力两个方面。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将人类本能分为生本能与死本能——总结来说,生本能是人类的自我保存与性欲,死本能从内部说是自杀与复仇,向外部看是攻击与暴力。在翁闹的小说中,无论是对生本能或是死本能都有所追溯,由于对外部机械世界的失望而从原始本能、从精神世界来描绘生命的状态,这也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特殊的时间段中翁闹对周遭世界特殊的表达方式。首先,对爱欲的疯狂热衷是翁闹一部分小说中主人公共同的显而易见的特点,同时翁闹更主动描写的并非男女之间热烈的情感状态,而是通过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渴望来表达欲望,如“终于,我的慢慢手伸了出去。我只想稍微碰一下女孩的身体,如果女孩和叔叔都没有发觉,我也未尝不想轻轻将她抱在怀里。”(《音乐钟》)“这个女人还很纯真哪!纯得像雪一样……高挺的鼻子、明亮的眼睛、小动物般惹人怜的薄唇、乌光动人的短发——多美的女人哪!”(《残雪》)“我所爱的女人啊!我要用尽我胳膊的力气将她抱紧,贴着她甜美的唇,那么,当这副身躯与她的肉体合而为一的时候,‘我’才终于能够展现出它完足无缺的容貌!”(《天亮前的恋爱故事》)爱欲的释放作为回归原始人性的一种方式,能够与焦虑、浮躁的末日情绪相抗衡,翁闹在作品中对爱欲的大量描写,更强调了自身难以逃脱这种精神困境。其次,在翁闹的小说中也时常出现一些暴力且具有攻击性的负面场景,如《戆伯仔》中老伯可怕的眼疾、《残雪》中春生对玉枝的情感暴力、《罗汉脚》中的小罗汉脚的车祸、《有港口的街市》中谷子被割断手指的情节、《天亮前的恋爱故事》中“我”常常出现的“发疯”以及“自杀”的念想。暴力作为另一种回归原始人性的方式,翁闹也试图通过“毁灭”来粉碎这种压抑而孤独的末日情绪。无论是疯狂的爱欲,或是自杀与暴力,都是从真正的自我中寻求解脱,从幻灭中获取新生。并且,翁闹对精神世界、对人类本能的探求并非因为刻意逃避现实,而是通过原始的本能来与绝望的末日情绪相抗衡,展现世纪末人类真实的生存状态。
无论是描述世纪末的精神困境,或是探求真实的人性,翁闹的写作意在展现人生内部存在的意义,在他看来,生活并不光明磊落,世纪末所有的生命力被焦虑、阴暗的空气所笼罩,人生的道路充满坎坷。在混乱的时代中,翁闹这种特立独行的写作方式曾遭到不少人的否定,古继堂在《台湾小说发展史》中提到“翁闹作品的主题思想与他所处的敌人疯狂,人民苦难,斗争悲壮的时代相比,是很不相称的,表现出逃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无力和苍白。”但事实并非如此,翁闹对现代文明同样有深刻的反思,对时代有自我独特的见解。他重视的并非是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的现实批判,而是向内探索世纪末环境中人类的精神困境,在他的作品中,对人性与心理的描摹远远多于外部的客观世界。因此,他并非逃离时代,而是将人文知识分子对当下时代、对世纪末这个特殊时间段敏锐的感觉,以崭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注释:
[1]张恒豪:《幻影之人——翁闹集序》,张恒豪编:《台湾作家全集·短篇小说卷·日据时代·翁闹、巫永福、王昶雄合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0年,第14页。
[2]张羽:《寻找台湾“幻影之人”翁闹——兼论翁闹与郁达夫的日本叙事》,2005 海峡两岸台湾文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
[3]杉森蓝:《翁闹生平及新出土作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2007年。
[4]萧萧,陈宪仁编:《翁闹的世界》,台中:晨星出版社,2009年。
[5][19]黄毓婷:《东京郊外浪人街——翁闹与1930年代的高圆寺界限》,《台湾文学学报》2007年第10期。
[6]翁闹:《破晓集》,黄毓婷译,台北:如果出版社,2013年。
[7]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春晖出版社,2010年,第84页。
[8]施淑:《翁闹介绍》,施淑编:《日据时代台湾小说选》,台北,前卫出版社,1992年,第206页。
[9]萧石君编:《世纪末英国新文艺运动》,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65页。
[10]张羽:《寻找台湾“幻影之人”翁闹——兼论翁闹与郁达夫的日本叙事》,2005海峡两岸台湾文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第26页。
[11][16]翁闹:《东京郊外浪人街》,黄毓婷译:《破晓集》,台北:如果出版社,2013年,第231页,第231页。
[12]李进益:《翁闹短篇小说论》,萧萧,陈宪仁编:《翁闹的世界》,台中:晨星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13][23]翁闹:《残雪》,黄毓婷译:《破晓集》,台北:如果出版社,2013年,第200页,第178~179页。
[14]翁闹:《可怜的阿蕊婆》,黄毓婷译:《破晓集》,台北:如果出版社,2013年,第220页。
[15][21][24]翁闹:《天亮前的恋爱故事》,黄毓婷译:《破晓集》,台北:如果出版社,2013 年,第305~306 页,第305 页,第303~304页。
[17]叶衽榤:《两个新感觉作家的欲望都市——重读翁闹与刘呐鸥小说中的都会元素》,萧萧,陈宪仁编:《翁闹的世界》,台中:晨星出版社,2009年,第125页。
[18]黄毓婷:《翁闹是谁》,黄毓婷译:《破晓集》,台北:如果出版社,2013年。
[20]翁闹:《新文学三月号读后》,黄毓婷译:《破晓集》,台北:如果出版社,2013年,第329页。
[22]翁闹:《音乐钟》,黄毓婷译:《破晓集》,台北:如果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
[25]古继堂:《台湾小说发展史》,台北:文哲史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