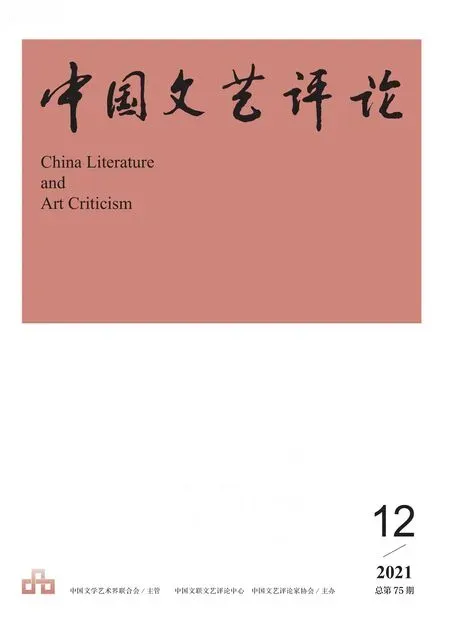“博物馆怀疑论”及其不满:格罗伊斯的辩护
周逸群 朱国华
一、“博物馆怀疑论”:从历史前卫到后现代
作为一座“致力于爱和艺术研究的殿堂”,1793年8月10日正式向公众开放的卢浮宫是公共艺术博物馆的发端,“它是革命时代新冒出的资产阶级国家自己给自己树立的纪念碑”。然而在卢浮宫诞生之时,德•昆西(Antonie-Chrysostome Quatremère de Quincy)就基于“语境论”立场对博物馆提出质疑,认为“博物馆的艺术、艺术品从原初确定的地方向某一博物馆的转移,都意味着打断那种总是存在于天才的创造与社会、艺术与风俗、艺术与宗教,以及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联系”,这也掀起了第一次博物馆怀疑论浪潮。事实上,在博物馆的演化过程中,对它的批驳一直甚嚣尘上。又如,阿多诺在《瓦莱里-普鲁斯特博物馆》一文中指出,德语museal(意为“博物馆的”“文物的”)一词描述的是对观察者而言不再生气勃勃的、正在死亡中的物品,保存它们是因为尊重历史,而非当下的需要。博物馆与陵墓(英文为mausoleum)之间的联系远甚于语音上的近似,博物馆“就像是艺术品的家族陵墓,它们证明了文化的中性化”。一般来说,德•昆西、阿多诺的批评代表了博物馆怀疑论者们最普遍、核心的观点,他们往往指控博物馆使艺术脱离了它原初的社会语境,抽象化为僵死之物。
不过,虽然对博物馆的质疑声始终萦绕其左右,但无论是理论家还是艺术家,博物馆怀疑论者大多是不加论证地断言,从未系统地予以说明或者付诸于艺术实践,这一现象直到历史前卫出现才终止。彼得•比格尔(Peter Bürger)在《先锋派理论》中说到:“随着历史上的前卫运动,艺术作为社会的子系统进入了自我批判阶段”,历史前卫率先对艺术体制发起攻击,冀望摧毁艺术体制,使艺术与生活实践重新建立联系。根据比格尔的界定,艺术体制“既指生产性和分配性的机制,也指流行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决定着作品接受的关于艺术的思想。前卫主义对这两者都持反对的态度。它既反对艺术作品所依赖的分配机制,也反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由自律概念所规定的艺术地位”。可见,艺术体制应从两个层面理解:在现实层面上,艺术体制指“出版社、书店、剧院和博物馆”等组织机构,它们“是个人作品与公众之间的中介”;在观念层面上,艺术体制是使组织机构得以运行的原则、认知,它决定人们对艺术品的接受效果。需要强调的是,机构与观念是二位一体的,博物馆等组织机构与自康德以来围绕着艺术自律观念而构筑的现代美学体系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缔造了隐秘、繁复的共谋结构。如此一来,对艺术体制的批判需在现实与观念层面上同时进行,反对以博物馆为代表的组织机构也是在反对艺术自律之观念,反之亦然。对艺术体制的双重批判从历史前卫贯穿至后现代,就博物馆而言,作为陈列艺术作品的物理空间以及艺术自律观念的现实展演场所,它一直是被攻击的靶心,不时遭到死亡宣判,这实际上是博物馆怀疑论的当代变种。
随着杜尚送展的小便池被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拒绝,博物馆以及其所表征的以个体创造、审美静观、有机艺术品为标尺的现代主义艺术观念被问题化了。即使历史前卫“在一种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功中走向失败”,他们意图摧毁作为体制的艺术却吊诡地使自身作品成为艺术,“非艺术的艺术品”(an artwork of non-art)抑或说反艺术(anti-art)与艺术合二为一,但是体制批判仍然在继续,历史前卫的议题被新前卫延续下来。参照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的观点,20世纪的现代主义艺术可归纳为两种迥然有异乃至彼此对立的艺术风格:形式主义者所主张的正统的现代主义与前卫主义者提倡的与过去决裂的现代主义。形式主义者认为,艺术应该继续追求媒介、形式的纯粹性,坚守力所能及的领域,维系过去的评价标准,以此获得存在的正当性。他们承继了经典先例,是在“时间、历史或者说纵轴上”构思,涵括立体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等艺术运动。与之对立,前卫主义者力图模糊、克服艺术与生活的边界,伸展其社会维度,他们“为了扩大艺术的能力范围,偏爱空间的、共时的或者说横向的轴线”。前卫主义者的现代主义既包括20世纪上半叶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构成主义等历史前卫,也包括20世纪下半叶的波普艺术、极简主义、观念艺术等新前卫。正如皮力所说,二者的区别在于,形式主义的现代主义“是一种自我批判的、自律的、朝向内部的艺术实践,而前卫艺术则是艺术家对于社会的批判、挑衅和自我生存策略。……前者的重点在艺术创造,体现为形式演进;而后者的重点在文化革命,体现为文化政治意识”。就前卫主义而言,比格尔控诉新前卫“将前卫体制化为艺术,从而否定前卫的真正意图”,新前卫不过是历史前卫毫无意义的重复,抗议不再具有攻击性,甚至只是故作姿态,而在福斯特看来,比格尔的论断既有其合理之处但亦失之偏颇。新前卫是一个过于宽泛又过于排外的概念,至少要依据两个特殊时刻加以区分:“其中第一个是50年代的劳申伯格和卡普洛,第二个是60年代的布达埃尔和布伦”。福斯特指出,比格尔对新前卫的诊断仅仅适用于第一波新前卫,不能粗暴地全然否定新前卫,因为第二波新前卫在反思历史前卫和第一波新前卫局限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新前卫(当福斯特笼统地说新前卫时,指的是第二波新前卫)“不是抵消了历史前卫的成果,而是史上第一次执行了它的方案”。对艺术体制的系统分析不是由历史前卫,而是由新前卫完成的。
新前卫是一项苦心经营的集体工程,横跨几代艺术家,而极简主义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论及极简主义,自然绕不开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对它的抨击(贬低为“实在主义”〈literalist〉),《艺术与物性》也被视为“对那个时代极简艺术的最好分析”。弗雷德围绕着“物性”(objecthood)与“剧场性”(theatricality)对极简主义展开分析。弗雷德认为,极简主义对物质材料的极端追求导致其被还原至物的实在状态,极简主义“将赌注全部押在了作为物品的既定特质的形状上,如果还不能说作为某种物品本身的话。它并不寻求击溃或悬搁它自身的物性,相反,它要发现并突显这种物性”,如此一来,本身空洞的物必须借助外部环境,通过剧场式的展示,使观看者获取意义体验。极简主义要求观看者在时间中持续体验,它是一种“无穷性的在场”,而好的艺术品在任何时刻都能够充分地自我显示,“一个单纯的瞬间就足以令他看到一切,体验到它的全部深度与完整性,被它永远地说服”。于是,弗雷德基于形式主义的现代主义立场攻讦极简主义,宣扬不显自彰的艺术品质与价值。在道格拉斯•克林普(Douglas Crimp)看来,形式派拒绝承认场域特定性(site specificity),即意义是由作品与展览现场的动态关系催生的,究其本质是一种唯心主义,“现代主义的唯心主义——艺术客体内部及本身被认为具有固定的和跨越历史的意义——决定客体的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其归属不在特定之处,此种无地方(no-place)在现实中是博物馆”,而极简主义主张的“场域特定性通过对循环流动性(circulatory mobility)的拒绝,对特定场域的归属,来反对唯心主义,揭示被遮蔽的物质系统”。福斯特则称之为“艺术的知觉条件和惯例限制”,在极简主义的知觉分析下,“观者拒绝了形式艺术向来保有的安全的、独立自主的空间,退回了此时、此地;不是要审视作品的表面,寻找其媒介属性的地形分布,而是受到激发去探索在一个既定地点的某个特别的介入所造成的知觉效果”。不满于作品停留在博物馆这一被净化的永恒空间,极简主义标榜艺术的在场性经验,关注艺术在此时此地制造的感性印象。极简主义的艺术史意义在于,它既是现代主义的顶点又是与现代主义的决裂,为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到来铺垫。极简主义对艺术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新定位,在此之后,格林伯格所谓的艺术本质不再重要,后来者念兹在兹的是粉碎艺术的体制界限,否定艺术的形式自主。这正是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在未完工的新泽西收费公路夜行时得到的启示——艺术,“你没有办法给它加上框,只能体验它”。
极简主义作为一种知觉分析旨在反映艺术的语境条件并拓宽对它的种种限制,这影响了后续对于知觉条件的进一步分析,生发出观念艺术的体制批判。根据亚里山大•阿尔贝罗(Alexander Alberro)的考证,“体制批判”(Institutional Critique)作为术语最早出现在梅尔•拉姆斯登(Mel Ramsden)《论实践》(On Practice
)一文,用来描述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政治化的艺术实践,“一种完全不同的基础正是在这一时刻形成,可以由此批判性地介入决定着当代艺术生产和接受的话语和体制”。要而论之,体制批判包括“对于艺术空间的批判(如迈克尔•阿舍的作品),对于艺术的展览惯例的批判(如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的作品),对于艺术的商品状态的批判(如汉斯•哈克[Hans Haacke]的作品)”。以汉斯•哈克为例,《所罗门•R古根海姆博物馆董事会》是汉斯•哈克1974年创作的艺术品,在该作品中,哈克用七张文字档案展示古根海姆董事会成员的财务纠葛,其中部分成员既是文化精英又是政商权贵,他们跨国投资了右翼独裁专政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矿业公司,影响当地政经政策的制定,为正在进行的压迫行为推波助澜。在哈克看来,博物馆绝非中立的艺术万神殿,其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从反思企业赞助到批判政治现实,哈克通过揭露博物馆的政商关系,阐明博物馆内在的权力结构,戳穿艺术体制的政治性,攻击意识形态对艺术的工具化征用。如果说极简主义、观念艺术仍然是在晚期现代主义的谱系中攻击博物馆,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到来则致使对博物馆的质疑达到顶点,代表人物是道格拉斯•克林普。克林普毫不避讳他对福柯知识考古学的信服与接受,认为倘若知识型发生变革,新的权力体制以及与其彼此依存的新的话语会随之出现。在他看来,“我们所理解的艺术,直到19世纪才随着博物馆和艺术史学科的诞生而产生,因为它们与现代主义具有同样的时间跨度”,也正因为此,它们成为现代艺术观念发轫的先决条件。就博物馆而言,它既是现代主义艺术的栖息之地,亦是艺术史的具象呈现。然而由于后现代主义的降世,旧有的艺术机构无法规避地走向灭亡,博物馆注定成为废墟。克林普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一,博物馆不断地排除异质,使艺术按照某种叙事逻辑呈现,构建统一、系统的艺术史,“博物馆的时代与艺术史的时代同时发生”。但是,后现代主义“怎样都行”的观念颠覆了博物馆的同一性叙事,证明博物馆陈列的艺术品之连贯性只是一种浪漫构想,招致现代主义标榜的艺术自律走向破产;其二,“通过复制技术,后现代主义艺术失去灵韵。那种创造主题的虚构让位于赤裸裸的挪用、引用、截取、叠加、复制现存图像。原创性、真实性和现场性,作为博物馆既定的话语本质,被悄然破坏”,复制技术瓦解了筑造于主观性、创造性设想之上的博物馆的概念框架。
二、收藏的内在逻辑:作为第一性的博物馆
对博物馆的反对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博物馆被视为须挣脱的束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既定的艺术世界的封闭圈子之外,在博物馆的高墙之外,成为流行的、有生命力的、当下的”。博物馆的死亡意味着艺术回归现实,再度变得鲜活。然而在格罗伊斯看来,正是博物馆收藏本身的内在逻辑迫使艺术走进现实。
格罗伊斯扭转了现实是第一性的根本前提,认为现实以博物馆为参照,是第二性的。博物馆不比“真实的”现实次要,不是对发生在博物馆之外的现实的被动反映与记录,恰恰相反,现实相对于博物馆是次要的,博物馆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历史构架,现实只有通过与博物馆已有收藏的比较才能被定义。现实是所有尚未被博物馆收藏之物组成的领域,与博物馆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现实是无价值的世俗空间,博物馆则是被赋予价值的、区隔出的文化档案库。以博物馆为参照点,高墙之外的现实世界看起来才是鲜活的,博物馆是观照现实世界的窗口。这也是博物馆的主要功能,“历史中的新的、现实的、鲜活的东西都是通过与‘死亡的’、归入档案的、旧的东西的对比而确定的”。基于博物馆是第一性的认知,格罗伊斯立论道,博物馆拒绝重复存有已被收藏的作品,它们被当作属于过去的死物,仅接受从现实之中、藏品之外选取的东西,某物被收藏的唯一可能是跨越博物馆、进入生活,作为异于博物馆已有藏品的真实而鲜活的新物。如此便造成一个悖论状况:“你越想把自己从博物馆中解放出来,你就越会以最激烈的方式受制于博物馆收藏的逻辑,反之亦然。”
格罗伊斯设置了两组二元对立:“死的”(dead)/“活的”(alive)与“旧的”(past)/“新的”(new),其中“死的”意味着“旧的”,“活的”意味着“新的”。世俗之物与博物馆收藏之物虽呈现为“活/死”关系,但其实质是“新/旧”关系。于是,问题由生成来自现实的鲜活艺术转换为创新。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曾指出,“冷文化”社会浸淫在传统之中,时下和未来的生活由过去支配,人们凭借反复复制过去保持自身文化身份的完整性。格罗伊斯继而补充道,崇尚过去、遵循传统具有正当性的条件是过去的一切尚未被收藏,一旦它们被保护,对已有作品的复制就变得不必要,不再被鼓励乃至被禁止。随着传统被技术手段稳固,人们将会对“新”产生兴趣。格罗伊斯称之为“博物馆禁忌”(museum taboo),“博物馆没有规定新作品必须是什么样子,它只表明了新作品不能是什么样子”。故而,新作品的“新”不是来自与已有作品的事后比较,比较发生于新作品诞生之前,恰是这种比较塑造了新作品,“新颖性的要求不仅意味着没有两件作品是相同的,而且它们之间的差异激发了作品的生产与观众的兴趣”。“新”即是反对重复的他性和变化,是“一种基于差异概念的‘反传统之传统’”,我们“对新的理解必须建立在与旧,以及传统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艺术品对自身进行了历史定位,新之所以为新,是因为它对于文化档案库来说是“新”的。
由是,格罗伊斯强调,创新不是时间性事件,而是空间性事件。在他看来,创新机制的运作是由世俗空间与文化档案库两个空间的互动维系的,世俗空间与文化档案库之间存在着不可消弭的价值层级差异,创新发生的契机便是世俗空间与文化档案库内的事物之间进行的估价比较,它诱发两种层级之间的价值交换,创新旨在使价值发生变化。格罗伊斯提请我们注意,创新往往被视为对已有文化价值的贬损,而非对世俗物价值的提升,产生新的文化价值,但实际上作为创新的必要手段,后者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当杜尚在蒙娜丽莎画像画上胡子并命名为《L.H.O.O.Q》时,《蒙娜丽莎》所表征的文化价值虽遭贬低但未受到切实损坏,在杜尚之后仍然为人称道,价值得到提升的反而是杜尚制作的复制品。也就是说,创新一般表现为世俗物的升值,从世俗空间进入文化档案库。那么,如何才能创新?
显而易见,创新绝非自由、任意的,而是一种策略上的选择。一方面,由于“博物馆禁忌”,选择的世俗物必须迥异于博物馆藏品,与传统典范有着激烈差异,此种“根据美学上的对比、陌生、异域性或是他者性的原则做出的选择,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去迎合由博物馆确立起来的传统而做的适应——但是这种适应所延续的传统不是肯定性的,而是否定性、对照性的”。另一方面,文化传统并非一味地被否定,为了获得美学的完整价值,世俗物以肯定方式指涉文化传统,经由和文化传统建立关联而与经典相提并论。所以,创新不是对文化传统的单纯反叛,其实是“一种否定某种文化传统后再适应传统的行为”,它“将肯定性的和否定性的对传统的继承如此连接在了一起,于是传统的连续性和断裂性便以最大程度上的清晰性和强度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每件能被放入档案库的世俗物的内部总是分裂的,指涉着文化价值与世俗的无价值两种价值层面,在保持各自特征和可辨认性的前提下将二者并置在一起,形成张力。张力越大,影响越大,那些最受瞩目的作品是“那些既有最崇高的文化追求的,也包含极其世俗、无意义和无价值的东西的”。当然,创新始终是事件性的,随着世俗物被纳入档案库成为有价值物,区隔出世俗空间和档案库的价值标准也随之改变,下一次创新就开始了。
格罗伊斯笃信,创新的机制具有普适性,存在于每一次创新活动中。在这里,我们以马奈的《奥林匹亚》和现成品艺术为例,依据格氏的论点解释它们是如何创新的。《奥林匹亚》“竭力想要揭示它与欧洲艺术的伟大传统之间的关系”,该画的人体卧姿与画面构图挪用了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背景刻画则受到戈雅《穿衣的玛哈》的影响。但是,马奈对二者的重复姿态是不同的:对于戈雅,马奈持致敬态度,正面引用了戈雅的“黑暗主义”;对于提香,马奈的重复是挑衅的、反讽的,“传统在《奥林匹亚》中被滑稽化了”。《奥林匹亚》的表现方式(包括形式手法与绘画题材)有别于欧洲古典传统,在当时毫无疑问隶属于世俗范畴:在形式手法上,“提香用深色幕帐进行区隔,以制造空间的纵深效果,而马奈彻底取消了纵深,创造了一个平面化的画面”;在绘画题材上,《奥林匹亚》表现的是“维纳斯”的裸体,这一题材是西方艺术史的母题之一,是学习美术基础知识必需的练习。问题在于,按照惯例以“维纳斯”的裸体作为题材要表现绘画对象的平静状态与圆满身体,勾勒出象征着美的理念的女神,其要旨是得体,而马奈修正了符号能指,女神的幻象破碎了,《奥林匹亚》充斥着力比多(libido)与性暗示。更不能容忍的是,扮演“维纳斯”的女模特是妓女,并且她“没有任何道德的伪饰,她既不悲惨,也不下贱,也没有妓女该有的那种谄媚,相反,她傲慢、自负,她的眼里流露出比男人还要坚定的目光,她用这道目光宣示着自己的离经叛道,还用它注视着观画者,用它挑衅观画者猥琐的欲望”。就这样,《奥林匹亚》一经官方沙龙展出便引起轩然大波,学院的冬烘们为之震怒,对其展开道德审判。
至于现成品艺术,格罗伊斯说到:
当一个文化上有价值的事物和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的事物可以明显地被区分开来的时候,人们会完全自然地在心理上去尝试将这种外部的差异看作是这个“艺术性的”事物和日常事物之间会有价值差异的原因。但是,如果人们一旦不再从外观上改变这个事物的话,那么关于什么是价值发生变化的原则这个问题就变得相当激进了。
文化档案库是基要性的前提依旧成立,这是杜尚在未改变日常事物外观的情况下使其升值的原因。杜尚选择小便池不是自由任意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行为。做出该选择的先决条件是博物馆的存在,小便池与博物馆保存的文化传统有着巨大断裂,站在已被赋予价值的美学风格的对立面。换言之,现成品的产生仍然借助于“形式的特异和世俗的无价值这二者的结合”,它一并直观地呈现文化价值与世俗的无价值这两种价值层面:形式的特异使现成品以先否定再肯定的方式指涉文化传统,现成品一方面异于博物馆已有藏品,另一方面又引起一系列的文化联想;世俗的无价值则表现为现成品是工业大批量生产的复制品。对于现成品来说,文化价值层面和世俗的无价值层面不可能形成有机统一,这种无法相容性既是现成品进入档案库的原因,也是它造成轰动效应的原因。
三、艺术展示机理的嬗变:从偶像破坏到偶像崇拜
博物馆不仅是收藏空间,同样是展览空间。如吴琼所言,如果说“收藏是让物脱离原有语境,展览则是为物建立新的语境,并在新的语境中来定位物的意义。在博物馆对物的展示中,所展示的并非物本身,而是一个被阐释的对象”,博物馆作为展览空间是一个叙述空间,总是根据某一逻辑线索(如年代、流派)讲述艺术的故事,从而引导观众观看。在格罗伊斯看来,博物馆的叙述方式自诞生至今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偶像破坏更迭为偶像崇拜。
我们知道,艺术品起源于某种礼仪,最初是巫术礼仪,后来是宗教礼仪,艺术品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受宗教支配,被视为偶像圣物,这一境况直到启蒙运动时期博物馆的出现才得到彻底扭转。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说道:“艺术是否降临人间,就看是否产生一块理念与实体不可分割的地盘,同时属公民和市民的地盘”,艺术需要从教堂或宫殿中分离出来,拥有一个独立存在的特定场所,博物馆便是这一场所。博物馆虽然是艺术的万神殿,是多时代、民族、地区的创造被共同收藏的场所,但它“修建的目的在于取消圣礼,因为渎神者试图施压使其革新”,祛除艺术的神性。当静物画、风景画放置在宗教画之旁展出时,博物馆推崇的就不再是上帝的至高无上,而是人类的主体自由。在这种温和中性的氛围下,博物馆把象征性的偶像符号消解为纯粹的艺术品,它们被剥夺了故有的宗教意义以及相伴随的功能性(本雅明所说的筑基于礼仪之上的“原始的、最初的使用价值”),作为静观的审美对象存在。艺术如其所是,只是艺术。作为偶像破坏行为,彼时博物馆对物品的展出显然是一种制造艺术的手段,它将“活的”偶像降格为“死的”艺术。
随着杜尚命名为《泉》的小便池进入博物馆展出,博物馆的空间语法发生了翻转,“圣物曾经被贬值以生产艺术;相比之下,今天,俗物被赋值成为艺术”。现成品艺术被宣扬为20世纪偶像破坏行为的典范,杜尚在多个场合强调偶像破坏是现成品艺术的重要维度,他曾对《L.H.O.O.Q》作出如下定义:“一个现成品艺术和偶像破坏式达达主义的结合体”,新达达主义者乔治•马修纳斯(George Maciunas)1973年为激浪派和其他前卫艺术梳理脉络时也明确将“拜占庭偶像破坏”列为源头之一,此类观点在艺术史家那里亦不鲜见。格罗伊斯对于现成品艺术与偶像破坏的关联并无异议,但在他看来,这里的“偶像破坏姿态被制定成一种艺术手段,与其说是为了消灭旧圣像,不如说是为了制造新图像——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新圣像和新偶像”。博物馆已取代教堂成为新的神圣之地,拥有赋格的资格,反偶像的物品进入展览空间只会变成新的偶像,不可避免地被经典化。博物馆不再需要破坏圣物的偶像价值以使其成为艺术,转变为承认普通物品为艺术品。普通物品进入博物馆意味着价值的施予,而非剔除。这样一来,博物馆也就“从启蒙运动激发的偶像破坏之地变成浪漫的偶像崇拜之地。把一件物品作为艺术展示出不再是对它的亵渎,而是圣化”。
由于现成品是直接取自世俗空间的普通物品,被置于有价值的艺术语境中成为艺术,致使艺术品与普通物品之间的差异不再是可视的,所以更加需要博物馆提供的保护。格罗伊斯将此种差异称为“超越差异的差异”(difference beyond difference),博物馆则是制造和展示“超越差异的差异”的方所,“那些与环境没有充分的视觉差异的艺术品只有在博物馆中才是真正可感知的。艺术前卫的策略,即消除艺术品与世俗物之间的视觉差异,因此直接导致了博物馆的建立,从制度上保护这种差异”。只有在博物馆中,普通物品才能享有它在日常生活中无法享有的关注,甚或说,博物馆传布的福音不是为天才创造的、内含原真性的作品准备的,而是为那些日常的、平凡的、若非在博物馆之中就会在高墙外的生活中沉寂的物品准备的。对高妙的吉光凤羽而言,它们被认为是独立于世、不证自明的,即使身处俗世也会被尊崇、欣赏,博物馆的主要功用是使之不受到物理损坏,其他方面几无裨益;相反,越是不值得提供担保的普通物品,博物馆提供的担保越有效。正是因为艺术品看起来和普通物品无法区分,才需要博物馆给予确证,博物馆“提供了将崇高引入平凡的可能性”。
那么,“圣化”(consecration)应该作何理解?在格罗伊斯看来,“圣化”即是“灵韵化”,“博物馆对物的展示就像是物的一次盛装演出,不论是悬挂在墙上,还是放置在玻璃罩内,它都处在某个类似神龛一样的位置。基座或画框、射灯、标签、解说牌,这些构件的功能不只是为了让物及其‘知识’的呈现变得更加明确可见,更是为了赋予物一种特别的‘灵韵’,一种崇高的品质”。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本雅明用“灵韵”(aura)概念标示原作与复制品之间的区别,尽管复制品可以抹除与原作物质层面上的差异,但是灵韵外在于物质属性,复制品缺乏原作所具有的灵韵。本雅明认为,灵韵应以原真性(authenticity)视之,原真性是由此时此地性(now and here)构成,“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此时此地性,即它在所处之地独一无二的此在。但唯有凭借这独一无二的此在而不是其他什么,作品在其存在过程中所隶属的历史才得以出现”。基于此,格罗伊斯引申道,灵韵是“艺术品与它所处场所的关系——与它外部语境的关系”,原作具备灵韵是因为它居于特定的场所,拥有由此而来的历史性,原作作为独特之物被镌刻进历史中,复制品缺乏灵韵则是因为它是“悬浮的、无场所的、非历史的”。灵韵并非原作的内部属性,而是由外部空间增值的。格罗伊斯称之为“灵韵的拓扑学”(Topology of the Aura),原作与复制品之间的区别完全是一种拓扑式的,复制某物就是将它“从它的特定场所抽离,使其去域化——复制把艺术品转移至拓扑空间漂移不定的流通网络中”。从此逻辑出发,当原作与复制品的差异仅是拓扑、语境上的差异时,对原作或复制品的确认便取决于“做出这个判断时的所处情境”,这意味着不仅原作可以去域化(deterritorialize),从中制造复制品,复制品也可以再域化(reterritorialize),升格为原作。这是一种“再生产变成生产过程的转变”,复制品倚仗历史语境的赋予变成原作。博物馆是使复制品再域化获得灵韵的场所之一。格罗伊斯指出,博物馆的运作是一种“复制的逆转”(a reversal of reproduction),它“从一个匿名流通的,不被注意的开放空间中拿取一个复制品,将其——如果只是临时的——放进一个牢固的、稳定的、封闭的语境中,这个语境被明确地定义为‘此时此地’”。博物馆为复制品提供一块场所,亦即一种历史性事件的此时此地性,复制品由此获得了原初的、有生命的、历史的灵韵,博物馆让复制品变成原作。
四、结语
对格罗伊斯来说,捍卫博物馆至少有着两方面意义:
其一,博物馆是对审美平等的重新肯定。如前所述,博物馆怀疑论者认为,开辟一条艺术回归现实生活从而变得自由的道路只能通过摧毁博物馆来完成,博物馆是“一个跟物质上的陵墓差不多的精神上的石棺”。可在格罗伊斯看来,这种呼声虽然现在已非常普遍,但其内里实际上发生了翻转——“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流行品味是由博物馆定义和体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针对博物馆的抗议都是对艺术创作主流规范的抗议,同时也是新的、开创性的艺术得以发展的基础”,然而在现今时代,博物馆已经被剥夺了它的规范作用。随着大众文化的泛滥,社会主流品位是由媒体催生并引导的,大众的艺术观念来自广告、电子游戏、好莱坞大片等,这导致“目前对博物馆的抗议已不再是以审美平等的名义反对规范品味的斗争的一部分,相反,其目的是稳定和巩固当前的主流品味”。在今天,从博物馆束缚中挣脱的呼吁,相当于要求将艺术包装并商业化,使之屈服于大众媒体所制造的审美规范。因此,捍卫博物馆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曾经存在的审美平等的艺术理想以及为此付出的努力,继而抵抗主流品味的独裁,拒绝审美褊狭。
其二,博物馆有助于确定何为真正新的、关于当下的真正的当代(genuinely contemporary about the present)。拆除博物馆的高墙常常被赞誉为对当下激进的开放,现实却是,由于文化记忆的缺乏,对何者为新、何者为当代的盲目随之而生,人们习惯性地从时尚的角度讨论新和当代的问题。作为媒体产物的时尚,因为全球媒体市场的流动性过快、种类过多,人们无法将今天手中的物品与旧物作比较,有效地区分新与旧。在媒体的裹挟下,人们既会感到被新事物无情地轰炸,又会永久地目睹同样的事物回归。“只有博物馆才能让观察者有机会区分新与旧、过去与当下”,博物馆是历史记忆的储藏室,那里保存并展示过时的陈旧之物,提供了比较框架,能够进行系统的历史比较,让我们得以区分什么是真正新的、当代的。
当我们回观中国时,格罗伊斯对博物馆所作的辩护也颇具阐释力。就中国而言,中国当代艺术自坠地之日起便遭到本土与世界、传统与当代的双重纠缠,这使得中国当代艺术呈现出清晰的混杂性特征,导致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本位主义与势不可挡的普适主义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国当代艺术就在这种相互作用下反复摸索,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挪用格罗伊斯的观点来看,在中国,博物馆作为稳定的历史空间,其功能在于为双重的纠缠树立一个坚固的判断尺度(尺度也会通过发生于已有艺术收藏基础之上的持续的艺术创新而更新),继而提供审美规范以及何者为新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