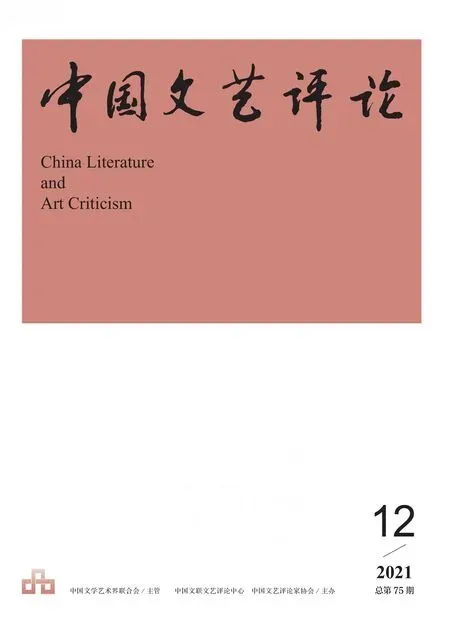余光中诗作与诗论表现的中华文化自信
黄维樑
一、向现代主义诗歌的“晦涩虚无”说再见
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大思想潮流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清朝到了末叶,国家贫弱落后,百姓泰半愚昧无知,而西方经济发达、船坚炮利、文化兴旺。众多忧患之士,为救国救民,要迎来“赛先生”和“德先生”;反过来,“孔家店”被打倒,线装书应扔进茅坑。知识界提倡“现代化”,也就是“西化”,甚至是全盘西化。在文学艺术方面,春柳社演出文明戏,胡适宣示旧体诗的各种“决不能”;文学、文化之根的方块字,甚至面临被废掉的厄运;欧美的诗歌、小说、戏剧以至文学理论、文化理论,形形色色全被引进神州大地。举例而言,1922年艾略特(T.S. Eliot)晦涩难懂的《荒原》(“The Waste Land”)有多个中文译本,其1917年发表的《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中文译本也有十多个。
1949年之后的中华学术文化界,西化之风继续不断吹袭,文学艺术的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包括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在台湾,在香港,1980年代之后在大陆,逐一或同时进入文艺场域,左右了无数作者和受众的口味。在有着两千多年诗学传统的中国,众多学者只用时新的西方理论,如心理分析、神话原型论、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这些,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患了“失语症”。西化之风劲吹,吹倒中华文化的大树小树。有知识分子忍不住了,向诗歌的“晦涩虚无”说再见,和语言的“恶性西化”划界限,这人就是余光中(1928-2017)。
余光中原籍福建永春,出生于南京;在南京和重庆读小学、中学,中英文俱优,先后在南京、厦门、台北的大学读的是外文系,对中西文学、文化有深厚的认识。可他在取西经的时候,并没有忘记中华,更没有一面倒地投向西方,他对中华有信心。余光中诗文双绝,又写文学评论,又从事中英文学作品翻译,著述非常丰富,影响深远。本文探研其诗作与诗论所表现的中华文化自信。
余光中在1949年3月初考入厦门大学外文系,读了一个学期。期间他在当地的报纸发表了六七首新诗,这段日子正是他诗歌创作之春。他是永春人,诗歌让他一生永葆生命之春。在厦门几个月之后,余光中与家人到了香港,失学的青年也失意。1950年5月,他乘船抵达台湾,9月入读台湾大学外文系,又写起诗来。1951年5月,余光中写的《序诗》自称为“晚生的浪漫诗人”,要和“表哥”雪莱(Percy Shelly)和济慈(John Keats)争胜。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外文系学生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仰慕。余光中曾表示一生最喜欢的西方作家是济慈,《序诗》提到济慈,两年后即1953年的《吊济慈》则专为其“逝世百卅二周年纪念”而撰。他誉济慈为“天才”,“像彗星一样短命的诗人/却留下比恒星长寿的诗章”。这当然是对这位西方诗人极高的评价。他虽喜欢英诗,创作受到英诗很大的影响,但中国的诗歌在他的心中早就生了根。
二、 “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余光中对屈原的颂赞,比对济慈早了两年。1951年的端午节,他发表了《淡水河边吊屈原》,称颂其人格的“洁白”,有“傲骨”,感动了“千古的志士”。人格之外,余光中还对屈原的诗歌艺术非常推崇:“但丁荷马和魏吉的史诗/怎撼动你那悲壮的楚辞?”换言之,屈原与西方古代的大诗人相比毫不逊色。屈原是滋润后学的水源:“那浅浅的一弯汨罗江水/灌溉着天下诗人的骄傲!”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天下诗人”,可夸张地解释为包括全世界的诗人。
说说屈原和汨罗江这个典故。2005年,湖南省岳阳市举办端午节祭屈原盛典,余光中从台湾来赴会,主持活动;长沙诗评家李元洛参与其间,事后为文记述:汨罗江两岸“簇拥”着约30万人,听余光中朗诵新写的《汨罗江神》,而江畔“许多横幅上书写的是‘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的字样”。李元洛追查这个句子的来源,发现出自余光中1976年6月写的《诗魂在南方》,其结语正有“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这十个字。重读余氏诗文,笔者发现这“十字真言”或这样的词意,在余光中的作品中出现了很多次。例如,199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文学研讨会上,他的主旨发言题目就是《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如果要为此语溯源,其源头显然就在1951年《淡水河边吊屈原》这首诗里。写此诗的时候,余光中抵达台湾大约一年。他想念忧国怀乡的屈原,且特别提到地理上远离台湾的汨罗江。这隐约有一种乡愁在里面,既是家国地理上的乡愁,也是文学的乡愁。
屈原是中国诗歌之祖,屈原之外,余光中还吟咏李白、杜甫、苏东坡、李清照等古代诗人,或论述李贺、龚自珍等历代众多诗人的作品,表示对中国文学的欣赏、赞美和受益。他的这些咏怀古代诗人的诗,或豪迈,或沉郁,或旷达,收获过很多掌声。非常著名的《寻李白》(1980年作)有这样的一段:
树敌如林,世人皆欲杀
肝硬化怎杀得死你?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从开元到天宝,从洛阳到咸阳
冠盖满途车骑的嚣闹
不及千年后你的一首
水晶绝句轻叩我额头
当地一弹挑起的回音
其中大气的“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几行,喝彩者、征引者无数。“不及千年后你的一首/水晶绝句”之说,更极言李白诗的不朽魅力。余光中读英诗、教英诗、译英诗、评英诗,笔者却未曾看到他对英诗有这样高度的赞誉。他有两首诗专写杜甫,1979年的《湘逝》对晚年诗圣遭遇寄予无限的同情;2006年写的《草堂祭杜甫》,则谓古诗人一生虽苦,作品却光照万代:“安史之乱最憔悴的难民/成就历史最辉煌的诗圣”。《文心雕龙》首篇首句是“文之为德也大矣”,余光中称颂杜甫,说其诗的文化功德有如是者:“安禄山踏碎的山河/你要用格律来修补”。2016年夏天余光中跌倒受伤颇重,自此身体转弱。此年诗翁88岁,可能感到来日无多,乃尽量奋笔疾书,倾吐未了的心声。2017年1月,他写了《诗史与史诗》一文,开篇即曰:
杜甫的诗,我每读一首,都在佩服之余,庆幸中华民族出了如此伟大的诗宗。……杜甫有诗史之誉,但学者每以他未曾写史诗而引以为憾。现在我要挺身为他辩护,肯定他一生写了那么多诗文,合而观之,其实也可称史诗。
经过一番论证,余光中在文末总结道:“‘诗史’(即杜甫)可谓创作了‘史诗’,可列于国际的史诗而无愧。”
流沙河1988年撰文评述余光中的诗,说这个时候他已萌生“向晚意识”,不到60岁时已如此,八旬之后应该更甚。一生亲炙中英诗歌的老学者,2014年秋天写的《半途》,回顾一生,至少是大半生,体会晚景,发现“远古/三闾大夫,五柳先生,大小李杜/……近得像要对我耳语”。请注意,《半途》提到屈原、陶潜、李白、杜甫之外,还在诗末尾提到苏轼;西方的呢,除了荷兰画家梵谷,没有其他,连他最欣赏的西方诗人济慈也“见外”。余光中生命之冬的思维,萦绕着的是他所尊所敬至圣至贤的中华诗宗。他对中华的诗歌文化一向肯定,对其艺术价值一向充满信心。
三、为什么要和晦涩难懂的现代主义诗歌告别?
本文开首提到“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一语,正是台湾1953年纪弦等人创办《现代诗》杂志时的宣言。他们写诗,要把现代西方的诗移植过来,因为西方的诗才好、才合潮流;他们不要继承中国诗的传统,因为它落伍了。这是全盘西化或接近全盘西化的论调。改革开放伊始,很多内地诗人或爱上朦胧或染上晦涩,一切向西方看齐。流沙河描述当时的情景,是那些新秀诗兄,穿必喇叭其裤管,言必称引艾略特。有在朦朦胧胧中获得明显盛誉的诗人,被问及对待中国传统文学态度时,竟答以不清楚传统更不受传统影响。这类人可谓为黄皮白心的“香蕉诗人”。
要说明崇洋骛新的严重程度,不能不举余光中和洛夫之间的《天狼星》事件。余光中1952年从台湾大学毕业,从事翻译工作,后来在大学任教。1958年他得到留学美国一年的机会,赴爱奥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进修,研习文学、绘画等艺术,对当年盛行的现代主义有第一类接触;这以后两三年间发表的诗,也带点“浪子”气味。所谓“浪子”,乃相对于“孝子”而言。浪子趋附西方文艺,孝子固守中国传统(“浪子”与“孝子”是余光中当年文章中所用的比喻)。余光中1961年发表的长诗《天狼星》,就有点“浪游”的痕迹。
1949年后,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依赖美国,其文化也顺势影响到台湾。洛夫在西洋弄潮,写出其前卫的《石室之死亡》《手术台上的男子》等篇,同时对东方同行写的《天狼星》加以批判。批判什么呢?竟然是:余光中的《天狼星》“面目爽朗,脉络清晰,(因而)诗意稀薄而构成《天》诗失败的一面的基本因素”。洛夫这篇《天狼星论》长文还指出:“在现代艺术思想中,人是空虚的,无意义的……研究人的结论只是空虚,人的生活只是荒谬”;可是余光中的《天狼星》对人的写法并非如此,因而此诗“是必然失败的”。台湾大学的张健,旁观事态,惊讶于洛夫的评论,认为洛夫所为是“观念中毒”的表现。余光中的惊诧应该过于张健,他奋笔直书写了回应长文,题为《再见,虚无》,决然与西方语言晦涩、思想虚无的现代主义诗歌告别。此外,1962年他发表《从古典诗到现代诗》一文,写道:
我看透了以存在主义(他们所认识的存在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以超现实主义为其表现手法的那种恶魇,那种面目模糊,语言含混,节奏破碎的“自我虐待狂”。这种否定一切的虚无太可怕了,也太危险了。我终于向它说再见了。
他这里所写,用西方比较时髦的说法(笔者本人对西方的种种,一向择其善者而用之)则是:余光中当年解构了西方关于诗歌创作的霸权话语。
为什么要和晦涩难懂的现代主义诗告别?先略说现代主义的来源。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破坏极大,战后西方众多知识分子对其文化产生幻灭感,心态灰暗;加上科学君临天下,人文的学者、作者为了有所创造,争取与科学具同等地位,乃狂力颠覆传统,而变化出新风新潮。中华的学者、作者,一直自卑于本身国家文化的落后,乃唯西化是务,事事跟风,成为“后学”,其“创作”也就颠覆传统起来,晦涩难懂起来。这是十足的东施效颦。
言为心声,诗人写作,当然都希望与人沟通、引起共鸣,作品传诸长远。然而,现代主义式的颠覆性写作却使其传播困难重重,以至不可能。吕进有“诗歌绝不是私歌”之说,认为诗人发表作品,作品“最终应该从诗人的内心进入读者的内心”,能如此,则传播成功;反过来说,诗人的“私语化”书写会大大“影响传播”。我们知道,现代主义的诗,其本色正是支离破碎、形同梦呓的个人化窃窃私语。梁笑梅也从传播学的观点,讨论余光中的诗如何广获读者“接受”:余氏作品“充实、明朗”;他不同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诗人,这些人“追求零散的思维、瞬间的感觉,记录‘自动语言’”,所作和读者沟通不了,因而“失去了民众”。
现代主义晦涩难懂的东西,至今存在,至今为人诟病,也至今有“拥趸”。余光中数十年来反对这样的东西,常常口诛笔伐。他、向明和笔者曾在台湾担任过好几届文学奖的诗组评委,我们发现大量参赛的作品,实在解读唯艰。十余年前的一届,余光中和向明有下面的评语(笔者当时把余光中的几份评语影印保存了):“意象跳得太快,甚至互相排斥”;“太晦涩”;“太杂太繁”;“读了三遍,仍不明所以”;“取象怪异,如入洪荒,乱相毕露”;“非常异类,难寻脉络”。笔者写的评语和他们同调甚至“同文”。2010年10月,余光中在高雄中山大学一个文学研讨会上,更针对新诗说了重话,笔者亲耳听到:“什么大报设的现代诗奖,我不再做评判了。现代诗沉沦了,我不再读现代诗,宁可读古老的《诗经》《楚辞》!”
盲目崇洋的东西,使他气愤,使他反感,以致使他失去对现代诗的信心——反讽的是,他自己写了几十年的新诗或谓“现代诗”(当然他写的现代诗绝不一样)。他的信心在中国的古典,因此才声称“宁可读古老的《诗经》《楚辞》”!有深厚雅正鉴赏力的读者,阅读李白、杜甫、苏东坡、李清照等古代作品,或西方19世纪及以前的经典诗歌,认识到古人的诗法、诗艺,才是正道。以篇幅颇长、情意沉郁的老杜七律《秋兴八首》为例,尽管内容古今驰骋、场景转换、人事众多、意象纷繁,但绝不支离破碎,绝不面目模糊,它有可解的主题、明晰的脉络、严谨的结构。须知道,诗的题材和主题,诗人可自由选定;诗的形式、诗的艺术,有其亘古传下来的普遍性规律。余光中对中华古典诗歌的艺术法则和价值充满信心。
四、“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紧义山所织锦”的美丽中文
1960年代批判了“恶性西化”的诗论,余光中回顾传统,在东方滋长出朵朵莲花,就是诗集《莲的联想》中那些被他称为“新古典主义”的篇章。他维护中国优良的传统,汲取西方文学的营养,但剔除西方现代文学中的“恶性”元素,“守正创新”地与缪思(Muse)交往,继续从事新诗创作。上文已举出了他所写的《寻李白》等诗,说明其诗的中国文化特质,说明其表现的中华文化自信,以下就此再加申论。
Muse多中译为“缪思”,为希腊神话中掌管诗歌、历史等的女神。余光中作品集的书名,有一本是《左手的缪思》,另一本是《敲打乐》,两者题目都西化。另一方面,书名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比前一类书名多得多,如《掌上雨》(来自唐代崔颢诗句“仙人掌上雨初晴”)、《逍遥游》(来自《庄子》)、《鬼雨》(李贺诗句“鬼雨泣空草”)、《举杯向天笑》(李白诗句)、《井然有序》、《白玉苦瓜》、《五行无阻》、《紫荆赋》(“赋”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文体)、《藕神》(讲的是李清照)、《蓝墨水的下游》(这里暗含屈原和汨罗江之意)等等,都有中国的典故,或用的是中国的成语。他持守中国文化。
余光中在重阳节出生,自称“茱萸的孩子”(傅孟丽写的《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即以此为名)。“茱萸”典出中国古代传说,他的出生日子就离不开中国文化。他除了十年在香港任中文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外,其余几十年都在台湾的外文系任教,他的英美文学修养深厚。其论著名字(包括书名和长文题目)有中西兼顾的,如《从徐霞客到梵谷》《龚自珍与雪莱》等,但无疑以涉及中国的为主。他翻译英美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种文类,但他以诗以文咏叹西方诗人的,寥寥只得沙浮、莎士比亚、济慈几个,吟咏中国的则多不胜数。关于屈原的诗,他写了约十首,李白的至少有三首,杜甫的至少有两首,此外还有关于陈子昂的、王维的、苏东坡的、李清照的,如此等等。一句话,这位外文系教授一生安的是一颗中国心。
为什么吟咏这些中国传统的诗宗文豪?因为余光中对他们及其作品,有感怀有喜爱有敬意。他吟咏中国历代杰出、伟大的作家,他称颂中文的美丽。笔者经常引他一句赞美中文的话。余光中在南京出生,曾就读于金陵大学(后来的南京大学)。2000年重阳节,72岁的他应邀访问南大,发表演讲,一年后撰写《金陵子弟江湖客》记述其事。演讲时他诉说自己对中文“这母语的孺慕与经营”,这母语是“仓颉所造许慎所解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紧义山所织锦雪芹所刺绣的”美丽文字。他一生坚毅地、喜悦地应用、经营这样的文字。
余光中写诗有快有慢,神来之笔一挥而就,与“含笔腐毫”式苦吟,两种情景都存在。他写诗时巧心经营,使读者得以享受其无尽的佳篇隽句;其散文也精彩迭出,更有“余体”之誉。随便举其美文一段为例。他这样描述从事创作的原由:“我写作,是迫不得已,就像打喷嚏,却凭空喷出了彩霞;又像是咳嗽,不得不咳,索性咳成了音乐。”他早年为创新散文而发表的主张,论者多知晓:
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在这一类作品里,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他汲取西方文学的营养,但拒绝“恶性西化”,他有信心美丽的中文能让他挥洒出璀璨的诗文。
五、《当我死时》:“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余光中用左手写散文,用右手写诗。“诗是余家事”,是他几种文类中的至尊;他用心以至苦心淬炼挥洒,成绩灿然伟然。这位诗宗文豪一生写诗一千多首,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历史元素丰富,中华各地的社会、文化各种题材包罗广袤。这里举其1966年2月写的《当我死时》,首先略析其写法,看他所树立的诗歌艺术范例;其次看他怎样写当时一个中华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先引述此名诗如下: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
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
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
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瞭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
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
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他反对台湾现代主义诗“晦涩难懂”的写法,这首《当我死时》贯彻他一向明朗(明朗而耐读)的诗风。1966年,余光中在美国密歇根州一大学当客座教授,身处异乡,非常怀念阔别17年的祖国,写了此诗。本诗的时空背景交代清晰,情意转折——祥和、满足、感叹、希望、怀想——有脉络可循,意象丰盈而眉清目秀,可读可解,写法简直是和西方盛行、东方趋附的现代主义破碎支离晦涩作风“对着干”。西方古典诗歌不是破碎支离晦涩的,中国古典诗歌更非如此。
余光中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写法有信心有鉴赏力,他行走在诗歌的高光大道,即讲究形象思维,讲究音乐性,有主题,结构完整,脉络清晰。余光中不排斥西方,《当我死时》援用的正是西方的经典诗体十四行诗(sonnet),这西洋的酒瓶,装的是中华的佳酿。余光中一生用大量的作品为实际例证,建构了一种“半自由半格律”的新诗体式,笔者认为这方面的诗学成就,堪与唐代杜甫的确立五七言律诗相比。余光中建立的诗法,可说是基于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自信,凭着这份自信,他抗拒了西方来势凶猛的现代主义。
《当我死时》在诗歌形式、诗歌艺术之外,还呈现了对国家的信念。“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这是余光中对家国的无上热爱和赞美。母亲,在这位诗人心中,就是乡土;《乡愁四韵》(1974年作)的末节写道:“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这一节可说是余光中《腊梅》(1968年作)中“想古中国多像一株腊梅/那气味,近时不觉/远时,远时才加倍地清香”句子的加强版。诗人希望死后葬在大陆,这反映了很多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要叶落归根;因为爱这个国家,其生命之根在这个国家。
六、“民族的意志永远向前”,向太阳
余光中的母亲就是中国,就是大陆。1974年他写的《白玉苦瓜——故宫博物院所藏》,笔者发表过长文详加析论,分明也有此情意。《当我死时》和《白玉苦瓜》的庄重深情表白之外,1998年发表的《从母亲到外遇》一文开玩笑谈“四个女性”时,其意不变:他认为“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他曾戏言自己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四个女性”说早有“前科”。)无论如何,说大陆是母亲,这是非常认真的。他爱这个母亲,不论她遭受过多少横逆不幸。1971年发表的《民歌》是一篇动荡时代对民族信心的宣言:中华精神不朽!2017年12月余光中逝世后,中央电视台的《朗读者》节目播出诗人在世时对此诗的朗诵,朗诵前他说:“这首诗是献给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民族,一代传一代,不朽的精神”。这首诗的知名度,大概仅次于《乡愁》,这里不引述了。
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余光中有或深沉或激越的慨叹,但他坚信国家会走向光明。1968年余光中所作的诗《有一个孕妇》有注释:他认为“下一代定比我们幸运,一个富强康乐的中国迟早会出现”。1986年,哈雷彗星“来访”地球,天文知识丰富、常常仰观星象的余光中,眼观难得出现的天象,心怀萦绕不绝的爱国情。这76年一巡回的彗星,又名“扫把星”,它出现时“带来恶梦、战争、革命、瘟疫与横死”;余光中为哈雷辩解,所谓天灾实在是人祸。下次来访时,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欢呼哈雷》(1986年3月作)这样结尾:
下次你路过,人间已无我
但我的国家,依然是五岳向上
一切江河依然是滚滚向东方
民族的意志永远向前
向着热腾腾的太阳,跟你一样
文化是一国的根基。若一国的文化博大深厚,历史上有辉煌强盛的时代,则虽然经历动乱苦难,应能拨乱反正,重至昌明。余光中对中华文化具有信心。1949年7月,他随母亲离开厦门赴香港,在香港逗留一年后到台湾,至1992年9月应邀从台湾赴北京讲学,和大陆分离了43年。此后二十多年,一直到离世,他参访大陆不下数十次。1995年厦门大学校庆,他应邀返回母校参加庆典并讲学,回台后写了《浪子回头》一诗,其中感慨万端的“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成为众人传诵的名句。1992年之后,返回大陆次数多了,亲闻目睹的事物多了,2002年6月他在《新大陆,旧大陆》的末段这样说:
是啊,我回去的是这样一个新大陆:一个新兴的民族要在秦砖汉瓦、金缕玉衣、长城运河的背景上,建设一个崭新的世纪。这民族能屈能伸,只要能伸,就能够发挥其天才,抖擞其志气,创出令世界刮目的气象来。
回顾上面引述过的1968年所作《有一个孕妇》的注释(余光中认为“下一代定比我们幸运,一个富强康乐的中国迟早会出现”),他的“中华文化自信”显然并不虚妄:他先是预言,后来目睹了实在的新气象。
七、余光中“以中国的名字为荣”,以自己的名字……
余光中怀有中华文化的自信,但他绝对不是个“国粹派”;他爱中国文化,也“哀”它。1966年2月他写的《哀龙》,“所哀者乃中国文化之老化,与当时极端保守人士之泥古、崇古”;同月所写的《敲打乐》,涉及对“我们文化界的抱残守缺”的批评,以及对“整肃了屈原”的责难。对于西方文化,他没有无端的排斥,只反对中华诗人盲目跟风西方现代主义的诗。余光中翻译《梵谷传》、王尔德的喜剧、海明威的小说、济慈的诗;他欣赏西方的音乐、绘画,为此写过许多相关的评论;他喜爱驾驶西人发明的汽车,在美国的公路高速甚至超速驰骋,他喜欢西式的牛奶和蛋糕早餐。然而,中华文化是他的根。西潮汹涌,甚至向东卷来时势如海啸;余光中在《从母亲到外遇》中激越地说:“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以本文重点论述的诗而论,现代主义的极端西潮是个例子。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等中国经典作家救了他,使他不致于“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在兼采西方之长之际,余光中守护中华诗学、守护中华文化的立场坚定。
以其天纵英才与毕生勤奋,“与永恒拔河”的余光中,其五色璀璨之笔成就了文学伟业。二十多年前,笔者曾这样概括余光中创作的成就:
余光中的诗篇融汇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题材广阔,情思深邃,风格屡变,技巧多姿,明朗而耐读,他可戴中国现代诗的高贵桂冠而无愧。紫色有高贵尊崇的象征意涵,所以说他用紫色笔来写诗。
余教授的散文集,从《左手的缪思》到《隔水呼渡》,共十多本,享誉文苑,长销不衰。他的散文,别具风格,尤其是青壮年时期的作品,如《逍遥游》、《望乡的牧神》诸卷篇章,气魄雄奇,色彩灿丽,白话、文言、西化体交融,号称“余体”。他因此建立了美名,也赚到了可观的润笔。所以说,光中先生用金色笔来写散文。
文学评论出于余先生的另一枝笔。在《分水岭上》、《从徐霞客到梵谷》等书和其他文章里,他的评论出入古今,有古典主义的明晰说理,有浪漫主义的丰盈意象,解释有度,褒贬有据,于剖情析采之际,力求公正,效黑面包公之判断。光中先生用黑色笔来写评论。
余教授又是位资深的编辑。《蓝星》、《文星》、《现代文学》诸杂志以及《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我的心在天安门》等选集,其内容都由他的朱砂笔圈点而成。他选文时既有标准,又能有容乃大,结果是为文坛建树了一座座醒目的丰碑。他批阅学生作业,尤其严谨。光中先生用红色笔来编辑文学作品。
第五枝,是余教授的译笔。这枝健笔挥动了数十年,成品丰富无比。他“中译英”过中国的现代诗;也“英译中”过英美的诗歌、小说以至戏剧。他教翻译,做翻译奖评判,主张要译原意,不一定要译原文。他力陈恶性西化的翻译体文字之弊,做清通多姿汉语的守护天使。在色彩的象征中,蓝色有信实和忠贞的寓意。光中先生用蓝色笔来翻译。
五色之中,金、紫最为辉煌。他上承中国文学传统,旁采西洋艺术,于新诗、散文的贡献,近于杜甫之博大与创新,有如韩潮苏海的集成与开拓。
现在如果要“修订”对其成就的评价,那自然是“五彩+”了。
“文化自信”是近年的热词。当代的中华知识分子,在认识中国古代人文与科学各方面的辉煌表现、在感知目前国家经济、科学、民生、文化各方面的飞跃发展之际,自应秉持这个理念。本文述论余光中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固然是为了写文章“与时俱进”,但绝无“为文造情”(《文心雕龙》语)之处。余光中并非“国粹派”,知道中国古今多有不美不善的人事物,却一生衷心守护中华文化,笔者也如此。笔者早在读大学时期,就尊崇《文心雕龙》,应用其理论于实际批评,多年来更致力让“雕龙成为飞龙”;笔者早在读大学时期,就为文推崇具中华文化自信的余光中。
至于余光中,上文已纵横多方面对本文的主题加以阐释。文章之末,笔者补充引述他一些文字。1969年7月他41岁,在第三度去美国的前夕写的《蒲公英的岁月》,记述他从前旅居美国时的游子“离散”(diaspora)情怀,他“向《纽约时报》的油墨去狂嗅中国古远的芳芬”;他的根在中国,他以中国为荣。这篇文章简洁的末段是:“他(余光中)以中国的名字为荣。有一天,中国亦将以他的名字。”这是对国家何等的信心,对自己何等的信心!20世纪以来,中华文学界众多人士,对西方主办的诺贝尔文学奖顶礼膜拜,趋之若鹜。2009年余光中在南京被记者问及对此奖的看法时,充满智慧的耄耋诗人淡定地说:“我们的民族要有自信一点,几个瑞典人的口味,决定不了什么。”他对中华民族有自信,对中华文学文化有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