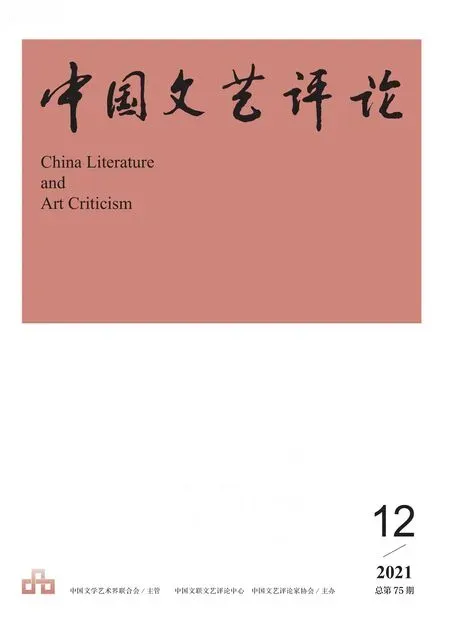从阐释学的角度再释契诃夫戏剧的现代性
顾春芳
“阐释学”(Hermeneutics)是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涉及人类知识的各个方面。19世纪以来,阐释学日益成为为人文学正名和辩护的理论,也逐步被规定为人文学科的一个普遍方法论。我们为什么需要语言来阐释和敞开艺术的意义世界呢?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智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切艺术的创造无法在时间中永续,唯有文字记载流传下来的东西,一旦被破译而解读,就成为纯粹而活生生的精神,就好像在现在一样对我们说话。由于这个原因,阅读的能力,理解书写文字的能力,就好像一种秘密的技艺,甚至像一种魔法,能够解放我们,也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这种能力似乎超越了时空。有能力阅读用文字流传下来的东西的人,就能够把过去转变成纯然的现在,并使之存在于当前。
跨学科的研究已经表明,对于经典的研究可以从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性别学、版本学、文化学以及哲学美学等多种角度对戏剧加以研究和阐释。阐释学对研究艺术和美学的作用不容忽视,艺术阐释学对构建“真理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艺术阐释学的目标就是阐释包含在艺术中的真理和意义,阐释创造和真理的相互转化的过程。戏剧阐释学依托经典艺术文本,进入艺术创造的深层,从而帮助我们有效地揭示和阐释艺术的美和意义,理解这种美和意义的历史性、真理性特征。而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阐释是一种创造,它所探寻的是最高的美和真理。
“戏剧经典阐释学”是尤其值得重视的一个学科方向。对艺术准确有效的阐释方法,都基于具体的文本展开。因此,合理的阐释方法是戏剧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所以,戏剧阐释学就是从理论和方法上提升和完善对人类历史中的一切戏剧文本(特别是经典文本)的理解方式,并揭示戏剧艺术的美和意义,以及关于理解这种美和意义的历史性特征。一切艺术的创造都是人类精神的客观化,我们通过理解和解释精神性的客观化,来参透艺术的奥秘和艺术家的心灵。阐释的过程就是赋予“精神的客观化物”以意义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照亮”。阐释照亮意义,在美和意义被漠视的今天,戏剧阐释学是照亮和确证戏剧艺术和意义的理论和方法。
阐释契诃夫需要反复深入细读文本,需要掌握叙事文本分析的经验和技巧,为了准确地理解文本,有时候还要比对原文进行确认。此外,在不同的研究者、传记作家、评论文章之间,就某些分歧和差异还需进行仔细辨析和确认。在此过程中会发现不同的阐释立场、阐释方法和途径,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和观点,这就是阐释契诃夫的难度所在,也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一项阐释研究的学术工作,首先要细读文本,对研究契诃夫而言,细读每一部剧作是关键;其次要细读传记、书信和札记,不同版本和类型的书信集,以及不同版本和类型的传记研究;再次是梳理国内外已有的契诃夫研究文献,对这些文献一一进行归类,并有计划地、有选择性地加以研究。在此过程中,我深感中国当代戏剧学研究亟待充实跨文化以及跨学科的研究。自苏联解体以及学术的诸多限制解除之后,英语世界的学者对契诃夫的档案、书信、札记、手稿进行了大量研究,有的已经翻译过来,有的还没有。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丰富了我对契诃夫戏剧的原有认识。已有的契诃夫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是也给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阐释契诃夫,文本和文献的爬梳和研究当然是基础,更重要的是要从以往契诃夫的研究中跳脱出来,回到契诃夫的文本本身,重走契诃夫的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以便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和核心观点。
超前的生态美学思想
重读契诃夫,最重要的收获是对于契诃夫戏剧中超前的生态美学思想的发现。
在感悟契诃夫的人生和艺术的时候,我找不出比“园丁”这两个字更合适的词汇了。很少有作家像他一样拥有文学之外的诸多才能和兴趣,从医学、科学、音乐到哲学和园艺。契诃夫说自己骨子里流着农民的血,他热爱土地和自然,喜爱俄罗斯乡间日益荒废的庄园,他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动手建造自己的花园,像一个真正的园丁那样培植土壤、种树栽花。他建造花园不是为了享用瓜果蔬菜,而是为了亲近自然,体悟大自然的规则。春去秋来、四季更迭,他像斟酌词句一样把握水分、土壤和阳光的互动与平衡。他在小小的花园里感受到造化的神奇与馈赠,感受到存在的本源,感受到所有形式的生命终有一死,人的灵魂与万物共有同一命运。培植花园的园丁,也培植着自己的心田,同时在文学中培植着关乎人类未来的良知的土壤。
契诃夫自小就热爱自然,极富有同情心。短篇小说《夜莺演唱会》表达了作家对于“森林歌唱家”的崇拜,以及对于杀死“伟大的歌唱家”的凶手的愤怒。他爱树、爱花、爱大河,爱森林、爱草原、爱鸟类:少年契诃夫宁可饿肚子,也要用仅剩下的几个戈比救下被人逮住的两只啄木鸟;他喜欢徜徉在伊斯特拉河畔,或者是普肖尔河畔,几个小时守着他的钓竿;在苦难的童年,大海和草原安慰过他的灵魂;他领略过古老的泰加森林隐藏的神话与秘密,它们无拘无束伸向远方的森林小径,曾赋予他无限的遐想;他赞叹泰加森林的威严与魅力,也曾热情地歌颂过叶尼塞河的雄伟壮观。《万尼亚舅舅》中的阿斯特洛夫医生对森林的热爱也是契诃夫的心声——
森林能使土地变得美丽,能培养我们的美感,能够提高我们的灵魂。森林能减轻气候的严寒。在气候温和的国度里,人就不必耗费太多的精力去和大自然搏斗,所以那些地方的风土人情就比较柔和,比较可爱。那里的居民是美丽的、灵巧的、敏感的,他们的言谈优雅,他们的动作大方。在那样的国度里,科学和艺术是绚烂的,人们的哲学是乐观的,男人对待女人是很有礼貌的……(第一幕)
契诃夫很早就意识到享乐的生活腐蚀着人的灵感和创造力,阻碍人领悟真正的幸福。他说每一次写作就是采撷自己最美鲜花的花粉,就是一次死亡,而每一次回归自然,便又是重获一次新生。他说:“大自然是一种良好的镇静剂,它能使人不斤斤计较,就是说使人淡漠。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也需要淡漠,只有淡漠的人,方能清晰的看待事物,方能公正,方能工作……”每一个春天,都让契诃夫感到幸福和满足。他曾这样描绘过梅里霍沃的春天:
野外的景色瑰丽迷人,那么富有诗意,使人耳目一新,因而也就抵偿了我们生活上有种种不便的缺憾。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一件比一件有意思。椋鸟飞来了,潺潺流水处处可见,积雪消融的地方草开始返青。时间充裕极了,似乎每一天都过不完。住在这儿,就如同住在澳洲的世外桃源。假如你不可惜过去的时光,也不期待未来,就会产生一种平静、悠闲、超凡脱俗的感觉。由此可见,从远处观察,人显得很美好,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我们来到农村,躲避的不是人,而是自己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在城里人的圈子里往往过分的强烈而荒谬,我眼望春天,心中渴望世界上能出现一个天堂。
他亲自照料花园,挖掘池塘、栽种草药,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花园散步,他希望自己如果不是作家就成为园艺师。他从国外购买花木种子,亲自栽培并精心护理,还给园林的花草编目。他对播种苜蓿、群鸟归来、孵化小鹅等一切事情都感到新鲜有趣,没事就喜欢待在花园修修剪剪,在那里观察果树、灌木和昆虫。日久天长,他逐渐养成一种习惯,无论侍弄花草还是垂丝钓鱼,或者与人谈话,都能同时进行和写作有关的思考和工作。对于花园的痴迷和身处自然的骄傲,洋溢在他写给友人的信中——“夜莺又在凄厉地悲啼,月亮彻夜都在苦闷地思念着情人。”“白头翁正陶醉在天伦之乐之中,高唱赞美大自然的颂歌。”他说亲近大自然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舍此不可能有幸福。
重读契诃夫,重新发现并理解了他超越宗教的信仰。尽管出身于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家庭,但是契诃夫曾明确表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作为一名医生和作家,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认为真理应该在现实而不是别处寻找。他曾对友人说:“在解剖尸体的时候,即使在唯灵成癖的人的头脑中也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灵魂究竟在哪儿呢?”他笔下那些出走的人物,令我们想起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伊甸园,非凡人的能力所能建造,那里的一切都尽善尽美,那是上天所赐予的花园。或许他们并不是被驱逐的,而是本来就厌倦了伊甸园这个“最完美的花园”——这一彼岸生活的终极想象。或许,在契诃夫看来,无论是天国的伊甸园还是贵族的庄园,无需耕耘的完美花园都游离于生命之外。永恒的花园,无论是吉尔伽美什的“神的花园”,还是古希腊的“极乐之岛”,都在时光之外,它脱离了大地,于是便无所谓美或不美。逃离宗教信仰,就是逃离伊甸园式的人生意象。真正的花园须经过辛勤的耕耘和汗水的浇灌,这正是契诃夫的人生感悟。
在细读契诃夫的小说、戏剧、书信、札记以及其他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有一些惊喜的发现,那些原来耳熟能详的“忧郁”“悲观”“抒情性”“散文化”的标签正慢慢发生着变化……契诃夫逝世之后,有一位评论家曾说契诃夫是继谢德林(1826-1889)之后因“绝望的忧愁”而离世,我想这不仅对谢德林是个错误的判断,对契诃夫而言也是个错误的判断。柯罗连科就认为契诃夫的作品并非是“绝望的忧愁”,而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信念和期盼”。对于一般人而言,在痛苦面前或许更多地是叹息、抱怨和沉沦,但契诃夫在面对厄运和无常时始终保持他的安详优雅和轻松自如,不管是作为医生面对病人和尸体,或者是面对自己因肺结核而咳血、面对死亡临近这样的事。
普宁(1870-1953)曾经问契诃夫的母亲和妹妹:“请告诉我,安东•巴甫洛维奇哭过吗?”他得到的回答是:“他一生中从未哭过。”普宁也曾引契诃夫自己的话说:“我算什么‘忧郁的人’?我算是什么‘冷血的人’?批评家却是这样称呼我的。我算是什么‘悲观主义者’?要知道我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最喜欢的就是《大学生》。”在我看来,契诃夫对于21世纪的意义不仅局限于文学艺术,契诃夫的意义在于他自身的存在方式,在于他可爱有趣的灵魂。他对于艺术人生的超越性感悟,诠释了人文精神在个体生命中的意义和光辉。他在《大学生》的结尾写道:
“过去同现在,”他暗想,“是由连绵不断、前呼后应的一长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他觉得他刚才似乎看见这条链子的两头:只要碰碰这一头,那一头就会颤动。
他坐着渡船过河,后来爬上山坡,瞧着他自己的村子,瞧着西方,看见一条狭长的、冷冷的紫霞在发光,这时候他暗想:真理和美过去在花园里和大司祭的院子里指导过人的生活,而且至今一直连续不断地指导着生活,看来会永远成为人类生活中以及整个人世间的主要东西。于是生活依他看来,显得美妙,神奇,充满高尚的意义了。
生命有限,美才成为必需。人类珍视和守望的应是一个时间中的花园,一个与生命一起荣枯的花园,一个由凡人所创造,并继续在时光中抵御速朽和衰老的人的花园。而凡人的幸福,就在永恒不息地抗拒腐朽和死亡的过程中,那里才存在着对时间和死亡的真切体验,才有着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切体验。在大地的花园里,心甘情愿做一位园丁,在艺术的花园里,俯下身去做一位园丁,辛勤劳作和挥汗如雨,唯其如此,花园和艺术才能真正成为人诗意的栖居。
审美空间和意义空间
重读契诃夫,也进一步理解了契诃夫戏剧的审美空间和意义空间。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中,有多少美好或凄凉的花园。“花园”是西方文化传统中躲避历史喧嚣与狂躁的圣所,也是契诃夫文学中最重要的生活空间和意义空间。在莫斯科、苏梅、阿列克辛和梅里霍沃,在一个个“寥落荒芜的花园”里,他选择不离不弃,一如在沉重的家庭重担面前选择全然的承担。在梅里霍沃,他带领全家修葺房屋、油漆地板、种植树木花卉、建起果园和菜地;他播种花籽儿、移栽花苗、嫁接花木;他在欧洲旅行的时候,还担心花园里的两棵百合是否被人踩坏;他为培育的幼苗寻找瓦罐,精心照料和浇灌刚刚栽下的树苗;在雅尔塔的白色别墅中,当看到亲手培育的茶花盛开的时候,他雀跃如同孩子。他给一生中唯一真爱的人献上自己栽种的玫瑰,他从自然万物和草木的生长中感受到生命的馈赠和幸福的恩赐。
花园的意象在《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中都作为一个重要的形而上的审美空间和意义空间出现。花园是大地的最高馈赠,每一个新的日子都是从过去的一天中生长出来的,就像每一株新芽都从苍老的树干上萌发。安妮雅幻想着未来会有一个比樱桃园更美的花园,特罗菲莫夫说不必惋惜旧的园子,契诃夫则怀着无限关爱凝视着他们,期待着人类有朝一日懂得:为了未来,我们可以有牺牲的信心,但更要如同园丁一样耐心,即便我们看不到新的花园,也要为这样一个希望、为未来的人们而躬身劳作。契诃夫的戏剧虽然透出忧思,但是远离颓废主义的灰色地带。他笔下站立于世纪悬崖边的人,即便在人生凄凉和困顿的图景上,依然能感受到清风吹过的美,依然有着生生不息的希望和力量。
契诃夫笔下没有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生活的强者,他的形象世界有着很多做梦的、理想主义甚至不切实际的人,他们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很难逃出既定的牢笼,面对庸俗和罪恶,他们甚至无力反抗。契诃夫笔下的佩索茨基、《花匠的故事》中的老人,包括樱桃园最后的仆人费尔斯都固有一种园丁的处事态度,要求得少,给予得多。没有谁比园丁更能体现人类那渗透着忧思与关怀的本性。唯有真正的园丁才会懂得,你给予土地的必得超出你所索取的,正如罗伯特•波格•哈里森说:“给与取之间的不平衡,首先是一个生命的原则,哪里给予多于索取,哪里才有生命。”纳博科夫说:“一个会生产这类特殊的人的国家,才是一个应该受到祝福的国度。这类人错过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他们躲避行动,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去筹划建造他们不能建造的世界;但是,这些人充满热情、自我克制、思想纯粹、道德高尚,这些人存在过,而且可能在今天那个残酷而肮脏的俄国的某个地方仍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着,只要这是一个事实,那么这个世界就仍然有着变好的希望——因为也许让人敬慕的自然法则中之最让人敬畏者恰恰是弱者生存。”因为在一种无以名状的强力压迫之下,依然本能地抵御着庸俗和罪恶,依然保有着微弱的高尚、无害的软弱、稀缺的美德,他们虽然弱小但是远离邪恶。因为在契诃夫的眼中,他们才是一个民族和国家需要珍惜和培植的土壤。
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深邃的目光在回望一个“日益荒废的花园”,这个“日益荒废的花园”就是俄罗斯的过去,是行将告别的19世纪。与此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他跳动的心脏在守望一个“新生的花园”,这个“新生的花园”就是他无缘见到的新世纪。就在这“荒废”和“新生”之间,发生了多少悲欣交集的故事,甚至是充满荒诞的故事。就在这“荒废”和“新生”之间,契诃夫鄙视一切无所作为的空虚颓丧、哀叹愁思,鄙视一切不切实际、凌空蹈虚的无聊口号,他以园丁的姿态弯下腰去耕耘大地,这个大地既是脚下的土地,也是文学的土地。
契诃夫笔下的草原,就是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后花园,是俄罗斯历史的隐喻空间。如丘特切夫的诗歌所言:“一切都仍将存在,暴风雪仍将照样哀嚎。黑暗仍是黑暗,而草原仍是草原。”在萨哈林岛上,他所赞叹的永恒的希望,是萨哈林的白桦、柳树、榆树、白杨和野樱,是那些作为残酷图景底色的绝美的风景。在这绝美的风景中他所要赞叹的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劳动和创造,以及稀疏的小块土地上的庄稼,泛着翠绿的黑麦,一垄垄的马铃薯,还没有长成的向日葵。苦役犯和移民所开辟的花园比之贵族的花园更深刻,“庭院和菜园里鲜花盛开,窗台上摆着洋海棠……牛羊的哞哞声,牧羊人的抽鞭子声,驱赶着牛犊的妇女和孩子们的喊声……杜伊河在这里也是迷人的。它在几家后院菜园子旁边流过。河的两岸长着山水杨和香蒲,一片翠绿。当我来到这里时,河中平滑如镜的水面上落下了黄昏时的阴影,河水好像一动不动,静静地入睡了。”即便终身服役,也根除不了人对于美和善的信仰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与花园相对的是修道院。契诃夫笔下的修道院是“充满令人窒息的烟雾、折射光线和嘈杂声的妖邪王国。在用焦油桶燃起的一些巨大的火堆和在天空闪烁的火箭的光照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心灵不安……我打量一下大家的脸,所有的脸都现出活泼的高兴神情,然而没有一个人细听那首歌,谁也没有认真揣摩歌里唱的是什么,谁也没有听得透不过气来”。绝大部分人认为,园艺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契诃夫领悟到,生活才应该是园艺的一个组成部分,花园在契诃夫的信仰中占据重要的部分。契诃夫认为自然、科学和艺术是真实的、有意义的,他毕生致力于生态、科学和艺术的使命:追求真理、懂得生命的意义、给予弱者以关怀,这些追求彰显了契诃夫穿越时空的永恒意义。
存在论的哲学思考和现代性品格
1888年到1889年是契诃夫文学和戏剧的一个新的起点。在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中都出现了崩溃的人。对托尔斯泰而言,死亡是肉体战胜自我欺骗的最高的胜利,是托尔斯泰把他笔下的英雄拯救出来的终极方式。对契诃夫而言,灵魂“一直不停地滚下去”是较之死亡更可怕而又普遍的精神状态。无论是俄罗斯非常有才华的作家加尔洵的自杀,还是他哥哥尼古拉的死,都促使契诃夫直面这个问题。在思想上他转向研究马克•奥勒留、歌德和叔本华,转向对于文学世界的审视和反思。
现代人遭遇过的问题和困惑,契诃夫早就思考过了,他笔下的人物也早就先于我们而经历过了。他的第一个剧本《伊凡诺夫》中伊凡诺夫的自杀是一个深刻的象征,一方面是契诃夫对于“多余的人”的文学传统的终结,也是契诃夫有意识地对西方古典主义戏剧的一次模仿和终结。他敏锐地看到伊凡诺夫身上所呈现的群体性的心灵危机,这种心灵危机的根源是没有信念,找不到出路的。他在《伊凡诺夫》中,以“软体动物”伊凡诺夫的死,揭下19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矫饰的面具,同时也以伊凡诺夫的自省揭示“启蒙者的困境”。契诃夫把可爱的性情、本能的善念赋予那些渺小、软弱且貌似无用的人,让他们在一个充满欺骗、庸俗和敌意的世界里遭遇困境,在流下眼泪的同时仰望苍天、守望未来。他把自己的境遇和心灵赋予他所同情的那些弱者,在人生艰难的跋涉中,在二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为了挤出血管里残留的奴性,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独自咀嚼着思考的痛苦和快乐,体验着大自然的美好和生命的庄严,将善和爱变为自己的生命容器,并怀着深深的同情和悲悯冷观世态众生。他揭示了艺术的根本意义——艺术可作为通向智慧和超越的手段,这个过程本身苦乐相随、悲欣交集。
重读契诃夫,对于契诃夫戏剧中的最本质的矛盾冲突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在《再释契诃夫及其诗意现实主义》一文中曾经指出契诃夫戏剧的冲突:“不是戏剧人物之间的外在矛盾,而是生活本身的悖论性,人物一切的痛苦和荒诞,均来自于他们与其环境的冲突,却又无法摆脱既定的荒诞生活。所以契诃夫刻意消解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外在冲突,而深化人与环境、人与时间的内在冲突。”人如何以有限的生命面对无限的时间和宇宙,并确证存在的意义,这是契诃夫戏剧包蕴的根本性问题。契诃夫的戏剧之所以呈现出现代性品格,源于其剧本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常常被忽略的角色——时间,以及被时间析出的危机感和焦虑感。
契诃夫的戏剧超前地呈现了人生的虚无以及如何超越虚无的哲学气质,对于“有限的存在和无限的时间”这一最重大哲学问题的思考,一方面令我们发现契诃夫笔下的人物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境界,另一方面向我们敞开了契诃夫本人在存在论角度的哲学思考。人究竟应该如何活着?生命的意义应该如何得到彰显?如果世界上存在幸福,幸福是什么?所有这些戏剧引发的问题,都是“存在论”层面的哲学命题,也即是海德格尔所探讨的:“迄今只在其存在论的可能性中被筹划的向死先行是否与被确证的本真能在处于本质联系之中?”契诃夫从存在论的角度进行哲学思考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戏剧冲突和传统戏剧具有本质的差异,它不再呈现人与命运、人与神、人与社会或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甚至消解一切表面形式的冲突,而保留和呈现人与时间的冲突。在时间这一强劲的“对手”面前,人的一切言行显得渺小和无意义,其他一切形式的冲突显得微不足道。这或许与契诃夫本人在二十多岁身患肺结核有关,他对于时间和死亡的体验比常人更加深切和紧迫。
在《三姊妹》中,那部被摔坏的母亲的瓷钟,就是时间和空间冲突的表征。钟的打碎,是一次彻彻底底的终结,时间令人绝望地停止了,时间失去了对未来的效力,三姐妹注定在这个坟墓里永远地挣扎下去。从“存在与时间”这一根本性的冲突视角,我们或许可以重新阐释契诃夫戏剧中的“停顿”。“停顿”在契诃夫那里不止是戏剧内部的、心理的动作,或是戏剧节奏的需要和把握,“停顿”是对“时间”的倾听。“停顿”是眼睁睁看着命运的车轮碾压过去,是生活的猝死和希望的休克;“停顿”是最后的审判,是面对荒诞的束手无策;“停顿”是不可解的存在的困境,是突然被抛向另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的茫然……最激烈的冲突全都潜藏在这无声的停顿之中,这就是契诃夫创造戏剧潜流的笔法和功力所在。如海德格尔论“此在的时间性”时所说的那样:“实际被抛的此在之所以能够‘获得’和丧失时间,仅在于它作为绽出的、伸展了的时间性又被赋予某种‘时间’,而这种赋予是随着植根于这种时间中的此在的展开而进行的。”一旦这一时间的展开停止,一旦这种被赋予的时间丧失,人就被迫以另一种方式去发现存在和时间的关系。
在契诃夫的戏剧中,最根本性的冲突体现在空间和时间的冲突,就是作为承载以往历史空间及其文化的人,因无法融入新的时间隧道而被析出的深刻冲突和矛盾,并在顺从或抗拒中呈现其历史伦理。契诃夫的戏剧所呈现的是在时间的流光中被无端浪费和破坏的美好,那些被浪费的美好,无所谓伟大或者渺小、悲剧或喜剧,也丝毫不再有英雄的痕迹。所有的一切是那样平常,在永恒的时光中一个人的毁灭犹如一朵花的凋谢,平常但是令人感到心酸。他在人类心灵的最深处探测到“最朴素而真实的情感”,在历史的至高点洞察苦难人生“永恒不变的戏剧”。正因如此,契诃夫的戏剧具备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和永恒性。
沃罗夫斯基在分析俄罗斯19世纪80年代“多余的人”时精辟地指出:“民粹主义文化派以哈姆雷特精神来对抗平民知识分子的堂吉诃德精神。”剧中,沙尔比斯基认为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荒谬,荒谬,荒谬的,荒谬和骗局”。伊凡诺夫强烈地感觉到生活和世界的荒谬感。这种精神状态和心灵危机不是他一个人的,是俄罗斯许许多多青年人的真实心境。契诃夫生活在俄罗斯黑暗与光明交替的时期,站立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悬崖上,时代的精神、寻求真理的痛苦,都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重读契诃夫,也是对契诃夫戏剧的现代性的重新认识。契诃夫的《三姊妹》和《群盲》以及《等待戈多》遥相呼应,共同体现出“世纪末的悲观情绪”。契诃夫笔下那些站立于世纪悬崖上的人,他们等待着新世纪的到来,但是这种等待注定徒劳无望。历史也已经证明,新的世纪并没有为困惑挣扎的人类带来希望,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拆散了无数的家庭、夺走了无数的生命。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所写的:“杀害和毁灭的景象使被激发起来的人都逃离了,而绝大多数的人更愿意闭上他们的眼睛、塞住他们的耳朵,但首先是堵住他们的嘴巴。与大规模屠杀相伴的不是情绪的激越,而是死一般寂静的漠不关心。它不是公众所喜,而是公众的冷漠,这种冷漠‘成为了无情地围在千千万万个脖子上的套索的一根加固绳’。”在此意义上,《三姊妹》和《群盲》中的盲人,《三姊妹》和《等待戈多》中的流浪汉并无太大的差别。“永远回不去的莫斯科”就是人类无法实现的、徒劳等待的共同命运。
现代戏剧的体验和反思直接根植于现代社会的意识,战争和杀戮的恐怖、暴力和流血的残酷、劳动者的贫困、虚伪和谎言的恣意横行、信仰和道德的缺失、文化工业对人的麻醉……所有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普遍面临的处境,在一个“荒诞无处不在”的世界里,人被迫正视自己的非人处境。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伊凡之口说:“知道吗,见习修士,世上太需要荒唐了。这世界就是靠荒唐支撑起来的,要是没有荒唐,世界只是一潭死水。”在道德瓦解的现代社会,反常的、琐碎的、畸形的事情触目皆是。皮兰德娄曾写过一篇《幽默主义》的论文,他的幽默主义绝非逗人嬉笑、引人发噱,而是赋予你“一种相反的情感”——相对于悲剧性、喜剧性、崇高、卑下等感性范畴而言,那些出自作品中相互矛盾的形象所引起的深刻的理性,借助“面具”获得一种怪诞和自我矛盾的样式,从而无情地暴露人类自我欺骗的真实情况。
1904年6月3日,契诃夫和妻子克涅别尔去德国巴登维勒疗养,在7月2日午夜时分,他感到呼吸困难,等到给他治病的德国医生施韦列尔赶到的时候,契诃夫已处于垂危状态。他的妻子记录了他最后的时刻,他用德语对医生说:“我要死了!(Ich sterbe!)”医生递给他一杯香槟酒,他接过酒杯安详地说,“我很久没有喝香槟了。”他微笑着望向妻子,一饮而尽,然后静静地朝左边躺下,不一会儿就永远地沉默了。施韦列尔医生回忆说:“他在瞑目前直到最后一分钟都非常镇静,像一个英雄。”
契诃夫的离世,一如他的文学那样静美而简洁。
契诃夫离世的情景无数次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理查德•吉尔曼认为:“在所有作家中,我认为他是最具世界性、最能够超越历史背景和地理限制的一位作家,他的思想和魅力在传播过程中遭受的损失也是最少的。这是因为没有哪个作家能更好地诠释存在与表达之间永恒的关系。”我对研究这样一个深邃、深情而有趣的灵魂,以及他和整个世界的关系,个体有限的生命在时光中的安顿,以及他所留下的一切艺术人生的印记都充满了惊异和兴趣。追寻着契诃夫的精神路标,便可以进入一个纯粹和美好的世界,阅读和追寻契诃夫,体验着穿越时光的心灵上的相通,本就可以超越民族、超越时代、超越语言和文化上的一切隔阂。
在我看来,契诃夫的意义在于其整个生命以及他那颗诗人的心灵,契诃夫本人是比契诃夫的文学更伟大的杰作。星星早已陨灭,但他仍在人心中闪耀。他属于19世纪,属于20世纪,也属于21世纪,他永远亲切地生活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