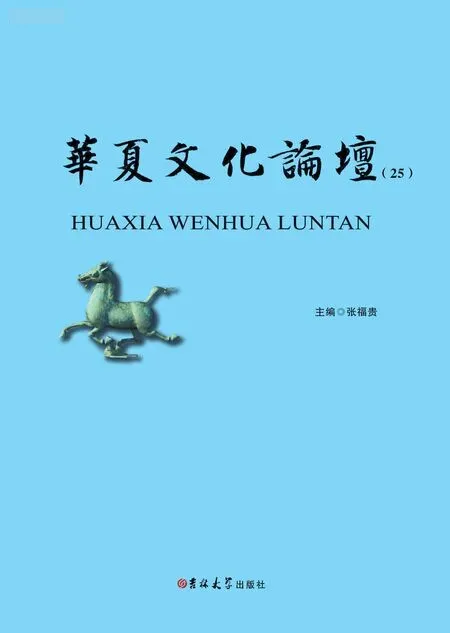“非现实”的现实:“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形上追问
于 洋 殷晓峰
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法国的超现实主义,作为重要的文艺流派之一,深深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创作风格、审美思维和形上追问,“在雕塑、建筑、电影特别是绘画等方面,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它的重大影响”。因为,超现实主义以超越现实的方式重新理解了现实,提出表征现实的创作路径、体验现实的审美原则、追问现实的形上准则。从超现实主义的先贤坚持“解放欲望”开始,超现实主义就在超越浪漫主义的意义上重新定义现实的本质。从超现实主义的思维来讲,现实不是实存的固定,而是主体反抗实存的固定性与给予性能力的本质力量的具体化。超现实总是能够从日常的平凡中发现神奇与超越,从梦幻与潜能中发现真实与力量,从幽默与重组中发现逻辑与秩序。超现实主义以非实存的“非现实”重新理解现实的思维范式一方面来源于先锋文艺家对一战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来源于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宰制的强化。超现实主义从“梦境”“潜能”“欲望”中来重新挖掘现实的本质,并不是简单地要把现实的本质还归于非理性,而是理性安排下创造力缺失的一种形上突围。
超现实主义绘画作为超现实文艺流派中的中坚力量,一方面具体地体现了超现实主义的形上追求,另一方面以独特的艺术话语与创造方法推进了超现实主义的形上追问。因为,绘画虽然在直观上是借助于物象、色彩、形体等来表达对存在的理解与追问,本质上却是本体语言、色彩要素、创作技法、审美体现来建构对现实的理解。超现实主义绘画特别以其“怪诞”的创作主题、“离奇”的创造手法勾勒、反应和实现艺术家心中的现实本身。一方面以作品呈现的方式拉开与现实的“距离”,以艺术的方式再现了现实的维度,具有否定性与超越性,在审美过程中通过艺术家与观者的再度融合与创造形成作品的主题,表达作品的意义;另一方面则以具象化的作品肯定了艺术家对现实超越性的理解与建构,通过观者的审美共鸣从而达到自我的内在创造性与现实实存性的辩证统一。因此,超现实主义绘画转向内心、追求现实的艺术创作不是还原既定的物象存在,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形上追问。
一、现实与超现实
安德烈·布勒东在1924年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批判了现实性的平庸、道德的自负、价值的固化,提出了精神的自动主义。这既宣告超现实主义正式登上舞台,又表达了一种关于现实的观念。超现实主义对现实既存性的否定、逻辑确定性的蔑视、价值一贯性的轻视,一方面击中了理性主义现实主义现实观的根本问题:对人主体性的限定,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由人主体精神产生梦、潜能等内在因素的存在论意义。或者说超现实主义力图走出实证主义的思维范式与价值观念来重新理解现实,从而将人的精神性力量再度推到前台。超现实主义从精神先验层面来追问现实的理念,是对实存逻辑与定存的一种突破,通过糅合人的本能、潜意识和梦等精神经验来重塑现实的理论与价值追求,展现了一种近乎幻想的现实观念。超现实主义以此表征了无意识的存在论意蕴,动摇了实证主义现实观念的存在论根基,超现实主义画家则以梦幻的奇异、精神的自主和方法的另类将此汇聚于作品之中。超现实主义绘画以此“撕裂”现实的方式,艺术地强化了非现实,以“缝合”非现实的方式表征了对现实的向往。
超现实主义绘画艺术化地实现了超现实主义对现实的否定,凸显了超越现实的非现实的存在论意义,也敞开了超现实主义绘画创作的基本维度。其一,在主观主义超现实主义画家看来,超现实主义绘画在突破传统绘画范式的基础上重塑了绘画。弗朗西斯·皮卡比亚和塞尔·杜尚就认为,“我们所接触到的不再是绘画,也不是诗歌或者绘画原理,而是一个早就向其自我极地进发的人的某些内心景致。”面对人的内心景致转变了绘画主题选取的艺术视角,表达人的内心景致革新了绘画创造的技法逻辑,呈现人内心景致的现实生成了绘画审美的价值观念。其二,超现实主义绘画沉溺于无意识自动状态的艺术态度,以自主绘画的方式确证了无意识的现实性。自动主义绘画的创始人安德烈·马松总是以动物这种自然存在物与建筑这种人为创造物组合在一起,在自主“写作”中表达自己的现实观念。比如他的作品《自主绘画》(Automatic Drawing
)就显然超越了绘画物象的前定限制,在诗意的灵感中跨越了现存现实的界线,使人从理性的狭隘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创作了一堆由自动线条组成的图像,从而确证不被意识、不被干预的内心的现实性。其三,超现实主义以打破现实的方式重组现实,预示现实并非是现存在的物象定在,更是人重组的存在。被誉为“最超现实主义的人”胡安·米罗(Joan Miró)就特别善于在打破中重组,“没有任何人能够像他那样,准备同不可能联合在一起的联合,并且无情地把我们不敢期望到其破碎的东西打碎。”在《小丑的狂欢节》这一作品中,我们就发现各种现实不可能组合成物象自然而和谐地共存于画面之中,无序与凌乱只是实存留给我们的刻板印象。艺术家呈现给我们的现实恰恰就是这种跨界的组合,这一方面符合人存在不断超越自我界限的事实,另一方面也体现艺术家被所谓现实捆绑的不自由。超现实主义绘画以魔幻的艺术手法与视角冲击力,在与常识的现实拉开距离的前提下建构一种能够体现的现实存在。在超现实主义绘画创作中有两种基本创作手法,一是拟态的抽象,在形变的意义上来表达潜意识、梦境等非理性意识的现实支配性;一是割裂逻辑边界性的幽默和自动写作,在与实存的距离中重审现实,表达无意识。无论超现实主义绘画中的写实还是精神表达,都力图超越既定的束缚,追求现实。或者说,超现实更加认可那种必然实现出来的“非现实”本身。在超现实主义绘画中,固定的时间与空间不再是物象与主题的标准座架,恰恰是错置的时间与空间才是现实的表达方式。就是时间与空间本身也是变动不居的,任何历史空间中滞留下来的节点,都不过是时间与空间的偶然相遇之后的永恒记忆。1931年达利创作的《永恒的记忆》无疑就是代表。时钟的折叠与空间的死寂不过宣布现存现实生命力的耗尽,蚂蚁和苍蝇活动于钟表之上则预示着现实由偶然际遇组成,平静如镜的海和一马平川的海滩不过是固定下来的实在,时间的折叠不过是隐喻了实存现实观的非现实性。因此,超越永恒、获得生命才是现实本身存在的方式。因此,当观者站在诸多《永恒记忆》这样的作品面前的时候,其颠覆常识的物象形态绝对不是艺术家怪异与个性的表达,而是艺术思考现实的思想冲击。
超现实主义绘画不仅不再停留于常识的时间与空间座架,更愿意借助形体错置与嫁接来表达现实的存续。超现实主义打破物象形体、重构生存形态是对事物的质疑,艺术家在作品中对物象形体进行拆解、形变和夸张,然后在组合、安置和复写,一方面已经打破形体给予观者视觉上的冲击,另一方面表达着主体意识对存在的重新安排。这样的绘画意味既定的形体下面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错置与嫁接不过是表达现实可能存在的面相。在恩斯特所创作的《女子、老人与花》这幅作品中,女子的娇态与柔美不再通过肌肤的质感与神情的媚惑来表达,一个大大扇面作为青年女子张扬个性的头饰,质感突出的工业化的马甲勾勒出青春的体态,臀部的肌理构成自然身体的浑圆,手指的纤细结合着胳膊的丰柔,……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对一个年华正茂女子的刻画。这一重构的女子,我们第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一个与现实同行的时代女子。而与此对比的老人没有特意去描绘面目的沧桑与行动的迟缓,只用裤管中的棍状物就完成对了衰老的表现。这是什么?这就是现实,年龄不再借助于身体的体态来表现,而只需“简单”借用时代性标志形体就达到了绝对的视觉冲击。这自然会让人们去思考一个问题,现实是什么呢?是那个老态龙钟的病态,还是娇媚丛生的脂粉?都不是,是现实生活中将现实的元素自身构成化的存在形体。超现实主义绘画把现实从现存的定在拉到了现实存在的表达之中,这种表达在于现实总是由于某种内在的神秘力量不断错置已有形体,嫁接成全新的样态,铭记着时间与空间的印迹。
超现实主义绘画还特别注意超越现实所带来的对比冲击力,一方面是艺术家以荒谬的视觉效果将现实与超现实进行二元的拆解,另一方面是观者在审美体验中不断去缝合这种对比,从而形成一种改变现实的内在力量。谈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简单地述及超现实主义入世的政治取向。如果我们考查超现实主义的发展史就会发现,超现实主义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将改变世界的政治实践作为自己重要的内在追求之一。这一点其实也深刻地体现在超现实主义绘画创作的方法论与审美观之中。从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图像特征上看,我们发现超现实主义绘画坚持超越现实的图像表达、体现艺术家个性与幻想的色彩表达和体现“精神自主”运动的主题表达。超现实主义绘画首先就是拒斥实体理性对图像的思考与安排,在激活精神内在动力的前提下去表达艺术家和观者内心的现实世界。这一方面体现了超现实主义绘画具有突破现实陈述的艺术勇气(在此意义上超现实主义是先锋派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另一方面则表达了现实必然要通过某种渠道表达自身。而且,超现实主义绘画特别注意色彩的冲击力,一方面力图用绚丽的色彩使观者脱离现实的灰暗达致内心的纯净,另一方面则希望表达现实存在可能还有另一个样态。精神自主运动作为超现实主义流派的理念一直体现于超现实主义绘画的作品之中。正如布勒东所说,“因为他们相信人类只能再创一种多少是有关他之事物的适巧意象,画家们在选择他的对象这点上所表现的态度已经太过怀柔了。他们的错误乃是相信一个对象只能从外在的世界里获得,或者相信它只能从此地获得……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舍弃……如果造型艺术乃是在于迎合一种现实价值之完全的根本的需要,在于迎合一种今日大家所同意的事物的需要的话,则他们因此更应该寻求一个纯粹内在的世界,不然就停止存在吧。”
因此,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形体构造、表现语言、创作手法造就了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独特的艺术地位和独立的艺术风格,其吸引人的色彩、震撼人的形体以及感动人的体验给观者带来独特的视觉冲击与审美享受,更使观者不得不进入到艺术家的生活背景、创作时代和生存体验中去追问艺术家的形而上学拷问。因为,在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创作中,艺术家们以艺术的手法否定了现实、再创了现实,在消解现实与超现实的实然界限的艺术表现与审美体验中,一方面通过艺术化表现超现实的方式使人与现实拉开距离,另一方面则以作品具象化非现实的方式使人重回现实。这意味我们必须深入讨论超现实主义绘画中为什么必须坚持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的问题。
二、肯定与否定的绘画统一
超现实主义绘画超越本身就意味着否定。但当我们综观超现实主义绘画的时候却发现诸多艺术家都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肯定早年的生活经历、曾有梦境臆想以及时代给予他们的生存体验等。肯定与否定的并存似乎肯定了超现实主义绘画是一种矛盾丛生的艺术。事实上正是肯定与否定并存于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创作逻辑和审美逻辑之中的时候,才构成了超现实主义绘画独特的魅力,也才构成了超现实主义绘画对时代与存在的艺术反思。总体上而言,超现实主义否定的是作为幻觉的实存、表达确定的关系和呈现意义的物象,肯定的则是生存体现的现实、梦境与无意识的存在性和潜意识的自由性。当然,超现实主义绘画作为一种激进的艺术流派,其更多注重的是否定意识的艺术表达,而非肯定意识的艺术再现。如此看来,超现实主义绘画虽然强调潜意识、梦境、神秘性等非理性要素,本质上却是理性主义的方式重新追问“画什么”与“怎么画”的根本问题。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成其核心的方法论就在于以否定既成绘画主题的方式重构和肯定了现实本身。
超现实主义绘画质疑物象与指称之间的确定关系,以叙述手法切入主题的同时去肯定艺术家独特的生存体验。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生存经历都会内化成个体独特的潜意识,人们潜意识的表现都可以在还原其形成过程的时候追溯独特的生存经历。公认的观点是认为超现实主义绘画受意识理论、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深入到超现实主义绘画否定物象与指称之间确定性关系的问题之中去追问其否定性的本质。按照李夏商先生的观点,超现实主义肯定具象世界与抽象世界之间的统一,在渴求内在精神要素真实性意义上否定外部世界的具体性,是超现实主义一贯的基本逻辑。因此,超现实主义的否定本质上是对现实深化的理论策略,其肯定则是印证非现实之现实性的根据。如果我们把这一观点具体化为超现实主义绘画的时候就会发现,超现实主义绘画形成了处理肯定与否定的独特的艺术路径。
在超现实主义绘画创作中,无论是复制、截取既定形体,还是自主绘制无意识的潜在意识,抑或拼贴与重组,都具有浓厚的叙事特点。也就是说,超现实主义绘画的本体语言、表现色彩与创作技法都具难得的直白性。这既使超现实主义绘画和传统繁复的描绘区别开来,又使之和现代其他流派专注色彩和形体区别开来。平实的叙事,本质上就是对存在绝对的肯定。但是,超现实主义绘画的超越性又使之不断否定。叙事作为人类讲故事的哲学方式,一方面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以内在的线索肯定共同体的存在。叙事平和的语言与直白的言说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肯定的逻辑。就此而言,当雷尼·马格利特以叙事的手法创作超现实主义的名作《情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爱情的热烈似火,而是爱情的朦胧与暧昧、距离与无间。其肯定爱情的方式简单直接:以白色面纱否定那日常爱情的卿卿我我,肯定了情人之间因独立而爱得深沉。白色的面纱是否定情人之间距离的艺术话语,面纱相依的阴影则是情人之间的无间与亲密。我们无从知晓面纱背后男女的俊俏与姣好,只知道情人的关系产生于相互吸引的异性之间。诸如马格利特的叙事手法作为超现实主义绘画的用语方式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如达利的《我妈妈的肖像》等。但如果我们深入去体味这一用语的方式就会发现,正因为超现实主义充分发掘了叙事语言在艺术表达中的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性,才使得超现实主义绘画在形象而夸张的色彩、零乱而穿越的构图中内蕴着严密的故事情节。这也是为什么说有学者认为超现实主义绘画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理性叙事。
否定作为超现实主义绘画建构超现实意象的创作方法,其根源则在于对常见物像部分或者是重复的肯定。正如前面我们提到的那样,复制、重组、再构是超现实主义绘画经常采用的创作方法。而当我们驻足于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之前时,我们自然就会发现构成超现实意象的那些要素与成分我们都似曾相识。为什么呢?因为那些都是来自对日常不可转移关系物像否定之后的解构要素,而日常生活的逻辑与体验又使之跃然纸上。这不得不说是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的重要魔力之一。因为,超现实主义绘画在对常识(当然直接对象是物像)的从属性与视角否定中,凸显了日常存在不可见而又现实的一面。或者说,超现实主义绘画之否定是将主体从常识中拉出来的艺术手法,而这种艺术性的拉却是要根本上肯定常识性的存在。这当然和超现实主义几次宣言中提出的改变现实、解决人生问题的宗旨分不开。但更为重要的是,超现实主义这种基于肯定的否定在直观上打乱物像实存、引发视觉冲击的同时,更让主体深入去探问那物像、主体和意识之间的内在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才有超现实主义绘画中将光的白画成色的黑,将活的马与死的树交织在一起,才有石头一样的苹果和不是烟斗的烟斗这类的艺术“奇观”。表面上看,这是语言上能指与所指的混乱,实际上却是“意象”的含混与艺术的挪移。其根本目的在于,在重组与建构之中,贯穿一种“扯断日常联系,另眼看世界”的幽默观念,表达一种主体超越世界的认识论方式,建构一种主体生成的存在观念。
否定更是超现实主义画家陌生化现实、肯定艺术超越性的创造方法,不仅使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具有独特的视角效果,而且更加凸显了否定作为创作方法的对于精神的影响力。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艺术创作都力图与现实拉开距离,但是超现实主义陌生化常识的方式特别值得人寻味。因为,超现实主义绘画通常将自由拼合作为否定常识定在的艺术方法。拼贴似乎是艺术家对物像、时空的随意安排,本质上讲却是艺术对既有秩序的怀疑与否定,以及对新秩序的设想与追求。问题在于,经过拼贴创作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画面与艺术家所要表达的主题之间的统一恰恰是对拼贴之否定性的艺术肯定与存在理解。而且,超现实主义的拼贴类似波普二维组合对象的艺术风格,但是却比波普拼贴艺术更加激进和彻底。特别是超现实主义通过对空间的切割与拼贴更是改变了日常物像的呈现方式,一方面使拼贴之后的画面具有独特的立体感与层次感,另一方面是空间与物像之间的拼贴更加肯定了物像在空间中呈现的事实以及空间感表达对物像分割与组合的依赖。这意味着在超现实主义绘画的拼贴中,物像与空间之间的关系被艺术进行了打乱与重构,其反常的视觉效果与幽默的艺术风格既让人体验到艺术眼光的犀利,又让人内视地直面自我潜意识。无论是达利的《记忆的永恒》还是《天降》,或是马格利特的《愉快的捐赠人》,无一不是超现实主义绘画中拼贴的代表。当我们遭遇这些艺术作品的主题与画面,直观的感觉是艺术家在和我们开玩笑,而一旦我们沉浸于作品之中时,我们会突然发现画面本身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无意识重复的活动而已。这种直指内心的审美观照,显然肯定的不是画面上杂乱无章、违反日常的拼贴,而是人内心那个不受理性规制的潜意识自主的表达。或者说,艺术家通过拼贴的方式,在否定日常中呼唤出了另一个真实的主体。
因此,超现实主义绘画在创作方法上的否定性并不是形而上学直观否定,而是融合肯定的艺术方法。对肯定与否定的艺术统合,更切合了超现实主义绘画表达梦境、表征潜意识的存在论追求。客观地讲,超现实主义绘画因其对物像、时空乃至意义的一种割裂与重构,很容易使人们产生虚无主义的印象,但是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的完成因其否定与肯定的统一从来都不是由艺术家自身独立完成的,而是由观者在审美过程中不断内视、不断想象、不断增加而完成的。因为,否定本身就具有激发象征意向的艺术功能,肯定则有主体确证功能。超现实主义绘画虽然遵从绘画语言不能从单一视角解读的传统,但是却更加依赖观者的主体性体验及其象征性意象的阐发。比如马格利特就特别注重“幻觉景象”的象征性意象问题。其“逼真的”超现实主义作品《错误的镜子》就极为具体地体现了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根本特点。因为,眼的自然形态与镜子的明澈组合,加之黑斑的中间凸显,以及镜片内在的天际等等,我们显然可以将之解读为自然物像的拼贴与组合,但是我们会更加看重其凸显出来的象征性意象。我们会去追问,错在何处?是物像之错?结构之错?还是我们主体的视觉之错?一旦我们追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开始深切地关注我们的眼睛之视觉功能。是还原?还是再照?这些问题会层出不穷地映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这一过程显然不是单一的作品呈现,而是观者象征性意象的产生以及作品的完成。而这恰恰就是对否定与肯定的存在统一。
三、守护绘画本体与追问存在
超现实主义绘画之超现实,并非是脱离现实的不现实,而是在对传统绘画的批判与重构中,以“纯视觉艺术”守护绘画本体,以无意识的“观看”来追问存在。虽然超现实主义借助梦境的看与依赖精神分析的纯粹受到了实证主义的诟病,但是超现实主义绘画以超现实的现实观念突破现代主义绘画同一性逻辑的宰制却从根本上推进了对存在的艺术追问。
超现实主义绘画梦境的看与精神的纯粹是突破不在场隐喻控制的艺术方法,在反叛传统绘画同一性逻辑的基础上重拾绘画本体的艺术追问。传统绘画之所以走向非艺术,成为社会叙事法则的线上木偶,根本原因在于艺术家之看不是主体之看,而是社会现实符号传达的方式。绘画本体与绘画主体的遮蔽源于社会现实的艺术化,而非艺术现实的社会化。超现实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根据精神的纯粹性与梦境的非现实性使绘画艺术一方面获得艺术语言的独立,重述绘画的本体;另一方面则是逻辑中断的幽默使绘画艺术摆脱历史与现实的纠缠、价值与文学的支配。当超现实主义绘画以否定的方式质疑形体再现与语言指称的同一性的时候,就从根本上切入了绘画语言的本体性问题。马格利特在《词语与图像》这一著名的语言—视觉的文章中重点谈到了物像符号化的任意性、取代性和现实性的问题。他的这一观点显然是深化与推进了达利对视觉与物像符号相对独立的思想。视觉语言与符号语言的平等在传统绘画因同一性宰制而消弭不现,因而凸显视觉语言对于现实的表达就成为绘画核心的艺术追求。因此,在马格利特《这不是一只烟斗》这一作品中,符号语言与视觉语言之间的矛盾与差异表面上看是艺术家生硬的否定,实质上讲却是在否定一致性的前提性追问视觉语言的不可还原性、不可转述性等本体论特质。如此看来,在超现实主义绘画中,视觉不是认识的补充与物像的再现,而是对现实的把握。这一方面因为艺术和哲学、科学一样是可以直接触及真理的文化形式,具有天然的纯粹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艺术家切近世界的方式是艺术的直观,类似于现象学的方法有不可还原性。超现实主义绘画正是看到绘画语言这种独特的本体性,才在绘画的创作以纯粹的精神与不受社会“污染”的梦来形成创作的主题和言说的方式。
超现实主义绘画在追问绘画本体的过程中,通过逼问绘画语言内涵的方式切入了对主体如何确定所指与能指的存在论追问。超现实主义绘画在此完成的形上追问主题的转换,预示了物像的逃逸词汇与绘画的可能性。这意味超现实绘画只有重建本体才能够真正融合主体的所指与绘画语言的能指问题。这就意味着画家不再是在看世界,而是表达世界,无论是梦境的内涵还是精神的纯粹,都是艺术家体验的现实本身,也是其追求的现实本身。所以在马格利特的《望远镜》中,我们看到透明玻璃的“蓝天与白云”和窗户缝隙中的“漆黑无边”。这既意味看的贫乏,又意味在的真实;既体现出看的无力,又体现出真的穿透;既呈现了想象的必要,又呈现绘画的必需。也就是说,在超现实主义绘画看来,绘画语言作为一种本体,不是对物像的体会,而是现实的自我呈现——无论呈现的内容是梦境还是自动写作表达出来的精神的结构。因此,超现实主义通过绘画语言表达的本体性,不仅捍卫了绘画艺术的独立性与不可还原性,而且意味绘画的本体其实就在于作品本身——那种自然地呈现出精神的内在性与本体性的作品。如此看来,超现实主义绘画钟情梦境与精神,并不是因为这二者是现实不同的另类存在,而是因为梦境和精神能够从本体上超越社会文化的预设与物像系统的干预,是现实艺术澄明的手段与方式。这从根本上解决了实存作为被符号截取与阉割存在的局限性问题,是对符号秩序的一种艺术反抗和对现实存在的艺术建构。在此,我们可不必借助弗洛伊德凝缩和位移的梦就可以感知和认可拉康的重要判断:梦具有某种文字形式的结构,但是这种结构只有不被文字编码,而被直观画面展示出来的时候才是现实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绘画的本体论特质,才使超现实主义画家相信,不是画家在画,而是画在画其自身。超现实主义绘画的自动写作就是最好的例证。
超现实主义绘画呈现梦境与精神结构除了艺术上的守护绘画以外,更是直接指向了人内心的慰藉。超现实主义绘画的这一形上向度在于“建构一个与物化世界判剖有别,将现实生活与本能冲动、无意识和梦的经验交融贯通却能主宰整个生活世界的超然境界,借此获致个体的本真存在。”追问本真的存在正是超现实主义绘画的魅力所在。因为,超现实主义将梦境作为唯一的希望即是意味着梦境是一个能够还复人性、表达存在的纯然存在,无论梦是曾有生命经验还是生活经验的意识化,或是人潜意识或无意识的表现,都可以在不受社会现实编码的意义上完整地叙述存在本身。达利就在自己的画作中不断回溯原初的梦境,并且宣布“超现实主义是指人的充分自由及做白日梦的权利。”当然超现实主义绘画并不是要在此向人们宣布只有在梦中才是现实,而是说梦的无意识本身是一种改变生活、改变世界、建构存在的意识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原初的、未曾剪辑的整体性使主体能够获得整全的存在体验与整个世界。比如马格利特也一直在自己的绘画作品中重复无面孔的身体形象。因为脸其实是一种被雕琢的面相,既有主体自觉的雕琢,又有主体非自觉的雕琢。因此,去除特异性的面孔直面身体本身,就使人真正超越了福柯所言的“权力框架”与“政治架构”,在不与他者相遇的途中与自己相处。
因此,超现实主义绘画在形成自己创作方法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改变运笔的方式与调色的策略、选题的视角与造型的角度,而是从绘画本体的角度来思考画与人、人与画之间唯有艺术才能言说的本真关系。超现实主义不是技术性改造了创造手法,而是形而上学地思考了存在的艺术表达。在其创造的逻辑之中,既体现了这种绘画艺术对现实历史的艺术直观,又表达了现代人存在的生存焦虑,更是从艺术的角度去重建了现实与非现实的艺术张力。超现实主义绘画在对非现实的现实性的形上追问中,使绘画从现代绘画的父权中脱离出来,自由地叙述不稳定的稳定性来反抗稳定性的暴力和现实的暴政。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超现实主义会在一战之后兴起,并积极地介入政治;超现实主义绘画为什么总是将梦境与自由勾联,将精神与主体同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