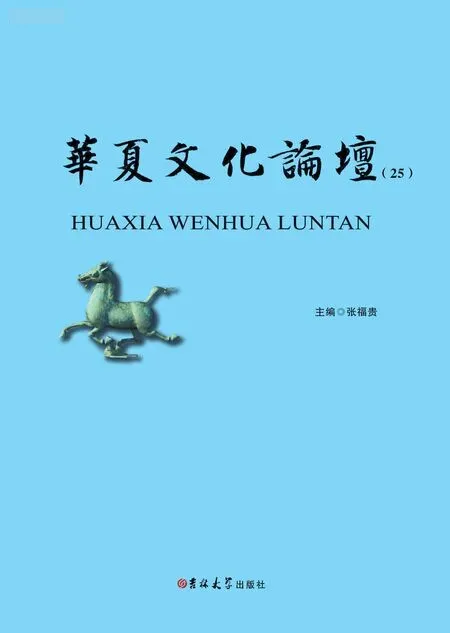“非虚构”视角中的小人物形象创作
戚 萌
一、小人物形象流变及其生成语境探幽
小人物形象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学根基。1830年,俄国作家普希金用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作为笔名发表了《别尔金》小说集,其小说《驿站长》中的主人公“维林”,开创了俄国文学史上小人物形象的先河。小人物最初就是指如“维林”这般在俄国历史中没有地位、受尽权贵阶层欺辱的下层小公务员形象,诚如有的学者所总结的那样:“‘小人物’就社会地位而言,是与统治者权贵们相对而言,处于社会底层或边缘,如破产的农民、劳力、流浪汉、小职员、小官吏、小市民、小知识分子等平民阶层。”在俄国历史上有很多通过描写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来抨击当时丑恶社会现实的作家作品,如普希金的《驿站长》、果戈理的《外套》《狂人日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被欺凌与被侮辱》以及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等等,他们下笔恣肆淋漓,指涉左右逢源,在日常化的叙事中制造了种种令人讶异的震动。这些对小人物形象的刻画描写,不仅鞭挞了种种荒谬丑陋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是用蘸满悲凉的笔触书写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凄苦人生。
但小人物是一个流动性的概念,从西方到东方,从古代到现代,其受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制约,所呈现的形象面貌也全然不同。在中国文学史上,虽然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有关其概念表述的定义,但是对小人物形象的创作早就是一个屡见不鲜的重要写作传统。先秦时期,小人物形象并不作为一个完整的叙述主体存在,“提及小人物常常是为了借小人物劝诫君主,或止战息戈,或表达婚恋哀愁,或反映世风民俗。”其重点并不在于对小人物形象的精雕细琢,而是通过诗歌来表现对哲理的反思;两汉时期,小人物的形象创作逐渐丰满起来,《陌上桑》中不畏权贵的采桑女罗敷、《十五从军行》中年迈困苦却无家可归的老兵、《孤儿行》中漂泊无依的孤儿等等,这些小人物形象的刻画都较之前更加完整细致,但囿于诗歌体例的限制还是略显单薄;魏晋南北朝时期,“丛残小语”式的志人、志怪笔记体小说将人物刻画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世说新语》《笑林》等小说都有一些人物形象的简笔勾勒,虽字数寥寥,但却对后世的小人物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唐代,小人物形象的塑造日臻成熟,诚如《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所言:“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的发展使作家对于人物的思考走向纵深,趋于内化;元代时期的“话本”艺术以及明清时期古代长篇小说的长足发展,让作者的视角从王侯将相的英雄身上转投到社会底层无力抗争命运的小人物上,如《金瓶梅》《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众多作品都是将笔触伸向了那些广泛存在于社会最底层而无力抗争的小人物;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史,更多的作家将目光聚焦到市井小民的悲苦生活中,有“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出疗救的注意”的鲁迅,也有擅于将老北京五行八作市井生活作全景式描绘的老舍,也有将笔下人物从革命英雄渐渐调整成为小人物的巴金,他的《憩园》《寒夜》《第四冰室》(“人间三部曲”)就是最好的证明。进入到新时期文学,以池莉、刘震云为代表的新写实作家,将小说深入到了生活的本源,刻画了处于逼仄生活空间中被压迫变形的普通人的日常;20世纪90年代之后,“底层文学”“打工文学”成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在这一文艺思潮的影响下,迅速涌现出了一批混杂于知识分子与底层平民的作家,虽然对于“底层文学”合理性的讨论仍不绝于耳,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存在对于小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呈现与主题深化都有着无可比拟的推动作用。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随着时代的变化,文章的思想内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进入到21世纪以来,小人物的形象创作与社会转型期的冷峻现实细密交织,让我们看到了在高楼大厦之后还有破旧低矮的小房、在觥筹交错和推杯换盏之外,还有衣不蔽体残羹冷炙的凄凉。在泥沙俱下的复杂背景下,小人物形象也在新时代显现出了某种混杂性,它不再拘泥于人们呆板词条中的“被剥削阶级”或者是“底层”,他既可能是曹征路《那儿》中优秀的共产党员、时代劳模“小舅”,也可能是石一枫《地球之眼》中出色的名校毕业生安小南。“小人物之‘小’,不仅仅在于其物质方面的食不果腹、金钱匮乏、地位低下,这些只是小人物的外部标识。小人物之‘小’,更在于其精神世界的被压迫、人格心灵的被扭曲,以及长期处于这种物质、精神双重挤压下的低贱的生活状态和卑微的心灵感受,这才是小人物的内在实质。”在当下大众文化、网络文学沸沸扬扬的文学场域里,还有能够对小人物持久、热情的关注以及真实、细致的描写,不仅彰显了作家的平民情怀,同时也是一种回归现实、回归文学的责任担当。而“非虚构”性视角的介入,使小人物的刻画描写变得更加真实,也使文学成为能够窥探社会真实图景和时代巨变的一双眼睛。
二、“非虚构”的写作传统与指向意义
1888年4月,恩格斯在给英国女作家玛·哈克奈斯的信件中曾写道:“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以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这里,恩格斯强调的是文学不仅仅要写出现实的真实,同时还要在现实的真实刻画中达到某种典型化的程度。更有学者直接表示:“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的确是这样,“在传统文学叙事领域,人类作者在叙事创作时,叙事是受到作者自身认知水平约束的,是从已知的知识储备到已知的叙事空间。”进入了新世纪,文学对于真实的渴求似乎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峰状态,“非虚构”在文坛上的集体亮相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它的出现,是在现实与文学之间重新搭建桥梁的某种尝试,为我们理解世界开启了一个新的渠道。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随处都可以窥见“非虚构”的踪影,尤其是在有着“主流文学”称号的乡土文学阵营当中。鲁迅在定义乡土文学之初就强调了,他们的作品大多都是“回忆故乡”的,因此这种“回忆重组”之下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自身文本的解构意味。早期的乡土文学创作,如鲁迅、沈从文或者是萧红的作品,大多都是作品中包含着作者对于故乡的“真实记忆”,加之后来佐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升级成为“艺术真实”,而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像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空山》、贾平凹的《秦腔》等作品,则是让乡土文学以一种更加现代的方式进入到大众视野,其作品也从“艺术真实”慢慢转变成为一种“生活真实”,不管百年中国文学如何发展,在种种变换的审美需求当中,可以说对“真实”的渴求一直都是其最本质的一项。回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优秀作品,作家创作之初的记忆重现,使得其作品本身就带有更多的“自传”意味,也就不乏真实性的因子浸透其中。鲁迅小说中浓郁的浙东风情,他笔下的咸亨酒店(《孔乙己》)、烦琐的祭祀场景(《祝福》)、甚至是小说的人物闰土(《故乡》)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其原型,鲁迅自己也承认,他作品中“所写的背景以绍兴居多。”沈从文笔下壮美的湘西景色,萧红笔下那个充满纯真美好童趣的呼兰河镇,贾平凹笔下不能抛弃的清风街、徐则臣笔下那条反复出现的花街,所有这些作家笔下闪现的坐标与建筑,都是其真实的人生经历和生活过往。贾平凹就曾经在《秦腔》的后记中写道:“我的故乡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风街,棣花街是月,清风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风街是镜中花。”在《秦腔》中,贾平凹用大量对话性的语言代替了虚构性的叙事语言,这种情节的背后不再有逼仄紧绷的张力,反而有一种这就是我们平凡人过着普通生活的慢节奏。他用近乎白描的艺术手法将日常琐碎的生活描绘出来,构成了真实的农村生活的图景,也展现了近二十年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贾平凹称《秦腔》的创作,就是想要为家乡“树起一块碑子”,这碑子不仅仅是贾平凹故乡镜花水月的体现,同时也是作者无意识地进行“非虚构”创作的证明。
“非虚构”是文学企图与世界对话最直接的方式,它的出现使“小人物”与“大时代”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进入到21世纪以来的文学场域,大量充斥着的大众文学、网络文学似乎总是处在尽情狂欢与无病呻吟的虚无当中,文学在20世纪百年文学当中所起到的那种“引领”作用早已日渐式微,如果文学仍然抱残守缺,本着一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南北与西东”的冷漠态度,拒绝面对社会现实的话,这种文学注定与时代脱节。新世纪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小人物形象以及非虚构的写作,恰好及时解决了文学场上的疲软状态,给了人们强有力的一击。
三、“非虚构”视角中的小人物创作
在我们梳理新世纪小说当中的小人物形象之时,我们总是有一种错觉,仿佛这些小人物就在我们之间,他们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这种真实感,除了作者力透纸背的着力刻画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作品本身就有着“非虚构”的艺术特质。诚如张福贵先生所言:“文学要关注个体的人,要发现人的价值。”因此,真实的表现人,发现人的价值就成了20世纪的主旋律。用“非虚构”的艺术视角解读当下描写小人物的作品,可以将小人物大致分为三类:源于作者生活中所见所闻的原型、源于真实的社会新闻报道以及源于作者自我经历的闪现。
如果说20世纪乡土文学中隐隐浮现的“非虚构”因素更多的是作者对于故乡的“回忆重组”,那么到了新世纪以后,在小人物形象的创作上,“非虚构”艺术手法的介入,更多的则是为了反映社会现实,构建社会人物与大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的后记中他曾坦言,《高兴》中的刘高兴以及《秦腔》中的书正的原型都是他小时候的玩伴——刘书桢。刘书桢独自在城里拾荒的事情深深地触动了贾平凹关于社会小人物生活状态的思索,他认为从他们的生活碎片和精神状态中能够触摸到这个城市的脉搏。正如贾平凹自己在后记中所写:“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因此,贾平凹在写《高兴》之前,深入地做了一番实地考察,他亲自联系拾荒的远房亲戚去到他们集中租住的小平房里去搜集资料,采访了近百位在西安拾荒的老乡。无独有偶,同样以刻画小人物见长的作家陈应松,也是喜欢用“非虚构”的视角来观照自己的创作。他曾经在荆州和神农架挂职,因此创作了很多以其为背景的小说,无论是人物还是故事情节,很多都取自这段挂职锻炼的经历。他曾说过:“我写的任何细节,吃什么,用什么,什么植物,花形花色,都是可以考证的真实。直面人生,让一个人、一种生存现状站在你面前,真实得让你颤抖。”对于诸如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华丽雕琢的艺术手法这种创作捷径,他坚决摒弃了,并且亲自深入到了神农架的深山老林之中去探寻一手新闻素材。他的很多作品,像《松鸦为什么鸣叫》《马嘶岭血案》《滚钩》《狂犬事件》等,都是以真实事件为背景的小说。为了采访《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的主人公原型,陈应松在满是冰面的山路中穿行,甚至险些丢了性命。梁鸿的《梁庄》更是“非虚构”视角聚焦新世纪农村现状的典范之作,梁鸿利用了2008年到2009年中近5个月的寒暑假时间,对其故乡河南省穰县的梁庄进行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真实农村现状的《中国在梁庄》。小说中大量引用的受访者的原话,以一种近乎白描的艺术方式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留守儿童教育资源欠缺等现实问题,引发了人们得思考。对于自己作品的成功,梁鸿坦言:“独到之处就在于对真实的理解。”由此可见,“非虚构”的艺术视角为小人物的创作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仅仅是生活原型,新闻报道也是很多作家塑造小人物的灵感来源。囿于作家自身社会阅历的局限性,很多再现作家社会真实经历的作品已然不能满足读者,因此很多敏锐的作家将创作视角深入到了一些新闻报道之中,并进一步审视了其背后的社会意义,继而用小人物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陈应松的《狂犬事件》以及《滚钩》就是以现实新闻报道为蓝本而创作的小说。《滚钩》是陈应松第一次将虚构作品与真实事件双重咬合的作品,他创作的灵感来源于很多人都知道的“挟尸要价”的新闻。在神农架探访农家搜集资料的陈应松,其创作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应该写更真实的东西,结束胡编乱造……从单纯依靠想象力和虚构的状态中走出来,老老实实向生活学习。”因此,在后继的《狂犬事件》创作中,他采访了闹过疯狗的小山村,细致地采访了当事人、村干部以及乡长,为了让整个事件更加贴合实际,他甚至还参访了防疫站,翻阅了当地卫生局的相关档案。正因如此,陈应松笔下的小人物才活灵活现,他“非虚构”的手法创作,更加凸显了其捕捉现实生活的敏感度以及对于现实社会的观照。
刘继明发表于2004年的小说《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以及李锐发表于2005年的小说《扁担》曾一度在天涯论坛中激起了“抄袭门”的热议,因为两人所写的都是一个农民工被包工头打断了腿,最后千辛万苦爬回了老家的故事。但其实“抄袭门”纯粹是一个乌龙,因为两位作家的创作灵感皆是来源于当时在媒体上广为流传的一则新闻,这种“巧合”也恰好说明了两位作家不再满足于剖析“自我”与私人生活,而是将笔触和视野深入到广阔的现实生活中去的一种跨越。
除了将自己真实生活中的周遭人物以及新闻报道纳入小人物创作,还有作者甚至直接将作品中的小人物与现实世界中的自我双重糅合,实现了一种超越真实的“非虚构”质感。例如非常擅长于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李铁和鬼金,他们这辈子的生活都与工厂、工业文明交织在一起,因此他们的小说背景都是在东北某个轧钢厂或者是电力系统的发电厂里展开的。李铁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谈道:“当年的工人里面藏龙卧虎,我感触太深,写这些人物几乎就是真实。我觉得生活底子深厚的作家写作是一种流淌,虚构反而是强加给它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管道。”在李铁的小说中,我们能够捕捉到在时代差序的社会转型下,小人物无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凄苦现实以及精神世界对于未来的困顿和迷茫。他的文学创作中有一系列出色的“女工形象”,如《纪念于美人的几束玫瑰花》中的于美人、《乔师傅的手艺》中倔强、好强的乔师傅以及《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中的优秀机械厂女工杨彤,这些穿梭于作品之间的小人物,既让我们透视了李铁真实生活中这一代工人对于技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对工人身份的尊重和忠诚,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技术时代与商品时代的巨大虢隙中,工人阶级的尴尬身份以及时代的悲剧。与李铁的身份相似,鬼金也是一名在工厂工作的吊车司机,与别的作家始终徘徊在人物“身份焦虑”的痛苦之中所不同的是,鬼金似乎从一开始就有着某种“身份认同”。贯穿于鬼金笔下“轧钢厂系列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叫作朱河的吊车司机,朱河与鬼金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烈的自我指涉意味,小说中的朱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鬼金本人的自我镜像,一样都是开天车的司机,一样热爱文学,一样关注工人的命运。在小说《追随天梯的旅程》中,鬼金称朱河是“纸片人”,一方面是指其长期处于繁重工作下孱弱的身体,但更重要的是指其精神世界的贫瘠。类似于这种自身经历与小人物创作重合的“非虚构”创作还有很多,比如同样关注工人生活的作家曹征路,他之前就在部队里当过通勤兵,在1973年转业之后就在安徽铜陵的一家工厂里面上班,其后又来到了下属的机械总厂上班,这为他日后书写矿场工人们的日常工作以及其心路历程的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毕淑敏曾经有十几年的时间在一家重工业的工厂卫生所里担任所长,她能更直观地感受工厂女工的喜怒哀乐,注视着其人生的起起伏伏,因此她创作了《女工》这部长篇小说。再如十分擅长描绘底层人民生活的李佩甫,他也曾经是许昌市第二机床厂的一名普普通通的车工,在工厂工作也长达八年之久,因此他对于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十分熟悉;再如擅长于煤矿“酷烈叙事”的刘庆邦,他的小说《卧底》《红梅》等都揭示了矿工悲惨的底层生活,其中对于很多细节的描述,精准得令人发指,这也完全因为他曾经在煤矿工作了整整九年,这些宝贵的经历无疑成了他日后创作源源不断的灵感和资源。
小说未必能昭示历史,小人物的悲欢也未必可以替代社会现实中所有的底层生活,但是“非虚构”的视角必然可以让小说奏出更加铿锵有力的回响。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正因如此,小说更不能仅仅沦为当下社会生活的简单记录,小说聚焦的更应该是挣扎于社会泥淖中苦苦求生的普通人,聚焦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所处的真实的社会背景以及这个时代所回馈给他们的真实的心灵感受。如果仅仅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那么我们就很难真正体会到小人物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就算是用虚构的艺术手法加以想象,可能也会造成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的偏颇。以“非虚构”的艺术视角介入新世纪小说中的小人物书写,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些小人物并非是天马行空的恣肆臆想,而是笼罩在社会转型期之下的严峻现实,这是大时代的产物。“非虚构”的艺术创作增强了小说的叙述力量,同时也是创作者们视角下移、有着当代作家责任感和道德良知的复归的真情流露,有着深厚的审美意蕴和价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