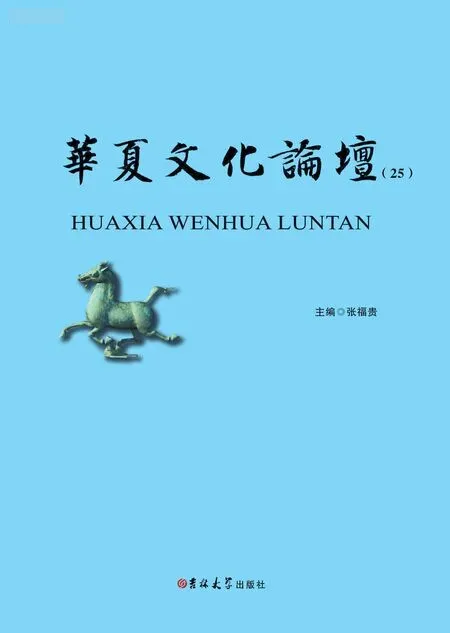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偏向与调整
王兆胜
在所有文学学科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饱和度”可能最高。作为一门显学,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汇聚了庞大的研究队伍,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其间,既有值得总结的经验,也有应该汲取的教训。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过程中,也有难以为继的不足,需要进行反思和做出调整。
一、资料性与思想性
资料之于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具体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几乎与其研究相伴而行,甚至直接关乎研究的广度、深度、力度,也标志着研究的突破性与跨越性发展。如薛绥之的鲁迅研究,林非之于散文,范伯群之于通俗文学,孔范今之于现代小说,朱金顺之于新文学史料,陈子善之于张爱玲,张桂兴之于老舍;又如刘增人和黄发有之于文学期刊,吴秀明之于中国当代文学;另如近年来李宗刚出版了多部(套)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还有金宏宇和徐勇的版本与副文本研究,彭林祥的中国现代文学广告研究等,都是可圈可点的。
不过,另一情况和趋势也同时产生,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资料性有弥漫甚至覆盖之势,它成为影响研究者的一大困境。这具体表现在:第一,各类课题项目中,资料性内容占比相当大,这既与当下的新媒体大数据资料库建设有关,也与人们的“资料思维”相连,也不排除一些有目的性的跟风。应该说,高度重视和大力强调资料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并不过分;但要避免课题中的“资料”跟风,更要避免以“资料”之名行投其所好之实,还要避免被“资料性”遮蔽了主体性。第二,在硕士、博士论文中存在着对资料的过分追求。翻开许多硕士和博士论文,里面的知识性和资料性占比相当大,这既包括前期研究成果的繁琐梳理,也包括大量的常识性陈述,还包括呈堆积化的观点引注,而真正能显示出作者自己的话语部分则相当薄弱。不少硕士、博士论文往往给人这样的感觉:“又大又厚一张皮”里包裹着苍白的内容,巨大的论述空间不得不用很多“资料”进行填补。第三,不少学者包括有的知名学者之研究也被“资料”闭锁。一篇文章往往包含铺天盖地的“资料”,如设想一下:将其“引注”删除,所能剩下的属于作者自己的表述恐怕就不多了。这就造成研究者极大的局限:只有依靠别人的话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有人甚至离开别人的观点就不会“说话”,也无法写文章。然而,此类文章还常被美其名曰:言必有据、学院派研究、有系统的知识谱系,它们实则是一种懒汉式研究,是知识和资料的简单的搬运工。
我们绝不反对“资料”在研究中的具体应用,更对倾其一生做资料梳理、发掘、斟酌,特别是不断有新资料和新发现的学者充满敬意,他们是一些为后来研究者架起学术“天梯”的人。不过,我们也要强调,学术研究不要用别人的资料和观点充斥自己的论文,也不要做没有思考或思想的学问。更需要强调的是,真正在资料中有所开拓和发现的学者,其实也是有思想的,是独特的思想和价值观使其在资料的甄别中不断地有所发现和突破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解决从表面甚至机械地理解论文写作过程中的“资料性”问题。
二、碎片化与整体性
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许多领域都得到开拓,所剩空间在逐渐缩小。今天,在此领域中要想找到一个有价值的选题往往是很难的,这确是一个客观事实。不过,当前学界似乎走入了一个怪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碎片化倾向愈加明显,有些文章狭窄逼仄得让人不忍卒读。
翻开一些学术杂志,整体性研究变得越来越少,碎片化研究越来越多。这包括:其一,单个作者作品研究盛行以至于泛滥。以往,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宏观研究以现象、思潮研究为主,我们比较容易看到那些有分量、力量、气势的研究;相反,作家作品研究算是微观的了。而今的情势正相反:作家作品研究成为主体,也成为刊物的主打;中宏观研究则较难看到,更不要说那些富有思想性和文化深度的宏大问题的研究了。其二,作家作品研究又被分得很细,像鲁迅、张爱玲、钱锺书、赵树理、汪曾祺、路遥等人的研究都在走向细化。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好事,因为通过细化研究可达到中宏观研究所达不到的地方;但这种细化有时也有碎片化之嫌,即许多研究往往属于过度阐释,与主旨、主题关系不大或游离于主题。其三,在发掘一些被人忽略的选题时,有碎片化的不足。目前,不少研究特别是硕士和博士论文选题过“小”,不少人总是从“边边角角”去寻找研究对象,一般说来这也有意义;但是,也要避免过于拔高和夸大边缘作家作品之价值,因为经过文学史淘洗过的作家作品,不是所有遗漏都有重要价值,还需站在整个文学史背景对之加以认真考察和仔细判断。
如从补漏拾遗角度打捞某些被忽略的作家作品,这对中国现当代研究是有益的;但一定要赋予某些影响不大的作家作品以巨大的价值意义,甚至无原则地进行拔高,也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我们在发掘曾被遗漏和低估的作家作品时,一定要有整体感,要站在文学史、文化史上对其独特价值进行审视。另外,要改变“捡漏儿”的惯性思维,而要从整体上关注那些重要的事件、作家作品,特别是一些重要重大问题。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现在还远未到资源枯竭和山穷水尽的地步,像散文就是一个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其研究空间和价值是巨大的。季羡林曾对散文评价甚高,有石破天惊之感。面对人们长期以来对小说和诗歌等文体已形成的共识,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散文第一大国”,在中国古代只有“诗文”并称,没小说的什么地位。“我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它“给‘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增添了无量光彩”,而“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至今人们对诗也没能找到一个形式”。这样的评判是否准确,我们姑且不论;但季羡林如此推崇散文成就,与当下人们普遍不重视、看不起散文,特别是不愿意研究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另如,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许多母题、现象、问题都得到关注和探讨,像吴义勤的新潮小说研究,张清华的先锋派文学研究,谭桂林的佛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研究,李宗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父权、母爱叙事研究,都很有代表性。不过,与当下充斥的更多碎片化研究相比,这样的宏阔选题却变得越来越少。
三、滞后性与前瞻性
不少中国现代作家是有前瞻性的,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和李大钊的《青春》就是如此。中国当代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也是有方向感的,像许多国体文学作家刘白羽、杨朔、秦牧、魏巍等都写出不少经典作品,为新中国成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初期的巴金、冰心、臧克家、林非等人,以《随想录》《无士则如何》《博士之家》《招考博士生小记》等关注现实问题,进行新的思想解放,都是值得给予充分肯定的。然而,随着市场化、商品化、信息化特别是新媒体技术的冲击,文学创作开始迷失了方向,至少是大大滞后于时代。这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也有突出表现。
一是研究者跟不上作家创作,只跟在作家后面匆忙地进行解释,更缺乏对于现实的高度重视和大胆超越,未来性向度既不明确也缺乏长远考量,这就导致批评和研究的严重滞后。当研究者的主体性被弱化或丧失,他就只能亦步亦趋,失去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以至于迷失了自我。二是许多研究者不读作品,更不要说细读、精读,于是用各种理论大词进行套用,写出自己不懂、作家不认的花样文章。这也是为什么不少当代作家对于评论家和学者没有敬意,甚至觉得他们的评论和研究与自己的创作无关,根本看不到问题的症结,更不能对其创作起到引导与启示作用。三是研究者缺乏真知灼见,在知识和概念的硬壳中艰难穿行,进行所谓的“强制阐释”,这势必落后于学术、时代、社会,更难以获得穿透力和前瞻性。一方面,不少学者由于视野所限和对现实的冷漠,所以,对于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难做出正确选择和准确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与我们长期以来刻板的知识生产和学术运作方式有关,学院派研究在这样的潮流底下明显失去了方向感和引领性。可以说,在五四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前瞻性,在当下的文学研究中则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很难看到了。
没有思想和智慧作为引擎,学术研究就会失去方向和动力,也不会真正获得广大的读者受众。在新时代,学术与文化的引领性和预见性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需要具备富有远见的成熟的认知能力。作为时代和社会的敏感神经,文学研究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感,在这方面学者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如在城乡关系中,我们的当代作家和学者普遍趋向保守,即存在强烈的“乡土情结”和“都市恐惧症”,缺乏长远的建构意识和引导性。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作家和学者为国家和社会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提出了富有前瞻性的建设性意见,如巴金的《随想录》振聋发聩;但是,后二十年,他们却明显滞后于时代,更没能提供应有的智力与智慧支撑。
四、顺势化与反思性
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变得越来越习惯于“说好话”,五四时期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热烈争鸣与严厉批评现已很难看到,甚至变得有些销声匿迹。换言之,目前的文学研究界,“顺势”研究越来越多,“逆势”甚至反思性和批判性研究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严峻问题。
“顺势”研究有其优点:它能充分看到作家作品的价值,以低调甚至谦虚谨慎的态度对待作品,以避免过高估价批评家和研究者自身的水平和作用,更不容易使自己变得自高自大、狂妄无知。但这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批评家和学者对作家作品缺乏挑剔的眼光,不能看到和指出其局限不足,将自己与作家放在同一水平上,不能发挥作为一个批评家和学者的独特眼光,久而久之容易失去自己的独特判断力和审美力。“顺势”研究大致有以下情况:一是圈子研究。学者和作家的关系非同一般,有的甚至是黏在一起的朋友关系,所谓的评论就是“多说好话”和“大肆吹捧”。与作家有着共同的利益使研究者只能说“好”,不能说“差”,更不能说“坏”。二是跟风研究。不少研究者与作家并不熟悉,更不是朋友和利益相关者,但这也不能影响到前者对后者的认同甚至崇拜,于是,目中所见处处为“是”,所看到的也是处处闪着耀眼的金光。可以说,不少研究者缺乏反思意识和批评精神,也没有基本的鉴赏能力和审美判断,那么他的研究就很难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更不要说尖锐的批评意见。因此,只在“顺流而下”中不断地褒扬作家作品,成为不少研究者的基本思维定式。三是为研究而研究。不少研究者往往缺乏文学史、文化史背景,也没有基本的公正公平和客观判断,所以容易出现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一味地说好”和“无限地拔高”的局限。似乎说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好,就降低了选题的价值似的,于是一个很一般甚至拿不上台面的作家作品,却被研究者捧上天并赋予了巨大价值。在边缘作家的发掘和研究中,此类情况最为常见。四是研究名作家的情结所致。如今的当代文学研究有这样的趋向:哪个作家有名,学者就跟在后面研究;名作家出版一部作品,学者就争相对之进行阐释,于是出现跟在名家名作后面有无数“研究者”的局限。相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即使作品写得再好,也往往少有甚至无人问津。五是变脸研究。学界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同一个研究者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竟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当然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时代在变,人的观念和认识也在变,所得出的结论就不可能一成不变;但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价值观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所得结论的变化太快。这是一个世纪以来应该进行反思的:为什么对于不断变换自己观点的人,人们容易给予赞许;而对那些坚守自己的观点者,人们却多有存疑,甚至以保守者视之并予以否定?比如,长期以来,人们对辜鸿铭的整体评价不高,这不仅因为他的不少观点语出惊人的怪诞,更因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且是一个守旧者和不变者,于是对他严厉的批判和嘲讽。不过,林语堂对辜鸿铭却赞赏有加,他这样评价辜鸿铭:“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林语堂更加佩服的是,辜鸿铭能在众所纷纭中坚持己见,更能在这个没有操守的易变世界中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近现代以来,中国往往不缺少变化的思想者,但稳定的有真知灼见的思想者却特别难得。
“顺势”研究是当前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这就使一些有问题的作家作品得不到批评,对那些普遍被看好的经典作家作品缺乏反思和批评,刚刚出道的作家就会被吹捧得发晕。以余光中、李国文、史铁生、张承志、苇岸、周涛这样的优秀作家为例,至今对他们的高扬之声不断,但反思性的研究极为少见,学界的“顺势”研究将其存在的不少问题和局限简单地遮蔽掉了。
五、技术性与审美化
科学技术特别是互联网传媒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作家的创作方式,也影响了研究者的研究方式。就作家而言,至今仍保持原来纸本写作的人越来越少;就学者来说,不用电脑写作的人可能也极为少见。从正面说,不论是作家还是学者,新科技一定为他们带来便捷与效率,但也要注意其负面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在这方面也不例外。
技术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的积极作用,此不赘述;在此,主要谈谈其负面影响。一是剪贴。以往,大家引用别人的文字,往往需要跑很远的路,有的甚至免不了车船劳顿,从小地方到大城市的图书馆;但这种求知方式有个优点,即对他人的研究成果充满敬畏,自己也保持着谨慎态度,还会反复进行核对,以免出错。如今,有了剪贴技术,只要动动手,转瞬之间即可将别人的观点插入自己的文章。但这也带来不少问题,即在自己的文章中大量堆积着他人的材料和观点,研究者连抄写一遍和核对一下正误的耐心也没有,从而导致不应有的诸多错误。因此,剪贴技术在方便的情况下,也导致了“资料性”论文的大量出现,转引者跟着原作者的引文一起错,这是一种典型的懒汉式研究和写作。二是统计。现在不少文学研究论文有大量表格、数据,特别是大数据为研究提供了巨大方便。从表面看来,这是一种新技术催生研究的有效方法;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如不动脑筋、不考虑具体语境、忽略数据的真实性,都会将研究导向失误甚至于虚假。另如,从读者、传媒、生产等角度研究文学,不少人可能就忽略了当时的社会与文学产品存在的虚假接受问题,从而导致表面数字的正确精微所遮蔽的实际虚假。三是模式化。时下有血有肉、有文学性、有心灵参与、有审美趣味的论文极不易见,倒是概念化、模式化、格式化的研究非常盛行。究其原因,新科技的影响不可忽略:研究者像机器一样操作、运行、选择、表述,于是成为千人一面、毫无生气、面目可憎的论文写作。读这样的论文仿佛在受刑遭罪,也是没有多少收获和乐趣的苦差事。对于高科技要有清醒的认识,它是一把“双刃剑”,具有正负面的双重影响,文学研究者对此不可不慎重考虑。
读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李长之的鲁迅研究、宗白华的艺术研究,甚至读梁启超、梁漱溟、钱穆、费孝通的论文,都有一种普遍感觉,那就是:在自然、平淡、常识性的表述中,有真知灼见,充满灵性与诗性,是智慧与美的显现。今天,能达到这样高度和境界的学者比较少见,倒是被技术化了的人甚多,这在今后是需要进行一番审美洗礼的。
六、僵固化与创新性
就数量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呈几何增长,其间也不乏有价值的成果;但毋庸讳言,真正发自内心、经过头脑思考、有新意的经典之作,并不易得。这就造成这样的现象:一方面,众多学术刊物在铺天盖地的投稿论文面前,选择起来感到无能为力;另一方面,真正的优秀之作又极为难得。我们面临学术研究被固化、硬化、僵化、异化的危险,特别需要呼唤有创见的论文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文艺创作是如此,当前的文学研究更应是这样,创新成为新时代文艺创作和研究的一个急迫任务和重要使命。
关于观念的固化和僵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至今已经较为成熟,许多观念被固定下来;但也要看到,观念的固化甚至僵化严重束缚研究的推进和创新。这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城与乡、中与外之间等都是如此。我们似乎进入一个固定的观念轨道,在惯性和自足中运行,从而导致研究过于墨守成规。其实,今天有许多研究观念都需要进行反思和调整,也需要进行不断地大胆创新。比如,“人的文学”观念在五四时期甚至较长一段时间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自由、民主、平等和科学特别是人的解放和个性解放已经深入人心;然而,这一观念的局限并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其负面影响更被淡化了。如人的个性不受限制后的欲望膨胀,爱情至上导致的道德伦理特别是天地伦理的丧失,对于天地失去了敬畏和谦卑之心的自大狂妄,集体、群体被个体覆盖以至于践踏,都是“人的文学”不受规约后产生的弊端。关于这一点,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西方式的个性张扬和自由追求决定了疫情很难得到控制,我国的制度优势和集体主义精神在疫情防控中得以彰显。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要想真正得到历史性突破,反思、突破和更新观念至为重要。
关于方法和路径的依赖。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主要还是学院派研究模式,这一方法有其学理性强的特点,但也有过于刻板和模式化的不足。当这样的文章看多了,特别是学院派研究积重难返,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八股文风气。这主要表现在:首先,三段论式的结构,即先梳理当前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后堆积与此问题相关的理论,再以个案论证自己的选题。其次,理论先行的分析论证,即预设一个理论模型,以此为标杆,用作品进行说明甚至填充,从而造成理论大于作品、主题大于结论的不足的问题。最后,叙述方式和语言表述死气沉沉。文章不是越写越明白,而是越表述越糊涂;西化的长句子拖泥带水不说,细加分析还有不少的语法错误;有的文章经过千回百转的论证,结果得出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常识结论。至于说灵气、才情、文气、诗意,往往像沙漠抽水一样难得。在此,作家毕飞宇用心用力所做的“文学论”值得学院派研究、学习和借鉴。我曾谈到“作家的散文论”,多是充满生命质感、有创新认识、灵动飘逸、无八股气的妙文。
中国现当代文学本身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也是最鲜活、最灵敏、最多样化的,对之进行学理性思考,特别是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阐释,无疑是必要的,也是一条重要的深化之路。不过,我们不能进入模式化、形式主义、八股文的写作,这就难免将论文写“死”,从而造成与研究的问题无关甚至于相去甚远。新时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成为虎虎有生气的新的创造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