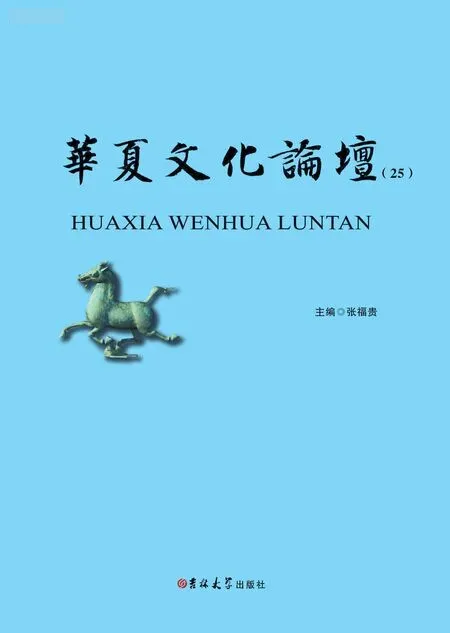《奔丧》:家庭视角下的瘟疫叙事文本
杨厚均 方韬慧
一
伴随着百余年来现代化追寻的历史,中华民族也面临过不少自然灾害和流行瘟疫,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损害。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因为科学技术的落后以及社会的动荡,这种损失与损害,尤为深重。灾难本是文学表现的重要母题,“人类历史在较大程度上而言其实就是一部人类受灾史、受难史,人类面对灾害灾难的各种‘考验’受到了文艺家和学者们的共同关注。”然而新文学以来的中国文学关于灾难的客观叙事整体上是不够充分的。现代性追求的心理焦虑,作家们更多地聚焦于由社会文化落后造成的人的精神的萎缩,以为重铸民族灵魂之动员,或者作为革命合法性论证之铺垫。前者以鲁迅为代表,后者以左翼文学中的革命叙事、社会主义文学中革命历史叙事以及农村合作化叙事等为代表。纯粹的灾难叙事并未成为新文学的真正自觉。新时期以来,开始有一些较为充分的灾难叙事文本,但这些灾难叙事仍然不过是作家控诉历史、发掘人性的美好或者复杂的“方便之门”,其策略以及叙述效果与前面所述并无二致,这样一种“方便”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灾难的深度介入。
湖南作家彭家煌发表于1928年1月出版的《小说月报》十九卷一期的短篇小说《奔丧》,是一篇难得的客观叙述瘟疫灾难的文学文本。小说以纪实性的笔法,讲述了“我”为在虎列拉(痢疾)瘟疫中去世的母亲奔丧的全过程,详细地记录了“我”一家在瘟疫中遭受的灾难,其真实性和精神上的痛苦体验。小说对20世纪20年代流行多年的“虎列拉”(痢疾)瘟疫中社会底层所遭受的深重灾难进行了客观详尽生动的记录,在真实披露黑暗社会现实的文学价值之外,另有一种记录那个时代底层社会疫情场景的历史文档价值。
和一般的关于灾难叙事的文本一样,彭家煌笔下也有对疫情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问题的揭露与批判。小说以一个底层知识分子囚于日常生活的困境而悲观绝望的精神世界为底色,聚焦于从上海经武汉到湖南乡下奔丧的全过程,一路上(包括返回)也写到当时的军阀混战、民众的愚昧、党国要人的霸道等等,但实在说,这些我们过去所看重的“革命性”“批判性”元素相对于瘟疫本身的叙事,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小说百分之90%以上的篇幅都是直叙疫情惨状,给我们留下了沉重难忘的印象。
根据历史记载,20世纪20年代在全国各地瘟疫流行,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对民众的生活造成巨大的损失,对民众的生命带来严重的威胁。单以湖南为例,“1920年、1922年、1925年和1926年,疫病为患均超过10县,特别是1926年疫灾所及多达20县,……而1918年至1927年10年间,平江疫病流行竟达9个年份。”《奔丧》所涉及的就是发生1926年秋流行于长沙、湘阴(包括现汨罗)、平江交界区域的那场疫病。小说写主人公“我”回家奔丧的过程中,也多次提到当时瘟疫在全国各地的流行情况,这一家庭瘟疫叙事背景,让我们对20世纪20年代虎列拉瘟疫时间上的持续性和空间上的广泛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小说在写收到丧信之前有一段当时生活和精神困境的铺垫,从这里开始,就不断地提到瘟疫:“实在,七八年来我简直是在尸堆中出入,在坟墓里盘桓,吸够了腐臭的空气,饱尝了疫疠的滋味,也见惯了赤血的横流与野兽的攘夺,在种种凄切的流浪的经历中,不由得我的心炼成了硬铁。”在这一段言及“我”与家乡关系的文字中,“七八年来”“饱尝了疫疠的滋味”,道出了家乡瘟疫的持续时间及伤害程度,紧接着作者就写到了当时所在的城市上海的疫疠惨状:“今年七月间,我住的这城中又照例的蔓延了虎列拉,医院里塞满了病人,街上时时可以看见出丧的队伍,好像死神特来收罗过剩的人口似的。”瘟疫不分乡村城市,广泛流传,无处逃避。在从上海经武汉到湖南的路上,有三次提到南方的瘟疫:第一次是上船不久,在“不见天日”的统舱里,听乘客们“谈他们年成的薄收或缕述战地的惨状与天灾的流行”,这里的“天灾”就是指的瘟疫,因为他紧接着写道:“我想这中间总有不少是战地或虎列拉区域的难民,也有不少是奔丧者”;第二次是到九江“革命军的辖境”后,和北伐军战士的交谈中,得知北伐军战士“在韶州湘南一带遭瘟疫病死了不少”;第三次是下火车到湖南家乡后,听轿夫说“他们那块秋收不好,又遭瘟疫,有一家十三口瘟死了只剩一个孩子,差不多是一屋一屋死的。那才凶险呢!”。
这些都是关于社会的面上的瘟疫叙事。
二
《奔丧》最震撼人心的地方还在于对“我”的家庭所遭受的瘟疫之痛的叙述上。作者家庭叙事的角度让我们获得和其他文本中不一样的瘟疫体验。人类的构成,哪怕到了最现代的社会,最小的最基本的单位也依然是家庭。人类的灾难包括瘟疫,所造成的痛苦,最直接的最不堪的承担者依然是本人以及由血缘婚姻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家庭了。因此,从家庭的角度来叙述灾难,无论是外在的灾难现场呈现还是内在的精神痛楚的表达,当是最能深入灾难本身的角度。《奔丧》以近乎自然主义的冷峻而精微的笔调,为我们展现了瘟疫中的家庭惨状,感受到在瘟疫中的处于自然家庭状态下人的无奈与绝望。
分裂的家庭叙事,是《奔丧》叙述的基本结构框架,这一基本框架与现代家庭特殊结构方式相关联,也与这一框架结构中家庭成员的情感撕裂相呼应。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家庭的分裂是一个带有标志性的社会现象,这种分裂是由年轻一代出离家庭走向城市融入现代化进程所引起的,走向城市的年轻一代不再回到乡下传统家庭,在城市恋爱结婚成家,但同时又与乡村原生家庭保持着无法分舍的联系,传统的大家庭由此而分裂成多个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家庭单元。彭家煌走过的正是这样一条现代路径:1915年随其舅杨昌济到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18年毕业后又随杨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补习学校任教,并与其学生孙珊馨恋爱,1925年在上海结婚组建家庭。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家庭,这个家庭处在竞争更为激烈的都市社会环境中,需要他努力工作,赚足够的薪水去支撑现代都市的生活方式。而与此同时,来自湖南乡间的彭家煌又不能不时时牵挂着千里之外的那个传统家庭,那个家庭希望他光宗耀祖,希望通过他摆脱贫穷。这两个在传统社会中本该合二为一的家庭,因为现代知识分子生存方式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思想观念与物理空间的差异与分离而割裂为两个不同的家庭单位。两头牵挂心猿意马便成为这样的家庭结构中主要成员的结构性精神模式,这是一种撕裂的痛苦的精神模式。
如果说,在正常情况下,这样一种撕裂还可以理解为一种必须承受的现代性阵痛的话,那么,当瘟疫袭来,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更需要家庭成员共同承受、共同呵护时,这样的一种撕裂就会成为这个社会乃至每一个个体所不能逃避且不能承受之重,这是一种没有任何退路的撕裂。《奔丧》一开始便从“我”在上海家庭思念湖南乡下家庭着笔:眼前的上海家庭困境与心中的乡下家庭给自己带来的种种苦楚交织在一起。而最后的落笔,写离开乡下家庭回归上海家庭,对乡下家庭的牵挂与对离别几个月的上海家庭的担心再次纠缠不清,“我”始终处在一种精神撕裂的痛苦之中。一头一尾,在“撕裂”中展开,又在“撕裂”中收束:离家七八年来,“我”饱尝了上海湖南两个家庭的“疫疠的滋味”,“耽心自己会传染,同时也耽心数千里外家乡也会有这种病症”,一方面“二哥,三哥,两侄,和母亲染疫死去的消息接连的传给我”,另一方面,想“我自己也处在虎列拉的环境中,说不定也将有死耗传给家里”,更为现实的是,当我打算回湖南家为母亲奔丧时,却还要面对来自上海家妻子的担心:“这如何能去啊,瘟疫这样凶险。”当“我”执意要回去时,又担心妻儿生活为难。到最后,在湖南乡下为母亲办完丧事返上海时:“我遥望家乡的水程,又极目船行的方向,我全身抖颤的临风语道:父亲啊,大哥啊,我由汉口动身了。妈妈和二哥三哥他们省下的口粮,年内总还够你们吃几顿的吧!妻啊,儿啊,我离别你们后两个月中,你们是怎样活的啊!”小说就在这样一种两个家庭两相牵挂的苦情中结束。
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看到,通过瘟疫叙事,作者把这样一种现代家庭结构性撕裂逼到无法回避的死角。在同时期或稍后其他作家的家庭叙事中,也有涉及家庭撕裂的文学叙事,但往往城乡两个家庭的撕裂更多地来自形而上的观念层面,而在彭家煌这里,因为瘟疫的“逼迫”,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这种撕裂更多地具有“形而下”的原始意味。
三
被瘟疫逼到没有退路的最原始层面上的苦难的,还有传统家庭的无能与渺小。
《奔丧》的主体部分是关于湖南乡下那个家庭的瘟疫叙事。
通过文本,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我”的乡下家庭在瘟疫之前,还算是一个有一定实力的家庭。首先是人丁旺盛,有十多号人,光兄弟就有七八个,包括死去不久的祖母,也算是四代同堂,据说祖母去世时,(非瘟疫所致)“大厅上一片白茫茫,满跪着披麻戴孝的儿孙”。其次是居住条件不错:有正屋侧屋,有上厅下厅,有卧房厢房,有厨房伙房。此外还有一定的家业:有祖田,有猪牛。而且,在当地应该还有一定的威望,祖母出殡的那天,“送柩的有五六百人,延长到两三里,乡人不能亲来祭奠的,都在道旁设案遥祭。讲到开销,光肉猪都杀了八只。”这在20世纪20年代的湖南乡下是非常可观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殷实的家庭,在瘟疫来袭时,却是迅速颓败,不堪一击。《奔丧》详细地记录了在瘟疫面前家庭应对的手足无措与悲惨结局。
瘟疫传染之快、后果之严重,是这个家庭始料不及的。秋收之后,先是在离家颇远的高等小学寄宿的二哥的孩子礼儿染病,回来后第三天就传给了其弟文儿,然后逐渐传给大人“我”二哥、三哥、父母亲及全家,以至于“满屋都是病人”。更为可怕的是,病情发展迅速,极短的时间里,病人很快便接二连三被病魔迅速夺去生命:礼儿在得病的第四天落了气,当一家人围着大床哭得起劲的时候,窄床上的文儿又落了气,刚把两个小的马马虎虎抬出去埋了,二哥三哥又不行了,当晚又落了气,第三天两个兄弟刚出完殡,当晚母亲又落气了。几天之内,五位家庭成员相继丧命。作者是通过“大哥”向“我”诉说的方式来叙述这一段惨状的,用“大哥”的话说,是“世上没有这样凄惨的”。
面对这样的疫情,作为家庭亲人似乎也显得无能为力。他们只能是疲于应付,照看这个那个,掩埋那个这个,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好的办法,甚至跑药铺请郎中都来不及。大人小孩,最多的就是抹泪、哭泣。《奔丧》是一部充满哭泣的文字。全文约一万字的篇幅,而明确使用“眼泪”“哭”“抽噎”就达30余处,平均300多字一处,30余处哭泣,除开头5处发生于上海家庭,结尾2处发生于回上海途中,属于前述“撕裂”之哭外,其余23处都发生在乡下家庭,更多的是悲哀与无助。其中最集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大哥”向“我”倾诉家里疫情惨状的那段文字,这一段文字包括叙述倾诉行为、场景以及“大哥”的原话,只有大约1200字,但上述字眼出现频率却高达12次,其中“大哥”回忆当时情景的直接引语约1000字,这1000字中,出现了5处“哭”的行为,有“我”(这里是指“大哥”,不是文本“叙述者”)的“哭”、二嫂的“哭”、妈妈的“哭”,还有两处众人的“哭”。这五处“哭”把这个家庭的无助推到极致。
彭家煌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不苟言笑的冷静的人,他的创作风格也基本体现出一种沉郁的风格,而在这篇看似冷静的并不很长的篇幅中却如此高频率出现“眼泪”“哭泣”“抽噎”等在同时代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自述传抒情小说”中常见的标志性字眼,可以想见作者对家庭在瘟疫中的无助到了怎样的一个地步。
《奔丧》还多次提到瘟疫给这个家庭带来的身体和物质上近乎毁灭性的摧残与打击。“我”是在下了火车后走了三十多里的山路才到家的,到家的时候,那么大的一个家庭居然已没有一点生气,除了饿猪的嗥叫,什么声音也没有;正在彷徨无计的时候,从伙房里奔出一个衣衫褴褛的人,那是“大哥”,“大哥”已经瘦得“头突出胸脯尺把远”;天气并不太冷,父亲苍老枯瘦,穿得非常臃肿在火炉边烤火;家里也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了,也没有菜吃,听说我还有旅途剩下的牛肉罐头,父亲竟喜形于色;一连死了几个人,当时连棺材都买不起。母亲下葬后,欠了一笔债务,靠变卖猪牛还了一点零头,大数目需要变卖祖田,在瘟疫环境下,还不知道祖田能否变卖出去;婶婶家四五个人每餐围着桌子吃那么一小碟没有油盐的干菜,家里连过冬的口粮都无法保障;甚至连“我”返回上海的路费都没有着落,要花人家送来的五块钱份子钱,而且还远远不够,只能走一程算一程;“我”临走时,把自己的卫生裤、妻子的绒毯、洋瓷脸盆、手巾、牙刷、牙粉都给了父亲,父亲还不忘交代“我”:“有钱就寄点回,就一块钱也是好的,家里的情形你是清楚的”。上述种种,哪里还有一点曾经人丁兴旺能送出两个男子外出读书当兵的殷实家庭的影子?
如此近距离写出瘟疫对一个家庭的无情打击,是《奔丧》在众多瘟疫叙事文本中的特别之处。
四
和任何灾难一样,瘟疫往往把人逼到生死的绝境,在生死的绝境中,日常生活中人性的虚伪往往被无情撕破,人会呈现出他最为真实的一面。
正如前述,家庭本是人类最小最稳定最具有安全感的社会单元,寄托着人最原始的社会性需求,维系着诸如血缘亲情、孝悌礼仪、权威秩序等各种家庭伦理。而这一切,在瘟疫来袭时,到底能经受多大的考验,却是我们经常需要反思的问题。鲁迅先生曾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我们都需要时刻警醒,当我们一旦被打回到只剩生存的选择时,我们会是怎样的一种面貌?作为家庭瘟疫叙事的《奔丧》为我们给出了真实而残酷的答案:在瘟疫威胁下,在生存欲望面前,即使是最基本的家庭伦理也可能变得无足轻重。
先从“我”的家庭之外的亲戚说起。亲戚是由每一个家庭成员在组成这个家庭之前的原家庭成员构成,与现在的家庭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旦回到原家庭,互相之间也需要遵循原家庭的一切伦理。瘟疫之下,家庭伦理的坍塌最先便是从关联密切之间亲戚温情的疏离开始的。亲戚的人情往来被决然斩断。当“我”深夜到家,正是母亲停柩期间,“我”看到的人中间,除了父亲、两个哥哥、嫂嫂和说不出名字的小孩外,没有一个亲戚,更没有一个乡亲,要知道,这是一个在地方上有着一定声望的家庭,而且十几个人的家庭该有着多少直属的戚族呢?如此清冷,大概是怕传染?“大哥”后来说:“可怜呢,害了这种病,什么人都不敢上门。”颇为吊诡的是,在母亲出殡那天,却来了一批“借吊唁为由在我家吃上半个月的戚族们”。其实,当时父亲的病也还没有好利索。可见,怕传染虽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生存绝境下,“吃”又能让每一个生命无往不前。“吃”之外,亲情不再重要,或者只是一个幌子。
如果说,亲戚之间的疏离还多少能够理解的话,那么,危难时刻,家庭成员之间的疏离,则直接预示着家庭伦理的败退。当然,在极为困难的时刻,我们看到了“大哥”和“贵弟”的担当,看到了母亲对患病的疯子“三哥”不离不弃的母爱,但我们也看到了弟弟“端伢子”的不孝。母亲八个儿子,临死前,两个在外,两个瘟疫中去世,一个过继,只有两个儿子送终,这是母亲“死都不甘心”的。过继的“端伢子”其实就在附近的十叔家,且是母亲一手养大,但母亲生病后一直没有来看一下,快落气时母亲想见他,着人去喊了两次,他也只在窗外望一望,没有进屋。当“大哥”跟“我”说起这些的时候,“我”试图替“端伢子”说话:“这种病本来就使人害怕,也难怪……”,“大哥”立刻打断“我”说:“他的性命这样要紧啊,我跟贵弟又没有瘟死,他又不是没传染过,他自己那几天也肚子泄,为什么都不能来啊!妈妈落气的时候还在骂哈,这家伙将来遭雷打得。你看喽,后天就要开吊啦,他还有心思到巴陵去贩虾子,这样没看见过钱,这又不是别的事,死了娘咳!世上没有这样不懂事的东西。”“大哥”的话由“悲哀”变了“愤怒”,这“愤怒”正是对瘟疫之下家庭亲情丧失的愤怒。而在“端伢子”看来,瘟疫威胁之下,“怕死”和“贩虾”谋生也许远比为母亲尽孝要来得重要。
在这个家庭中,“端伢子”似乎并不是一个个例,只是表现的形式有别。《奔丧》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这一人物形象。在传统的家庭中,年龄最长的父亲代表了权威,处于家庭伦理的最高层。《奔丧》中的父亲,不仅是可悲的,可怜的,甚至也是无情的。“我”回家时,第一个见到的并不是最想见的多年未见的父亲,“我”的回来,也没有引起父亲的注意,天气并不冷,父亲在伙房烤火,穿得很臃肿,见到“我”的时候也显得特别的冷静甚至麻木,只是慢慢地抬起头来说:“唔,蕴松,你回来了啊!唉,想不到你也回来了!”父亲染病还刚刚好转一点,他已经被自己的病和家人接二连三的死去折磨得毫无一点生机。然而在听说“我”提篮里还有罐头牛肉时,父亲却突然变得兴奋起来:
“啊,有牛肉呵,好,好,就从明天起不必吃斋了。绍丹,你关照婶婶一声顺便把牛肉拿来。”父亲听到有牛肉,喜得什么似的。绍丹将牛肉拿来了,父亲一把接住,在小碗柜上取了筷就吃。“我是今晚就要开荤——嗯,牛肉味不错噢,哈!哈!哈!这一罐不知要多少钱呢?——嗯,我还吃点看。”
我瞧着父亲的白胡子一翘一翘,脸上的筋骨的震动,舌儿答答的响,我又掉在悲哀的海里了。我想:父亲不知有多少年没吃过牛肉呢!——对着我便忘却一切过去悲哀与将来的苦楚,喜笑颜开的打哈哈,我走了之后,他又将怎样呢?
母亲还停柩在厅上,家人还在吃斋之日,本应在悲哀之中的父亲,却因为有牛肉可吃而“喜笑颜开的打哈哈”,并且断然宣布自己“今晚就要开荤”,完全看不到为父的任何尊严。当“我又掉在悲哀的海里”时,传统家庭的父亲形象已完全坍塌,剩下的就只是可怜了。临走前,父亲居然很羡慕“我”的卫生裤,也居然接受了“我”脱下来给他的裤子和其他“我”路上必需的生活用品,在这里,我们也丝毫看不到父亲对再度远行的儿子的那种慈祥的父爱。
父爱不再。只有自私无情而可怜的父亲。家庭伦理的支柱遥遥可坠。这才是瘟疫之下家庭的深层困境。
五
瘟疫之下家庭的困境,对作者而言,纯粹是一种个人情绪的发泄还是另有意义?
《奔丧》发表于1928年,而“奔丧”的事发生在1926年,为什么在时隔两年后再来写《奔丧》?也许最直接的回答就是赚稿费,因为彭家煌写作的一个最直接的动机就是赚钱谋生。但彭家煌又是一个有责任感有思想的青年文人,谋生之外,也应有别样的逻辑。
如果联系彭家煌的创作轨迹及其创作背景,我们也许能更好地理解《奔丧》家庭瘟疫叙事的意义。
据严家炎、陈福康的《彭家煌生平与创作年表》记载,彭家煌的第一篇作品是1925年2月发表于他自己参与编辑的中华书局的《小朋友》杂志的《一个很长的故事》,属于童话。之后他转入商务印书馆助编的《儿童世界》,他又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诸多儿童故事,直到1926年2月才开始在徐志摩编的《晨报副镌》发表小说《Dismeyrer先生》,可以说,这一时候,彭家煌才算是真正以作家的身份获得承认。因为之前的儿童故事的发表,还带有自编自作的性质。事实上,这篇《Dismeyrer先生》最初交给当时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并没有获得认可,直到在《晨报副镌》发表并引起了较大反响后,才引起注意。据说郑振铎后来还向彭专门道了歉。大约是因为这个原因,到1927年前后彭开始在与文学研究会关系密切的《文学周报》《小说月报》陆续发表作品。彭家煌的第一部小说选集《怂恿》出版于1927年,被列为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周报社丛书”之一。这期间直到1928年6月《晨报副刊》终刊,彭很少再在徐志摩主编的这一刊物上发表作品。这一切表明,真正走向文学创作的彭家煌很快就与文学研究会同仁靠得更近,事实上,从创作倾向上看,彭家煌的创作也更倾向注重社会人生的文学研究会。彭家煌出生社会底层,也曾怀抱社会理想,和毛泽东等一批湖南青年到北京准备参加赴法勤工俭学。这一切也为他后来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奠定了基础。
如果这样的一种判断大致不错,那么,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我们来看《奔丧》的家庭瘟疫叙事,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奔丧》的家庭瘟疫叙事,是彭家煌进入文学研究会同仁圈后的作品,其写作既保留了早期带有自述传色彩的个人苦闷抒发的痕迹,又融注了他对社会的深入冷静思考:不仅批判了在瘟疫面前当时社会的无能与混乱(在作品里,几乎看不到执政者对瘟疫的有效防控),更为深刻的是,在彭家煌看来,传统家庭的力量在社会苦难面前的苍白,尤其是瘟疫加剧了社会灾难时,家庭的无力就显得尤为突出,社会的颓败,家庭也没有出路,而社会的出路,也许要从破除家庭的枷锁,打破传统家庭的幻想中去寻找。而这,离左翼革命文学中的灾难叙事如同为湖南作家丁玲的《水》、叶紫的《丰收》也许只有一步之遥了。
悲观、沉郁的背后,《奔丧》也许涌动着另一种激情。
然而,也正因为还有这一步之遥,《奔丧》的叙事还没有被这种激情所覆盖,但也没有简单而急切地附会到这之前鲁迅那样的国民劣根性叙事之上。彭家煌执着于灾难中家庭的苦难,执着于真实的细节与尖锐的痛楚,通过一种近乎自残的方式,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在瘟疫中再也无法回归的家庭。
如果要从文学史的角度做一个定位,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叙事,彭家煌的《奔丧》和他的同类的作品大约处在由鲁迅的国民性叙事到左翼的革命叙事的过渡地带。又因为这一地带在中国现代文学仓促的进程中并没有获得更为充分的空间,彭家煌的作品包括这一篇《奔丧》便显得更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