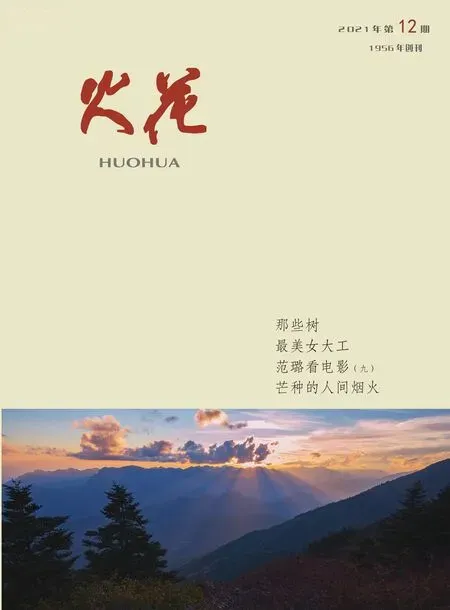蔡润田:后乐先忧古士风
杨占平
2013年的最后一天,作家韩石山先生读过蔡润田作品集《南华杂俎》后,致函蔡润田先生,称其“既见学识,又见文彩”,并手书一联相赠:“老安少怀平生志,后乐先忧古士风”。这两句话应当说是对蔡润田一生为人为文相当准确到位的评价。作为山西文学界当今资深的编审、评论家、散文家,蔡润田是伴随着新时期山西文学的发展一路走过来的。他没有大起大落的官场经历,没有轰轰烈烈的文坛焦点,也没有让人经常议论的人生风雨,总是兢兢业业干事、认认真真写作、老老实实做人,工作任职期间业绩圆满,作品虽然不够多却没有劣质,跟人们相处一贯谦谦君子,传承了古往今来文人士子的风节,口碑很好。
蔡润田的祖上原本居住在山西省平定县石门口村,祖父在天津一户商铺做账房先生,收入尚可维持全家生计;可惜英年早逝,家境很快陷入困厄。迫于生计,奶奶携幼小父亲改嫁到本县朝阳堡村白姓人家。奶奶明事理,让父亲幼年即进入私塾,接受孔孟蒙学教育,把《三字经》《论语》《孟子》之类四书五经都读烂了,课余还要下地做农活。长大之后,结婚生子,继续祖父之业,外出行商,足迹遍及晋冀多个县份。
1943年阴历六月十五日,蔡润田出生。有父亲经商供养,全家生活能够保障。然而,那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平定县作为敌我“拉锯”地带,经常有战事,人心惶惶。他刚刚四岁时候,为避兵燹,一家人离开老家,跟随父亲到了省城太原,仍然是战乱不安。当时铁路已经中断,父亲多方努力弄到机票,带领全家人乘坐慈航班机,飞到天津,又转至唐山,伙同先期到达的亲友,从事印染业买卖。四岁的蔡润田,坐飞机的奇妙印象并不深刻,只记得颠沛流离,幼小的心灵对大千世界产生的是恐惧心理。
蔡润田一家在唐山安顿下之后,十来年光景,依靠父亲自任掌柜,先后辗转唐山郊区、滦县、滦南县的多个乡镇开染坊,做实业,付出很多辛苦,收入也不错,虽然是国家新旧交替时候,却让全家的生活过得还是比较顺畅。父亲喜欢他,带他跟随各地,给他留下美好的记忆,这在他的散文集《独语集》里有极其鲜活的表现,至今他都能讲出当时去过的小新庄、甸子等地的许多故事。平原的广袤辽阔、乡民的淳朴友善、生活的优游无虑,正是这些自然与人文环境,铸就了他幼年率真乐天的性格。
但是,到了蔡润田七八岁时,他的母亲患上痨病,不及三十岁就去世了。这个变故对他的打击非常大,感觉未来的生活一片茫然,快乐的日子再也没有了。虽然不久父亲再婚,继母也能满足他生活的基本要求,毕竟感到隔膜,难以给他精神上的慰藉;同时,父亲看他到了读书年龄,为了他长大后能成才,管教也严格有加,这样,年幼的蔡润田越来越拘谨,不敢在大庭广众下多讲话,做事总是小心翼翼。
1956年,国家对各类企业实行大规模的公私合营政策,蔡润田父亲经营的染坊被合并到公有制企业,父亲不再参加管理,收入也大不如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次年他们一家迁回山西平定老家。起初在镇上开裁缝铺,不久停业,就回到本村。家境、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吃饭居住条件更是下降很多。在村里,他们家是唯一的蔡姓外来户,当时,宗法意识很浓的农村,都是以家族为伙伴来往,他们家本来就是外来户,再加上新回到村里,自然要受到排挤打击,人际关系比较紧张。新的生存环境让蔡润田非常不适应,进而使他已经少言拘谨的性情更为加重。那时,他尚未读完高小,转到锁簧镇学校读了几个月毕业了,凭着优异成绩考入平定中学。
中学生规定住校,能够暂时脱离家庭的烦恼,让蔡润田似乎找到了新的净土,一切都向顺畅惬意目标进展。他靠着出色的学习成绩,当上学校大队委、语文课代表等等,除了认真完成各门功课,还积极参加课外活动。然而,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迅猛到来,就在他们学校里,同样进行得轰轰烈烈,他眼见一些平素所尊敬的老师骤然成了右派,被批斗的场面让他这个好学生无法接受,他感到惶惑甚至悚惧,想到自己将来想靠好成绩谋前途是多么不容易。
如果说反右运动中蔡润田还只是一名观看者,那么,转年又掀起的反右倾运动,他就没那么幸运了。这场运动有所谓“拔白旗、插红旗”内容,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成了运动的对象。当时,十四岁的蔡润田是初一第二学期学生,初露文学写作才华,在老师的指令下,为学校的墙报写了一篇稿件,题目为:《汪洋一幼鱼》,大体内容是抒写了一个热情上进却感到迷茫无助的少年,期望得到党的引导,以便走出迷茫,走向光明。不料,稿子被团支书认为是倾向不正确,拿去交给了一位由轻工局派到学校的专职“红旗”班主任。这位政治至上的班主任如获至宝,多次找蔡润田谈话,要他交代写作动机是什么,这让他惶惶然不知所措。接着,班主任召集全班同学以及科任老师开他的批判会,说他稿件中的“党”,是国民党,说他是小右派、反革命,等等。一个初一学生,哪里经历过如此屈辱,本来就脆弱的心灵受到了严重挫伤,极大地改变了他的思想性情和生活态度,只能以消沉畏缩的心态观察社会,与人交往也因为压抑而变得沉静甚至于冷漠;于是,中学生蔡润田不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除了上课,就是寻找各种书籍阅读,好学勤思的习性悄然形成,他感觉到,只有读书和思考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在书海里,他可以畅快游动,获取丰富多彩的知识。
经历了那次“运动”,蔡润田与读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读书也成为他终身不弃的爱好。整个中学时期,他以近乎狂热的状态披览所能得到的益智悦性的书籍,尤其是鲁迅著作,尽管似懂非懂,囫囵吞枣式阅读,却能领略到鲁迅作品中那种不屈辱的品格,让他受用一生。喜欢上读书,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购书、藏书的嗜好,李国涛先生说“他对藏书颇有兴趣”,兴趣在当时就开始培养起来了。他把家里给的不多的生活费精打细算,伙食标准降到最低,节省出一点钱来跑书店,遇到喜爱的或者觉得稀奇的书,毫不犹豫地买下,一些书至今还珍藏着。读书多了,就有想自己写的想法,于是,开始了读书笔记的写作,记述自己的思考与烦恼,也成为他后来文学写作道路的开始。
1960年中考,蔡润田以出色的成绩,考入阳泉二中,进入高中学习阶段。他已经十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遇到国内大饥荒年代。家里同样遭受不测,继母与慈爱的祖母都于当年去世,父亲虽坚韧、勤苦,也无补于事,他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也难免窘迫,经常处在饥饿状态。好在换了学校,政治上对他的压迫不再明显,他喜欢读书的特性得到充分发扬,客观上,也是由于读书可以减少饥饿感。高中阶段,接受能力有了提高,他把兴趣从现当代文学转向古典文学,不少名篇佳句当时都曾熟背,并和二三有相同嗜好的同学学着写诗唱和;同时,把古诗文选本放在身边,随时翻阅;让他最喜爱的是由中华书局刚创刊、装帧简朴、价格便宜、旨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华活页文选》,几乎期期都买。假期住到北京表姐家,表侄带他跑书店,到东安市场古旧书店买下《三苏文萃》《经史百家文钞》《李长吉集》等线装书,回来半懂不懂地阅读浏览。应当说,他对古诗文的兴趣与修习,是从那时培植起来的。蔡润田喜欢读书,让许多同学和老师赞赏有加,毕业时,一位因病不能高考的同学送给他一套范文澜注的《文心雕龙》,语文老师送给他一本《何其芳散文选》。或许这位同学和那位老师想不到,研究古典文论与写散文,真的成了他毕生的喜好,尤其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使他进入了国内“龙学”研究的学者行列。
充实的高中生活,让蔡润田收益良多,从一个青涩少年进入有思维有理想的青年时代。1963年高考,他的成绩自然是优秀的,出于对文学和教育事业的爱好和尊重,报志愿时,他报了中文系与教育系,理想是要做一个文学家或教育家,到校后才知道,教育系招收名额不够,便从报教育系的考生中把他录入了。二者不可兼得,他也只能接受。
接收录取通知书还出现了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插曲。当年夏末,得知录取通知书已经下达,蔡润田兴冲冲地从平定县的家里骑了自行车赶到阳泉二中去查看,结果同班四位考上的同学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就是没有他的。他觉得自己不幸落榜,特别沮丧和失望,但也只能丧魂失魄地往回返,老天也发难,刚出市区,就遇到瓢泼大雨,一路上坡,行进维艰,苦苦行至平定县城。他鬼使神差地到了县教育局,向一位领导讲述自己高考情况,表达想当一名教师的心愿。那位领导知道他成绩优秀,动了恻隐心,要帮助他,让他去一所乡完小当临时教员。这个结果在当时,真可谓是根救命稻草了,他深表感激,欣然从命,当即到了那所学校,履职任教。一星期后,他回家看望老父亲,竟在大队办公室看到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原来是阴差阳错,通知错发到昔阳县,又辗转回到他的村里。这个插曲,还是让他感受到了人间有温暖。
1963年秋天,二十岁的蔡润田带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进入山西省最高学府山西大学就读。尽管不是中文系,但教育系所设立的科目,诸如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教育史、逻辑学、习作、古代汉语等等,新颖而杂多,都是他比较有兴趣的。大学生活不像中学管理严格,课业也不重,课余他就去读那些爱好的文学书籍。图书馆的阅览室,晚上,那长长的栗子色书桌上,绿油油的玻璃灯罩下洒出一片清辉,清幽、静谧的氛围令青年学子蔡润田特别陶醉。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读郑振铎编的《世界文库》,读赵家壁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读蒙田的散文,读尼采《苏鲁支语录》,读世界名著《美狄亚》《死魂灵》《简爱》,读古典诗文《唐传奇》《花间集》,读鲁迅、冰心、朱自清……时日既久,竟招来系主任老师的注意,在其学生花名册上,给蔡润田名字下注明“跑图,不巩”的字样,意思是爱泡图书馆,专业思想不巩固。但他并没有太在意。可惜这样安心读书的日子不长久,1965年就断断续续走出校门参加“社教”“四清”运动了。
1966年夏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山西大学是全省的运动中心之一,三年级学生更是主力,蔡润田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到运动中。1968年10月,中央下达命令,全国所有大学生到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于是,他跟同学们奉命到了河北获鹿的解放军农场,在解放军官兵的带领下,每天或劳动,或军训,或政治学习。
1969年底,各地大学生结束劳动教育,分配工作,按照当初离校前的校方分配方案,绝大多数下到基层的工厂、学校、乡镇,而蔡润田是比较幸运的,被分配到阳泉市文化系统,并且就留在文化系统革委会机关业务组,这让他感觉到命运的垂青。他的工作主要是编辑刊物《文化战线》,组织全市文艺汇演,还有其它日常具体工作。由于他年轻肯干,乐于出力,尽管事务很多,却也深得领导和老同志们的关爱。三年后,文化系统革委会撤销,恢复文化局,他也随之成为文化局工作人员,主要工作仍然是组织业余创作,经常下厂矿、农村开会或者审看各类稿子。不久,局领导让他创办《阳泉文艺》,集中刊发本市作者的文学作品。这项工作基本上是他一个人做,但这正是他喜爱的,自然干得非常上劲,把刊物办得有声有色,推出了不少后来成名的作家。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蔡润田感觉到自己也应当创作,用作品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先后写出表现一位煤矿工人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崇高精神的长诗《张启林之歌》,写出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矿工斗争生活的多幕剧本《矿山怒火》,还在一些省内外报刊发表文艺评论文章。这些作品初步展露出他的文学创作才华,也受到省里文化部门领导的注意,曾经被抽调到省文化局观摩各地市戏剧汇演,撰写相关评论文章,并且参加过几次省里召开的创作、评论会议。
1975年10月,山西省文艺工作室(也就是后来的省文联、省作协)在太原召开创作会,为《汾水》杂志创刊组织稿件,蔡润田应约与会。工作室负责人马烽、西戎等进一步考察了他的写作水平、工作情况,对他的知识积累、为人处事都满意,这样,会后就被留在文艺工作室,随后办理了调动手续,正式成为《汾水》杂志的一名编辑,参与创刊选稿、编稿、撰稿事宜,重点负责诗歌栏目。工作单位的变化,让他从市级进到省级,环境随之改变,与过去仰慕的老作家马烽、西戎、胡正,与前后调来的有成就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段杏绵、郁波、李国涛、顾全芳、冯池、周宗奇、张石山、王东满等成为同事,让他既高兴,也有压力,决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且也要在写作上有成果,做一名名副其实的称职的文学编辑。
蔡润田在《汾水》以及后来改名为《山西文学》编辑部,做了整整十年编辑,主要是编辑诗歌和评论。他特别敬业,一方面向老编辑虚心求教,把握当编辑的基本功,另一方面自己潜心琢磨、研究,几年过来,就成为一名非常熟练的诗歌和评论编辑,能够从大量的来稿中发现最好的作品,发现有培养前途的作者。那个时期山西活跃的诗人文武斌、梁志宏、马晋乾、张不代、陈建祖、秦岭、周所同、李建华、赵国增、华丹、郭志勇等,都因为诗歌稿件跟他成为很好的朋友;而评论家郑波光、张仁健、张厚余、程继田、高捷、武毓章等,同样跟他成为终身来往的学术研究同道。
作为一名文学编辑,工作之外,一定要用创作来证明自己,蔡润田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完成编辑工作之外,他努力写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配合编辑部编稿需要,以“编者”或者笔名茹辛、茹歆、金梓等,撰写编辑手记、评论,或者配合文学活动撰写述评,配合形势和刊物需要写些新诗;另一方面,伴随思想解放大潮,适应文艺事业发展,对文学创作、理论研究领域的问题进行反思,写出了一些辩驳与解析文章,代表作有: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略论典型化》,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的《文学与人性》,在《山西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朦胧诗风格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浅探》,在《汾水》发表的《试论“写中间人物”》等。这些文章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学术界和文学界都产生过积极影响,其中《文学与人性》一文被选入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一书中。《试论“写中间人物”》获首届赵树理文学奖。此外,按照他自己的研究兴趣,纯粹出于学术研究,认真研读中国古代文论中最经典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其相关的“风格”问题,写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文章,在国内研究《文心雕龙》领域,自成一家,得到众多学者的首肯,不少篇目被权威的《文心雕龙》研究文献著录,被《新华文摘》《文艺理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等杂志摘介。评论家李国涛在给他的文集《泥絮集》序中说:“润田浸渍《文心雕龙》十年,又是为了继承古代文论的传统,对当代文学进行评论。润田的评论文章,字斟句酌,简约清丽,在文体上也很受了刘勰的影响。”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山西一批青年作家凭借丰厚的生活积累、充足的知识准备,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在全国文坛闯出一片天地,被称为“晋军崛起”。但是,作为与创作同为两翼的山西文学评论,却不能跟创作同步发展,并且比较滞后。这个问题成为制约山西文学发展的瓶颈之一,也引起山西省宣传文艺部门领导的重视,顺应广大作家和评论家的呼声,决定由省作家协会主办一份文艺评论杂志。
省作协党组研究,决定由董大中做主编、蔡润田为副主编,具体创办。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并征求意见后,把刊物定名为《批评家》,得到领导的认可,得到广大作家和评论家的赞同。他们从最基础工作做起,找办公室,落实经费,跑印刷厂和邮局、书店,选调编辑,外出约稿,于1985年4月,出版了《批评家》创刊号,打造了山西文学史上第一份专门的评论杂志,对于推动山西文学创作发展、培养青年评论人才、及时评介作家作品,起到了特殊作用,在全国文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他编辑工作的一贯认真负责,同年五月,获得首届“山西省优秀文学编辑奖”。
在做好《批评家》编辑工作的同时,蔡润田写了不少关于山西作家作品的评论;同时,他注意到在新时期文学的蓬勃发展中,渐渐地显露出一些不好的苗头,有感而发,写了一组力图纠偏的文章,如《新潮求疵录》《文学的成熟、人类的悲哀》等。后者以封面标题形式全文选入1988年11月《新华文摘》,并获“双塔”全国征文奖一等奖。这些文章都是扎根于现实,有时代特征。
1989年底,《批评家》杂志因故停刊。一份有过很大影响、培养出一批中青年评论家、刊发过许多优秀文章的杂志,留下诸多遗憾,留下诸多话题,结束了使命,也结束了蔡润田在省作协长达十五年的编辑生涯。三四十岁的大好年华,都贡献给了编辑事业,他有欣慰,也有感慨。在出版《泥絮集》的自序中,他引用清人王苹诗句“身如上水船难进,身似沾泥絮不飞”,取“逆水行舟”“沾泥之絮”的意思做书名,自谦之余,寄托了编辑与写作难以兼擅的感慨。同年,还出版了他与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恒合作搜集、译注的《中国历代谐趣诗》,此书出版后,颇受欢迎,很快销售一空。此外,编辑之余,还应约参与了《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唐宋元小令鉴赏辞典》的词条撰稿、《山西民歌》的评点等项撰述。
《批评家》停刊,他转到省作协文学理论研究室任主任。杨占平、阎晶明、谢泳同时转入。这个理论研究室在作协是工作职能部门,不是研究机构,主要是配合作协的行政和业务工作起草相关文字材料,重点关注本省各项文学种类创作动态,研讨创作成果,包括评介作家作品、组织研讨会等。
在理论研究室任职,不用按时编辑出版刊物,工作量少了不少,就相对多了自己读书写作的时间。蔡润田出于兴趣,同时,也因为大学期间有过心理学的知识储备,集中精力推出了长篇文章《文学气质论稿》,受到了相关研究人员的高度评价,有学者说:“蔡润田在《文学气质论》中,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研究了古今中外对气质的探究和这种气质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有硕士论文引用蔡润田的理论观点分析贾平凹的创作。在这期间,他还写出较有分量的阐述散文发展及特征的《散文散论》,应约参与了《中外文学名著人物辞典》《唐诗精品》等书籍的撰稿。
1996年,蔡润田意识到自己年事已高,应当抓紧时间创作,不太适合继续担负部门负责人,于是,向作协党组提出请求,辞去理研室主任,到文学院从事专业创作。党组尊重他的意愿,批准了他的请求。不过,两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虽然不是上级提名的候选人却破例被选为省作协副主席,充分反映了全省文学界人士对他工作和成绩的认可。当了副主席,就得完成一些主席团交给的工作,但毕竟不占用他太多精力。
有了比较宽裕的时间,蔡润田投入到读书写作中。他感觉到自己的性格和兴趣多半在古典文学上,因此,集中研读古代文学史上魏晋之际嵇康、阮籍等人的书籍,撰写出了一批相关论文,比如《难以评说的嵇、山之交》《婞直之风与龙蛇之道》《嵇康论敌与挚友》等;同时,在《太原日报》《太原晚报》《合肥晚报》等报刊开专栏,写散文与学术随笔之类的文章,数年后结集出版了散文随笔集《独语集》。评论家孙钊说:“书名独语,其实非也。书中的文字都是在同读者进行和平的交流,属于那种温文尔雅的性情中语。所谓独语,我觉那无疑是作者的自谦,不只是有意规避炫耀之嫌,更透着一种儒雅的矜持。这和一些文人轻狂、矫情乃至自我炒作显然成一反观。从头至尾读一遍《独语集》,让我们想到中国文人慎独的传统品质——它所蕴含的审慎、平和、谦谨,独善其身,大体和我们今日的道德自律意思一样。因为它的久违,这些流利而质朴的文字里读出了自觉的人格意识,我们被感动着。”作家韩石山说:“书名《独语集》,想来是说,这一切不过是心灵宁静的回眸,繁华落尽的独白,不妨说是抖落了世俗的桎梏,显出了本真的心性。这一抖落,显现出来的不光是心性,就是文字,也变得清纯自然,充溢着妙曼的生机。别说那些记述少年憨直、青春恋性的文字了,就是抨击世态的文字,也同样显示着一种内在的活力,感人的深情。”
此外,为纪念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省作协交由他主编全面展现山西文学五十年进展历程文学史著作《山西文学五十年纵横论》。他和大家首先梳理了这一时期山西文学史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制定出详细而有专题性特点的提纲,然后依章节先后,由杜学文、傅书华、苏春生、蔡润田、阎晶明、杨占平、段崇轩、谢泳、孙钊、王春林、杨矗等评论家分头撰稿,这些人都是省内年富力强、学术有成的一时之选,为著作质量提供了可靠保证。蔡润田参与撰写并逐篇审定,倾注了大量心血。这部书出版后,受到省内外广大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好评,成为最具权威性的山西当代文学史著作之一。
2003年,蔡润田年满六十周岁,按政策规定,办理了退休手续。不过,这个退休对于像他这样的作家、评论家来说,只是一种体制身份的转化,研究和写作并不受任何影响。他仍然跟过去一样,有规律地读书、写作、生活,有选择性地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十年时间,继续进行自己的选题,先后出版了《三边论集》《南华杂俎》《纵横且说宋之问》等作品集和专著,后者还是国内少有的有关宋之问研究的专著。这些作品和专著更为成熟、老到,文学界诸多人给予很高评论。诗人、作家寓真2015年元月赋诗说:“雅才成杂俎,酌古复斟今。谈艺诠人性,论儒辨道心。熔裁文若锦,惜墨字如金。健笔勤无辍,新年耕愈深。”热情赞扬了他的学问根底和文字功力。
总结蔡润田走过的七十多年人生与文学道路,可以说,他是个富有深厚学养与艺术追求的评论家、散文家、编辑家,是个认认真真为人处事的文化之士,是个有情怀、爱憎分明的学者型人物。2014年春节,他写了一首《马年自嘲》的诗:“桑榆有马难着鞭,独行踽踽且安然。闭门哪知风头劲,嚼蜡不觉世味艰。煮字但求七成熟,应物倒要十分憨。情知寸金不多让,却道晓岸近客船。”这首诗虽说有些自嘲意味,却也折射出他立身处世的行为,是对自己很好的评价和写照。蔡润田用严谨的为文态度和坦荡的为人品格,书写了自己的平凡而不平淡的人生与文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