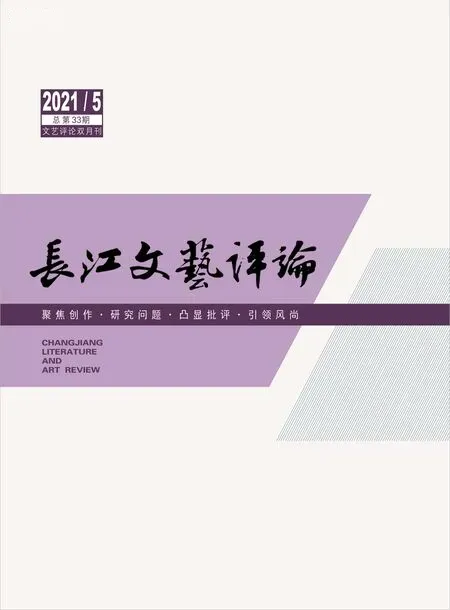谍战片的类型演变与工业化制作
——以《悬崖之上》为例
◆汪梦菲 范志忠
谍战片在近几年很受观众的欢迎,据统计,近三年谍战片上映了超过24部,票房达26亿元;与之相关的谍战剧也是经典迭出,例如《潜伏》(2008年)、《黎明之前》(2010年)和《暗算》(2005年)等优秀作品直接带火了谍战片的制作和热播。纵观国内的电影发展史,谍战类的题材因其情节的跌宕起伏和悬念设置的紧张刺激等优势而经久不衰。谍战剧是以表现间谍活动及我方反间谍活动为题材的一类影视剧,以特务、悬疑、爱情、暴力侦讯等元素的杂糅为类型特征讲述敌对国家或势力派出间谍到对方阵营中刺探情报的故事影片;其在民族大义、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中糅合亲情、爱情的人物情感,具有浪漫传奇色彩。由张艺谋导演拍摄的《悬崖之上》,在2021年“五一档”上映之后反响强烈,其紧凑的节奏配上几位老戏骨的在线演技,再加上张艺谋一贯善用的色彩艺术和动静对比手法,将谍战剧的传统题材优势发挥到极致。更为重要的是它在高难度工业化制作上,采用了兼顾电影商业性和娱乐性的叙事类型,迎合当下社会消费文化的逻辑;还加入了新的美学元素和视觉效果,为谍战剧的更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启发。
一、谍战片的类型演变
谍战片,顾名思义,是一类以间谍活动为主体的影视作品,它因其谍报色彩,通常依赖于或脱胎于战争题材。中国谍战片的发轫,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丁亚平认为我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间谍片是1937上映的《密电码》;而虞吉在其编著的《中国电影史》中认为,香港在1939年摄制的《孤岛天堂》不仅是一部抗战电影,而且无形之中还完成了特定题材的类型化开拓,成为间谍侦探片的滥觞。被学术界广泛接受的是,谍战类题材的真正兴起是由于“十七年”时期的“反特片”的盛行。
中国的第一部“反特片”是1949年出品的《无形的战线》。“反特片”是冷战意识形态下的产物,反映的是敌我分明的二元对立且不可调和的斗争的重大主题的表达,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聚焦于呈现美蒋特务的阴谋、以西方为代表的阶级敌人的威胁及来自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渗透,并在敌我双方二元对立中感化人民群众,呼应了当时对两大对立的国际阵营“间谍战”的想象性描述和中国关于宣传“隐蔽战线”斗争的客观需要。在“十七年”时期的“反特”主题题材的创作中,相对侧重艺术本体方面,糅合了“惊险”的情节设置,因此较多地将其视作“惊险片”进行讨论。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虽然从表面上看阶级斗争已不复存在,但事实上,敌人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从明处转而隐匿于暗处。因此,这段时间的惊险片表达的主题是:与暗藏在人民内部的无形的“敌人”之间的斗争。与此同时,通过情景设置和故事情节的加入,使观众获得了强烈的紧张惊险的观影快感和难得的娱乐性。1956年至1959年是反特题材惊险片的创作高潮,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高潮期,如1957年的《羊城暗哨》、1960年的《林海雪原》、1963年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和《跟踪追击》等,均通过设置悬念情节和塑造人物等方式融合了“惊险”成分。蓝天等就该时期的谍战类题材作品提出了“惊险影片是阶级教育的一种生动教材”的观点;尹鸿等认为反特片“是和平时期的战争片”。由此可见,当时的“反特”题材作品大多都是基于现实的创作观,具有浓厚的政治导向性。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电影体制也从“计划型”转变为“市场型”,逐渐打破了纯粹政治意识形态,开始追求影视的本体艺术,电影的娱乐性得到进一步的重视。1981年播出的《敌营十八年》虽然在美学意蕴、艺术规制等方面依旧未能摆脱“反特片”的影响,但开始跳出政治的束缚,更注重强调人性光辉。此后,随着《誓言无声》(2002年)、《暗算》(2005年)、《潜伏》(2008年)、《黎明之前》(2010年)、《伪装者》(2015年)、《麻雀》(2016年)等佳作热播,以及《风声》(2009年)、《谍海风云》(2010年)、《听风者》(2012年)、《触不可及》(2017年)等豆瓣高分电影的成功,谍战类题材壮大为剧作类型,逐渐摸索出自己的生存模式。相比于早期的反特片,此类作品中的敌我对立关系开始变得模糊,具有鲜明的阶级斗争色彩的反特片命名逐渐式微。根据“谍战迷(http∶//www.diezhan.me/diezhan/)”统计的信息,到目前为止,国产“谍战剧”共出品多达240部,“谍战剧/片”成为大陆谍战影像最为主流的命名。
区别于反特片中的单一叙事结构,呈现出敌我之间泾渭分明的状态,以及对自我身份的绝对认同和不同阵营的意识形态的不容混淆,在情节的设置和人物关系的处理上,“谍战剧/片”更注重追求多线索叙事结构。例如《潜伏》(2008年)在塑造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余则成的同时,也突破了李涯等单一、平面化的反面人物形象,赋予了他们兢兢业业、忠于党国、爱家护子的有血有肉、更加立体的人物形象。可见,现如今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后冷战时代,那些传统反特片的特点已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阶级或民族、国家之间的分界和矛盾已逐渐变得模糊不清。原先的阶级对抗、家国矛盾都幻化成人性的选择,善恶的取舍,情感的表达更加丰富多元。电影《悬崖之上》(2021年)也通过将张宪臣、王郁与孩子的亲情和楚良与小兰的爱情进行糅合表达;在保证传统的谍战剧大多以硬汉、铁血、高智商的前提下,融入家庭伦理剧的温情元素,符合女性观众的审美需求,也表明谍战剧在自我定位上变得更加宽广和包容。
谍战剧/片在受众审美的剧变、资本的强势进入和艺术创新的时代要求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一系列的探索之后,完成了“间谍片—反特片—谍战片”的类型演变,以新的叙事策略、新的文化诉求、新的审美趣味不断适应市场和观众的需求。但总结类型的演变,是为了打破类型的樊篱,继续推陈出新,以谋求谍战片的商业价值最大化,艺术追求完美化。
二、以《悬崖之上》分析谍战类型电影的工业化制作特征
以上述谍战剧/片类型的定义与特征,观照张艺谋导演的国产谍战电影《悬崖之上》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影片的世界设定、主题立意、家国情怀,还是从电影本身所呈现出的极具美学价值的宏大场面及制作精良的品质感来看,《悬崖之上》都是一部优良的,展现国产谍战片创作新风貌的佳作。不仅如此,此片在探索和推进中国电影工业化进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借鉴意义。从“工业化”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工业化”是动态变化的,是一个螺旋式转型升级并不断演进的长期过程,其核心是快速发展和升级更新现代工业,而本质是在生产经营的方式下,从现有“工业化“水平逐渐向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市场化、专业化发展的过程。结合“工业化”理论和《悬崖之上》导演、摄影指导的访谈及相关文献的梳理,以此片为例,我认为谍战类型电影的工业化制作特征主要有三。
(一)制作工业化
《悬崖之上》讲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四位曾在苏联接受特训的共产党特工组成任务小队,回到哈尔滨执行代号为“乌特拉”的秘密行动的故事。导演为了将观众快速代入到故事中,自影片最开始,画面就处于一个“雪一直下”的环境氛围中。然而即便是最寒冷的东北,也不可能保证整个拍摄周期持续下雪,为了不影响拍摄计划和周期,摄制组采用了自然雪和人造雪相配合的置景方式,利用最新的环保技术去造雪。其制雪材料是一种膨化食品,无毒无害,不会造成环境污染;还有一种平常用于冬天滑雪场的造雪机,通过机器将加入的温水变成雾状,在低于零下三度的环境温度下,喷射到空中。通过这两种技术造出来的雪花晶莹剔透,成雪的质感和重量感与自然雪花无异,为影片营造出非常具有诗意的“雪一直下”的环境氛围。除了造雪以外,在白天的雪地环境中拍雪的难度也很大。因为雪花是一种晶体,在光线的照射下会出现反射和折射的现象,这就对拍摄时的曝光技术产生很高的要求。
此外,本片采用了多机位和多机种的拍摄方式,尽可能多地抓取每个演员瞬间的表演,在大大提高了拍摄效率的同时,也将谍战的紧张感和氛围感烘托得恰到好处。以火车车厢戏为例,这场戏是在摄影棚中拍摄的,空间很狭小,但通过前期对机位的规划,在不穿帮的情况下,同时架了四台摄影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拍摄。由于整场戏中列车几乎是一直处于运动的状态,这对光线的流动性要求非常高。为了模拟出最真实的效果,摄制组事先采集了列车在行进过程中,车窗外的光照进车厢内及车厢内的光的变化过程的样本,通过Skypanel进行电脑编程,控制拍摄中的动态光感。
(二)视觉奇观化
电影中的奇观概念源自法国哲学家居依·德波关于“景象社会”的分析。德波认为:“在那些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中,生活的一切均呈现为景象(景观、奇观)的无穷积累。”穆尔维认为:电影的视觉快感由观看癖(窥淫癖)和自恋构成;前者通过观看他人获得快感,后者通过观看达到自我建构。斯皮尔伯格于1975年拍摄的影片《大白鲨》(Jaws,1975)是较早应用奇观概念的电影。《大白鲨》通过人们与“大白鲨”的搏斗夸张地描述了超乎寻常的自然生物,配合精妙的音效,在电影本身情节并不丰富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荣获第48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提名奖。到现在,奇观电影已经取代叙事电影成为主流的电影模式,如采用大量惊险刺激的动作的动作奇观电影《卧虎藏龙》(2000年),速度奇观电影《007》(1962年)、《生死时速》(1994年)系列,给予观众视觉上的震撼与冲击力的场面奇观电影《星球大战》(1977年)等。电影的视觉奇观能够通过其直接的视觉冲击力,给观众以震撼,引人入胜,彰显电影作为一种视觉艺术的独特魅力。
酷刑作为谍战类影视作品的标志性元素,恰当的运用能够展现出震撼的视觉奇观场面。在影片中运用酷刑景观镜头,令酷刑中的身体成为敌对势力彼此较量的直接载体,一方面在于考验革命党员的信仰,检验其是否具备崇高的理想和舍生取义的高尚精神,以承受突破生理极限的痛苦为方式,造就英雄;另一方面,当鲜血淋漓的画面如此直观地展示在观众眼前时,观众会因这种非同一般的冲击力和感染力与影片中的角色同命运、共呼吸,共同感受那种不惜为民族大义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的精神境界,使影片所要表达的关于崇高信仰的主题得到升华。典型代表是2009年的经典谍战片《风声》,在该片主要奇观之一是在阴森恐怖的古堡里,导演用大量的笔墨去渲染各种酷刑的残忍和角色遭受的非人待遇,如对“老枪”这种硬汉采用的毒针刺穴,残忍到整个头上扎满了银针;对待具有同性恋倾向的白小年则是用钉椅,椅子上竖立着钉子,中间的大钉子格外醒目,利用其不同于常人的性取向来对其进行人格上的侮辱。解读《风声》的导演陈国富的访谈,可知《风声》中的酷刑奇观是导演的精心设计,试图以一种出乎观众意料的酷刑场景给观众带来不同的观影体验,从而出奇制胜,这为奇观化在谍战类题材酷刑叙事过程中的应用提供了启发。
不同于《风声》中观众对受刑人的人设的未知,电影《悬崖之上》中,受刑对象张宪臣不在意个人生死,只求舍身成仁的正面形象在一开始就已经被观众接受。故而,《悬崖之上》一方面选择了较为普通的电刑,以此来削弱观众在满足其娱乐性的同时,来自道德层面的愧疚与不安;另一方面,通过给张宪臣电击到口吐白沫,意识涣散的特写镜头,伴随着他浑身是血和大量的红色充斥着画面,使得张宪臣在这个黑白世界中更加瞩目。虽然没有过多直观的暴力镜头,但却通过蒙太奇的剪辑方式同样制造出骇人听闻的残酷感,渲染出了紧张的氛围,运用暴力美学升华了主题,即用饱和度极高的血红色来凸显革命者的不屈和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的信仰至高无上。让人不禁联想到《惊魂记》(1960年)中经典的“浴室谋杀”片段,希区柯克通过黑白画面效果,采取近距离拍摄手法,同时运用雨夜、荒野旅馆等场景结合,凸显影片的悬疑色彩,渲染紧张的氛围;进而通过1分40秒内44个1秒左右镜头的交叉蒙太奇的手法,让观众产生了双重错觉的效果;在没有使用让观众难以接受的血腥场景的情况下,通过音效、剪辑的配合使观众的精神始终紧绷。酷刑奇观在一定程度上是牺牲叙事的整体性而去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如何做到电影思想主题与艺术张力兼得,同时又不失文化内涵和人文关怀,不让酷刑奇观化沦为华而不实的消费情节,张艺谋导演给出了一个范例,但仍需进一步地摸索改善。
(三)叙事类型化
类型是工业化制作电影的重要叙事范式,这是电影工业和观众互动的客观要求。近年来中国电影工业化制作体系逐渐系统化和成熟化,这种趋势充分体现在电影作品的类型化上。相较于张艺谋早期的作品《红高粱》(1987年)、《大红灯笼高高挂》(1992年)、《秋菊打官司》(1992年)等作品中呈现出的“大红大紫”的具有导演个人独特的艺术追求和鲜明个人特色的画面处理,《悬崖之上》这种符合“谍战片”类型的去饱和度、黑白影像风格的转变可以看出张艺谋在拍摄这部电影中或多或少地摒弃了以往的影像风格追求,而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部类型电影来加以完成,实现了诸多电影工业化的尝试和挑战。《悬崖之上》上映之后,张艺谋曾在访谈中提及,这部作品难点在于掌控节奏,将情节化为无形。为此,他花大量心思构建雪境的氛围,试图通过研究光线、镜头角度、镜头焦距,以及雪跟人物的疏密关系传达出雪凛冽又富有深意的内涵。北京大学李道新认为:“这是一部将主旋律电影基因融入谍战电影创作进而创新谍战电影类型的尝试”。笔者也是非常赞同这一观点的。
其次,由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在电影工业化制作生产背景下,谍战片这一类型为满足观众观影需求,也进行了加强影片的商业性和娱乐性的尝试。比如《悬崖之上》电影中,导演张艺谋加入了两位特点鲜明的女性角色。其一是中年女性王郁,她不仅是张宪臣的妻子,也是拥有一对儿女的母亲。电影通过车厢戏中的不动声色、吞下自杀药片换取和楚良单独交流的机会、在打开水龙头的厕所哭泣等场景成功塑造了其女性角色所独有的中国伟大母爱的特质,以及相比于同小组男性成员楚良更清醒、更警敏的特征。另一女性是小兰,一个被赋予拥有快速记住联络暗号能力的小女孩,通过车厢戏中的打斗与跳车、多次出入往返避难所的机警、电影院与众多敌方特务的斗智斗勇等场景,导演塑造了与其稚嫩的声音、懵懂外表形成强烈反差的坚毅、果敢、冷静而沉着的形象。这种将女性性别特质和巾帼英雄进行融合的叙事手法超越了“十七年”时期的反特片中刻板的女性形象。
此外,《悬崖之上》区别于之前谍战片着重通过男性角色的铁血、硬汉特征塑造英雄形象,而是以女性角色为主导。这种对女性角色的处理是对之前传统反特片中,在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女性话语权往往被男性政治话语权所覆盖、抑制甚至摒弃,使得女性成为一种“在场的缺席”的一种弥补,是真正平等对待历史长河中每一个英雄人物的方式。正如俞洁所言:“女性在宏大的政治叙事背景下,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觉符号,压抑了自身的个性和性别特征。”这既体现了当前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的转变,也是因为当前社会处在一个以工业化为基础的消费时代,资本的介入使谍战片成为当前的文化消费品,是电影工业化制作生产背景下,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和政治文化与消费文化博弈的产物;摒弃了之前的刻板与僵化,缔造了奇观性与时代性并存的新主流叙事语法。
三、工业化制作下谍战片存在的问题
从电影工业化的角度来说,涉及到一个“标准化”的问题,也就是类型化的创作都有其一定的创作标准。影片在创作初期就会先贴上一个“类型”标签,这个标签就是创作者与观众的一种市场契约。在以好莱坞电影为引领的时代,中国电影应当积极尝试新的类型叙事和审美表达,力争在电影的产业化、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探索出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与主流价值融合的审美表达。而不是被文化资本和现代科技的进步倒逼,过于注重工业化及其视听效果,忽略中国电影在叙事等方面一直传承的优点。这不仅仅表现于《悬崖之上》,也是很多工业化制作下的电影的通病。
众所周知,电影制作的工业化对团队精诚合作、各工种人员调配、演员水准等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中国工业化电影制作目前还难以摆脱工期短、团队配合难带来的影片质量问题。其中一个难以忽视的原因是中国电影的制作的主流依然是导演中心制,导演在电影生产过程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其他人员难以对其创作进行监督制约。如《悬崖之上》中,篇幅过于集中于分头行动的两个二人小组如何接上头,而具体如何营救幸存者,这一最能体现英雄高尚动机的最终目标却被一笔带过,影片直接跳到结尾,这大大削弱了最后一场戏带给观众的冲击力和感染力。相比之下,打造众多工业制作电影范本的好莱坞制片人中心制值得借鉴,这既是现在电影经济和社会文化双重属性的要求,也是工业化赋权、资本冲击和观众审美博弈的结果。
自2002年张艺谋电影《英雄》作为第一部商业大片横空出世以来,中国电影产业开始默认了电影的产业、商业、工业特性。这一方面缔造了电影行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中国电影的急功近利,对细节追求的疏忽。在电影《悬崖之上》中也有体现,比如一些镜头略显违和:电影院门口居然贴着怒斥日本海军的《中国海的怒潮》的海报,这与哈尔滨当时作为日本关东军统治下的“满洲国”的核心城市违和;张宪臣在经过电击、迷幻剂的酷刑后,还能背手开锁,再杀两个人的剧情设置略显浮夸,而且对于电影叙事本身也没有特别的提升,有画蛇添足之嫌。诚然,《悬崖之上》的高水平工业化制作,试图在主流与边缘之间、雅与俗之间、精神诉求与商业需要之间寻求共鸣共情的“匠心”大家有目共睹,但对细节的精益求精,对情节合理性的深思熟虑,也是体现一部电影“工匠精神”的重要部分。否则不仅会让观众“跳戏”,而且容易陷入为了视效而不断炫技的误区。
四、结论
尽管新时期我国谍战剧创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一系列的探索之后,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就如同五十年代“高大上”的创作理念早已被抛弃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现在的流行也终将过时。不断发现新的创作领域、发掘新的创作题材、创造新的叙事策略、提高电影制作的工业化水平,依托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新的表现形式,推动谍战类题材作品的真正创新,占领影视剧行业的高地,才能做到真正的经久不衰,打造出带有各个时代特色与历史痕迹的经典。正如王晓晖强调:“中国电影仍处在黄金发展期,电影强国建设征程已经开启,前景光明、未来可期、大有可为。要凝心聚力打造献礼建党百年电影精品,努力打造中国电影品牌。”张艺谋七十多岁高龄,依旧在不断探索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转变之路,尝试风格的转变,他在工业化中处理的好的点和存在的问题,对未来中国电影工业化存在不可磨灭的借鉴意义。
本论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ZD19。
注释:
[1]贾磊磊:《中国电视批评》,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页。
[2][4]丁亚平:《中国电影通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版,第454页,454页。
[3]虞吉:《中国电影史》,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6—77页。
[5]蓝天:《对惊险片的几点议论和希望》,《电影艺术》,1963年第6期。
[6]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7]魏后凯,王颂吉:《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现象剖析与理论反思》,《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1期。
[8]杨贝贝:《我国科幻类型电影创作与工业化发展策略》,《电影文学》,2020年第5期。
[9]《悬崖之上》主创做客:“赵小丁:这是一次中国“电影工业化”全流程制作的突破”,https∶//107cine.com/str eam/136570。
[10][12]孟建:《视觉文化传播:对一种文化形态和传播理念的诠释》,《现代传播》,2002年第3期。
[11]【英】劳拉·穆尔维:《恋物与好奇》,钟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13]潘磊:《〈风声〉:欠缺的情节叙事 炫目的视觉奇观》,《电影文学》,2010年第5期。
[14][17]陈旭光:《新时代中国电影工业观念与“电影工业美学”理论》,《艺术评论》,2019年第7期。
[15][18]张李锐,范志忠:《新主流电影的工业化制作与类型化叙事》,《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16]俞洁:《“观看”与“承当”——21世纪中国谍战片中女性形象的生产及其危机》,《当代电影》,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