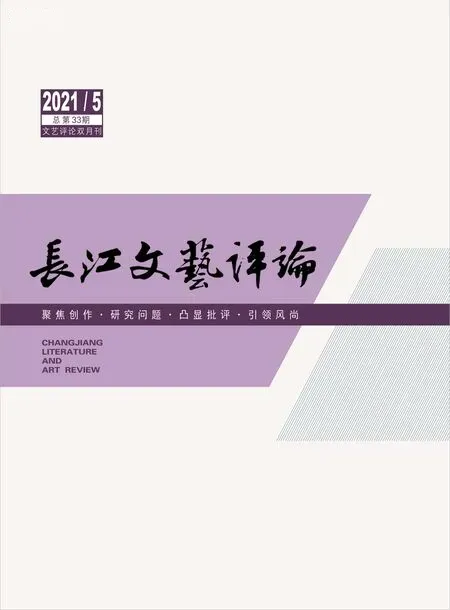风景与风景摄影
◆藏 策
一、风景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断章》
在卞之琳的这首诗里,第一句与第二句里的“风景”,是一样的吗?明月装饰了的窗子,又是一种怎样的风景?你在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吗?——夜不成寐者眼中的风景?而此情此景,在酣睡者的梦中,恰又成为了梦中的一道风景……
W·J·T·米切尔在《风景与权力》中讲道:
风景不是一类艺术,而是一种媒介。风景是人与自然、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一种交换媒介。用类比的方式来讲,它就像货币一样:它自己本身并没有价值,但是它代表了一种潜在的无限的价值储备。风景是一种由文化中介的自然景象。它既是被表现的空间又是表现的空间,既是象征者又是被象征者,既是一个框架又是被框架所包含的,既是一个真实的场所又是它的幻象,既是一个包裹又是包裹里面的物品。
W·J·T·米切尔的这段话,是不是可以与卞之琳的《断章》形成某种相互阐释的关系?
风景(landscape)这个词源于德语的landschaft,指的是与城镇毗邻并隶属城镇的土地,既与城市相对立,又相互彼此依赖,且被纳入了政治生活、财产及商业关系之中。德语中的风景,并不是指原始的自然景色,而是指一个由行政边界划定的地理区域。在1670年的《词汇注释表》中:
风景(比利时语):副产品,是对土地的表述,包括了山脉、森林、城堡、海洋、河谷、废墟、飞岩、城市、乡镇,以及所有我们视野范围内所展示的东西。在一幅图画中,所有这些非主体或非主题的东西,就是风景、副产品或附属物。在有关救世主的苦难经历的主题中,有一幅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图画,画中的两个盗贼、圣母玛利亚、圣约翰是主题,而耶路撒冷、周围的乡村、云,以及类似的其他内容,是风景副产品。
从比利时语、荷兰语与德语原型中得到的“风景”这一英语词汇,都加上了“装饰品”“附属物”“副产品”或“辅助装饰”的概念。根据《牛津英文词典》的解释,其含义是(在其他东西中的)一个附属及辅助品。Landscape在英语中是一个合成词,其中land有土地、大地、国家等含义,scape一词也可单独使用,就是风景的意思,属于一种古旧的用法,现在则普遍作为词根使用,但仍具有原来的含义,如cityscape、lakescape等。
风景从陪衬到主体。伴随着“透视法”,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景绘画,象征着世俗和平民的目光,从神话和宗教的世界中抽离了出来,从文学插图、宗教启迪和装饰画等次要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在其中自然“因其自然”而被观看。中国风景画是史前的,早于“因其本身而被欣赏”的自然的出现。“另一方面,在中国,风景画的发展……与对自然力量的神秘崇拜结合在一起。”(参见威廉·钱伯斯《东方造园论》)
关于对风景的认知,有三点需要特别强调:1.风景(landscape)这个词从出现的那一天起,指的就不是原始的自然景色,而是由行政边界划定的地理区域,是与政治、经济等权力关系密不可分的。2.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风景,如有关山水的概念,远早于西方,也同样是特定政治语境中的产物,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精神逃离,是隐士文化在寻求精神世界中“避难所”的一种想象性建构。其中对自然力量的神秘崇拜,也可以看作是对世俗世界权力关系的抗衡。3.地志画与风景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的分歧。一方强调的是真实与自然主义,另一方强调的则是风景的象征意义。这种分歧在摄影史中同样存在。
W·J·T·米切尔是当代图像学的创建者与代表人物。他一反以往把风景视为有待解读的文本的思路,把风景视为交互关系中的媒介。
简言之,米切尔的观点就是,风景并非全然是自然的,而是由各种权力关系建构起来的文化幻象。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视点。然而米切尔的观点仍然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他仍停留在观看者与观看对象(风景)的对应关系之中。事实上,风景并非媒介,观看才是媒介。风景本身并不能显现为风景,而只能在观看中得以显现。风景不仅是文化幻象,同时更是一种视觉幻象。我们不仅需要揭示其在各种权力关系中的建构过程,更需进一步去反观主体在这一建构的过程中,对风景的识别与认知,又是如何被一步步规训了的。
二、风景摄影
风景在传统摄影中属于题材范畴,既属于艺术摄影(画意的、美学类型的),也属于文献摄影(科学和文献领域)。如19世纪的摄影师埃梅·斯维亚尔拍摄的大量风景照片,就力求摒弃“艺术的视角”,为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和气象学家提供视觉文献。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称此类风景摄影为“风景照”。“风景”属于美学评价,“风景照”属于科学评价。前者认为摄影是艺术,后者则认为摄影不是艺术。从摄影术诞生之时,摄影就在科学与艺术之间徘徊……其实摄影根本就不是一种媒介,而是很多种媒介。摄影的“范式”可以是光的物质痕迹(拉兹洛·莫霍利-纳吉)、可以是决定性瞬间(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以及个人视角的纯摄影探索(爱德华·韦斯顿),直至新客观主义式的“冷面”(杜塞尔多夫学派)等等……
“风景”在中国被理解为“风光”(画意摄影的重要题材),而属于文献摄影的“风景照”在中国则并未形成传统,以至于风景摄影被曲解为以“风花雪月”为特征的画意摄影。又因为中国的画意摄影经过“祖国山河一片红”式的意识形态“基因变异”,以及大众文化的“美盲”式误读,最终沦为了视觉俗套“糖水片”,于是本该属于摄影史早期的科学与艺术之争,以及属于艺术摄影内部的美与恶俗之争,竟然被奇葩地转换成为了风光与纪实之间的题材之争。更为讽刺的是,就在国内的这种“关公战秦琼”式的论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此时的世界摄影已然进入了“后摄影时代”,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摄影还是文献摄影,都早已经成为了明日黄花……
简言之,如果从艺术摄影发展的大致脉络看,人们对风景的认知,先是经历了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的迷思,而后从中解脱了出来,不再沉醉于原始自然、田园牧歌式的审美幻象,开始探索属于摄影媒介自身的本体语言。艺术摄影发展到现代主义阶段以后,风景摄影也超越了模仿新古典主义绘画的画意摄影窠臼,将自然界简化为物体,将物体简化为机械,将风景抽象为视觉元素的几何图案构成。而伴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出现,对“社会风景”“景观社会”“空间政治”的关注,又极大地拓展了对于风景的观看视野。
1975年,在乔治·伊斯曼大厦,由威廉·詹金斯主持的《新地形:人为改变了的风景照》展览,是摄影史上的一个标志性节点。这是第一次把摄影家与艺术家(如贝歇夫妇等)聚集到一起的展览,源自摄影史脉络的“观看的艺术”,与来自当代艺术的“概念的艺术”在此首度会合……
三、风景:题材,主题,问题
如果仅从摄影史的视角梳理风景摄影,显然太过于表面化,我们不妨从多学科多角度的视野再做一番深层的分析,首先从“题材史”与“主题学”的视点切入。题材一直是摄影分类中的一项重要参考,也就是依照拍摄对象所涉及的题材来分类。比如拍风景的,就属于风景摄影;拍人像的属于肖像摄影……世界上的第一张照片——尼埃普斯拍摄的《窗外》——就属于风景摄影。风景作为一种题材,可以出现在各种不同目的不同理念的摄影之中:探险、勘探、军事侦查……以及作为艺术摄影中的审美对象。
然而,无论是作为各种实用性摄影还是艺术摄影中的对象,风景这一概念的边界,其实都是变动不居的。作为原始自然与田园风光的风景,其实只是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虚构出来的一种幻象,根本就无法替代风景本身。就如风景(landscape)这个词从出现的那一天起,原始的自然景色就不是它的本义一样,世界上的第一张风景照片《窗外》,拍摄的也不是所谓的“自然”,而是摄影作为“窗”的某种隐喻。“窗外”的世界,目之所及皆风景。当人们对风景的认知,走出了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所建构的刻板印象之后,风景本身就成为了需要重新思考的对象——到底何为风景?于是风景也就由一种特定的题材,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主题学的意义。比如“社会风景”等概念的提出,其实已经标志着,风景无处不在,风景即社会,社会即风景。当风景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时,实际上也就意味着风景作为一种特定题材的意义也已经不存在了。
从安塞尔·亚当斯遗世而独立的“先验主义传统”中的风景,到沃克·埃文斯只在由人构成的场所发现“等值”,再到“走向社会风景”,直至风景成为一种“新地志”式的“文本”……风景从远离尘嚣(社会)的所谓“自然”,到滚滚红尘即风景,这种对“自然”观念的改变,其实也是对问题的发现——对风景主体的持续深化,其实意味着的是:风景不再仅仅是一种供人们想象与陶醉的审美对象,而是对我们自身所处语境中,各种被常态化了的“问题”的发现与提问。进入到当代艺术语境后,风景已不再是一种题材,风景摄影更不再是一个类别,而成为了一种图像互文关系中的符号。有关对风景问题的提问与思考,也有了“元影像”式的反身性视角,诸如:风景是如何成为“风景”的?人们对“风景”的视觉识别,是如何被规训与建构的,等等。
四、从文献到文献之上,从记录到洞察
如前所述,风景在摄影史早期,既属于艺术摄影(画意的、美学类型的),也属于文献摄影(科学和文献领域)。罗莎琳德·克劳斯在论述奥沙利文的作品时就认为,其作品在本质上是科学的,是科学的“景观”(views)而非风景(landscape)。文献摄影与艺术摄影就如两股道上跑的车,沿着不同的方向分道扬镳……然而,科学维度的风景摄影,又能否最终作为科学的依据呢?乔尔·斯奈德在《领土摄影》中指出:“奥沙利文并不能够提供科学意义上的精准照片。”
将摄影局限于实用性的文献用途,这本身就是对摄影的一种压抑。人们之所以会相信摄影的所谓“真实性”,乃是被囿于“真相机制”之中而不自知的深度幻觉。摄影从来就不等于真实,照片只是事物的图像而非事物本身,越是看上去“真实”的照片,其实就越具有欺骗性——“照相机从不说谎”这句话本身就是最大的谎言。那么是不是就由此可以认为,文献摄影是毫无意义的呢?恰恰相反,文献摄影的意义非常重大。然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文献摄影在摄影史上真正的意义所在,并不是作为实用性的文献本身,反而恰恰是成为了艺术摄影中的重要手法。
文献摄影的手法,在艺术摄影领域成为一种可以直达当代摄影的重要方式,是由尤金·阿杰开辟的,即艺术家的纪实。约翰·萨考夫斯基在《尤金·阿杰》一文中说:“他是捉摸不透的艺术家和胸怀大志之人。某种意义上,他是首创者,因为他未从前辈中获得帮助。其他的摄影师曾考虑描述既定之事实(即档案),或者探索个人的情感(即自我表达)。当阿杰开始使用视觉语言试图理解和解释复杂、古老、存活的传统时,他就已本能地超越这两种方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拍下了看似简单实则平衡、谨慎、质朴、真实的照片。”
戴维·卡帕尼在《一抔尘土——曼·雷与马塞尔·杜尚之后的摄影》中,分析阿杰拍摄的巴黎郊区模糊地形时写道:“空间被简略成过去行动遗留的痕迹。事件从镜头下逃离,但仍可当作谜语般的证据。对虚构情节的投射使空间变成叙事舞台,因而,阿杰场景的复杂特性得以迎刃而解。可以说,将一张照片描述为‘空无一物’是将其投射在它曾经是(或者可能成为的)事物。”
文献摄影之所以能转身为艺术摄影,成为“艺术家的纪实”,就在于其以文献的方式超越了文献的属性,进入到了文献之上的意义层面。其中的奥秘就如戴维·卡帕尼所分析的那样:1.空间作为痕迹成为了指示性符号,曾经的行动本身则缺席;2.具体事件从镜头下逃离;3.谜语般的“证据”重组虚构的情节,将特定空间投射为舞台……
传统文献摄影是单纯记录物象或事件的,图像的意义也基本上局限于拍摄对象本身。而传统的艺术摄影,则是局限于画面本身的,不外乎营造画面本身的视觉美感及探索摄影本体的形式语言。但当摄影本身不再被认为等于真实时,传统文献摄影的特定价值就动摇了;当社会纪实(文献)被视为是利用苦难去追逐个人名利时,其人文价值也被质疑了;当艺术本身走出“艺术自律”的语境后,以审美及形式语言为自身追求的艺术摄影,也已经与艺术本身渐行渐远了……相反,艺术家的纪实,则在沃克·埃文斯等艺术家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渐成摄影史发展脉络中最具贡献性的遗产。因为艺术家的纪实,不再仅仅是记录事物本身,而是将事物转换成为视觉符号,将符号的相似性转换为指示性,其意义系统溢出了复制性的画面本身,从而超越了文献自身的属性,抵达了文献之上的层面。从摄影语言的维度看,也不再仅仅是以视觉秩序来营造美感或修饰拍摄对象,而是构建了视觉上的召唤机制,让观者透过画面中“谜语般的证据”,去思考画面之外的问题。由于释放了被传统文献摄影长久压抑着的影像潜能,超越了表象的真实,将被动的记录发展成为了主体的洞察,同时又将对摄影媒介自身的探索带出了“艺术自律”的围城,所以艺术家的纪实,即超越了“真实性”的困惑,又与艺术在当代的进程同步,甚至都可以进而发展成一种观念艺术,故而在当代艺术语境的摄影中,仍是一种重要的资源。
五、“摄影完结了吗?”
早在2010年,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就举办了一个备受瞩目的论坛,其学术主题是:“摄影完结了吗?”很多艺术家、策展人、学者和批评家认为:在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摄影”一词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也有人觉得,这个术语只是对机构来说还有一定用处。总之,作为一种传统理念之下的文献摄影及艺术摄影,或许真的已经完结了。而作为文献摄影与艺术摄影的题材,风景摄影也已经完结了。因为风景在当代摄影中,不再是一种门类,而只是一种可调用的视觉符号了。
风景就其外延而言,包括自然、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面相,并非仅仅只是所谓的风光。而国内摄影界长期以来却把风景曲解为自然风光,把其中的社会风景理解成为了景观。景观一词从中文的字面意义上看,确实既可以是风景又可以是社会风景,然而只要进行理论层面的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其实大谬不然。景观(views)可以是一种风景,但景观(spectacle)不仅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风光+社会风景,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还有“反风景”的意味在内。景观(spectacle)在今天所指涉的,其实是一整套有关景观的理论。
景观一词出自拉丁文spectae和specere等词语,意思都是观看、被看,而且也有“奇观”的意思在内,指的是取代了存在的表象。据胡塞尔考证,景观一词最早源自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不过让景观一词最终成为了一种学术“景观”的,是法国人居伊·德波。其实早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开始质疑表象了,居伊·德波有关“景观社会”的理论,可以说是既前有古人(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卢卡奇……)又后有来者(凯尔纳、鲍德里亚……),并非什么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发现。德波所做的,只不过是对景观进行了重新梳理与思考,并将其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牢牢地绑定在一起。同时,德波还将他的理论付诸艺术实践活动(“情境主义国际”),并因法国1968年爆发的“红色五月风暴”而暴得大名。
简单地说,景观指的是虚假的视像。因为“符号胜于所指、摹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现实”,所以“直接经历过的一切”(历史)“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真实的世界沦为简单的图像,影像却升格成看似真实的存在……在这种景观社会中,大多数人将彻底偏离自己本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沦为景观控制的奴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变成了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人在景观中被隐性控制的,不得不无意识地臣服于景观制造出来的游戏规则,从而遮蔽了现实中真正出现的分离……
德波在把景观社会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绑定在一起时,自身也陷入了悖论的境地。他在描述景观的特征时认为,景观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手段,既不是暴力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不是商业过程中的强买强卖,而是“在直接的暴力之外将潜在地具有政治的、批判的和创造性能力的人类归属于思想和行动的边缘的所有方法和手段”。但德波却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来分析前苏联斯大林时代强化国家权力时引入集中景观的现象。前苏联绝非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同样出现景观?斯大林时代的景观也是“直接的暴力之外”的吗?德波在此陷入了自相矛盾中。其实只要想一想连“资本主义尾巴”都割了的“大跃进”时代,遍地“亩产万斤”式的景观,答案便呼之欲出了。
著名哲学家、媒介理论家威廉·弗卢塞尔在《摄影哲学的思考》一书中写道:“影像自身的时空不是别的,而是魔法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在重复,而且一切都参与到赋予意义的语境当中。这样的世界在结构上有别于历史的线性性,因为在线性的历史中,一切都不是重复的,一切有因必有果……相反影像用情境取代了事件,把事件转化为场景……影像是世界与人类之间的中介……人类无法直接理解世界,所以影像使世界变得可以想象。不过一旦它这么做了,影像就处在了世界与人类之间。影像理应是世界的地图,却变成了银幕:不是把世界呈现出来,而是把它伪装起来,直到人活着就开始成为他所创造的影像的功能。人不再破解影像,而且把影像投射成没有进行破解的‘外在的’世界,世界本身也具有了影像性,成了一个场景和情境的语境。”
弗卢塞尔从人与视觉媒介的关系入手,分析了景观的形成及其特定机制,应该说比居伊·德波更富于洞见。继德波之后,凯尔纳将景观发展为“媒介景观”理论。而鲍德里亚则从后工业时代的角度,将对景观的思考推向了极致,提出了“类像”(simulacrum无原本的摹本)的概念。著名法国当代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Rancière)在批评居依·德波时指出:德波所持的立场源自德国浪漫主义,以及他所强调的———真实即“不分离”的理念,并不能令人赞同。
暂且不论有关德波景观理论的具体得失,现在只讨论涉及到所谓景观摄影的问题。国内那些以记录(再现)方式拍摄所谓社会景观的摄影师,以为凭借摄影的凝视即可揭示景观奇葩之处的想法,其实恰恰是出于对德波理论的一种误读。德波在《景观社会评论》中明确提出:“他越是凝视,看到的就越少;他越是接受承认自己处于需求的主导图像中,就越是不能理解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欲望。”
对于景观的再现,只会是另一种对景观的再生产,而非“景观的破裂”。所以景观根本就不应作为传统文献(纪实)摄影中的题材,而应成为在当代摄影中展开思考的问题。
威廉·弗卢塞尔在《摄影哲学的思考》中指出:“摄影哲学必须揭露,在自动化的、被程序化和使其他东西程序化的装置的领地中,人类的自由无立锥之地,并且最终表明,为自由开辟一个空间仍然存在可能性。”威廉·弗卢塞尔所说的,其实就是影像装置的既定程序对观看的异化。弗卢赛尔所说的“装置”,指的就是已经程式化、套路化了的既定模式。比如我们所熟悉的“风光摄影”,从器材到技术以及对拍摄对象的选择,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模式化了的“影像装置”。
对于人类而言,异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人类文明的意义,即在于在异化中反抗异化。然而当代艺术虽然挑战了影像装置既定的可能性(边界),但同时又进入了理论(思想)的装置之中……当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洞见已退化为一种“思想装置”,并以“政治上正确”的陈词滥调为“理念”规定了边界后,当代艺术影像则面临着又一次新的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