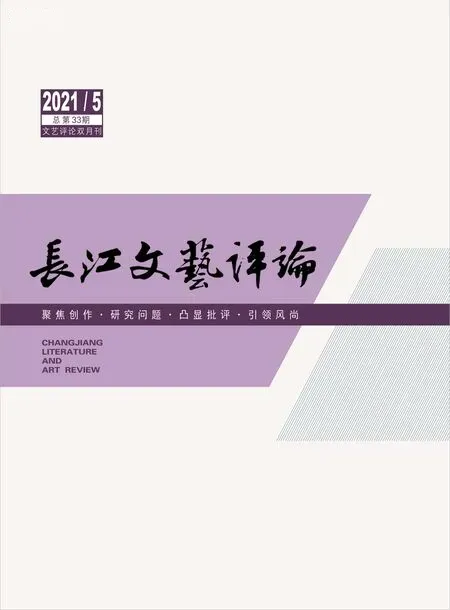佛语禅思悟诗心
——论王先霈的佛教诗学研究
◆高文强
对于“佛教诗学”这一概念的界定,学术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本文而言,佛教诗学是指使用佛教方法观看诗歌而形成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实践。当然,这里的“诗学”一词按照惯例还可以扩展到“文学理论”这一层面,本文使用这一词时,广义狭义都有涉及,在此不做强行区分。儒学观诗而有言志教化,道学观诗而有自然直寻,佛学观诗呢?自然有其独到的看法。佛教文化自两汉之际入华,在两千余年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对中国传统诗学影响可谓深矣。不过,学界对佛教与诗学之关系的研究,多着力于从文献、语言、概念等层面考证佛教对诗学的影响,而较少关注佛教方法或者说佛教智慧入诗学后所形成的独特的诗学理论和批评方法,这一现象至今依然。王先霈在研究中国诗学的过程中,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在佛教诗学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开拓性工作,为这一学术领域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就如佛教诗学本身较少受到学界关注一样,王先霈在佛教诗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也极少受到学界关注。因此,本文在此欲就王先霈的佛教诗学研究做一扼要的分析与介绍,以呈现佛教诗学研究固有之成就,以期推动佛教诗学研究向前发展。
王先霈的佛教诗学研究成果,主要包含在《佛语哲思》(1997)、《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2000)、《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2006)、《中国古代诗学十五讲》(2007)等著作以及一系列相关文章中(可参考《王先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其研究特色概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禅之哲思
如何研究佛教诗学、研究佛教对诗学的影响,一直是学界颇具争议的话题。受传统诗学研究中重考证、重文献、重直接证据等方法的影响,学界研究佛教对诗学影响时也多延用此方法。故研究中若无法找到语言或文献层面的直接证据,论证佛教影响诗学时便常常会有牵强附会之感。因此,当有限的语言或文献层面的影响关系被探讨过后,再想进一步研究佛教与诗学之关系就会寸步难行。这一研究方法显然是存在问题的。汤用彤在论及研究佛教的方法时曾言:“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他认为“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研究佛教应如此,研究佛教诗学亦如此。若不能将“陈迹之搜讨”与“同情之默应”相结合,将很难发现佛教之于诗学的独特影响。王先霈无论是对佛学的研究还是对佛教诗学的研究,都能够做到不停留于“陈迹之搜讨”,且尤为重视“同情之默应”。
在《佛语哲思》一书中,王先霈便借佛教“四依四不依”之说,提出了自己理解佛学的方法。首先,王先生指出,“佛语中最为珍贵的,是它具有的启示般若的功能”,“般若”即智慧,或者说是一种大智慧,“是洞达人生、社会、宇宙的本体性的一种玄思与彻悟”。王先生认为,“我们读佛语,谈佛语,把它当作一种触媒,一种引线,由此寻访宇宙和人生的奥秘,寻访般若智慧之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会是极有兴味的”。其次,王先生认为,理解佛教之般若智慧不应拘泥于文字表面,“而要努力把握语句背后的深刻含义,并且遵照这种含义去思维、行动”,如此方得体悟。王先生还以杜甫《漫成二首》中的“读书难字过”句为例,赞赏诗人“不被一字一句遮挡羁绊,而是自在地徜徉于水光、山色、花鸟和诗美、酒香之间”潇洒自在的阅读方法,并指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学他一学?摊开一本佛书,左手端一杯清茗慢慢啜饮,右手掀动书页徐徐观览,不拘泥于一字一句的确解,在那会心之处展颜一笑”。就如佛祖拈花,迦叶微笑,菩提般若之智的悟得,不在于“陈迹之搜讨”,恰在于“同情之默应”。此外,王先生还指出,理解佛法智慧,“只要属于‘善言妙说’,不论出自何人,不论是出自佛祖还是出自哪一个小沙弥,抑或出自某个居士,我们都同等看待”。如此以般若智慧为旨归的佛学研究方法,引入观看诗歌或其他文学类别,自然能够发现独特的诗学理论抑或批评方法。
如在《佛语哲思·一丝不挂》篇中,王先生指出这一佛语的佛学意义是“修行者要完全摆脱尘俗的沾染和牵累,从烦恼中解脱出来,精神上获得高度的自由”,而这一修行方法不唯在佛教修行中有其意义,更可触类旁通,在诗学领域也有其独特意义。王先生指出:“在学术研究或艺术创作的创造性、探索性、研究性的思维活动、心理活动中,一丝不挂指的是,摆脱先入为主的成见,摆脱固有的模式的约束,摆脱学科思维习性的制约,虚心地面对事实。对于文学艺术创作,对于科学研究,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最真的功夫是无功夫。创作过程中间,研究过程中间,丝毫不要再去想到规则条例,把所有的本上的章程放下,那样,才可能有前无古人的大创造。”“一丝不挂”不仅是佛学的修行观念,也成为佛教诗学的实践方法。能于佛语中见到诗学方法,没有“一丝不挂”的智慧和境界,又岂能做到!再如王先生在《静坐胜于造塔》篇中,看到了“静坐也为审美的创造提供条件和助力,它让主体摆脱狭隘的、物欲的、占有的态度,用超脱于偏见、超脱于利害的眼光观审对象”;在《心心相印》篇中,看到了“哲人与诗人除了珍视思维中的人天冥合即人与天心心相印这种境界之外,他们也把心心相印视为欣赏心理中的高境界”;在《不二法门》篇中,看到了“无条件地相信语言的表意功能,以为语言可以完满表达一切思想情感,可以完满表达所有哲学思维,可以完满表达审美的微妙感受,可以完满表达宗教的全部意义,是片面的认识。否认语言的表意功能,以为要表达精妙的宗教、哲学、艺术思维就必须彻底抛弃语言,也是片面的的认识。不执著于语言,也不离弃语言,凭借语言之指寻望妙义之月,这才是恰当态度”。
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两千多年前佛祖告诫弟子们的佛教修行之法,对我们今天理解佛学依然具体启发意义,而王先霈不仅将这一启示用于今天理解佛学,而且还将之用于理解佛教诗学,这是今日研究佛教诗学者尤为缺少的一种般若智慧。
二、悟之诗道
佛学之悟在诗学中的妙用古人早已注意到,北宋韩驹《赠赵伯鱼》已有“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则说“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明胡应麟评严氏之论曾云:“严氏以禅喻诗,旨哉!禅则一悟之后,万法皆空,棒喝怒呵,无非至理。诗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然禅必深造而后能悟,诗虽悟后,仍须深造。”中国佛学关于妙悟的讨论则常有顿悟与渐悟之分,晋宋之际有顿渐之争,唐代禅宗则有南顿北渐之分,这一方法在古代佛教诗学中也有反映。如元方回《清渭滨上人诗集序》云:“然偈不在工,取其顿悟而已。诗则一字不可不工,悟而工,以渐不以顿。”不过,禅道之悟,在佛教内部往往论证得严谨而深入,但诗道之悟,在诗学内部论述中则多语焉不详,欲言又止。王先霈的佛教诗学研究在这一方面将前人的论述向精深方向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首先,王先霈还是从佛学智慧层面入手,深入剖析了禅道妙悟到底悟的是什么。通过对晋宋顿渐之争和唐代顿渐之分的分析比较,王先生指出,佛教徒的悟,目标就是追求“真如”“实相”“佛性”这一最高本体,而这一最高本体本身是不能分割的整体。既然不可分割,自然就不能一步一步地分开来体悟,只能整体地完整地去把握,只能顿悟,不能渐悟。因此,顿悟和渐悟,不是量的区别,而是质的区别。顿悟所要辨明的,不是体悟的快慢问题,而是对万物本质的终极关怀和把握方式的问题。所以,理解顿悟,最重要的是看清最高本体与纷繁万象之间的关系,即一与一切的关系,一与多的关系。悟了一才能悟一切,而没有顿悟就不能把握一。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先霈借鉴格式塔心理学中的一种表达,指出“悟是对于关系的把握”。比如一件文艺作品的创作,从素材到主旨的确立,中间必然有一个悟的瞬间,这种悟就可以说是对关系的领悟。再如“诗人炼字中的顿悟,必是集中在某字某词在音节上、在意味上与全句全篇的关系。书法家落笔时的顿悟,必是在一撇一捺与一字之结体、一行各字之连接呼应的关系。就单个元素考虑,无论怎样苦思苦想,也不可能有悟。”
其次,王先霈还深入分析了妙悟在诗学实践中的独特性问题。悟之顿渐在佛教修行中的实践,与在诗学活动中的实践是有差异的。王先生认为,在文艺创作中,各种不同层次的悟都会发生作用。其一如人生之悟,“文学艺术,表现人对生命的意义的探索和思考,作者对人生意义有了深刻的体认,悟了,作品才可能有很高的价值”。陶渊明《饮酒》、苏轼《赤壁赋》等都是如此。其二如审美之悟,“从谢灵运到唐代李白、杜甫等人,都是有意作文,但他们确实都有独到的审美感悟”,“艺术创作中的触发,常常是这种悟的结果”。其三如技法之悟,“这种悟,如皎然《诗式》中所说,常常是苦思之后的突破”。上述每一层次的悟,“都有由渐而顿,顿后复渐的沉积、铺垫和完成、完善的阶段。每一个层次的悟,都是对关系的把握,从人与宇宙、世界的关系,到人与某个具体的自然或者社会环境的关系,到文本的某个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的上下文的关系,对于这种或那种关系,找到一条全新的思路,悟就出现了”。
此外,王先生还指出,在一次创作活动的不同阶段,悟的侧重点也不同。诗歌写作中的顿悟,往往是在起初的触发,但是,顿悟,悟的主要是思路,而结构、语言仍需要推敲,推敲中有反复,那就不是“顿”了。
三、圆之批评
圆形批评是王先霈提出的一种批评方法,这一批评方法简言之是指将“感性与理性融合的、适合文学的审美特征的文学批评”。在与古代文学批评和现代文学批评比较后,王先生指出,“古代的圆形批评,偏重于思维的纵综合,偏重于整体把握,对局部的精细解剖往往较为忽略,即使作局部的细节的分析,手段也较单调。现代文学批评,有许多又走入另一极端,以致缺乏整体感,缺乏灵气,缺乏审美的韵味。现代的圆形批评期望两者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圆形批评的重点是思维的圆形以及圆形思维指导下的文学批评。王先生在考察圆形思维的文化渊源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中不同派别的圆形文化进行了分析探讨。可以明显感觉到,佛教文化中的圆融、圆照等方法,与圆形批评中的圆形思维关系更为密切。
圆形思维的关键是对感性与理性、整体与局部等一系列相互对立观念的融合,而这正是佛教圆融思维要解决的问题。佛教常将这些相互对立观念的形成视为执著于“分别心”的结果,所以,只有超越“分别心”,获得平等之无分别智慧,始可把握事物真相,佛教称之为中道境界,也就是圆融境界。佛教的这一修行方法与圆形批评所欲使用的批评方法具有极大的相通性。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说,王先生正是在佛教或佛教诗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圆形批评方法;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圆形批评也是佛教诗学所提倡的批评方法。这一批评方法在《文心雕龙》中曾有较好的体现,但诚如王先生所言,“刘勰的有系统性、逻辑性的文学批评理论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没有得到全面的很好的继承。中国古代的圆形批评观念,有待于发育完善,有待于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构”。而在王先生的诗学研究和诗学批评中,我们常能感受到其中的圆形思维和圆形批评。
王先霈的佛教诗学研究除了上述三方面特色外,还对自性与佛性、境与味、禅与诗学等等一系列问题有着深入研究,这些成果所呈现的研究视野、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对今天的佛教诗学研究依然有着重要的示范和启迪作用。
注释:
[1]汤用彤:《汤用彤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53页。
[2][3][4][5][6][7][8][9]王先霈:《王先霈文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大学2020年版,第105页,104页,102页,104页,112—113页,119页,193页,215—216页。
[10]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页。
[11]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2页。
[12]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
[13]李修生:《全元文》(第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14][15]王先霈:《王先霈文集》(第三卷),华中师范大学2020年版,第313页,314页。
[16][17][18][19]王先霈:《王先霈文集》(第四卷),华中师范大学2020年版,第64页,64页,64—65页,65页。
[20][21][22]王先霈:《王先霈文集》(第六卷),华中师范大学2020年版,第82页,94页,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