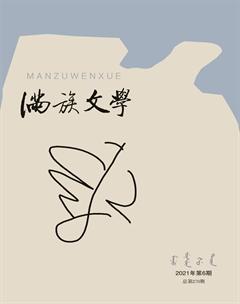老铁?老邱
程远
老 铁
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老铁一直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之一。
如你所知,树基沟小学坐落在沟里南山坡上,居高临下,目力所及,依次是居民房、托儿所、镇政府、火车站、医院、菜地、河套,过河套是北山。老铁家即住在学校下面的居民房里,应该算作小镇的上片,是我们上下学的必经之地。
我经常去老铁家玩,尤其是周三周六,因为下午没课,中午放学时就随他去家里打一站,看他收藏的小人书,或他画的画。对,老铁爱画画,这一点和我一样,用他大哥的话说:我们拥有共同的志趣和爱好。老铁的大哥是我们的美术老师。
那时,我们除了课堂上用的图画本外,往往自己也装订一两个放在家里,用于画其他的画。这些画,也多是临摹小人书或其它什么书。记忆中,我的画多是山川日月、梅兰竹菊。老铁喜欢画一些英雄人物,如杨靖宇、杨子荣、保尔·柯察金、瓦西里……其实我也经常画,只是不肖,不肯轻易示人。
可我们终没有坚持下去。上初中以后,我基本是不画画只练毛笔字了,老铁则几乎是什么也不练了,毕竟这只是一个爱好,与升学无关。若干年后,老铁总结:做什么事情没长性,浮精。这当然是他的自嘲。其实,老铁是一个学习比较好的学生,虽然也偏爱文科,但却不像我那么严重。
我们小镇的居民,除了大多数是矿山工人户和农民户外,还有一部分是地质勘探101队的职工、家属,老铁属于后者。初三时,当我们大多数应届毕业生准备复读一年再考矿山技校时,老铁因为是101队子弟,不在此列,他只有到矿上念高中奔大学这一条路。彼时,他家也搬到了矿上:一个比树基沟更大的矿山,全称中国有色金属抚顺红透山铜矿,是建国以来最著名的矿山之一。当然,这是题外话了,打住。
一年后,我到矿上念技校,老铁听说他们101勘探队所属的冶金系统也准备办技校了,就放弃了高中学习,只等技校招生。学习好,信心足,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冶金技校招生的消息迟迟不来,每日在家闲得慌,老铁就向父亲借了钱,去矿上冷冻库批发冰果卖。那几日,他时常骑着一辆28型自行车走街串巷,东一嗓子,西一嗓子,等人家推门出来买时,他却没了踪影,最后半箱冰棍化成水滴。
那时我住在职工宿舍,晚上没事,老铁就会来找我玩。我们虽然早已不画画了,但还是喜欢看书,尤其是一些文学类的书刊,甚至也偷偷动笔,写些诗歌、散文、小说,进行所谓的创作。除此之外,我们似乎就剩下喝酒了。
记得有一天,本来我已经吃过晚饭,一个人在宿舍发呆。老铁来,说今天是你的生日,走,请你喝点酒。我说算了,不老不小的过什么生日啊!咱们骑车子出去玩吧。
那时,矿山人骑自行车傍晚出来玩的很多,春风荡漾嘛,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出矿区,就是苍石乡202国道,我们沿着国道西行,边骑边玩,不觉就到了沔阳(毗邻202国道边的一个村落),村头正好有一个饭店。老铁说,就这了。
我们点了四个菜,两束白酒——不知为什么,那时管装白酒的搪瓷壶叫束,也许因其细高的缘故吧。每束装二两酒。酒菜上来,我俩也不说什么生日快乐,更没有蜡烛,哥俩好,就喝呗。这一喝不要紧,最后是每人四束下肚,时间已到夜半。老板娘见我们喝高,还没有走的意思,先说打烊,再说路远,最后干脆叫来几个小子,出来进去的,不时用眼睛睨着我们。
老铁说算账,不过身上只有二十块钱。几个小子看看桌上的杯盘,居然没吱声。老板娘赶紧说,钱不给都行,只是时间太晚了,担心你俩怎么骑车回去。老铁起身,穿过厨房,到后院撒了泡尿。
车,我俩肯定是骑不了了,只能推着走。可是,离开饭店没多远,我就连摔几个跟头——不仅车把扭歪了,链子也掉了,老铁只好把他的车给我推着(他个子比我高,也比我清醒),他扛着我的车走。最后实在走不动了,我俩索性就坐在路边。那时已是夜里一两点钟了,离矿山还有七八里路呢!除了狗叫,万籁俱寂。
许久,远处传来汽车马达声。老铁趔趄地站在路中间,挥手。车停了。这是一辆从抚顺拉啤酒开往梅河口的大货车,正顺路。司机说行,去推自行車吧。我俩高兴,谁知刚一转身,司机猛踩油门,汽车呼啸而去,但没走多远,就听几声脆响——原来大货车甩下两箱啤酒。也许司机没发觉或是发觉了也不想停下。我和老铁却高兴起来,酒,似乎也醒了一半。我们拣起没摔坏的啤酒用牙咬开,然后一人坐一个箱套,边喝边骂货车司机!
这是我与老铁喝酒最猛的一次,当然也付出了一定代价,比如我的一个手指甲戗掉了,他的裤子划破了。
1987年前后,老铁去抚顺上了冶金技校,然后参加工作,我们虽不能常见,但还保持着通信往来。当我今天要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翻出老铁写给我的信,一共七封。第一封写于1990年4月14日,最后一封是1993年8月3日,肯定有遗失的。信的内容包罗万象,工作、爱情、文学、艺术、前途、命运,即便后来都有了手机电话,也是无法替代那种笔与纸的真挚交流:
近来我的工作如往,自学考试已经不学了,原因是我们可能在九十月间外出学习,那样的话即便我学也不能参加考试。况且现在的精力也不够了,就此罢了。现在生活过得平平淡淡,没有什么色彩,更没有什么热恋了,也没有寻觅。这样也好,安静了许多,使我能有机会冷静地思考一些事情。未来的路还很长,还需要走啊!(1991.9.3)
今日收到你的来信,阅罢,为你茫然。那么多的不如意,想你现在必是很苦。是的,心太真,是容不得伤害的。可是老天也未必就有眼呢!不学会忍受怎么可以?不学会解脱怎么能行?而出家绝不是解脱的好办法。(1993.8.3)
1992年我结婚,和妻子租住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黄泥小屋。妻子在一家集体企业当工人,干计件,经常加班,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收入自是不多。我们每日为柴米油盐人情礼往所累,还要偿还结婚欠下的债务,所谓的理想早已烟消云散。那段时间,一定是我人生中最灰暗最苦闷的日子,才有了离家出走的想法,尽管只是一闪,却惹得朋友牵念。
老铁在信尾要求我去抚顺一趟,让我给他带些书。我知道这是借口,去,就是聊天喝酒呗。
那时,市场上流行一种叫作小红梅的二两装白酒,度数不高,辣而不呛。在老铁家附近的一个小饭馆,老铁喝了四个,我喝了六个。然后我们来到浑河岸边,那里有一片金黄的向日葵,开得正烈。一位头戴凉帽的画家坐在地上写生。借着酒劲,老铁也要画一幅。画家无奈,只好换上一张纸。刷,刷,刷,老铁将艳丽的黄色堆积到画纸中央,将绿色环衬周围,将蓝色渲染天空,将赭色涂满大地,最后,将灰色画成两个长长的身影,沿着浑河逆流而行……
画家说,小伙子练过啊!敢情。
老铁让我也添上几笔,算是合作。他说:说不定这幅画被谁收藏呢!到时候,咱哥俩可就发大财了。这当然是笑话。不过我还是在画纸一角写下了一句话: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见烟。
老 邱
老邱是老铁同学,也住在101沟。山东人,面黑,身材瘦而高,背略驼,方言重。
远子,老邱是我最为惦记的朋友,你多关照。
老铁在离开红透山去市里上班前,交代给我。
放心,喝酒时一定会叫他。
如前所述,我和老铁不仅是同学、朋友,也是文友和酒友,包括老邱。后者虽然是通过老铁介识,但彼此很快进入状态,说是相交甚笃也不为过。那时,我们都没有对象,更没有成家,即便长我和老铁三岁的老邱,也没有,不仅如此,他还没有工作。为此,邱婶很是着急,因为老邱是长子,身下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且父亲早逝。
但,待业青年找对象谈何容易。
记得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和老铁去找老邱出来玩,他说不行,一会儿要相个对象,我们就闪了。晚上,问老邱情况怎样,老邱摇头,说,女方在他家吃了午饭,然后两人呆在小屋里,老邱满以为女方会翻翻桌上的文学杂志,或是日记本什么的——那些都是他事先特意摆放上去的。可女方根本没看。没办法,老邱就叼支烟,望着窗外做沉思状。女方问老邱在想什么?老邱深吸一口烟,说:想那天上的白云为什么总是飘啊飘,多么像人的命运。然后问女方在想什么?女方答:在想晚上吃啥。
老邱对我们说:操!刚吃完午饭,就想着晚上吃啥,一点也不懂得浪漫!
邱婶说,啥叫浪漫?我看那姑娘挺实在的。
老邱说你不懂。
后来,矿劳动服务公司服装厂招工,老邱被录用。服装厂就在我们独身宿舍后身,每天上下班,都能看见老邱从我窗前走过,有时打声招呼,有时他径直来到寝室,也不敲门,一下就闪了进来。老邱曾被厂里派往大连皮口一著名服装公司学习,回厂后成为业务骨干,不久,赢得一青年女工芳心,对方虽然戴着眼镜,但也不爱好文学——想想文学算什么东西,又不能当饭吃。
而他们结婚的前一天晚上,我却喝高了。
那时,老铁家已经搬到抚顺市内去住了,为了赶上老邱的婚礼,他提前一天回到矿上,在老邱家,我们和一些朋友就喝开了,最后在回家的路上,我终于一头栽倒,把左眼眉骨磕出一道口子。朋友们赶紧送去医院,外科值班大夫刘姐说,醉酒真好,缝针不用打麻药。刘姐还说,阿远,我愿意在报纸上看到你的文章,而不愿意在医院里看到你这个样子!
刘姐曾是我家邻居,矿山名医。
其实,在我、老铁和老邱的聚喝中,这次醉酒还不算最严重的一次。比如那次,我和老邱去抚顺看老铁,在老铁家,我和老铁喝了一瓶榆树大曲,老邱喝了八瓶啤酒。一瓶榆树大曲喝完,未尽兴,又懒得下楼敲卖店,就索性将我带给老铁爸爸的两瓶黄鹤楼打开了。老铁说:反正我爸也不喝酒。最后,两瓶黄鹤楼落肚,我也扎在沙发上睡着了。次日得知,那晚老铁下楼,不仅将小区新栽的树苗连拔数棵,还把一对正在楼门洞里谈情说爱的情侣哄散,且美其名曰深更半夜,保护妇女。
老邱说多亏他在旁边罩着,不然对方肯定没完。
好景不长,几年后服装厂破产,工人下岗回家。
也许天性使然,或多少传承了作为矿山工人父亲的基因,更或生活所迫,老邱对地质勘探发生了兴趣,和朋友四处找矿,每天骑着一辆28型自行车,早出晚归,包里永远装着锤子、测量仪和卷边的图纸。不用说,脸,愈发黑瘦,背,也愈加弯曲了。
1998年,我离开红透山到沈阳工作,有时回到矿上偶尔也能碰到老邱,有时间,也会喝上几杯酒。老邱说,你看见门砍哨浑河边那座山没?那儿的风水很好,你不是一直想弄个民宿么,那山脚下最合适。
我说,我当然想啦!就等着你开矿挖到一个金疙瘩呢。你投点资,咱们办个作家创作基地,召集全国的文朋诗友到这里,边写作,边游玩,说不定还能拉动一方经济,为振兴东北做点贡献。
老邱说,你就数嘴行,总也落不到实处。
现在想来,老邱只到沈阳找过我一次。
那时,我借住在东塔机场民航大院的一间平房里。傍晚,老邱背着一个蛇皮口袋进屋。我说挖到金疙瘩了?他说嗯,这些都送给你。打开蛇皮口袋,我一看里面装的都是木条木框。老邱说,他不与人合伙开矿了,要去新宾县南杂木镇一木器加工厂打工,这些木条木框本来是作为样品给沈阳五爱市场客户的,但跑了一天没有几家要。你在报社,是不是能给免费打个广告,这可都是实木的,你们城里人装订字画用,高雅得很。
我说你真能折腾,喝酒吧。
这一晚,我俩都喝多了。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痛快地喝上一顿酒了。
次日,老邱背着他那个蛇皮口袋回家。之后我们虽然保持着联系,但不多,也很少见面。有一年春节,我回乡,三十那天闲着没事去他家玩,他立刻让妻子温酒炒菜。我说,大过年的我怎么也得和家人在一起啊!老邱说,在哪儿不是一样过。结果,我们又是喝聊半宿。始知,他早已不在加工厂打工了,又和朋友去外省承包了一个金矿点,但最终将本金都赔了进去,才不得不回来,由于常年在山里作业,患了一身病,尤其静脉曲张让他常常生不如死。说着,老邱提起裤管,让我看他那两条黑黑细细的腿……
我说:你这不是在拼命吗?
老邱:孩子大了,哪儿都用钱。
现在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年了,老邱打一辆摩的(摩托出租车)在矿区公路上行驶,突然与一个拉着带车子的人相撞,车仰人翻是一定的了,最为凄惨的是带车子长长的木杆扶手竟直接戳到了老邱前胸,致使内脏破裂流血。几日后,我去医院看他,老铁说同学们正在募集捐款,因为摩托车主是下岗工人,带车车主是附近农民,哪一个都拿不出钱来承担高额医疗费,宁可坐牢。握着老邱的手,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一个从未用过的词:命运多舛。
不久,老邱在故乡红透山病逝,享年四十七歲。
因为什么事耽搁,我没有回去与老邱告别。
转眼夏天来临,我和老铁一起开车去新宾,在县城接上老邱的妹妹,由她带路,去往乡下的一个深山沟里。我不知道,老邱的坟地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偏远的地方,难不成是风水宝地?其实,那里仅仅是一片普通的山地,有一些果树和庄稼,还有一间土坯房。老邱的坟就在房前。
老邱的妹妹说,土坯房是哥哥生前亲手盖的,没事的时候,他总愿意一个人来这里住上一阵。边看果园,边伺弄庄稼。
哦,好兄弟,老邱你终于可以安息了。
【责任编辑】王雪茜
程远,自由写作者,鞍与笔文旅工作室创办人,现居沈阳。文字作品散见于《山西文学》《福建文学》《北方文学》《鸭绿江》《小说林》《草原》《西湖》《散文百家》等数十种报刊,部分作品被收入年选。著有非虚构文本《底层的珍珠》。执编散文随笔集《活着,走着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