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
胡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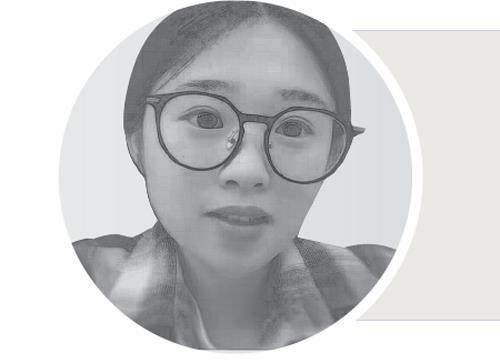
刚才,奶奶给我的包里塞了三个苹果,还有一盒茶叶。起初我并不知道,背起书包的时候,才感觉到背上的重量。回家后,打开书包,把包里的东西倒在床上,三个苹果从里面滾出来。
一个礼拜前,她还给我的裤子口袋里塞了两百块钱。那两百块钱原先是我给她的生日红包,生日那天,我特意找同事换了连号的新钱,顺便还要了一个写着“福禄双全”的红纸包。老人家讲究送礼的时间,得赶早,过了十点都不得行。这句话,我往常都记不起,但是临近她生日的那几天,这几句话赶着趟儿,冷不丁就往我脑子里钻。
她生日的那天,是农历七月初九,礼拜一,但为了把一大家子都凑到一起,就把生日挪到了礼拜天。一大清早,我就赶过去了。
没想到,隔了一个礼拜,那两百块钱又回到了我的口袋。那天晚上,她把我单独叫到房间,硬是把那两百块钱塞还给了我。
“你现在又没钱,拿着,那个红包壳我收下了,福禄双全嘛,好兆头。”话还没起,她就笑了,话音落了,那笑还在嘴角挂着。
夜里,我躺在床上,陡然想到了放在裤子口袋里的钱,猛地从床上弹起,从脏衣篓里找到了那两百块钱。两张连号,是我给她的新钱。
这两张新钱现在夹在我的书里,就在刚才,我把那三个苹果搁在了那本书的上面。我望着这几个苹果,它们又大又红,拿起一个,掂量掂量,足有半斤多重。几个小时前,想必她趁我正在客厅逗弄小孩的空档,拉开了房间衣柜的玻璃移门,然后绕开摆在矮立柜上的瓶瓶罐罐,从一堆苹果里挑了三个红苹果出来,又依次把它们拿出来放在日光灯下左右看看,生怕自己挑的苹果是不是哪里磕坏了。
她总是这样,给别人的东西务必都得是好的,这份仔细跟慷慨从来不分亲疏。
方才我们在广场上散步,谈及她明天要去医院看病的事。这几天,她的右脚脚踝莫名肿起来了,她左手拄着小表妹的推车扶手,右手拉高裙子,将右脚翘起,露出那只病脚给我看。
“是脚踝处吧?我看着都肿了呢。”
“是噢,这下快成跛子了,走路干活全靠这跛脚了。”她又笑了,像是打趣自己一般,说话间她佝着身子,去摸那只已经肿起来的脚踝,用力捏了两下,而后直起身子。
她讲最近手也不灵活,“早上起来,手指都握不了半个拳头,到了晚上要稍微好一点,你看,现在能握大半个呢”,她在我面前摊开手指,又做了握拳的手势,我顺势将她的手拉到眼前。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呢?手指骨关节已经肿胀得完全凸出来了,而黏连在骨头上的皮肉却像反复揉碎,最后又展开的草纸一般,褶皱连连。我伸出食指,轻轻抚摸了她其中一个关节,感受着那皱下去的皮肉在我手指上的粗糙程度。
“夏天还好哩,等再过一段日子,手就全都肿起来了,到时候又得开始贴膏药贴了。”她收回手,右手捞起准备从她身边跑开的小表妹,话到这就算是聊完了。她们一老一少往前走,我推着车跟在后面。
借此机会,我观察起她的背影来。她牵着小表妹,缓慢穿梭在好几个广场舞方阵的空隙里,走三步歇两步,一是为了看顾孩子,二可能是因为她的病脚,所以走起来有点高低脚,身子重心往一边移。才两岁多的小表妹已经齐她的腰了,贪玩好动,走起路来,扭扭捏捏,她亦步亦趋跟着,两只手臂微微张开着,随时提防着孩子摔倒,像是只护崽的老母鸡。
她就是用这样的姿势护佑了好几个孙辈,最先被护佑的人是我。二十多年前,她亦步亦趋跟在我身后,追着我喂饭,又在水泥地上拿粉笔教我写字,带我去后山砍茅草,把茅草枝削成小木棍儿,教我算术。
她确确实实老了,从那一双手脚开始老的。自她出生起,这双手脚就被她使唤惯了。
幼儿时期,一双小脚在堂屋跟正门前来回徘徊,父母兄弟外出干活了,她得守着家里,一双嫩手轻轻摇着睡在摇篮里的弟弟。等再大一点儿,就开始背着背篓上山砍柴,有时候还跟着男人们一起去伐树,临近饭点得约着族中姐妹去田野里薅野菜喂猪喂鸡,赶上三年饥荒,得去挖草根树皮。后来长大了,跟着蹩脚村医学了些接生的手段,又开始上山下乡给村妇们接生,平时还不忘种地插秧做农活。她跟绝大多数农村妇人一样,生在了这片土地,长在了这片土地,拿起锄头刨完了这片土地。
现在,她成了这个城里的一分子,满六十五岁那年,办理了老年人公交免费乘坐卡,她开始坐着公交车接送孩子,跑菜市场买菜,带着孙女一个个商场转悠。近一点的地方就步行,她无非是在菜店、游乐园、家里这几个地方来回转悠,像拉磨的驴一样在固定的地方打转,每天竟然转出了两万多的步数。
七十年里,她这双脚走过太多地方了,蹚过无数条大河,跨过数不清的沟壑,从山上走到山下,从农村走到城市,从少年走到暮年,从故乡走到他乡。她一刻不停地在走,几乎从未停歇,于是,这双手脚脚渐渐有了毛病,手指头骨关节早就变形了,膝盖也越来越弯曲,有一阵子膝盖里还有积液,现在,就连脚踝也开始犯毛病了。
这大概是身体在抗议,抗议它的过劳,所以时不时搞出点毛病来,好让她不舒坦,但没想到她是极度能忍,从不轻易哼唱痛苦的人。好多年前,她跟我说,她身上多出了好多小肉球,而且这肉球还能在身体里游走,我伸手去摸,果然能摸到。后来她去医院查了,医生说是淋巴结,但暂时也没什么影响。
前段时间,她突然告诉我,身上的淋巴结少了很多,现在就腰上还有一些了。但关于这件事,我很早就忘记了。这么多年里,有关于她,我忘记的永远不止这一件。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因为她在诉说这些身体病痛的时候,脸上没什么大的表情,甚至还带着笑,没哼过痛,也没讲过苦,在讲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一般自在地把这些事聊了出来,所以我不记得,我忘记了。
我开始在脑袋里搜刮跟她有关的事情,但发现能够清晰记住的少得可怜,大多数事情只有一个片段,甚至只有些模糊的影子。
在绍兴念书的时候,她背着包去看过我两次,自不用说,那包里都是塞给我的零食,有些是她省下来的,有些是她买的。
前年,我过得大不如意,当然,也是我自己不成器上蹿下跳得来的苦果。临近除夕,一家人在厨房里夜谈,一边唠家常,一边数落我的不是,我沉默不语,没敢搭腔,只顾着往灶膛里添火。人群里响起她的声音:“我看伢儿还是有出息的,我对她有信心。”大概是一句话还不够坚定,她又补了一句:“奶奶对你有信心,你也要对自己有信心。”
那天夜里,有好几串泪滴在了干柴上,那些浸满了我眼泪的柴火被我一根根递进了灶膛,随即燃起了熊熊火焰。
这些故事跟夹在书里的两百块钱,还有面前摆着的三个苹果一样,是她给予我的。我反复询问自己,我有给过她什么吗?
我没有!
她七十大寿那天,吃罢晚饭,我躺在她床上,两个表妹躺在我的两边,她靠坐在床头,嘴里念叨着:“人生再也没有七十了,再也没有七十了……”我转过头去看她,她似乎在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