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在孤寂中酿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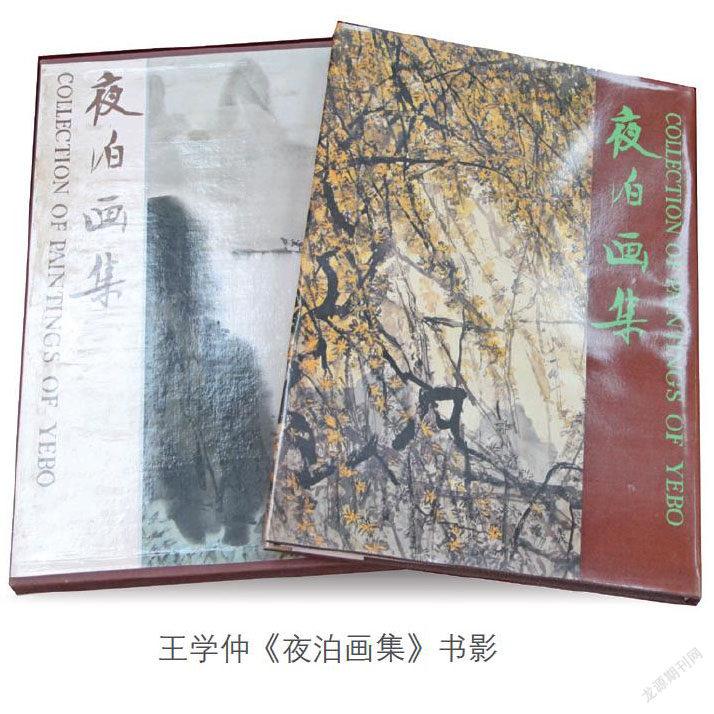

老式卡带录音机沙沙地响着,里面贮存着王学仲先生20多年前的一段郑重托付:“侯军同志,我总结我这一生,其实是个悲剧人物,外界并不了解我心里的孤寂。我从来不惧怕孤寂,因为我坚持认为,艺术就是在孤寂中酿成的……我今天之所以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是因为你还年轻,我年纪比你长,今天说了也不一定现在就写出来,我是希望你在我百年之后,能说句公道话,告诉世人王学仲是个什么样的艺术家!……”
录音机中,声音是那么洪亮,笑声是那么爽朗,思路是那么清晰,语气是那么真挚。当时王学仲先生66岁,眨眼之间,22年如电光石火一闪而过,王老以88岁高龄驾鹤西游,我远在南粤未能亲至送别,只能在这个孤寂的日子里,重聆先生之雅教,追念黾园之芳馨。同时,将王学仲先生当年之所思所言,录之于文,公诸于世,以酬黾翁老人对我这个晚辈后生的百年重托!
一
我与王学仲先生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我在津报司政教之职,自然与高等院校往来密切。王学仲先生任教于天津大学,且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应日本筑波大学之邀东渡讲学,这在刚刚开放的中国还是一件新鲜事,由此,也就与他有了一些新闻报道方面的接触,但交往并不深。我与他的深度交往,缘于我在天津日报上刊发的一组《漫议书法的现代意识》系列文章。他对这组谈论书法艺术的12篇短论给予了超乎我意料的赞赏,亲自出席为研讨这组文章而召开的书法理论研讨会,在发言中语多警策,勖勉有加,令我十分感动。会后,他邀请我到天大的黾园做客深谈。而我的住家恰好就在天大的后门,距离很近,于是,我此后便成了黾园的常客。
1992年秋天,一次高规格的“王学仲艺术国际研讨会”即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会前一个多月,王学仲先生就给我打来电话,希望我写篇文章参加这次学术盛会。这是无法推辞的盛邀,我立即答应下来。可是,写什么?怎么写?我心里没底。我必须与王学仲先生进行一次深入透彻的长谈,否则无法下笔。我把这个想法电告于他,他说:“我早就想跟你好好聊一聊了,还怕你没时间来呢!欢迎你来,今晚就来吧!”那一天是1992年10月16日。
这是一次双方期待已久的对谈,我特意带着采访录音机,而王学仲先生则准备得更加充分,把自己的多种著作都备齐了,且一一题上我的名字,计有《中国画学谱》、《黾勉集》、《王学仲研究》(首辑)、《夜泊画集》、《书法举要》、《王学仲书法集》、《王学仲书画诗文集》(日文版)、《王学仲书画旧体诗文选》等,厚厚一大摞。黾园的秋夜静谧而清冷,窗外竹影婆娑,园内一灯独明。王学仲先生与我没有一句寒暄,落座之后就开始侃侃而谈——他的身世,他的家族,他的成长环境,他的文化背景,他少年时期的诗教渊源和书画启蒙,他青年时期得遇恩师徐悲鸿的求学经历,他“三怪”之誉(这是徐悲鸿当年对他诗、书、画三艺的“一语定评”)的由来……
我当时拼命地记笔记,几乎顾不上提问,事实上也无须提问。王学仲先生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学艺之艰辛和从艺之甘苦,阐发着他独特的艺术观念与“不合时宜”的审美取向,毫不忌讳地坦言自己的得失成败,无所顾忌地直斥世风之污浊与书生之无奈……我绝对没有料到他会如此坦荡地向我陈述这一切,更没有料到在采访已近深夜时分,他忽然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口吻,向我这个晚辈说出了前面引述的那段肺腑之言——请允许我依照当时的录音,将王学仲先生当时所言之要点笔录出来,以告慰西行不远的黾翁老人。
二
下面记录的就是王学仲先生彼时彼刻的一番“夫子自道”:
我总结我这一生,其实是个悲剧人物。回顾一下,至少有四个悲剧已经在我身上发生了。
一个是早年因为艺术观念的不同,徐悲鸿先生与我由近而疏。我很敬佩徐悲鸿先生,尤其是他的那种大气磅礴的气势,震撼了我的心灵。在(19)47、(19)48年间,我还参与了徐先生领导的新旧国画之争,还写文章参加了论战,我赞成徐先生要改良中国画的主张,反对那种保守观念。当时徐悲鸿先生很欣赏我,给我题词,夸我是天才,是“三怪”。但是,在我接触到古代文人画艺术之后,我就感到徐先生的画过于拘泥于造型了,画外之趣太少,这就不能满足我的心灵了。我当时已经进入青年了,开始有了自己的追求,我就大步跨向了文人画。当时郭柏川先生组织了一个新京画会,传播一些西方的新派思潮,加上我接觸了梁楷、八大的艺术,这对我震撼都比较厉害,使我得到很重要的艺术启示,这就跟徐先生的艺术主张产生了矛盾。他很反对文人画“逸笔草草”的东西,我却喜欢文人画;他很反对西方现代派,把马蒂斯、毕加索都骂个臭死,可是我却对印象派以后的西方新潮很有兴趣。而他作为一个艺术大师,自然就看不上我的画了。这完全是“主义的分歧”。我的第一个人生悲剧就这样形成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这是我最重要的学习阶段。可是以我的叛逆性格和艺术观念,跟当时美院的风气还是格格不入。我画的油画、国画老是受到大家的讽刺,因为我重心性、重意象,不重造型,同代人都不能接受,我就成了另类,致使在美术界我一直是孤立的,知音稀少。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的那一代人都是正统的学院派,直到现在,执掌实权、主宰画坛的还是这一派,其实都是我的同学,可是我恰恰被他们视为对立面,是个叛逆,这就决定了我一生的悲剧命运。
如果说在中央美院的遭遇是我的第二个人生悲剧,那么我的第三个悲剧就是毕业分配——我怎么也没想到,美院会把我分配到天津大学建筑系。这是个工科院校,把我分到这里本身就带有惩罚的意味,也就是说,我被主流美术界给边缘化了。从此以后,美术界也没我什么事儿了。我本来就是学画画的,可是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么个画家存在——你说这是不是我的大悲剧!
当然,我并不抱怨命运。既然这条艺术道路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就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么些年,我已习惯了孤独和寂寞,我不卖画,也不炒作,也不希图让别人认可。我有两句诗:“懒从痒处搔,故而知音稀。”别人都是千方百计去“搔到痒处”,我却“懒从痒处搔”,那就甭怪没人理解了。幸好,我赶上了改革开放,日本人把我请去讲学,他们倒是能欣赏文人画。我在日本那几年画了不少好画,社会上也有了一批知音,可是我的悲剧命运并没有改变,这就说到我的第四个人生悲剧了——我从日本讲学归来,大家都以为回归美术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谁知在天津美术界却遇到了一些实力派人物的百般阻挠,硬是把我从美术界挤到了书法界,挤到书法界也同样不被认可,说我写得不好……
侯军同志啊,外界可能看着我现在也有自己的研究所了,社会上也有点知名度了,成天来来往往都是求画要字的人,挺热闹的。其实并不了解我内心的孤寂和悲凉。我的人生充满了悲剧,归纳起来就是八个字:“以小掩大,以一掩十。”说透了吧,书法只是我的一个余事,现在反倒成了我的“主业”,人们一说起王学仲,不就是个写字儿的么?其实我的绘画、我的诗词、我的学术研究,哪一样不比写字分量重啊!……我的艺术也许不成熟,但是我在追求。我从来不惧怕孤寂,因为我坚持认为,艺术本来就是在孤寂中酿成的。我今天之所以要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是因为你还年轻,我年纪比你长,今天跟你说了也不一定現在就写出来,我不着急,我早有思想准备,可能有生之年我都看不到自己的艺术被社会认可,我只是希望你在我百年之后,能说句公道话,告诉世人王学仲是个什么样的艺术家!……
三
从王学仲先生的谈话中,我领悟到老人家对我的充分信任和郑重嘱托,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写作激情,开启了我的思维空间。经过几个昼夜殚精竭虑的精研细审,我把王学仲先生讲明当时还不可披露的内容小心“匿藏”起来,把他特别强调的内容重新归纳完善,终于列出了一份详尽的论文提纲,题目确定为《王学仲艺术思维特征论》。重点分析王学仲先生艺术思维的发散性、多维性、逆向性和求异性,还专门辟出一个章节分析他这种艺术思维所带来的得失利弊,这在当时的学术空气中称得上是“胆大妄为”之举了。
10月21日上午,我带着这份提纲再次造访黾园。这一次,主要是我向王学仲先生阐述自己的论文要点,而他大部分时间是在静听,只是偶尔插几句话,或延展我的思路,或补充我的论点,或纠正我的口误。我的阐述结束了,王学仲先生对我的构想非常满意,说以往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他的艺术,而且我的解读还非常准确,有些论点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尤其令我钦敬的是,王学仲先生作为已经誉满中外的艺术大师,对我拟在文中批评他的艺术缺陷,表现出虚怀若谷的宽容大度。他说:“你不必顾忌我的年纪我的辈分我的面子,该怎么写就怎么写,你的批评越中肯越尖锐,对我的帮助就越大,对别人理解我的艺术也越有好处。”他甚至不让我在文中加称“先生”,他说:“学术本来就是平等的,你就直呼王学仲其名,这不是我客气,这是对学术的尊重。”时隔20年,如今的世风自然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此时此际,重聆黾翁之雅教,不禁愈发感佩老一代学人的襟怀和品格。
大概是我方才的阐发激起了王学仲先生的兴致,他忽然起身出屋,不一会儿,不知从哪里搬来一个梯子,架在大厅一侧的一个二层阁楼上。我见他要登着梯子爬上阁楼,连忙劝阻,他朗声大笑道:“我的腿脚还顶戗(天津方言,意为顶得住),登梯爬高没问题!”说着,老人已经麻利地上去了——原来他是到阁楼上取画去了。
这是几幅八尺乃至丈二的大画,有山水也有人物。王先生在大厅里一边展开画作,一边说:“这是我最近画的几张东西,是给自己留着的,不想给外人看,所以藏在楼上。今天要拿出来给你看看,因为你是能懂我的,知音难得啊!”他俯身在地,一张张指点着这些大画:“这幅《墨子观染》是依照墨子的故事来画的,带着一丝苦涩。墨子是我的老乡,他的思想对我影响非常大,比如他的非攻、苦行、尚俭、摩顶放踵等等观念,都直接影响了我的人生观;那张是表现庄子思想的,与我那幅《抱瓮灌园》是同样的主题,就是反对人类以机心来破坏环境,倡导一种回归自然、回归田园的朴素精神;这张山水用了许多特殊的工具和技法,比较有探索性,瞧,这些线条就是用帚笔画的……”我问什么是“帚笔”,王学仲先生立即把我带回他的画室,从笔筒中取出一支疑似笔的东西,实际上那些笔锋都是用扫帚苗捆扎而成的。王学仲先生见我一脸迷惑不解的样子,就铺开一张小宣纸,用这支特殊的帚笔濡墨挥洒,示范给我看。很快,一抹山影映现于纸端,接着又用毛笔略作点染,一幅小品就完成了。他顺势就在这幅小品右上方题了两行小字:“帚笔写出破败山,付与白军横目看。”我登时就笑喷了:“您这是送给哪家‘白军啊?”王先生一拍脑门:“哦,写错了,本来想写白春的(我的笔名),一不留神,把你的真名给写上了。”我说,这倒也好,笔名的姓,再配上真名,堪称珠联璧合,独一无二!王先生闻言哈哈大笑,说:“我还从没送过帚笔画给人呢,这个纪念品够特殊的!”于是,这件带有演示性的帚笔小品,就成为我珍藏的王学仲先生的唯一画作。
四
10月底,我把写好的论文交给了王学仲先生。他显然十分满意,却没说感谢之类的客套话,只是郑重其事地建议我以后如有时间,再把这篇万字长文做一些充实和完善,写成一本十来万字的专著,纳入王学仲研究所的研究项目,他将承担此书出版发行的全部事宜。他说:“你这本书不单是对我个人的艺术思维的专题研究,也是对整个艺术创作思维规律的独特探索,对那些希望从事艺术创作的青年人都有启迪作用。”我深知,这是王学仲先生对这篇论文学术性的一种肯定,还有什么比这种肯定更值得珍视呢?我为此而深感欣慰。
但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偶然变故却使我与王学仲先生这段“互为知音”的文缘,并未画上圆满的句号——变故发生在那次研讨会的当天,即1992年11月26日清晨。本来王先生预先就通知我,当日的研讨会要乘车从天津直抵北京人民大会堂,集合时间不能迟到,我满口答应了,而且我也被告知,因车辆位置有限,人数是经过严格计算的,我是特邀代表,且年龄最小,可见是受到了特殊关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前一天的夜里,我突然发起高烧,打针吃药折腾到半夜,大概是药物中有镇静剂成分吧,我竟然没有听到闹钟的铃声,当我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的时候,已过了集合时间20多分钟。电话里,王先生焦急地问我:“走到哪里了?马上就要开车了!”我顿时惊慌失措,语无伦次地说:“我……我发烧了,睡过了,对不起!您先走吧,别等我了……”
我可以想象出那满车的乘客是何等的焦虑和抱怨,更可以想象出王学仲先生是何等的遗憾和失望,然而,时间是无法挽回的。在我的内心深处,这种愧疚和遗憾又何尝不是绵延多年,至今想起来依旧无法完全释怀。
不過,王学仲先生很快就不再提起这段插曲了。那天从北京回来后,他还周到地安排助手把我那份北京研讨会的纪念品(一个镌刻着王学仲先生题字的铜牌和一个印着会标的手提包)专程送到我家里,并捎话说,你虽然没能赴会,你的论文还是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肯定。我猜这当中绝对有安慰的成分。
几天以后,我的高烧退了,我带着负疚的心情来到黾园,向王学仲先生道歉。他却朗声大笑着说:“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又不是你想生病,道什么歉呀!”我从他脸上读出的感觉是,他确实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只是在笑过之后,他轻轻叹息了一声:“你没有去,是我的缺憾啊——我这辈子大概不会再开这么大的研讨会啦!”
五
人生聚散,原本无常。此刻近在咫尺,不知何时就会远隔天涯。我和王学仲先生都没有料到,就在几个月后,命运的幻合就驱使我踏上了南下深圳的远行之路。
定下行期之后,我去黾园向王学仲先生道别。冬天的黾园木叶尽脱,有些荒寒之象。听我讲明来意,王先生神情有些黯然,对我说:“出去闯荡一下是好事,年轻人不能死守一地。古人讲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是有道理的。只是,你这一走,我又少了一个可以聊天谈艺的朋友,有点舍不得。”我说:“我会常常来看望您的。”他说:“随时欢迎你来,多给我介绍一下南方的情况。”因为临行前事情很多,我并无意久坐。王先生也看出了我的心思,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可能很忙,我们今天就不多聊了。有话我就直说,你要走了,我要给你写一件东西,你说吧,你想写什么?”
这实在令我大为惊喜,要知道,王学仲先生的墨宝是千金难求的。今天,王学仲先生主动提出要题字相赠,我深知这当中饱含着先生对我的一份深厚情谊。我想了想说:“请您给我题一个斋名吧!”
王学仲先生当即挥毫,为我题好了“寄荃斋”三字。写罢,似乎意犹未尽,又说:“这一张算是命题作文,我再写一张,是我的一首诗,算是我对你的赠别寄语吧!”
心羡九霄兔,
目驰八极鹰。
清风为益友,
明月是良朋。
接过王学仲先生这份沉甸甸的临别寄语,我的眼眶有些湿润了。
我是1993年2月南下深圳的。两个月后,需要回津办理调动手续,同时也正好把妻女带到岭南。这一次真是举家南迁了。我特意与王学仲先生约了时间,要带着家人一起去拜访黾园。
当时小女乐乐只有7岁,正是伶俐乖巧的年龄。王学仲先生一见小女就很开心,似乎返老还童了,问这问那有说有笑,逗得她咯咯直笑。他发现小女对糖果之类吃的东西兴趣不大,就跑去书架跟前翻书,找到一本《梁培龙水墨儿童画选》,连忙拿给小女看。乐乐翻了几页,立即被吸引住了。王先生说:“好哇好哇,小娃娃爱看书,这本书就送给你啦!”说着,就在书的封面上题了“悦斯小朋友,爷爷王学仲赠”两行字,还加盖了自己的印章。小女乐乐接过书,高兴地给王爷爷鞠了一躬。
这次会面给我妻子李瑾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尤其是王学仲先生对她讲的一番话,使她对这位老人充满了感激。王先生问她:“你是不是准备辞掉天津的工作,跟先生一起去南方啊?”她回答:“是啊,先去看看,再找工作。”王先生说:“这就对了!深圳那个地方我去过,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一个人去奋斗很不容易,要是两个人一块奋斗就好一些。再说啦,一家人,和和美美恩恩爱爱在一起过日子,就算开头艰苦点,那也好对付。要是让他一个人孤孤单单,清锅冷灶的,感觉就很难过。这个家也就不像个家了。”
妻子事后告诉我,那天,王先生还利用我带着乐乐去园子里看花的时机,单独对她叮嘱了几句,他说:“我跟侯军已经很熟悉了,跟你是初次见面。你们还没来到时,我就想,该不该嘱咐你几句?合适不合适?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要跟你说一说。因为我在深圳听人家说,很多家庭本来好好的,就是因为分开时间太久了,就散掉了。你们家可不能啊……”我对妻子说:“王先生这是真心实意为咱们着想啊,这老人家待人真是太实诚了!”
六
一转眼,我南下鹏城已经20年了。在此期间,我虽说时常南北往来,但是,像当初那样与王学仲先生挑灯夜谈不知今夕何夕的情形,却如梦幻一般沉入记忆之海了。一是因为来去匆匆无暇他顾,二是因为我离津不久就得到消息,王学仲先生因患脑栓塞病倒了。我闻讯十分焦虑,曾于1995年利用短暂的探亲之机,两次前往黾园探望,却被工作人员告知:王先生病体尚未复原,行动不便,还不能会客。
1996年,我应邀参与深圳龙岗区《百龙墨宝》一书的编辑工作。在列入名单的一百位当代书法大家中,王学仲先生是当然之选。我一看立即请缨,把约请王先生墨宝的任务揽在自己名下。就在那年的深秋时节,我专程回津办理此事。我把邀请函直接交到黾园,工作人员很客气,说一定转交,但是对我希望面见王先生的请求却未置可否。于是,我就在门房里借了纸笔,匆匆给王先生写了一封短笺,说明来意,问候安康。
转天中午,我接到黾园的电话,说王先生已经写好了“龙”字,约我下午四点钟在黾园见面。我按时来到那个熟悉的庭院,王先生已经在里面等候了。只见他手里拄着一根拐杖,缓缓地走过来。我吃惊地发现,王先生好像骤然间苍老了许多。坐定之后,我连忙探问病情,王先生似乎不愿多说,只是摇头叹息,显得很无奈。他也询问了我到南方后的情况,听我简单介绍之后,老人家只是说了一句:“唉,生命很脆弱,别依仗着年轻就拼命,悠着点儿!”
沉默。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言语来安慰老人家,王先生似乎也不愿意再像以往那样给我以鞭策和鼓励了。此时,天已昏暗,室内没有开灯,我望着暗影里的王学仲先生,有些朦胧、有些黯然。他从办公桌上取过一个牛皮纸信封,说:“这是你要的东西,我上午就写好了。唉,手还不跟劲,只能这么对付了!”我连忙打开信封,展读那幅书法,那是一个规规矩矩的楷书“龙”字,笔酣墨浓,一笔不苟。这种中规中矩的写法,是我以往从未见过的。我把我的印象说给王先生,他却苦笑着说:“我也想写个草书、隶书什么的,可是现在没办法,实在是潇洒不起来啦!”我感觉王先生情绪有些消沉,就劝慰老人家好好调养,慢慢恢复,将来肯定能随心所欲地潇洒挥毫。王先生点点头说:“我也有这个信心,还有好多事情没干成呢,不能就这么放弃呀!”从他的语气中,我品味到了他所特有的那种坚毅和韧性。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王学仲先生。不过,此后十多年间我与黾翁老人鱼雁往还从未间断,他还三次把自己的新书寄赠给我,一本是《墨海四记》,一本是《黾园丛书·王学仲散文选》,另一本是《三只眼睛看世界》。尤其是后者,令我非常惊奇,里面收录的是王学仲先生在新世纪旅行欧洲所写的新诗和所画的速写。我读罢此书立即给他写了封信,一是看到他行踪遍及欧陆,说明身体状况大有好转,为此,表示衷心的祝福;二是看到他的新诗,感到格外新鲜。一个写了一辈子旧体诗的老诗人,古稀之后却能“转换频道”写出如此精彩的新诗,这说明黾翁宝刀不老,且创新进取之心依然如故,真是可喜可贺!
近年来,津门老友刘宗武先生担纲编纂了一系列王学仲先生的研究专著。每出版一部,他都依照王先生的嘱托给我寄来,让我先睹为快,陆续寄来的大部头著作有《王学仲的艺术世界》、《黾学大观——解读王学仲艺术》、十卷本《王学仲文集》,等等。那年,刘宗武夫妇来深圳小住,更是向我详细介绍黾翁的健康状况已明显改善,这令我倍感欣慰。随后,我看到王学仲先生的书画艺术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所推重、所喜爱,其艺术成就和学术地位,也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越来越高的评价。在他的家乡山东滕州,在孔夫子的家乡曲阜,在文化名城徐州,先后建起了王学仲艺术馆、王学仲画馆、王学仲艺术展览馆等永久性展馆……凡此种种,都是对这位在曲折坎坷的艺术之路上踽踽独行的老艺术家最好的心灵慰藉。
王学仲先生,您还感到孤寂吗?不必了吧。您以自己一生的孤寂,酿造出醇厚甘美的艺术琼浆,足以令无数后来者为之倾倒为之仰慕为之陶醉!
王学仲先生,您还需要我这个晚辈后生来告诉世人,您是怎样一个艺术家吗?也不必了吧。您已经以自己一生的锐意进取和苦行僧般的辛勤耕耘,构建起令世人瞩目的“黾学”大厦:中华文化,为其根基;欧风汉骨,为其筋脉;书法绘画,为其躯干;诗文学术,为其灵魂。如此辉煌的人生乐章,又何须我来置喙呢?
“任君肥瘦论头脚,只管高歌独唱人”——这是我当年所写论文中的一个小标题,引用的则是王学仲先生自己的诗句。如今,当我们送别王学仲先生的时候,我想告慰于黾翁老人:您当年的“独唱”如今已汇成了无数人的大合唱,在您一生走过的艺术之路上,早已是遍地知音——为此,您应该含笑九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