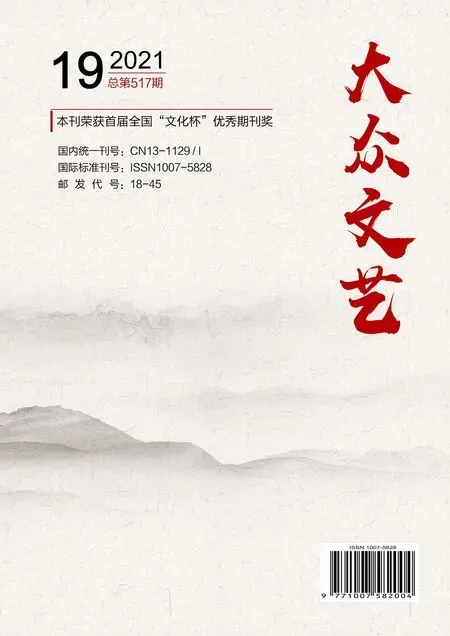他山之石:弗吉尼亚·伍尔芙与俄罗斯文化
季安凯
(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曲阜 273100)
1910年起,不懂俄语且平常对俄国极少关注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开始接触、阅读俄罗斯小说(英译本)并立即沉醉其中——俄罗斯文学不仅大大拓展了她对俄国和俄罗斯人的进一步认识和了解,还很快成为她追求自己小说形式革新、“意识流”写作、情节与故事、表现主人公复杂潜意识、表达全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等诸多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实验的重要灵感来源。其中伍尔芙对诸多俄罗斯作家都有十分精辟的见解。她在一篇随笔中称赞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所有小说家中最伟大的小说家”,其中“在托尔斯泰那儿生命占据着主导地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灵魂则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精准的判断一方面是基于伍尔芙本人的个人阅读体验(托、陀二人为女作家一生最喜爱阅读的俄国小说家),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她丰厚的艺术修养和敏锐的审美嗅觉。1917年伍尔芙撰写了《更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More Dostoevsky)和《小型陀思妥耶夫斯基》(A Minor Dostoevsky)两篇随笔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还写有一篇关于托尔斯泰短篇小说《哥萨克》的评论,1918年创作了关于契诃夫小说创作的随笔《契诃夫的问题》(Tchehov’s Questions)以及一篇关于“白银时代”著名俄国诗人布留索夫诗歌创作的评论《瓦莱里·布柳索夫》(Valery Bliussof)。1919年,伍尔芙完成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一篇新的随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克兰福德》(Dostoevsky in Cranford)。1921年撰写关于契诃夫戏剧的评论,1933年撰写关于评价屠格涅夫小说的另一篇随笔《屠格涅夫的小说》(The Novels of Turgenev)。另外在《伍尔芙日记》中伍尔芙评论了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原则:“我们从何知晓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屠格涅夫差还是比屠格涅夫好?文学批评的尴尬之处在于它总是浅层的……屠格涅夫总是从自己的视角记录巴扎罗夫的日常生活”。R.鲁宾斯坦认为,“伟大的俄国作家们在她(伍尔芙)创作原则形成的过程中几乎完全征服了她,在她的作品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虽然伍尔芙并不通晓俄语,但非常熟悉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其中她阅读的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多出自好友、著名英国文学翻译家康斯坦斯·哈内特之手,还打算跟后者学习俄语。1921-1922年间,伍尔芙和丈夫一起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片段《斯塔夫罗金的自白》(Stavrogin’s Confessions),并计划翻译陀氏晚年最后的一部小说《卡拉马卓夫兄弟》(因为写作繁忙这项工作最终未完成)。除了俄国文学,伍尔芙还十分关注20世纪初动荡俄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她在自己的日记中提道1905年俄国革命中“四处焚烧房屋,绞杀贵族”的可怕现象,认为“俄国缺少足够的文明来支撑并赢得一场革命”,这一观点与20世纪初英国社会普遍期待俄国国家制度实现全球性变革的愿望相悖。相反,关于1917年彼得堡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伍尔芙在随笔《俄国革命的一种观点》(A View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一文中则断定“在追求自由和摆脱专制暴政方面,俄国革命和法国大大革命一样意义重大”。1925年在一篇随笔《俄罗斯观点》(Russian Point of View)的开篇伍尔芙就谈道“俄罗斯文学逻辑上具有无法解释的神秘性,这一逻辑完全不同于英国人的世界认知、英国人的世界观:‘我们(英国人)经常怀疑和我们具有诸多共性的法国人和美国人是否真的能理解英国文学,而对于我们这些热情洋溢的英国人是否能真的理解俄国文学这一点就会生出更严肃的怀疑来’”。接下来伍尔芙还表达了她通过努力学习俄语、阅读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以及与伦敦的俄国侨民接触而对俄罗斯人的个人理解和看法:俄国人“心灵简朴”,“具有一颗简朴的心灵是俄国文学主人公的最主要特征”。他们“在因痛苦而分裂的世界中善于用整个身心和我们一起理解和同情受难者”。同年(1925)在另一篇随笔《现代小说》(Modern fiction)中伍尔芙进一步确信“有关英国文学最基本的观点都无法避免提及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而已“被自己的物质主义折磨得疲惫不堪的英国人”会在俄国小说中找到“灵魂与心灵领悟的瞬间”,“对人类精神的天然敬畏”,以及“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其中对俄罗斯文学之精神意义和世界影响的激赏溢于言表。
伍尔芙还把俄罗斯文化元素、俄国文学和俄罗斯人身上无法解释的神秘性、诱惑性和吸引力主题嵌入到自己的小说中。早在第一部长篇小说《出海》(The Voyage Out)(1915)中就涉及俄国革命者、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形象:女主人公艾维琳在与雷切尔的对话中提道她朋友的哥哥在莫斯科做生意,她热烈渴望着去“政治阴谋和无政府主义者成堆的俄国”好好体验一番,还转述了她自己听到的“令人激动人心的俄国事件”“西伯利亚流放犯”的故事和沙皇专制政府的残酷。对话的最后一句虽看似轻佻且与对话内容而言无关紧要,但轻蔑语调中却显示出对沙俄帝国的诅咒和谴责:“只要能让推翻俄国政府的革命爆发,我自己可以付出在世界上拥有的一切。这一场革命必定很快就会发生”。
不过,作为文化“他者”的俄国与俄罗斯人的形象集中出现在伍尔芙的《奥兰多:一部传记》(Orlando:a Biography,1928)中。《奥兰多》是一部具有鲜明巴洛克神话风格并带有浪漫主义自传体色彩的小说,记录了主人公奥兰多从16世纪的男性到20世纪的女性的漫长转变过程——完整“双性人格”(雌雄同体)的最终建构,小说对传统男权社会和性别对立政治的讽刺与抨击,印证了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即反对无限夸大女性与男性的差异,强调两性间的包容性和一体性。除了伍尔芙本男女人“雌雄同体”的理想人格意识展示以外,小说《奥兰多》中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充斥着英国人长期以来对俄国和俄罗斯人的历史想象,即对北方遥远的、几乎完全未知的俄罗斯世界的陌生感——关于俄国作为一个拥有广阔土地、童话般财富与可怕严寒的“莫斯科维亚”的地域性认知,以及关于那些“蛮野、残忍、淫荡”的俄罗斯人的文化印象。《奥兰多》中侨居英国的神秘俄国外交使团里的俄罗斯人几乎人人都留着“长长的大胡子”,“穿着不知名的绿毛皮衣裳,喝一种闻所未闻的黑色液体(即格瓦斯)并随意把痰吐在雪地上”,且几乎都沉默寡言。这进一步强化了英国人对异己世界的自然和空间认知:结冰的河流、野性未泯的劣马,积雪覆盖的荒漠、响彻草原的狼嚎,以及对俄罗斯人的“陌生化”印象:俄罗斯人(莫斯科人)淫荡、嗜杀,(男人之间)打斗中相互割破对方的喉管,有着令人好奇的、不可捉摸的脾性。另外在《奥兰多》中伍尔芙还以抒情的笔调塑造了一位如梦似幻的、神话般的狂野俄罗斯女性——萨沙的优美艺术形象:作为奥兰多的热恋情人,萨沙向英国贵族少年奥兰多诉说着一种谜一般令人无法透彻领悟,却如影随形,令人无限向往的深刻“自我”现实,并向后者描绘了河流如大海般广阔,同时又严寒冰封的遥远俄罗斯时空体文化意象。伍尔芙在《奥兰多》中对俄罗斯女性、俄国和俄罗斯人的描述和艺术铺陈充满异国情调和神秘传奇色彩,并不符合俄国的历史事实和真实状况。其中既有对异域俄罗斯女性——“莫斯科女人”的“雄风”最高程度的神化和美化,同时又伴随着英国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时空体和俄罗斯人的刻板印象或历史文化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