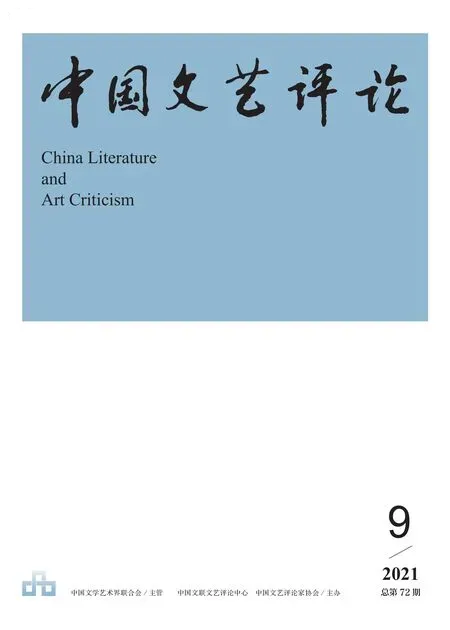大型漆壁画《长城颂》深蕴的百年风华
尚 辉
如果用一幅画作来形象地浓缩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沧桑岁月,那大概没有比映满朝霞的长城最能呈现这一恢弘、壮阔、雄伟的历史意象的了。的确,当人们从《旗帜》《信仰》《伟业》《攻坚》《追梦》这五组群雕环绕的广场,迈进那座巍峨挺拔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建筑时,迎面看到的便是这幅视野广阔、苍松吐翠、云蒸霞蔚的祖国山河画面。巍巍耸立的崇山峻岭辉映着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金色的长城蜿蜒于群峰之间。此作以长城象征中华民族绵长悠久的历史和坚贞勇敢的品格,虽历经沧桑却碧血丹心、雄健壮伟。这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浓缩,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初心永驻的写照。
几乎占据了党史展览馆序厅整整一面墙的漆壁画《长城颂》,以其罕见的尺幅和深邃的意境震撼着每一位走进展馆的观众。其形成的视觉张力既让人们迅速进入一种历史场域,也使人们沉浸其中,仿佛从那巨龙一般的长城意象之中,时刻可以感受到一个伟大的党的诞生与奋斗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刻改变。从艺术史的角度,这同样是刷新历史的一幅巨制,是新时代立足传统而进行创新性探索的民族艺术硕果。
一、新时代中国壁画对民族形象的重塑
隶属于建筑装饰的壁画在古今中外都是绘画艺术的高级形态,甚至远古时代的绘画艺术只有通过壁画才能得以保存而传世。18世纪对意大利庞贝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让古罗马时期的壁画重见天日,庞贝壁画中出现的埃及艺术元素揭示了罗马帝国对埃及征服的历史。中国古代壁画遗存丰厚,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从旧石器时代跨越到明清的阴山岩画、辽阳汉魏墓室壁画、敦煌壁画和永乐宫壁画等。壁画不止具备和附载物及建筑同等的永久性,而且大型石窟、建筑的政治、宗教、文化等功能,也往往决定了装饰其中的壁画所具备的公共性。人们对于人民大会堂的视觉记忆是和装饰在其中的《江山如此多娇》壁画紧密相连的。如果说,由傅抱石、关山月于1959年合作完成的《江山如此多娇》壁画,通过对祖国山河壮丽景致的描绘,展现了新中国社会精神面貌的巨大改变,其巨大的尺寸是对传统山水画的一次刷新;那么,蕴含在画面中的对传统笔墨的现实精神表达则更深刻地体现了一种时代诉求。
《江山如此多娇》所具有的时代标志性是这一时期其他作品所难能具备的。这幅作品的艺术挑战,还在于运用水墨写意来呈现传统金碧山水画所要求的富丽堂皇、雍容大度的庙堂气象。也因此有人曾质疑,认为其不是壁画艺术语言。壁画艺术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末迎来新的转机。众所周知,1979年伴随着首都机场落成而完成的《哪吒闹海》(张仃)、《巴山蜀水》(袁运甫)、《森林之歌》(祝大年)、《科学的春天》(萧惠祥)和《生命的赞歌——欢乐的泼水节》(袁运生)等一批壁画发出了新时期美术思想解放的先声。这些作品不仅描绘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远古神话、民族风情,而且以油彩、丙烯、陶瓷、玻璃和金属等多种材料探索现代壁画自身的表现特征与形式语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刺激了中国壁画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刘秉江、周菱《创造•收获•欢乐》,周令钊、陈若菊《白云黄鹤》,楼家本《江天浩瀚》,侯一民《血肉长城》,叶武林、闫振铎《受难者•反抗者》;乃至新世纪以来袁运甫为中华世纪坛总体设计的《中华千秋颂》,刘斌《百色起义——翻身道情》和孙景波、唐晖、王颖生等绘制的《一代天骄》等,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壁画蓬勃发展的标志性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借用历史题材来承载建筑所具有的纪念意涵,通过各种新材料的运用探索现代壁画在视觉、触感与形象塑造等方面所具备的公共性、恒久性与现代性。
历经岁月沧桑的百年建党历史通过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建筑及其建筑广场的群雕、场馆内的大型壁画而形成一种凝固历史的纪念性公共艺术。党史馆序厅壁画是走进这座建筑营造瞻仰仪式感最具标志性的一幅绘画,容纳这幅壁画的空间是一个进深25米、横长81米、净高24米的挑高横长立方体,其壁画净尺寸高15米、宽40米,壁画总面积达600平方米。这个画幅尺寸远远超过了人民大会堂的《江山如此多娇》(画幅尺寸为高5.5米、宽9米,画幅面积49.5平方米),也略超中华世纪坛的《中华千秋颂》(壁画周长117米、高5米,画幅面积585平方米)。《长城颂》漆壁画作为党史展览馆的第一幅绘画,其空间的挑战决定了壁画题材的选择与表现形式。在为序厅提供的多达数十种设计方案中,既有沿用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样式的山水画(通过水墨、重彩、岩彩、瓷绘等方式绘制),也有沿用中华世纪坛《中华千秋颂》样式的历史叙事(壁画以党史百年重大事件为形象主体,采用各种材料雕刻、拼贴或镶嵌)。但最终选择了程向军的《长城颂》,一方面,包含了《江山如此多娇》的江山、长城等元素;另一方面,汲取了现代壁画艺术语言,使之更具色彩表现的张力及远空间的透视性。也因党史馆广场上五组群雕具有党史百年的历史叙事特征而不必在这一序厅进行重复,才最终选择了以“长城颂”作为画面主题寓意,以进一步阐发中华民族精神与百年建党伟业之间的内在关联,审美的诗性情怀可于此获得升华。在此,更多的历史叙事、更复杂的材料镶嵌,都可能减损对这一序厅的精神营造。从这一角度看,序厅的这一幅《长城颂》漆壁画以及与壁画中朝霞满天色调相呼应的序厅雅安红石地面,是针对党史展览馆这一百年纪念建筑空间最大化的精神提升。伫立在这幅壁画所营造的历史空间里,人们思接千载,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有机地与中华民族精神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更加宽阔而宏伟的精神空间的营造。
作为这个百年纪念空间中的壁画,《长城颂》无疑承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壁画从复兴到繁荣的历史,它虽采用了漆画这种绘画语种,但并不局限于对漆画本体语言的彰显,而是将其成功地转型为壁画,使之更能体现出壁画公共性的视觉要求,从而探索了漆画进行现代大型壁画创作的潜在空间。而在这个百年纪念的时空里,壁画上的主体形象既融会了中国现代壁画史所有相关祖国山河描绘的视觉元素,也充分调动了最具中华文明历史标志性的长城形象,来寓意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血脉相承。尤其是长城形象自中国近代以来不断被赋予英勇不屈、团结奋进、勇往直前的精神意涵,使之早已成为家喻户晓、具有民族集体意识的中华民族伟大意志与力量的象征。这正是伟大的建党精神的形象凝缩。相信伫立在这幅壁画前的每位观众,都会被作品中宏伟的长城形象而激发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坚定的民族自信心和满腔的爱国热情。《长城颂》作品中所深蕴的历史情怀与现实精神,无疑是一个崛起了的中华民族对民族形象与民族艺术的重塑。
二、融山水与风景为一体的多维视角
《长城颂》以北京八达岭长城为原型而进行了形象再度创造。映入观众眼帘的首先是画面左侧四分之三处的烽火台,它虽位于画面左端,却是画面所画长城的制高点。观众正是从这座烽火台入口的石阶梯递进而上展开了对整个画面的远眺。这段阶梯与烽火台,无疑起到了观众视点定位的作用。画面正是从这个烽火台的制高点而将长城蜿蜒推向远方,形成了画面从左下角向上攀升,经过此烽火台而横向向右延展,再向左回折的多重S形曲线。这条曲线既是长城逶迤延伸、守护疆土的主要画面形象,也是在这40米的画幅宽度中将人们的视线极度拉开、却又能不断聚焦的视觉主线。画面是静态的,但这条视线的曲折回环设计却使观众的视线不断发生位移与跳动。富有意味的是,在左侧烽火台这一制高点之外,画面中间的那座烽火台却真正处于画面视觉的最高端,从而又形成了画面的第二个视觉中心,仿佛一曲旋律从画面的左下角开始攀升音阶,在经过左端那个最重要的烽火台的俯瞰之后,再度攀升达到旋律音高的极至。显然,处于中景之中的这座烽火台的画面高度是画家精心加高的,它使画面形成了第二个视觉中心,并以此拉开长城向右边蜿蜒行进的态势。而这第二个视觉中心的设计,也形成了画面金字塔般的视觉稳定性。
显而易见,大型漆壁画《长城颂》并非只有一个视平线。这是画家在考量了这幅壁画被设置在一个浅进深的观赏空间后为画作进行的一种独特设计。和人们可以在人民大会堂通往宴会厅的大扶梯的远处不断走近《江山如此多娇》的观赏距离不同,以党史展览馆序厅只有25米的进深来观赏远大于这个进深的40米宽的壁画,无疑是远远不够的。这意味着从党史馆前门三个主入口进入序厅时,只能看到这幅壁画的局部,厅内几乎没有一个纵深距离能够正面完整地观赏其全貌。因而,壁画的设计必须满足站在序厅的每个不同位置,观者都能获得相对完整的观赏效果的要求。这幅壁画的重要艺术特征便是将风景油画的焦点透视和中国传统卷轴画的移动透视有机融合,从而取得了远观具有风景油画的焦点透视性,而卷轴画的多点透视又满足了局部观赏的要求。
从整体看,画面的视平线定在了天际与峰峦的交界处,画面由此以俯瞰的视角展开霞光满天、云海浩渺、千峰潮涌的恢弘场景。左端近景烽火台的光影化体面塑造,明确了旭日东升的光色时间。画面虽宽阔无比,却因统一光源的色调处理及整体焦点透视的聚焦性而给人以风景油画的审美感受。从局部看,画面的视平线在发生着巧妙的位移。居于画面中间占据制高点的中景烽火台的视平线,显然已高于左侧近景烽火台的主体形象,而真正的画面统一视平线则在中景烽火台的更高端处,即前面所
述的天际与峰峦的交界处。而当我们接近于人站立高度的视平线时,看到的则是近景的松柏流泉,画面并不因其在画面底端的收口而减弱其描绘的精度,相反,这个拉得最低的视平线给了我们最真实、最细微的观赏角度。可以说,作品从上而下不断移位的视平线给观众提供了在不同距离、不同位置的观赏窗口,甚至于画面在纵向构图上也能够满足我们局部截景的拍照要求,使每个截景都能具备相对完美的景物配置与饱满构图。

图1 漆壁画《长城颂》局部
从更深的角度看,风景与山水的结合不止是焦点透视与多点透视的多维视线组合,也是中西不同文化观念在此作中形成的某种共融性。巴洛克时代古典主义的风景画看似是对自然时空的再现,但实际上是通过对历史遗迹的探寻来表达历史与现实的某种关系。因而,古典主义的风景画在某种意义上是理想风景画,是展示物质世界、理性和神话的一种相似性建构,是对神圣、恢弘和崇高人文精神的追求。从这个角度看,《长城颂》也没有停留在对山川自然美的一种再现,而是通过长城的蜿蜒不绝、敌楼的巍然耸立、烽火台的岁月沧桑来表达一种历史情怀,这便赋予了《长城颂》主题风景甚至是历史风景以美学深意。也因此,画面营造的境界就不是传统山水画的幽深、静谧、淡远,而是浓缩了中华民族百年来奋斗崛起的一种精神,她是如此壮阔、浓烈、响亮、宏远、鲜明、激越和豪迈,这种精神意象才是此作从人们心底点燃的一种民族自信。这种历史的风景,也决定了此作不再停留于写实再现。画作虽以八达岭长城为原型,但在八达岭的任何一个角度都找不到这样的景致。画作无疑借鉴了中国山水画的表现方法,从朝霞、云海、古松、溪流这些景观的理想化程度来看,画面都进行了像中国山水画那样的主观化的迁想与营造,尤其是云海的处理制造出画面的蓬勃气韵,使得那些崇山峻岭如潮水一样地涌动,山石因云烟而诡谲变幻,生机无限。虚实幻化,正是中国山水画以内观而获得的一种精神表现,这是一种更为磅礴、更为超脱,也更具宇宙灵性的一种道法自然。从山水画的角度,大型漆壁画《长城颂》呈现的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物我合一的精神观照。

图2 漆壁画《长城颂》局部
三、漆语的绘画性探索
《长城颂》的绘画体裁既不是水墨、重彩,也不是油画、瓷画,而是漆画。几乎和中华文明历史同样久远的漆艺,可谓承载了中国文化玄妙幽远的美学深意。虽然中国漆绘历史悠久,但作为一种绘画形态,漆画的独立却发生在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之中。由漆艺转换为现代造型艺术,漆画所要解决的不仅是如何将现代绘画观念融入传统漆艺的命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继承传统漆艺的基础上对漆画自身艺术语言特征的现代性探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前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就是中国现代漆画诞生的母地,雷圭元、乔十光等都是中国现代漆画开宗立派的艺术大家,而《长城颂》的作者程向军就是他们的后继者,他们对漆画现代性的探索形成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递进局面。
由漆树流出的浮汁所形成的大漆呈褐色稠液状,黑、红、褐是大漆的基本色。因而,凡属漆艺漆绘,大都由这三种基色构成,而漆画的镶嵌技艺,则产生了由贝、钿、珠、石、金等镶嵌材料生成的瑰丽色彩与肌理质感。漆画的基底大都由布、麻、木等构成,基底色彩一般均为黑色或深褐色。现代漆画要解决浅颜色的配置难题,常常使用铝粉、银粉、金银箔或蛋壳镶嵌予以解决。漆屏风是介于漆艺与漆绘之间的一种艺术,而漆壁画则是远远大于漆屏风,更能彰显漆画特征的一种绘画。因漆画的漆性语言大多要通过漆皱、漆磨、漆料来达到漆的色彩幻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漆画所能绘制的最大尺寸,而以木、布、麻等为胎底的漆画,如何保证画底尺寸在放大后不变形,也同样具有相应的尺寸限制。因而,漆壁画几乎不可能逾越一定的尺幅。唐小禾、程犁于1987年为荆州博物馆制作的漆壁画《火中凤凰》,由61块1.44平方米的漆板组成,总幅面达到90平方米(高3.6米,宽24米),这个数据曾经一直是漆壁画画幅尺寸的最高纪录。
从漆画艺术语言来说,《长城颂》满幅的正红色使用恰恰充分发挥了大漆本色的色彩语言特征,而松柏的黑色、长城与山岩坚实的造型等也都有黑色铺底作埋色,红、黑在此均体现了漆本色幽暗、浑朴、纯正的漆色质地。的确,《长城颂》虽借鉴了油画风景有关光色感的表达,但因发挥漆绘色彩语言而使这种油性的光色舍去了冷色的运用,而偏向固有色相或主观色相的中国传统色彩观念表达。甚至为了强化这种中国色彩观念,画面完全限制在正红、黝黑、铅白、金黄四色里,并不追求油画光色那种复色或补色的变化。画家凸显的就是这四种色彩的纯正感,让正红与铅白、金黄与黝黑之间拉开距离,形成明快、热烈、厚重、喜庆等中国化的色彩意蕴。此作尤其是在铅白的运用上形成了对漆画语言的突破。如果按照一般漆画语言规则,画面上出现的几乎占据了画幅面积四分之一的云海,只能采用银粉加铝粉来不断提亮,使云层的变化随着粉质颗粒铺垫的厚薄产生肌理的起伏,但即便如此,此作的整体亮度仍会显得幽暗,这或许是作者和观众不愿看到的结果。或者说,此作的标志性位置与主题内容都需要提高画面整体的鲜亮程度。这无疑是漆壁画的公共性要求而使作者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当然,就整体调性而言,云层的白色仍然泛出微微的米色,即便最白的地方依然通过漆的罩染而形成温润古朴的宝光,这正是漆画独特的色彩魅力。
有关漆语的独特性,无疑是通过漆料的预埋、多种材料的镶嵌,乃至特殊区位制造的漆皱再不断磨光而获得的一种釉变似的色彩效果。在此方面程向军有着较高的艺术修养和创作经验,具有他个人漆画艺术特征的作品,大多也是通过这些漆画本体语言来进行抽象绘画的探索的。但在《长城颂》这件大型漆壁画的创作中,他更考虑到西晒阳光的直射可能给光洁的漆画造成不必要的反射,而追求漆皱或各种预埋色料也可能造成整体形象的破坏。在此作中,他更多选择的是手绘漆自由绘画的绘画性,也即当代漆画界一直探讨的漆画姓“漆”还是姓“画”的问题。因过多追求漆画所谓的镶嵌、填料、磨变、推光,可能导致漆画工艺特征的增强而减损了漆画的绘画性;反过来,如果一味向油画、版画靠拢,也可能因此失去漆画自身的漆语特征。显然,在漆画姓“漆”还是姓“画”的问题上,始终存在创作实践与对漆画艺术语言理解的“度”的把握问题。《长城颂》漆壁画的超大面积在实操中很难做到不断打磨、不断髹漆的工艺。在600平方米的幅面上,要反复通过打磨和髹漆而仍能做到光洁平整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反倒促使画家去追求漆画的绘画性,甚至细微处尚留存漆绘时的笔触,如岩石体面的勾画,在受光面呈现的富有力度的笔触;如松针的层层叠加,笔线的挺拔柔韧;如烽火台与城墙的塑造,笔触堆塑呈现的斑驳沧桑;等等。这些细节都不是通过漆工艺做出来的,相反,这些绘画语言反而增加了漆壁画的灵动、鲜活和自由。
这幅超大型的漆壁画采用什么样的胎底是至关重要的。不论木胎还是布胎,可能都难以实现其丝毫不差对接拼缝的精准度,也都难以实现其不变形、抗冲击的恒久性,这的确是对大型漆壁画的一次全新的高难度挑战。而主创者最终选择蜂窝铝板作为这幅大型漆壁画的胎底,在此基底上进行打磨喷料,这已是对漆画绘制与创作的颠覆性挑战了。对于这样的挑战,还有什么样的新的漆画艺术语言是不能尝试与运用的呢?
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从党史馆广场四周那由数以百计人物群像筑就的汉白玉雕刻中,我们可以时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而当走进序厅,伫立在这幅气势撼人的漆壁画《长城颂》面前,我们仿佛找到了这一切伟大的根源,这就是悠久璀璨的中华文明历史和坚贞勇敢的中华民族精神。而站立在建党百年的历史端口,我们瞭望到的便是画面所描绘的这番旭日东升、百年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