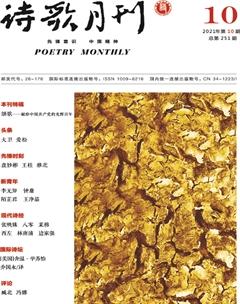主编荐语
记得去年8月,我受《草原》杂志之邀,为获奖者大卫写授奖词时,認真通读了他的近百首诗歌和他那组获奖诗。后来,我是这样写的颁奖词:从大卫的诗里,我们能感受到西方诗歌美学给予他的智慧诗学的文本书写,智性表达是他诗歌有别于他人作品的根本所在,其诗辨识度较高,有自己的诗歌叙述语境和系统,“大卫智性诗体”业已形成。时过一年,当他的新作又一次进入我的眼帘时,我再次被他的智性化表达所折服。比如,数字在诗歌里的表达,弄不好就会由于数字本身的枯燥而让诗失去灵性,而大卫就敢在他的诗里多次用数字乃至数学公式来进行诗歌的异化处理。他写出:“亲,我爱你腹部的十万亩玫瑰/也爱你舌尖上小剂量的毒”,“承受它一公斤的孤独/承受它3+2等于4的光芒”,如此等等。这次新作也有“青蛙写一遍,蝌蚪写两遍”“用一千遍写田野/用一千零一遍写田野之外”“喜鹊写八百遍与写一千遍是一样的/唯有布谷值得写一万遍”,有诗评家说他的诗风受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影响。我看不是这样,大卫有自己的表达。他喜欢用动词,比如“仿佛鸟鸣在荷叶上打了一个趔趄/但这鸟鸣,又不顺着荷叶边掉下来”“梅子将身子洗干净了,坐在酒里”“我所爱:马蹄踏翻草原,野花扑面而来,我与命运互欠一个趔趄——谁低于尘埃,谁就是大海……”,“你把我抽空了/旷野才叫旷野”。这些,特朗斯特罗姆不会想到或写出的,它是属于大卫的专利。
爱松是三栖作家。在诗歌、小说、散文的交响乐里奏出不同凡响的曲子。一曲《江水谣》是他的华丽变音,他把诗向短句进行制造,把诗的内核朝揭示灵魂真相里去精雕细镂。《江水谣》在我眼里可以是云南众多江河中的一条,也可以是西南斑斓文化的多层面的诗描绘,或是对西南多民族人们精神图像的诗解密和诗阐释。这组诗的外形为珠链式,一颗颗晶莹之珠,串起来之后形成一个精致的诗珠链。当你抚摸和细读每首诗时,它会给你一个难以描摹的侧面,这个侧面是关注西南的,这个侧面是西南的山水、人文及精神的最好的侧面呈现。爱松的取舍和裁剪是用心的,又是独具慧眼的。《江水谣》也可以当成小长诗来读,它有长诗的气象和内质。秋夜掩卷之时,你会为爱松多角度、多侧面地成功书写一个宏大主题而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