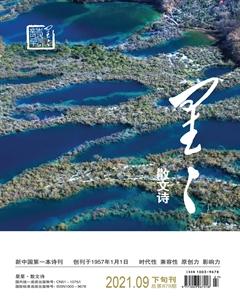白海螺(节选)
2021-10-30 02:27诺布朗杰
星星·散文诗 2021年9期
诺布朗杰
22
冷。我需要枕梦取暖。
我还要把没流完的那些眼泪带进梦里。
在梦里,死去的人全部活过来。我一个个地辨认他们。
我肯定一下子就能认出夺我眼泪的人,却无法把他们带出梦外。
我知道:我活着,就是他们活着。
23
我的世界,音量不多,得有一枚白海螺维持声音的秩序。
能把谎言都说得振聋发聩,大音还能希什么声?
你看,那群大谈觉悟的人,左手刚放下屠刀,右手又拿起枪。
26
天空是月亮的故乡。
我们的故乡在哪里?
蘸着月光的夜色在狗吠中,有了声音。
我还没有睡去。
我在寻找那个有白海螺之声的故乡。
是啊!故乡是永远的沉默者。当谎言在人群中传开,语言将毫无意义。
该说一句方言了。我怕时间久了,我们成为一群群会说话的哑巴。
28
半夜醒来。
我好像在黑纸上写着白字。
我写出满天星辰,它们忘记发光。
我写出凝固的河流;我写出行走的路;我写出移动的大地。
我写出白海螺,这白发如雪的忧伤。
29
历史是识字人的历史,还是一群群人的历史?
为什么我翻遍古籍都没有找到我要找的那些人?
我眼泪里活着的人,不多。
我敬仰过的人,不多。
让我内疚的人,不多。
我在写那些不多的人。没有人愿意煞费苦心去书写他们。我要把这些漏掉的人,一个个找出来。
我也要让白海螺聽见,我的声音。
猜你喜欢
少年博览(阅读与写作)(2021年8期)2021-09-08
红蜻蜓(2021年8期)2021-08-23
阅读(低年级)(2021年6期)2021-08-09
中学生百科·大语文(2020年4期)2020-01-13
作文大王·低年级(2019年9期)2019-10-11
初中生世界·八年级(2019年8期)2019-08-29
故事作文·高年级(2019年2期)2019-02-24
智慧与创想(2013年7期)2013-11-18
小猕猴智力画刊(2013年2期)2013-03-15
中学英语之友·中(2008年11期)2008-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