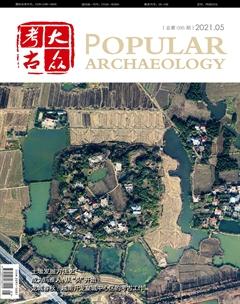宕昌县博物馆藏“十八年属邦”铜戈
茹实
宕昌县博物馆藏战国时期铭文铜戈出土于甘肃宕昌县新城子乡烽火台遗址,系群众挖土造田时发现,1991年由宕昌县文化馆从村民手中征集入馆。戈通长25.9厘米,援长12.1厘米,寬2.9厘米,内宽2.4厘米,阑长12.1厘米。援狭长上扬;中胡三穿,穿呈半圆形孔,穿径0.3厘米;内呈长方形,正中有一穿。援、内、胡均开刃。内正面竖刻3行15字铭文。此戈被定为战国时期器物,名为“铭文铜戈”。
时代与命名
从器形上看,此戈援狭长上扬,中胡三穿,援、内、胡均开刃,这种形制的戈多与矛配在一起作为复合兵器戟来使用。它与秦兵马俑坑和四川青川出土的三年吕不韦戟、四年吕不韦戟、五年吕不韦戟、七年吕不韦戟、九年吕不韦戟上所配的戈,以及1957年长沙出土四年相邦吕不韦戈,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由太原电解铜厂回收的秦王政五年“少府”戈,1978年宝鸡发现的八年吕不韦戈,1978年宝鸡出土二十六年铜戈等的形制基本相同。这种援部细长上扬、三边开刃、中胡三穿的铜戈,整体造型更注重铜戈的杀伤力和实用性,当属战国中晚期兵器。
经辨识,这件铜戈所刻铭文为:“十八年,属邦买之造,库绵,工奭。弟卅 五。”其中最后两字磨损严重,结合残存痕迹及其之前的“弟”字进行辨认,似乎为“卅五”二字,应为戈的编号。铭文整体结构整齐,形体趋于方正,刻痕较浅,笔划细如发丝,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秦国小篆,其字体与前述诸戈极为相似。依照青铜器定名惯例,若器物有铭文时一般要参考铭文内容而定,因此,此戈可被定名为“十八年属邦铜戈”。但“十八年”又是哪一年呢?
据《史记·秦本纪》和《史记·六国年表》,战国时期秦国在位十八年以上的国君分别是厉公、献公、孝公、惠文王、昭襄王和秦王政。秦厉公在位时间为战国初期,秦献公在位时间在战国中期,二者皆可排除。秦惠文王在位27年,但于十四年(公元前324年)更为元年,实际分两个阶段即前元14年和后元13年,故不存在“秦惠文王十八年”,也可排除。这样,这件铜戈铭文“十八年”所指秦国国君就只能考虑秦孝公、秦昭襄王和秦王政三位了。
从出土的战国时期兵器铭文可以看出,秦国在兵器制造过程中实行的是监、主、造三级负责制,此制度称作“物勒工名”。《吕氏春秋·孟冬纪第十》记载:“工师效功……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出于战争的需要,列国都希望在兵器上能够有优势,因此对兵器的生产非常重视。战国时期各国的铜器铸造都有制造者和督造者的信息,至于其起源,学术界存在着源于三晋和秦的争论,但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制度是战国时期法家提倡强兵的手段之一。可以肯定的是,秦国是在商鞅变法之后使这一制度趋于成熟并执行得更为严苛。考古发现表明,商鞅变法前秦国的刻铭器物有“秦子戈”“秦子镈”“秦公簋”“秦公钟”“秦公镈”等,行文风格与商、周、春秋时期铜器铭文基本相同,着重突出器物的所有者。秦孝公启用商鞅后,这一现象得到了改变。从见于著录的两件孝公时期刻铭兵器看,商鞅镦铭文为:“十六年,大良造鞅之造,雍,矛”(《双剑誃吉金图录》),商鞅戟铭文为:“……年,大良造鞅之造戟”(《三代吉金文存》),铭文中包含了器物的制造年代、监造者姓名、制造地和器物名称,而不再出现所有者的名字。袁仲一先生在《秦中央督造的兵器刻辞综述》一文中将这一时期称为秦国“物勒工名”制度的初创期,之后在惠文王到昭襄王时期进一步完善,至嬴政时代,勒名制度更加规范。宕昌县博物馆藏铭文铜戈上刻铭的体例和时代风格均不符合孝公时期兵器的特征,故排除该戈为孝公时期所造之器的可能性。
惠文王到昭襄王时期,秦国的“物勒工名”制度进一步完善,从考古发现和见于著录的秦国兵器和杂器刻辞来看,这一时期的铭文不仅有制造年代、监造者姓名、制造地和器物名称,还增加了工师、工匠的姓名。如见于著录的相邦冉戈铭文为:“二十一年,相邦冉造,雍工層(师)叶,雍,宩德。”(《双剑誃吉金图录》)“相邦冉”,即昭襄王时期的秦相魏冉。袁仲一先生在《秦中央督造的兵器刻辞综述》一文中仔细分析了见于著录和已发表的秦中央督造的兵器及杂器刻辞后认为,从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到昭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86年)的兵器,主造者为雍工师、栎阳工师和咸阳工师。即在雍、栎阳、咸阳等地设有工官,主管兵器制造作坊的生产事宜。而在秦王政时代主管兵器制造的中央官署机构见于铭文者有少府工室、寺工、属邦工(室)、诏吏等。宕昌县博物馆藏铭文铜戈铭文中有“属邦”二字,可见为秦王政时期之物。
综上可知,此戈的生产机构是“属邦”,长官叫“买”,制戈的工匠叫“奭”。无独有偶,1978年在宝鸡发现了一件八年吕不韦戈,戈内正面刻有“八年相邦吕不韦造,诏事图丞蕺,工奭”15字,背面铸“诏事”二字,为横书,又刻“属邦”二字。仔细比对二戈铭文中的相同文字,其结构、运笔极为相近,很有可能为同一机构的同一工匠“奭”所制造。八年吕不韦戈中的“八年”指的是秦王政在位的第八年,当时吕不韦任丞相,因而有其名。宕昌这件戈刻有“十八年属邦买之造”等字,应当是秦王政十八年(公元前229年)制造的,此时吕不韦已死,秦国不再设相邦,所以此戈上就不刻“相邦某某”了。
在刻铭制度上,大体可分为省者(督造者)、主者、造者三级。袁仲一先生在《秦中央督造的兵器刻辞综述》一文中对秦国各时期中央督造兵器的刻辞体例特征总结的极为精准:“在省者这一级,秦国在孝公时是‘大良造鞅之造,以后是相邦(或丞相)某‘之造或‘造。……在主者这一级,秦孝公时期的兵器刻辞不见主者。惠文王至昭襄王时为‘某地工师,‘工大人,始皇时代为‘寺工某(或少府工室某、诏吏某、属邦工[室]某)、‘丞某……在造者这一级,秦孝公时不见造者,以后有造者曰‘工某。”宕昌县博物馆藏铭文铜戈,省者名“买”,主者为“属邦”,造者名“奭”,其刻辞体例符合秦王政时期的特征。
属邦
关于“属邦”,文献记载不多。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中有一则涉及“属邦”的律文:“道官相输隶臣、妾、收人,必署其已禀年日月,受衣未受,有妻毋(无)有。受者以律续食衣之。属邦。”《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由此可知,“道”指的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秦设道,汉承秦制,根据简文内容可知,“道”属于属邦的职权管辖范围,“属邦”应与少数民族有关。
关于秦属邦的设立和职权范围,已有诸多学者做过专门研究。如孙言诚先生在《秦汉的属邦和属国》中认为,属邦是秦国专门设立的一个管理少数民族降者的机构,拥有军队和包括铸造兵器作坊在内的各类生产机构,其职权范围和汉初的属国是一样的。祝中熹先生在《嬴秦对汉渭文化圈的历史影响》中以为,出土秦简中所见的“臣邦”“属邦”,都是与嬴秦相邻的少数民族共同体的统称,其管理权各由其首领行使,只需向秦中央缴纳赋税即可,其首领由秦君授予某种爵号。日本学者工藤元男在《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属邦律及其相关问题》中认为,秦在征服临近地区的少数民族后,在其地设郡,并在其内部设臣邦(属邦),这二者便构成了道。陈力先生在《试论秦国之“属邦”与“臣邦”》中认为属邦是典属邦管辖下的少数民族内属国。刘瑞先生在《秦“属邦”、“臣邦”与“典属国”》中认为秦所设立的属邦是中央管理民族事务的最高机构,是唯一的,不同于汉代所设的若干“属国”。这里更倾向于最后一种观点。
从秦兵器中“属邦”铭文和秦封泥中“属邦工室”“属邦工丞”等文字来看,属邦下设有制作兵器的工室。如果属邦的性质形同属国,在归降少数民族地区制作兵器,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于情于理是说不通的;但若是作为专门负责民族事务的管理机构,其下设工室为秦国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可谓合情合理。
库绵
“库”即武库,是指官府收藏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专门场所。战国时期,兵器对于国家至关重要,因此,对于兵器的生产、保管,有着极为严格的管理制度,秦国尤为如此。“绵”应指绵诸道。“库绵”指的就是设在绵诸道的兵器库。
关于绵诸道,最早明确见于记载的是《汉书·地理志》,属天水郡,至于其始置时间却未提及。徐日辉在《古代西北民族“绵诸”考》中指出:绵诸,《山海经》曰“居繇”,《史记》称“绵诸”“繇诸”“繇”,《汉书》谓“绵诸”“繇叙”,《魏略》作“属繇”,被认为是西方东迁入陇之族,属西戎诸部之一。《史记·匈奴列传》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方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由此可知西戎活动范围在陇山以西,徐日辉、雍际春等先生认为其活动中心主要在今天水一带,其地紧邻秦早期立脚的秦邑及犬丘,曾经强盛一时。从相关记载看,绵诸戎与秦的关系时好时坏,时降时叛。《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厉公)六年,义渠来赂,绵诸乞援。”可知在秦厉公六年(公元前471年)左右,绵诸戎是臣服于秦的。而《史记·六国年表》又云:“(秦厉公)二十年,公将师与绵诸战。”可知从秦厉公六年到秦厉公二十年(公元前457年),仅仅14年的时间内,绵诸戎与秦的关系就由臣服变成了交恶。《史记·六国年表》又记载:“(秦惠公)五年,伐绵诸。”此后再未见关于绵诸的记载,绵诸戎应该就是亡于秦惠公五年(公元前395年)的这次征伐,之后秦置绵诸道,以便管理当地戎族遗民。
秦王政时期,统一天下的战争迫在眉睫,秦国中央政府对于军事用器的制造、发放及保管制度更为严苛,秦律规定“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书之。其叚(假)百姓甲兵,必书其久,受之以久。入叚(假)而而毋(无)久及非其官之久也,皆没入公;以赍律责之”(《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工律》)。兵器上不仅铭刻器物的制造时间、督造者、制造者、编号,甚至发放之所在也铭刻得一清二楚。宕昌出土的这件秦王政十八年属邦铜戈,就是由中央少数民族管理机构属邦工室制造,拨交至绵诸道兵器库中的一件兵器。
本文中铜戈的照片及相关基础资料由宕昌县博物馆杨志洁先生提供,在此特别致谢。
(作者为甘肃省博物馆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