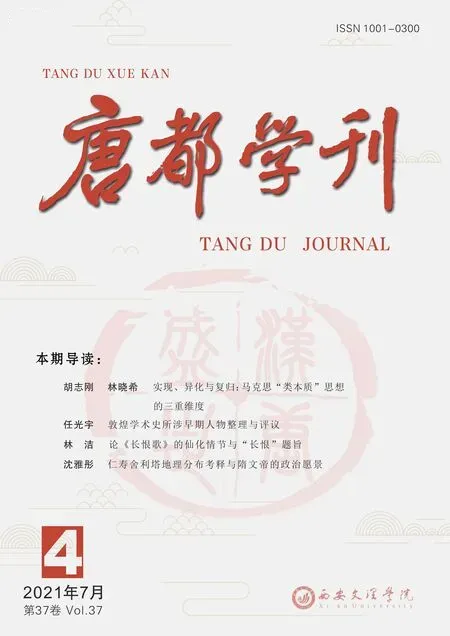《史记》三家注中的天文书写
李小成
(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院,西安 710065)
“史记学”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经过历代学人的不懈努力,研究范围不断扩展,由训诂到评点,进而考证,并及于历史、文学、思想、文化等领域。而对《史记》注的研究,基于历史上学人们公认最好的注本: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家注反映了从南朝到唐这一历史时期人们对《史记》的研究成果,从接受史的角度来说,这种方式也是“史记学”研究之一种。三家注中涉及的问题很多,天文学是其中很有特色的一个方面,它不只是及于《天官书》,于《史记》天文各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史记》之有《天官书》,且司马迁所任之太史令,其职责之一就是观天象而制历法,进而影响到三家注亦重视天文星象。天文星象不仅仅是记录天气和星象变化,它也是人们对宇宙天体的认知与探索,更是在天人感应思想导引下,被认为是上天意志的一种昭示。天文星象的变化预兆着上天对人们的警示或者祥瑞。对于帝王来说,天文星象更是意味着王权的更替和王朝的兴衰。所以,我国自古对于天文星象的记录颇多。这些天象的记载亦反映了一个时代人们对大自然的理解和认识程度。司马迁以太史令的身份,本着实录精神,在其《天官书》中记载了天象之运转,兼及社会人事的变化。这些内容对于当时天文星象的研究也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价值和意义,而裴骃、司马贞和张守节三家在《史记》的注释中,亦有诸多地方涉及到对天文星象的自我理解。
一、《史记》三家注的天文学史料
《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等都有不同程度天文学方面的记载,而《天官书》则是汉代天文学的专著,它是秦汉乃至先秦天文学最全面、最系统的权威文献,是对天文星象的专门介绍、集中记录和详细解说,保存并展现了中国远古时代到我国秦汉时期天文星象的现象和人文见解。《天官书》所记恒星有五百多颗,此外还有行星、分野、日月占候、奇异天象、岁星纪年和占验等内容。《史记》所列《天官书》体例,开后代史书“天文志”之先,此后“二十四史”秉承传统,皆有天文志。而三家注作为现存最完整的《史记》注解,对于天文学的释解也散见于各个篇目,其中最多的注解也是出现在《天官书》中,这部分注解最为翔实,对天文学方面的解说最为充分。三家注之天文方面的研究也集中于此。
首先,三家注天文星象基本概况。三家注对于《天官书》的解说基本上是基于南北朝和唐朝的天文研究和新的天文现象的发现,也有一部分通过先秦和汉代的其他文献,对文中出现的天文星象进行注解。例如《正义》里面引用了南北朝末期顾野编的地方志《舆地志》、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北魏地理学家阚殷的《十三州志》等等,主要利用南北朝的文献对《史记》中的天文星象作材料征引性解释。《集解》在注解中引用孔安国、郑玄之言、文颖之语、孟康之文等,作天文注释的材料比较多。《索隐》里面主要征引徐广、宋均、《尔雅》《元命苞》(1)《元命苞》,又称《春秋元命苞》,“春秋纬”之一种,其书已佚,今仅存遗编残图。它是西汉末的一部纬书,是纬书的代表作。纬书是西汉末假托经义而言符瑞应之书,纬即假托神意解释经典。《洪范五行传》等材料,相对来说,征引纬书的材料较多,文献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年代跨度较大。三家注对于《史记》中天文星象的注解立足于不同朝代的文献,各有侧重又博采众长,可以说是旁征博引,翔实充分。
其次,三家注天文星象的基本理念。《史记》中对于天文的记录尤其是星象,以相互映衬而又彼此分离的处理手段散见于各个篇目,但不同程度都体现了天人感应或阴阳五行的思想。从而一方面将中国上古以来的星占学理论基础加以承袭强化而达到鉴古知今、服务政治教化目的;另一方面则通过大量 “日食”“星陨”等天文灾变信息,反映各朝各代相关的经传德行与思想教化内容。而三家注也在一定程度顺应了司马迁这一理念,对于其中天文星象的解释也是多围绕在天人感应学说下侧重于这些现象的象征意义。其中的象征意义也是围绕君权、君臣、君民这几个意象,星云的变化往往昭示着君权的正统意义、君臣的相处之道以及民众的生活现状和未来发展。例如,具有非凡历史人物的出生,往往伴随着奇异的、非同寻常的天象。如颛顼出生之时,“瑶光如蜺贯月,正白,感女枢于幽房之宫”[1]11;大禹出生之时,则“父鲧妻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1]49。另外,二十八星宿各有独特含义,代表着不同的事物;每个星宿包含许多恒星,而含义各不相同。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民间说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是谓东、南、西、北四宫,各宫以动物之形比拟,并附会以吉凶祸福,天上人间,彼此贯通。这些注解也是将天文星象看成了上天不同寻常的预示或者提醒,每个星系代表着不同的事物,而事物的变化与其星系相匹配。这些注解从本质上来讲是受制于那个时代的认知和政权体系的束缚,亦在很大程度上承续了天人感应的一系列理念,对于天象的理解具有政治化、功利化、世俗化的趋向,而具有这些意义的解释在三家注对天文星象的注解中占据了很大比重。
三家注中对天文星象的解释虽然大部分顺应了“天人感应”学说,但其中还有一部分内容是基于后代人们对于天文星象的进一步了解,是对天文星象的进一步阐释。《史记》本身自成完整的星宿体系,三家注在《史记》星宿体系的基础上对天文星象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例如对于星象相互位置的标明以及对于星系的研究,这些都属于后代对于天文星象的进一步发现和研究。这一类的注释虽然在三家注中占比不大,但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代表了我国天文星象不断发展的历程和古人坚持不断的探索,是我国天文学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进步的标志,代表了古人对天象探索的历史成果,这对研究我国的天文学发展过程具有史料意义。
再次,三家注征引资料丰富。注释中涉及的人名、书名很多,三家注中引“某某人曰”者甚多,且多为两汉六朝学者(见表1)。《集解》多引孟康、晋灼之言,《正义》《索隐》所引之书相当一部分是纬书。纬书并非伪书,虽是假托圣人之言,但毕竟是两汉人著作,徐兴无认为它是“新儒学”:“谶纬文献的全部完成,也以两汉经学的建立为前提”[2]。人们一直认为纬书是经学的附庸。三家注注释中既有训诂,如《天官书》“平城之围”,《索隐》云:“汉高祖之七年”[1]1348。亦有校勘,如《索隐》:“徐广云:一云‘哀乌’。案:《汉书》作‘哀乌’。”[1]1300《索隐》多引《诗》,注《天官书》“曰口舌”,《索隐》则云:“《诗》云‘维南有箕,载翕其舌’。又《诗纬》云‘箕为天口,主出气’。是箕有舌,象谗言。《诗》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谓有敖客行谒请之也”[1]1298。还有既为之注音者,又为之训诂者,如《索隐》:“句,音钩。句,曲也”[1]11290。

表1 三家注征引天文星象资料统计
三家注的有些注释具有考据的性质,并在列出诸家解释的基础上,提出注者的立场。如《天官书》“日月晕适”,《集解》云:“徐广曰:‘适者,灾变咎征也。’李斐曰:‘适,见灾于天。刘向以为日、月蚀及星逆行,非太平制常。自周以来,人事多乱,故天文应之遂变耳。’骃案:孟康曰‘晕,日旁气也。适,日之将食,先有黑气之变’”[1]1351。总之,三家注在释解文本时,运用了很多训诂之法,且灵活多变。
三家注所注天文知识,既有严谨求实的精神,又有预知人间之兆。如《天官书》中的“末兑,进而东南,三月生彗星”。《正义》曰:“天彗者,一名埽星,本类星,末类彗,小者数寸长,长或竟天,而体无光,假日之光,故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若日南北,皆随日光而指。光芒所及为灾变,见则兵起;除旧布新,彗所指之处弱也。”[1]1317三家注中的天文星象预兆,乃基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学,人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实践,将天象与人事相勾连,进而将其发展为星占说,这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另一种体现,也展示了古人对天文学不断探索的历史成果,积累了关于天文学的重要史料。
二、《史记》三家注所释天象与天人感应的密切联系
我国自古以来就崇拜自然神,天与神对一个政权的确立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上古王朝更替中,刚掌政权者急需一种有效而快速的方法使四方臣服,以巩固自己政权的统治地位,而依托神灵与上天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史记》的记事就贯穿着这种思想,三家注对天文学的释解中,有相当多的内容都是有关于天人感应的理念。在古人看来,天文星象与人事社会存在密切的联系,星象的明、暗、薄、厚等现象,也预示着人事的吉凶祸福。《三国演义》中说诸葛亮观天象而知命不久矣,司马懿观天象,亦知孔明危在旦夕,这种观天知命之术,在历代典籍中记载很多。农耕社会的人们,每事多与自然相关,尤其天气的变化,久而久之,就产生了一种天人观念。
其一,天人感应影响下天象的象征意义。天文星象有其特有的象征意义,有些天文星象的象征意义是固定的,基本上是不变的。有些星象代表了固定的方位意义,例如《史记·正义》:“荧惑、鸟衡,皆南方之星,故吴、楚之占候也。鸟衡,柳星也。……辰星、虚、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齐占候也。宋、郑之疆,候在岁星,占于房、心。……岁星、房、心,皆东方之星,故宋、郑占候也。晋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参罚。……辰星、参、罚,皆北方西方之星,故晋占候也”[1]1346-1347。这些星象代表了固定的方位,意为这块疆土乃上天所赐,为其统治提供了合法与合理性,以天人对应的理念,从固定的方位象征而为其政治军事行动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为其军事行动提供了合理的理由。有些星象则代表了固定的政治地位,例如:“心之大星,天王也。前星,太子;后星,庶子”[3]。这些星象的象征更接近于天人感应的另外一种延伸的说法“君权神授”。史书上这一类星象记录的终极目的也是为了政治的合理化服务,星象本身不为任何政治势力而存在,它并不具有某一类政治意味,是人们赋予了它另类的意象,在长期生活中将它固化,代表了固定的祥瑞或灾祸象征,甚至将其做了审美化的处理。还有主寿命之星,用其固定的象征意义为政治服务,为其永久统治寻找合法性,或依据政治所赋予的特殊意义来对别国政治进行相应的约束。
三家注中还有一部分天文星象的象征意义是不固定的,不同的天文星象代表了同一个意象。例如三家注中对于代表寿命的星象就有三种。《史记·天官书》正义云:“长沙一星在轸中,主寿命。占,明,主长寿,子孙昌也。”[1]1304《史记·封禅书》索隐云:“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集解:“角、亢在辰为寿星。”[1]1376《尔雅·释天》:“寿星,角亢也。”[4]不同的星象代表着同一意象,这是由于人们受制于天文学的发展程度,所以对天文学的认知不统一,而且也说明了不同的年代对天文星象认识的不断发展和对其象征意义认识的不断变化。三家注中还有同一天文星象代表不同的意义,例如说白虹贯日,现代人对其认知是一种自然现象,指的是白色的长虹穿日而过,而“虹”其实是“晕”,是物理上所指的一种大气光学现象。三家注中有四处出现了长虹贯日:
一曰精诚感天,白虹为之贯日也。二曰白虹,兵象,日为君。三曰其解不如见虹贯日,不彻也。四曰夫言白虹贯日,太白食昴,实也。[1]83
这四处白虹贯日的象征意义不同,第一处和第四处的白虹贯日是一种祥瑞的征兆,是事将成功的预示,这里白虹贯日的出现是吉利的、令人欢喜的;而第二处和第三处则预示着事可能失败,是一种凶兆,这里出现的白虹贯日是令人厌恶的。同一种天文星象代表了不同的意义,有着不同的解读,这种现象是天文星象为政治服务的典型表现,同时也表明了这些天文现象代表的象征意义并非准确,而是人们对其解读的偏差。它不仅仅是不同时代人们认识上的偏差,也表明了在不同的年代,为了顺应人的不同需求,对天文现象赋予不同的意义罢了。天文星象的象征意义中固定的意象往往是天人感应意义的顺延,天人感应不只是某一个时代的思想,其在封建社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具体的内容变与不变、更改与否,都不能改变其天人感应的本质。
其二,天人感应意识下的天象与政治关系。《史记》三家注中释解天象时将天与君对应,君王代表上天而行事于人间,天上的一切均能兆示人世。征战、讨伐必有正当理由,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有很大一部分天文星象的象征意义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为政治服务的。君权、君臣、军事、国运这些与政治有关的方面成为天人感应天文星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俗语言“天上诸星,人间万事”。自古以来,人们都将自然的变化附会人事的变迁,加之“君权神授”思想流行,天文星象作为自然界的固有存在和人力无法撼动的现象,在无法用科学解释的情况下成为上天旨意的自然承接者和表达者,而君王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自然成为天象最合适的昭示者。所以,天象在君王的统治中具有很重要的暗示和正统意义。君王的出现往往意味着不同寻常的天文星象的出现,流星贯日、星宿异动等等都是常见的伴随者。君王的举动会被上天看见而且通过天文星象给予反馈,星象的解释往往是对于君王的评价,君王也会根据天文星象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当然君王也会假借天文星象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天文星象也会对未来的国运君权给予暗示。天文星象因为其年代限制性从而无法解释,所以也常常拿来为君主政治需要服务。《正义》云:“占以不明为宜,明,新君践极也。”[1]1290“大角一星,在两摄提间,人君之象也。”[1]1297《晋书·天文志》亦言:“大角在摄提间。大角者,天王座也。又为天栋,正经纪也。……将有天子之事,占于斗。斗星盛明,王道平和,爵禄行。”[5]《正义》前一处说星象的明暗是对最高统治者为政好坏的评价,后一处则是最高统治者为政好的星象表现。这两处都是把君王和星象进行了直接的关联,将二者进行直接对照。三家注的注解也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顺延解释。而臣子作为政治统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其好坏忠奸也有相应的天文星象的昭示,臣子也是天文星象非常重要的昭示对象。三家注中有关臣子的天文星象共有十八处,全是有关于臣子叛乱或者是不称职的天象的昭示,无一处是有关于臣子尽忠职守之类的昭示。例如:“金守,臣下兵起。危为宗庙祀事,主天市架屋”[1]1308和“月晕,蛟龙见,牛马疫;月、五星犯守,大臣相谋为,关梁不通及大水也”[1]1311,这两处都是臣子将要谋反的昭示。这些昭示虽然是有关于臣子的,但是其中并无于臣子有利的天文星象的昭示。于天文星象的昭示中,其中获利的仍然是最高统治者,这些天文星象的解释,给统治者治理臣子以理由,假借天文星象的变化来实施君权统治。所以虽然是显示臣子的天象,但仍然是服务于统治者,其服务的对象并没有因为其对应的对象而有所改变。故而对臣子昭示的解释权和控制权,往往还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上。
战争是政治的产物,战争对一个政权的建立和维护巩固都是十分重要的。战争讲求天时地利人和,而天时不仅仅指气候和天气,还指天象的变化。天象的变化也暗示着战争。天上有主掌兵的星系,从战争还未打响时的准备到正式的交锋都有相应的天文星象的变化。例如三家注中就有一部分的天文星象是暗示战争,《正义》云:“天枪者,长数丈,两头锐,出西南方。其见,不过三月,必有破国乱君伏死其辜”[1]1317。也有通过观测天文星象对战争进行预判的。南北朝到唐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人们无力改变残酷现实,不由得仰望星空,把希望寄托于神秘的上天,从星空中破解人间的密码。久而久之,人们对天象的认识在观念上不断发展,建立了一套更加完善的天人系统。从主兵星象的数量记载也侧面反映了古代人对于战争的重视程度。
人行有过,天象示之。“罪己诏”是君王表示自我反省、自我谴责,以求得百姓和上天谅解的诏书,也是君王在国内发生大的饥荒和灾害后进行的安抚民心的举动。出现日食,在古代被视为重大灾异现象,预示帝王背德亏理,应自行检讨,以谢罪天下。文帝二年(前180),天现日食,文帝良善,颁诏书,以为自己德行不够,招致上天之谴,与《史记》中“天大旱,蝗”这种通过生活生产经验积累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说法不同。观天象亦可推测国运,国家的兴起和衰败都与天象的变化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把这种国家的兴衰以天文星象的形式透露给民众,不仅有利于新政权的快速建立,还有利于展示政权的合理性。例如:
九游九星,在玉井西南,天子之兵旗,所以导军进退,亦领州列邦。并不欲摇动,摇动则九州分散,人民失业,信命一不通,于中国忧。以金、火守之,乱起也。[1]1307
月列宿,日、风、云有变,占其国。[1]1342
这两处都是讲星宿的移动,暗示了国家将要面临的变化,从天文星象的角度释解了国运的走向,释放了政权合理性和正统性的信号,以及国运无法人为阻挡的“天意”。透过对国家兴衰变化的表述,本质上还是为其政权服务。天文星象的象征意义从本质上来说还是掌握在史官手里,所以在顺应“天人感应”的理念下具有明朗的权力归属性,即服务于统治阶层。所以,有时天文学在这样的环境下往往会被权力阶层所利用,沦为御用工具,从而丧失了部分科学性,给天文学罩上了一层神秘面纱,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古代虽对天文星象的观察和测量并不落后,但天文学的发展并没有达至理想高度的重要原因。天文星象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被统治者所利用,故而虽受君王的重视而间接地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但所走的道路并非趋向科学性和系统性。
其三,天人感应意识下天象与农耕社会依存关系。自先秦以来,我国都处在农耕文明的体制下,农业作为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把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和政权的稳固。而农业的生产不仅仅靠经验的积累就能完成,还有许多不可控的因素。天文因素与自然灾害有着极其复杂的关系,即使科技发达的今天,预测自然灾害也是极其困难的。而天文因素的变化对农业的影响非常大,北方缺水,总是靠天吃饭,人们不得不看天的脸色行事,于是就促进了天象观测和历法的进步。古人观天象、订历法、振木铎以发时令,以利于农业生产。殷商时期,人们观天象而授时,把握农时,以扩大农业生产的发展。早在夏代已经有了天文历法,夏历《夏小正》中就记载了许多古代根据日月星辰来推测时间及日期的方式。《夏小正·三月》云:“参则伏。伏者,非亡之辞也。星无时而不见,我有不见之时,故曰伏云。”[6]在有关天灾星象中,饥荒往往有其独特的天象预示,而且还往往伴随战争和其他的天灾人祸一起出现。对于农业的天文星象的变化,往往体现了上天对于人们的暗示,所以大家就对农业生产不可控的因素进行解释,这种思维模式也影响了人们的其他活动,人们进行“祭天”活动,春祭“句芒”、秋祭“蓐收”,祀春、秋二神,祈求丰收与报答神灵。认识天象从而制定与农耕社会密切相关的历法,亦是对天命的遵从,而农业生产则是古代普通劳动者对于“天命”的理解。这种模式下的农业生产让人们更加尊重天时,这是积极发展农业的信号。
其四,天人感应意识下天文星象与现实社会的对照。天人感应之下的天文星象具有现实服务对象,所以这些天文星象具有现实的意义,其与现实的社会有着对照的关系,其内容有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和映照。这里主要有两点体现:一是与不同的现实社会人物具有对应性。除了上面列举的君主、人臣等,还有后妃,三家注中有关天人感应的内容里面共有六处关于后妃的注释,其中有一处记载了不同地位后妃所对应的星宿。“其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次北一星,妃也;其次诸星皆次妃之属。女主南一小星,女御也。”[1]1301天上与人间一样,相互映照,它是现实社会对应赋予的,与不同的现实社会的身份具有对应性。三家注中有关天事与天象的对照,对于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星宿与之对应。星宿像现实中的人们一样各司其职,各自代表着不同的身份。如“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1]1303。天上也有星宿对应人间的厨师,充分体现了天象的社会现实性。
三、《史记》三家注反映了天文学的发展
东汉以至隋唐,在天文学方面非常活跃,产生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新发现,在恒星观测、历法计算、天文仪器制作上都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为推动中国天文学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有关天文学的著作,如史志类的《汉书·天文志》《后汉书·律历志》《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等,历法方面的著作有《周髀算经》《太初历》《三统历》《乾象历》《皇极历》等。个人所著的天文学著作,如东汉时期的天文学家张衡《浑天仪图注》和《灵宪》,三国时期孙吴天文学家王蕃的《浑天图记》和《浑天象说》,以及陈卓《天文集占》《四方宿占》《五星占》《万氏星经》《天官星占》,南朝宋何承天的《验日食法》(三卷)、《漏刻经》(一卷),北周庾季才的《灵台秘苑》,隋朝刘焯的《稽极》(十卷)、《历书》(十卷),初唐李淳风的《乙巳占》,等等。这一历史时期的天文学著作,都为三家注在注释天文学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并被引入各自的注释中。
《史记》三家注吸纳了这一时期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其中的天文星象多是基于后代天文学的发展。对于天象的认知,裴骃、司马贞、张守节较之司马迁时代有了很大发展,对于一些星象的研究更加深入,从而体现在他们对《史记》天文学方面的注释之中。我们从三家注的注释里面可以看出有关星系的概念,其中有些星宿被归为一类,所以有的类别里面有不同的星宿,这些都可以侧面印证天文学从汉到唐的发展。虽然《史记》三家注有一大部分内容是有天人感应理念下的天文星象,其记录和观察具有政治性、现实性和功利性,但不能否认的是它对天文学发展的展示还是具有史料价值的。
三家注中对太白星宿的发现。《史记》中只是对太白做了笼统记录,并未有清晰而系统的介绍,而三家注中仅有关太白星的注解就有六十多条。从太白星的具体位置,认为其位于斗星的末端,勺子的末端;到太白星的星系研究,认为它属于天库的一颗星,是天库的主要星宿;再到太白所对应的天文星象的变化,“太白五芒出,早为月蚀,晚为天矢及彗。其精散为天杵、天柎、伏灵、大败、司奸、天狗、贼星、天残、卒起星,是古历星;若竹彗、墙星、猿星、白雚,皆以示变也”[1]1323;“日庚、辛,主杀。杀失者,罚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国。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东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1]1322。可以看出,人们在汉至唐这一时段,对太白星的认识更加深刻了,亦更为细致系统了,也对太白星的星系进行了归类和研究,这无疑是对天文学系统研究的成就。随着人们对天象的细致观察、认识的深化、研究的系统化,在对天文现象的整体审视上,某种程度上抛开了政治外衣,明显地迈向了科学研究的轨迹,这都是天文学不断发展的结果。这些注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天文学发展的进程,是我国天文学发展的见证。
三家注以其严谨性的注释,又使其具有史料学的价值,对中国天文学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安平秋将《史记》三家注的价值归纳为三类:一是引用古字的价值,为研究《史记》提供了文字上有用的材料;二是注明史料出处的价值,为研究《史记》如何运用史料提供了方便;三是引用许多今已亡佚的古书的价值,为后世辑佚提供了根据。三家注可以作为研究天文学的史料,这些内容能从侧面验证我国天文学不断发展的历程,也说明了我国天文学是在历史中不断进步的。天文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观测科学,三家注表征了古人对天文星象观测的记录,仰望星空,人们发现了宇宙中的种种星云,认识到世界是无穷大的空间,也促使人们探索“宜居”的行星,去发现更高级的生命体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