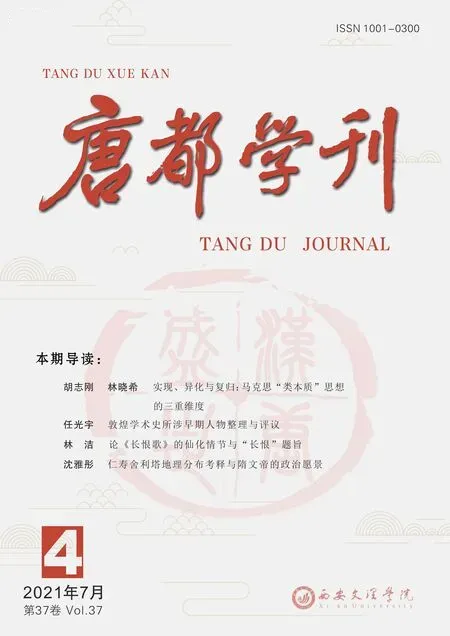“上邽”“下邽”考
陈云霞
(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
一、得名原委和设立时间
上邽、下邽均是先秦时期秦国设置的县,分别位于今甘肃天水和陕西渭南。目前学术界对于上邽名称来源的说法主要是参考《史记·秦本纪》,认为上邽是秦武公十年(前688)讨伐邽、冀戎,初次设县管理。而对下邽命名的依据则是来自《水经注·渭水》,郦道元记载:“渭水又东径下邽县故城南。秦伐邽,置邽戎于此,有上邽,故加下也”(1)参见郦道元《水经注》,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19。。之后史书对于两地名的来源说法均是依据于这两则材料。事实上,要完全清楚地解释两者命名,必须对这两则材料进行深入挖掘。
关于上邽最早的记载是《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当然学界对这里的“初县之”是否为秦国第一次设立县一级行政区划存有疑问,本文暂不作探讨。但这则材料确实可以解读为秦武公时讨伐邽戎所在地,并且开始设治所管理。裴骃在其《史记集解》中引《地理志》曰:“陇西有上邽县”,应劭曰:即邽戎邑也。《汉书·地理志》记载上邽是邽戎的故地,秦武公讨伐邽戎在此置县,地属陇西。这些都是关于上邽名称来源的记载,即上邽是因秦武公时伐邽戎置县而得名。但是邽戎的得名又源于何处呢?与上邽有何关联?
关于邽戎,郦道元记载:“渭水……北有濛水注焉,水出县西北邽山,翼带众流,积以成溪,东流南屈,径上邽县故城西,侧城南出上邽,故邽戎国也。”[1]卷17这则材料包含的信息是邽戎所在的上邽县与邽山在地理位置上相近。对于邽山的记载在《山海经》中就有,晋郭璞的《山海经传》:“……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音圭,其上有兽焉,……濛水出焉……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鸟鼠同穴之山 今在陇西首阳县西南。”(2)参见郭璞《山海经传·西山经 第二》四部丛刊,景明成化本。《水经注》中记载的邽山与《山海经》所提邽山当属一处,清代《山海经》研究集大成者郝懿行在注疏时提到:“……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音圭 懿行案《地理志》云:‘陇西郡上邽,应劭曰《史记》故邽戎邑也,《水经》云渭水东过上邽县,《注》云渭水东历县北邽山之阴’。”(3)参见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山海经第二》,嘉庆十四年阮氏琅环仙馆刻本。郝懿行的注疏也表明邽山与邽戎所在的上邽县位置很近。查文献可知,先秦时期戎的称呼许多因其地理位置命名。如《史记·秦本纪》载:“周厉王时,西戎反王室,灭犬戎丘大骆之族”,这里的犬戎据钱穆先生考证就是西戎,以其居地犬丘而得名(4)参见钱穆《西周戎祸考(上)》,载于《禹贡》第2卷第4期.。此类先秦时期以少数民族所居地点命名族名的现象在《史记》中已有记载,而邽戎的命名当是如此。地名当中尤其是自然实体,如山川、河流名称等在流变过程中最为稳定,加上先秦时期多有戎以居地命名的先例,因此可以断定邽戎的称呼来源于其居地近邽山。于此,秦武公十年讨伐邽戎时又以该地所居戎的名称来命名,是为邽县,也就是上邽县。
目前所见有关下邽最早的考古信息是北京文雅堂主人收集的秦封泥中有“下邽丞印”,这批秦封泥涉及郡级16种、县级54种(5)参见周晓陆等在《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一文中有相关论述,载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116-125页。。另外《史记》在记载先秦时期事迹时就已经提到下邽[1]卷28,可见下邽县在先秦时期已经设立,但对于其名称来源和设置时间文献说法不一。最早记载下邽县设立原委的是南朝宋范晔所著《后汉书》,其中有:“……赤眉虽降,众寇犹盛,延岑据蓝田,王歆据下邽 秦武公伐邽戎致之也,陇西有上邽,故此有下也”[2]。此后《水经注》中郦道元也沿用此说,即“渭水又东径下邽县故城南。秦伐邽,置邽戎于此,有上邽,故加下也”。这两则材料的时间相距不远,所透露的信息也趋于一致,即下邽是因迁徙邽戎至此而命名。与前文邽戎因邽山得名相同,此类因迁徙戎而命名行政地名的例子在先秦不在少数,即古代行政地名还会因人口流动而迁徙。永嘉南渡过程中大量北人南迁,在南方侨置了北方郡县,虽然不能将两者的根源、影响划为一类,但事实上都是因为人口的流动而使得行政地名迁徙。当然范晔和郦道元的记载都是容易产生误解的,原文为“有上邽,故加下也”,这句话可以解读为在下邽设置之前就存在上邽县。其实不然,而是在下邽设置之前,陇西有邽县。为了区别于徙戎后的新邽县,将原陇西邽县加“上”、新邽县加“下”,以别。无论是邽山的邽县还是迁徙后邽戎的邽县根据《水经注》的记载均是以渭河为参照物,且分别位于上下游,因此可以断定上、下邽也是因两者与渭河的相对地理位置而定。
尽管文献对下邽县设置的记载均是与邽县有关,但对时间没有明确的记载。文雅堂主人收集的那批秦封泥涉及郡级16种、县级54种,数量较多,可知肯定是在郡县制较为发达的时期。另外,下邽县即为今天渭南市临渭区东北,当属周王朝的核心区域。至西周末年,“恐倍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令秦无得通阳城。秦昭王怒,使将军□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 《索隐》秦昭王之五十一年 ,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惮狐”[1]卷4。此次周王朝向秦献邑三十六,而后周民遂东亡,可以说明这三十六邑应是周王朝在宗周附近的最后势力范围,尽献以后秦国才有可能在此设置县治。又《索隐》云该事件为秦昭王之五十一年(前264),亦即下邽县的设置时间应在秦昭王五十一年前后。
二、北魏上邽、下邽有无避讳
关于中国古代避讳的记载,在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中就有,但对其深入研究的是清代学者,顾炎武、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王昶等人著作中均有提及。此外也有一些论述避讳的专著,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黄本骥《避讳录》[3],目前学界关于上邽、下邽地名演变的观点主要为北魏时期为避道武帝拓跋珪讳而分别改名为上封、夏封(下封)。其中在《避讳录》中就记载:“道武帝名珪,避嫌改上邽县为上封。”[3]卷2近人对避讳研究集大成者当属陈垣的《史讳举例》,也认为上邽在北魏时期为避道武帝拓跋珪讳而改名为上封[4]105。其他如《历代避讳字汇典》《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均持同样的观点。但是笔者发现上邽避讳一说在文献中存有矛盾之嫌,考其原委,并不符合史实。因为上邽、下邽避讳一事文献记载避讳原因一致,下文作一处讨论。
将上邽避讳的相关文献排列出来,可以发现最早记载该事的是北齐魏收(507—572)所著《魏书》:“秦州治上封城,领郡三、县十二。天水郡,汉武帝置,后汉明帝改为汉阳郡,晋复。领县四,上封,前汉属陇西,后汉属汉阳……犯太祖讳改”[5]卷160。除了北魏当代的文献外,相关文献中《魏书》立著时间距离北魏史实最近,最为可信。正因为如此,《魏书》中关于上邽避讳一说为后世文献所沿用。代表性的有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长道县,下,南至州五十里,本汉上禄县地,后魏之天水郡也……西汉水东北自秦州上封县界流入。”(6)参见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5,清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稍后的《旧唐书》《太平寰宇记》均口径一致,语言表述都无任何差异,可以看出是沿用《魏书》之说。后世学者在考证此事时也多引用《魏书》和《元和郡县志》两则材料,认为上邽因避拓跋珪讳而改为上封。最为明确记载的是清代乾隆年间《水经注》订伪学者所著《水经注集释订讹》,其中记载:“又东过上邽县,渭水东历县北封当作邽,《元和志》云渭水在秦州上邽县北十三里西,自伏羗县界流入,按 今秦州西南有上邽故城,封山本邽山,后魏避其主珪嫌名改,上邽曰上封,山亦随而变山”(7)参见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卷17,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从以上文献中可以看出自《魏书》记载上邽在北魏时期因避道武帝拓跋珪讳改为上封后,之后的文献均沿用此说。近人关于上邽避讳问题的论断也多依据于此。
与上文所引文献相左的另几种文献透露的信息是上邽不曾避讳。就记载的可靠性来说,文献距离史实的时间越近,可信性相对越高。北魏道武帝拓跋珪(386—409在位)是北魏建国初的君主,其中时间相距较近的两本著述是《水经注》和《十六国春秋》。《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生活的时间是在公元6世纪,其中“渭水”部分一再出现上邽、下邽两地,但均未提及避讳一事(8)参见郦道元《水经注》卷19,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同样,崔鸿是北魏末年史官,其著作《十六国春秋》是记载东晋时期北方十六国(304—439)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其中一再提到“上邽”这一地名,均没有避讳一说。著者崔鸿为北魏史官,并没有对上邽、下邽避讳。尽管该书的现存版本为清代汤球编写,但汤球是以明人所辑佚的《十六国春秋》为底本,史料力求信而有征,且考证工作扎实。汤球既以崔鸿身份著书,且考证可信,那么就可说明崔鸿没有要避讳的意向。另外,明人屠介孙、项琳在辑佚《十六国春秋》时曾以魏收《魏书》为据,这就是说屠介孙、项琳、汤球都不认为上邽避讳,在避讳上邽、下邽避讳问题并没有沿用《魏书》说法。北魏当代的文献记载上邽时并没有避讳,而自北齐魏收所著《魏书》以后诸文献均记载上邽避道武帝讳一事。也就是说,年代愈近的文献没有,反而较远的文献却有记载,矛盾由此衍生。
由上可见,北魏当代的《水经注》和《十六国春秋》中上邽并未避讳,而之后的《魏书》却有记载,可以推断上邽在北魏时期并未因避讳改名。
首先,《元和志》关于此事的记载不可信。其卷2中有:“下邽县,望,东南至州八十里,本秦旧县……后魏避道武帝讳改为夏封。大业二年复旧。”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卷29也同样记载大业二年恢复原名。但《元和志》卷39却又这样记载:“武公伐邽戎,灭而县之,今州理,上邽即秦之旧县也。管县五……上邽县……后魏以避道武帝讳,改曰上邽,废县为镇。隋大业元年复为上邽县。”《寰宇记》卷150陇右道则载:“上邽县……后魏以避太武讳改为上邽,隋开皇初复为上邽县。”(9)参见《元和志》(清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与《寰宇记》(清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均记载“改曰(为)上邽”,据文意此处“邽”应为“封”,疑为传抄错误。既然同一个字避讳,上、下邽取消时间应该一致,这里不仅两地恢复原名时间不一致,且同样是上邽复旧名的时间也有大业和开皇两种说法。可见,《元和志》对此事的记载并不可靠,有待核实。对于《元和志》关于上邽记载的不可靠清代杨守敬已在其《〈隋书·地理志〉考证》卷1中有所提及:
上邽,今秦州西南,故曰上邽。按邽当作封,各本皆误,本秦上邽县。《地形志》以犯太祖讳改为上封。又《周书·宗室传》宇文导魏恭帝元年十二月薨于上邽,“邽”亦“封”之误。又按《元和志》后魏避道武讳改曰上封,废县为镇,然各书无立镇之说,恐《元和志》之说未足为据。带天水郡,汉郡,开皇初郡废,《寰宇记》秦州长道县,下,云:开皇十八年,改天水郡为汉阳。按开皇三年废天下郡立州,至大业初复置郡,不应开皇十八年有改郡事,恐《寰宇记》误大业初复置郡县改名焉。《元和志》大业元年复为上邽县,《寰宇记》谓开皇初复为上邽县。
杨守敬虽然注意到《元和志》与《寰宇记》在上邽复旧名时间及废县为镇史实上的谬误,但并未对避讳一事辨伪。杨提到《隋书》及《周书》等均将上封写为上邽,而事实上其它所有同时期文献均写作上邽(10)令狐德棻:《周书》卷25《李贤传》:“封下邽县公,邑一千户”;卷45《儒林传·樊深传》:“大统十五年,行下邽县事”等等。即使是《魏书》中也有称上邽的例子,如《世祖太武帝纪》。,这并非《隋书》和《周书》一两处舛误,而极可能是没有避讳一事。
其次,从拓跋珪在位期间北魏的疆域来看,最西也就到达今山陕交界地区,最南抵今河南洛阳一带。此时,上邽所在地先后分别属于前秦和后秦。《魏书》记载直至太武帝拓拔焘在位时上邽才为北魏大将刘洁等人所攻取,归属于北魏[5]卷4;卷28,《中国历史地图集》复原的疆域也是如此(11)该时间段内上邽不可能避讳,但《中国历史地图集》却在此标注为上封,因此有误。。由此,道武帝拓跋珪在位时不可能因避讳擅改前秦或后秦领土内的上邽县名称,《魏书》等文献在记载上邽避讳时没有任何一种指明上邽避讳是于拓跋珪在位期间。可见上邽在道武帝拓跋珪时因避讳改名一说不成立。尽管如此,不能排除北魏强大以后封建政权出于对祖先尊崇而避讳的可能。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详尽了中国古代避讳的种类,其中提到有因避讳追改一事,但是其情况均是为避当代讳而改前代地名、人名等等,并不存在为尊崇前代人物而改当代地名、人名的现象。同时,中国古代的避讳仅是在当朝施行,翌代就会取消[4]。倘若存在后世为尊崇道武帝改上邽为上封避讳一事,那么较拓跋珪晚的北魏《水经注》《十六国春秋》为何没有上邽避讳的记载。更为让人质疑的是魏收在《魏书》却提到上邽避讳为上封,但除此处外,《魏书》中涉及该地的记载均为上邽,而非上封。可见,上邽在北魏时期并没有因避拓跋珪讳而改为上封。
上邽因拓跋珪避讳不仅与史料中记载的当时北魏疆域以及文献本身前后矛盾,同时也与南北朝时期避讳的风气不相符合。对南北朝时期的避讳风气,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有所论述,总的来说,就是南北朝时期避讳风气不盛,讳禁甚宽。最明显的例子当属当时的父子不嫌同名,陈垣先生例举晋王羲之的儿子五人,是为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宋王弘,子僧达,孙僧亮等等。此种现象在清代学者研究避讳学时就已经注意到,《廿二史札记》谓魏宗室多同名,列举同名者凡五十九人。有同父而同名者,明元帝景穆子阳平、济阴二王,俱名新成,至称济阴为小新成以别之(1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5,清广雅书局丛书本。。王斯福在其《帝国的隐喻:中国的民间宗教》一书中指出,中国民间群众的信仰许多成分是来自于对最高权力——帝王或封建社会上层的模仿。出于同样原理,社会底层的许多生活方式也是在模仿上层社会,避讳也不例外。从以上所例举的史实来看,北魏时期,无论统治阶级还是普通民众对同名的忌讳并不盛行,这在清代黄本骥《避讳录》的统计中可见一斑[3]。据笔者统计,以《避讳录》的记载为总样本量,魏晋南北朝时期避讳的情况很少,单独就少数民族所建立政权来看西晋以及十六国时期中的后赵石勒、后秦姚苌讳长为藏,前秦、北燕,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再无避讳,相反南方的宋齐梁陈避讳很多。关于道武帝避讳,该书只记载“道武帝名珪,避嫌改上邽县为上封”。之后北周和北齐存有避讳几例。对比看来《避讳录》中南北朝以后的隋唐时期避讳的案例举不胜举,可见名称避讳这一现象也只有在政权强大时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威望和权力才会被推崇。而拓跋珪所在的北魏立国初期,受汉文化的影响甚小,在政权不够稳固的情况下因避讳而改动上邽县名的概率极小,何况是在拓跋珪以后追改避讳。
当然以上论述并不是否认南北朝时期有避讳习俗,北齐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风操》篇所述为:“江南轻重,各有谓号,具诸《书仪》。北人多称名者,乃古之遗风。……河北人人士全部辨之,名亦呼为字,字固呼为字”。当然颜之推也举有避讳严格的几例,但都是南朝梁人[6]。颜之推为北齐人,后仕南朝梁,虽然距离北魏立国时间稍长,但可大体反映南北朝时期避讳风气散漫,标准不一。拓跋珪时期北魏少数民族的特征十分显著,避讳也有所不同。根据现代人类学的研究,禁忌和避讳的习俗曾广泛地存在于未开化的民族之中。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在其著作《金枝》中论述文明发展程度不高民族或种族的禁忌时,就包括名字的避讳。国王和酋长有自己的禁忌,普通民众出于对权力的敬畏而不得碰触国王的器皿等等。而对于名字的避讳,由于其名字均表达一定意义或者来源于一个实物,主要禁忌的是那些与其意义相似的事物[7]。对于北魏帝王的避讳,《避讳录》说道:“魏追尊始祖神元帝拓跋氏讳力微,至孝文帝改称元氏,文帝讳沙漠,汗章帝讳悉鹿……少帝讳普根,穆帝讳猗庐,幼帝讳义平,文帝讳郁律……炀帝讳纥那,烈帝讳翳槐,……道武帝讳珪明,元帝讳嗣,太武帝讳焘。皆无考”[3]补正一卷。从这里可以看出鲜卑民族的避讳与汉族是不一样的,他们更倾向于与名字意义不同的方面,而非具体的个别文字,且此处指明道武帝时讳珪明,无从考证。
三、《魏书》为何要记避讳
上邽、下邽避讳一说的种种不合理如下:首先,记述北魏当代史实的《水经注》等文献均没有记载上邽曾避拓跋珪讳,反而之后的《魏书》《元和郡县图志》《水经注集释订讹》等沿用舛误之说,文献记载矛盾;其次,拓跋珪时期上邽所在地当属前秦或后秦领地,《魏书》记载至拓跋焘时期才归属北魏,当不可能翌代避讳;再次,拓跋焘以后下邽也属于北魏,倘若行上邽避讳之说,《魏书》中为什么没有关于下邽避讳的记载;最后,南北朝避讳风气不盛,献文帝拓跋弘与其后的孝文帝元宏(即拓拔宏)取名同音并不避讳,而上邽要回溯几代追讳拓跋珪是不可能的。综上,上邽并没有因避道武帝拓跋珪讳而改为上封,那么何以《魏书》中首先记载此事?究其根源,要分析魏收其人以及所撰《魏书》本身。
魏收(505—572)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北魏末年节闵帝普泰元年(531)就被委以“修国史”,至北齐天保二年(551)被正式受命撰述魏史。首先从魏收撰写《魏书》时所能参考的材料来看,《北齐书·魏收传》和《北史·魏收传》均记载当时可以直接继承和借鉴的文献主要有:北魏初年邓彦海所撰《代记》十余卷(太祖拓跋珪时);崔浩编年体《国书》(太祖拓跋焘时);王遵业、邢峦、崔鸿等撰孝文帝以下三朝起居注(宣武帝、孝明帝时);元晖业所撰《辨宗室录》30卷(北魏末年);有关谱牒、家传等等。此外,魏收“搜采亡遗,缀续后事”,其可参考的文献今皆亡佚[8]。可见,《魏书》所记载的内容以北魏初年尤为无从考证。《魏书》虽在编撰上是精心设计的,如以《序纪》为例追叙拓跋氏的远祖上至二十余代的史事,虽然大致阐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渊源,但未可尽信。也就是说,魏收对北魏初期的史事并无可靠的资料供参考来修撰《魏书》。
另外,魏收生仕北魏,不免有为北魏正名之嫌。就《魏书》的内容来看,它称东晋皇朝为“僭”、称宋、齐、梁为“岛夷”,这些都是在说明北魏是正宗皇朝,北魏是中原先进文化的继承者。在《魏书·序纪》中记述了拓跋氏先人诘汾与“天女”相媾而得子,是为“神元皇帝”。《太祖纪》中又载,献明贺皇后“梦日出室内,寤而见光自牖属天,欻然有感”,孕而生太祖道武皇帝。这些都是以神话来编织“天命”的理论,与魏收历仕三朝的经历不无关系。无独有偶,史书修撰过程中这类现象绝非仅此一例。中国古代避讳的种类繁多,但大多是当代人为避当代某事物或人名的讳,也存在当代避前代人或事物讳将前代人、事物名改掉的案例。长孙无忌在修订《隋书》时就将杨坚改成杨固以及帝祖名祯,李季祯改以字行曰元操。当然在隋代也存在这一种特殊情况,即为避前代人讳,改当代人名或官职名等。如隋文帝父名“忠”,以“诚”字代,兼避“中”字,以“内”字代,凡郎中皆去“中”字,改侍中为侍内、中书为内史 ,此例避讳牵扯到的官职、地名达20处,这些都是在长孙无忌撰写《隋书》时表现出来的,甚至他将《忠节传》改成《诚节传》。黄本骥在《避讳录》中推测是因为长孙无忌“以身生隋世故入唐,尤避其讳”[3]。这一点就提醒我们,目前所见关于拓跋珪避讳改“上邽”为“上封”一事最早的记载是在魏收所著《魏书》中,其他北魏当代的文献并无记载,那么很可能存在的情况是魏收仅在文献中将“上邽”改成“上封”,而事实上未曾避过讳。如同长孙无忌一样,隋代并没有关于“忠”字避讳之例,而是他在追撰《隋书》时将杨坚改成杨固等等。否则无法解释魏收避讳、而在其之前的郦道元不避讳。魏收生于北魏,但是著《魏书》时在北魏灭亡后的北齐,结合《魏书》内容来看应是出于为北魏政权正名抑或对前朝祖帝的尊崇而撰写“上邽避道武帝拓跋珪讳改为上封”。
黄本骥认为:“避讳兴而经籍淆,汉唐以来改复不一,至宋尤盛,淳熙文书式有一帝之名避至四五十字者纷纷更易。”也就是说,避讳使得文献记载混乱,如果不加以辨别很可能会导致对史实的误读。陈垣先生也在其《史讳举例》专辟一章详细讨论“不讲避讳学之贻误”。魏收在《魏书》中的追讳使后代史书认为北魏为避拓跋珪讳改“上邽”为“上封”,以致后世文献沿用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