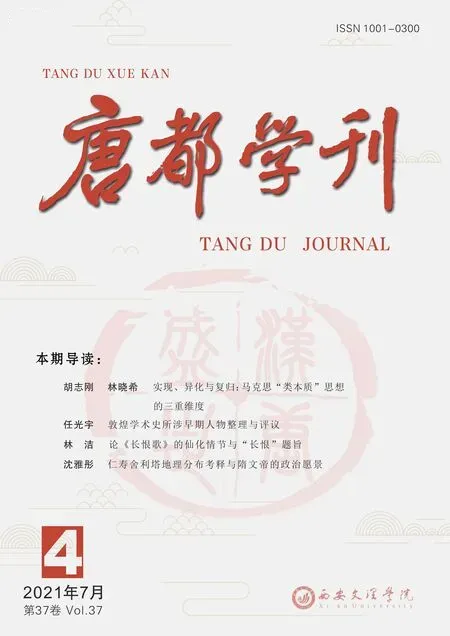新时代乡约文化与乡村治理的理路探讨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乡约文献辑考及乡约文化与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研究”开题学术观点侧记
魏 冬
(西北大学 关学研究院,西安 710127)
关学宗师张横渠在其有名的“四为句”中曾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乡约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根植于“乡土中国”背景下乡村道德建设和乡村自治智慧的结晶,在传统乡村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当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陕西省社科联名誉主席、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赵馥洁先生认为,儒家不但创立了系统的道德价值体系,而且十分重视价值的实现方式。儒家的价值实现方式,在先秦孔孟原始儒学时期是以个体人格和朝廷权力相兼顾、相结合为价值实现的基本方式,而以个体人格为基础。到了北宋时期,儒家的价值实现方式发生了变更,就是在个体和政权实现方式之外,出现了以民间社会为本位的价值实现新方式、新力量。而这种新方式的标志就是《吕氏乡约》。正因为如此,《吕氏乡约》是一种新的道德价值实现方式,相对于个体、官方朝廷而言,这种实现方式是一种民间社会性价值实现方式(1)选自赵馥洁先生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约文献辑考及乡约文化与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研究”课题开题仪式暨“乡约文化与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本文中所引专家观点,均出自本次学术会议发言记录。不再一一注明。。近年来,以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为首席专家的专家团队致力于乡约文化与乡村治理研究,立足于新时代乡村治理、乡村文明建设的需要并结合本土文化特点,在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吕氏乡约》框架的基础上赋予新时代精神文明,形成新时代新乡约的范本《蓝田新乡约》(2)参见《光明日报》2018年7月14日国学版。,此新乡约在蓝田、渭南等地实施后,取得了初步成效。2020年,以刘学智教授为首席专家的专家团队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成功申报了“乡约文献辑考及乡约文化与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研究”这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下简称“该课题”)。2021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颁布。5月,全国各地知名学者与“该课题”组成员相聚于《吕氏乡约》的诞生地——陕西蓝田,召开课题开题仪式暨“乡约文化与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研究”学术研讨会,共同探讨乡约文化与当代乡村治理的途径、方法和面向,随后在陕西渭南下邽镇开展了新乡约实践基地考察交流,为该课题研究的展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的贯彻落实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借鉴。现以此次学术会议和考察交流活动专家交流发言为基本参照,并结合笔者思考,对乡约文献的整辑、乡约文化研究及乡约与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建构等问题开展研究的学者重要观点予以提炼总结,以为发掘乡约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借鉴。
一、乡约文化与乡村治理体系研究要有历史和现实维度
传统乡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遗产,乡村振兴必须立足乡村实际和发展需要,从传统乡约文化中汲取智慧。当今乡村治理如何从传统乡约中汲取智慧?刘学智教授提出,“该课题”的研究,是要在全面系统整理海内外乡约文献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乡约文化所体现的乡村治理智慧,进而为当今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提供借鉴。基于此,乡约文化与乡村治理的研究,应该从传统乡约文化的历史研究和乡村治理的实践研究两个层面展开。最终落脚点是传统乡约在当代乡村治理实践中的现代转化,即把传统乡约的文化精神,即道德教育和乡村自治、乡村和谐秩序建构的文化精神,贯彻到当今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的实践中。“该课题”下设“中国历代乡约文献辑考与整理研究”“乡约历史变迁与乡约文化研究”“传统乡约乡村治理智慧与当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研究”“传统乡约现代转化中《民法典》与当代乡村治理联动体系研究”“新时代背景下乡约的现代转化与乡村自治实践经验研究”五个子项目。该课题期望通过五个子项目的研究,助力乡村文明建设、推动乡村自治,促进当今乡村治理体系完善。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该课题”以史实材料为依据,梳理出历史上众多乡约文献,探讨历代乡约对乡村治理、培养良风美俗的重要作用,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村规民约的建设,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很有意义。华东师范大学潘德荣教授认为,乡约文化研究,将会进一步说明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相比更为注重自身的实践活动的“中国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丰认为,把乡规民约与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结合起来,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拓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与会学者还紧密结合新时代,提出要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考察乡约的现实可能性及其对当今乡村治理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编审柯锦华研究员提出,乡约文化与当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研究,既要有历史维度,更要立足现实,考察传统乡约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和价值。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吴根友教授提出,乡村治理的体系建构更多的是一个对策性研究,今天的乡村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与传统社会相距甚大,“该课题”的研究除了要了解乡约及其历史,还要注重现代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知识,只有这样,对策性研究才更有力量。
二、乡约文献的搜集整理要系统全面
乡约文献是乡约文化研究的文献基础。乡约文化的研究,必须在对乡约文献全面系统整理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展开。根据课题组目前的调研情况,在《吕氏乡约》问世后的八百余年间,乡约不仅传播到国内广大地区,而且也传播到国外;不仅有典籍所载的,而且有碑石所刻、口头流传的;不仅有汉文的,还有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由于乡约传承历史悠久、民间性强、存世散乱、体裁不一,因此,乡约文献的搜集整理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
刘学智教授提出,乡约文献的搜集整理带有文献抢救性质。为了全面搜集乡约文献,课题组拟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对中国历史上的乡约文本及其背景文献的深度整理,包括对乡约文本的搜集、点校、辑佚、考证,以及对历代乡约研究文献的整理等;二是对存留于海外的乡约文本及乡约研究的文献进行搜集、整理。据初步调查,仅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就存有大量的乡约文本和关于乡约研究的文献。
对于乡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浙江大学董平教授提出,乡约文献是一个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理论视域下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乡约的形式、文献的类型都是多样的。因此,乡约文献的整理,首先要对乡约文献本身做出合理的概念界定。北京大学王中江教授提出,乡约文献的整理辑考不能局限于《吕氏乡约》及其之后古今中外的乡约文献,同时还应注意地下新发现文献和国外保存的中国乡约文献。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邵汉明教授提出,乡约文献的搜集要尽量全面,同时也要做系统分类、考量甄别,建议选择重要的、具有代表性意义乡约文献编成传统乡约萃编,而对于其他乡约文献做目录梳理,在此基础上建立乡约文献数据库。
三、乡约文化的研究要有社会文化的大背景
“乡约文化的历史变迁、历史反思与现代价值研究”是从文献整理向乡约实践转化研究的过渡,其目的是探讨乡约文化与古代乡村结构、国家政权、风俗文化、社会组织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乡约文化在历史过程中的核心精神、基本类型、社会影响、实践效果和经验教训。刘学智教授指出,这一部分涉及的主要问题有:(1)宗法、礼制、家族、土地、乡绅与乡约产生、变迁的内在机制;(2)古代国家管理体制、政治体制、社会运行机制与乡约文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调适;(3)社仓、社学、族规、家训与乡约的互补整合;(4)儒释道等不同文化背景、各民族传统习惯、地域风俗、宗教信仰等文化对乡约精神的塑造及其表现;(5)乡约以及其衍生出来的变体即士约、学约、会约、商约、行约、兵约的关系。“该课题”将通过这些研究,为探讨当今乡村治理体系中要关注的诸种要素的具体展现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与会专家肯定了乡约文化研究的重要价值。赵馥洁先生认为,乡约是官方方式和个体方式之外的实现儒家道德价值的第三种方式——民间社会方式。《吕氏乡约》不但具有乡村治理的社会政治意义,更有创新儒家价值实现方式的文化哲学意义。董平教授指出,就传统社会来讲,一个乡村就是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不只是生活的共同体,同时是道德的共同体,乡约文化就是在这个意思上显现它特别的意义和价值,孟子讲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可以说是乡约的核心精神。乡约文化的研究可以与中国治理制度的研究构成补充。与会专家提出,乡约文化研究要有整体性的思路。董平教授认为,从中华文化发展的脉络来看,乡约本身是儒家文化长期向社会基层渗透的一个产物,乡约文化实际上和儒家讲求移风易俗、天下和平的社会理想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法生研究员提出,在传统社会里,乡学、乡约和乡绅是三位一体的,乡约的研究要与乡学、乡绅的研究结合起来。专家们还提出,乡约文化的研究,还需要注意三个方面:其一,乡约文化虽然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但从根本上仍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对乡约的研究,要考量其中的陈规陋俗,不能全面肯定;其二,乡约文化也是地域文化的体现,各个地区的乡约乡规因为地域差异而呈现不同,在研究中要非常注意乡约文化的地域特色;其三,对乡约文化的考察不能仅仅局限于约文,而且要考察乡约的组织机构、执行方式及其社会效果。只有通过对乡约文化客观全面的分析,才能对其应用研究提供良好的基础。
四、乡约文化的转化要立足于乡村实际
乡村振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是乡约文化研究的现实起点。乡约文化研究的终极指向,是要在此基础上着眼现实、着眼当前乡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当代乡村治理,助力当代乡村振兴。刘学智教授提出,我国社会治理已进入“私法自治”的新时代,人格平等、意志自由、利益衡量等现代意识已正式以法典形式得以确立。传统乡约蕴涵的乡村治理智慧向当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模式的转变,是一个非常具有现代性的研究课题。乡约文化精神的当代实践是我们此项研究的重中之重,但农村情况很复杂,各地情况差别很大,这就要吃透中央有关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政策精神,把握好政治方向,抓住核心问题,注意处理乡村治理体系建构中的原则性与差异性、普遍性与多样性问题,运用社会学方法进行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积极探讨乡约或乡规民约在乡村的实现形式。
学者们提出,应该从当前中国乡村的古今变迁和当今乡村的特点出发,考量乡约的现代价值。柯锦华提出:目前,我国的社会结构与传统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农村城镇化就是最大的变化,城镇化使得农民的流动性增大,农业人口不断减少。吴根友教授提出,当今传统农村社会已经解体,这个变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乡村的空心化,认为基于现代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大背景,治理中国的乡村社会,首先在经济上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其次是有办法让那些有理想、有能力的人回到农村,并让他们在农村有所作为;再次是如何让乡贤回乡养老,这对乡村治理、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四川师范大学蔡方鹿提出,在乡村治理层面,要重点考虑城乡之间良性互动的建立、乡村相比于城市要具备可移居性、乡村在新的经济结构中保持自身的活力这三个因素。只有把乡村建设拉入现代经济结构中考虑,中国传统的乡约文化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学者们还探讨了乡约文化与当今乡村建设的主要结合点以及基本思路。湘潭大学陈代湘教授提出:乡约文化对乡村治理有其作用,但不能夸大其作用,不能说一个乡村有乡约文化,就能把乡村治理搞好了。赵法生教授提出: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乡村治理,要把乡约文化落到实处,不是在村里挂几个规定、横幅就解决问题了,还要解决村民的思想问题,因此讲乡约文化对现代乡村治理的现实作用,就要把它跟整个的文化、儒学、道德教育联系上,把法治和儒家的礼治结合起来。在乡村恢复儒学教育,把儒学讲堂建立起来,在这个基础上推进新乡约文化,就会真正发挥作用。
五、乡村治理的研究要根植于实地调研
乡村振兴不仅要深入历史文献的研究,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还应该紧密结合农村实际,从现实中寻求乡村振兴的智慧。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不应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更应该写在中华大地上,写进社会实践中,写到乡村农民的心坎里。
王中江教授提出,儒家的精英文化与下层文化中层文化上下是紧密互动的。现在讲重新建设乡村文化,传播乡约文化,但真正能深入乡村的人很少,希望课题组能深入做一些田野调查。柯锦华研究员指出: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书本上谈的多,真正下去考察的比较少,因此要把乡约文化和乡村治理结合起来,就要自觉、切实地去做调研,从实际中发现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汲取民众在乡村治理中的宝贵经验;同时还认为,乡规民约这种东西都是宝贵的地方经验,但在“推广”要注意它的内生性和民众的自愿性,不能硬性强加,只有提取出其中的“精神内核”,才具有更为普遍的价值。
刘学智教授对如何深入实地调研开展课题研究做了总结发言。他说,在《蓝田新乡约》调研的过程中,课题组曾在蓝田县委宣传部和芸阁书院、渭南市临渭区政协、山东尼山圣源书院等单位的支持下,在蓝田县董岭村、临渭区下邽镇村建立了乡约转化实践基地,开展了相关的调研和新乡约的推广实践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近期,临渭区聘任了十余名专家作为“新村民”,为乡村振兴献策助力,为“该课题”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课题组将利用已有实践基地,同时拟在全国一些有代表性的地区开辟一些新的有特点的实践基地,开展课题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