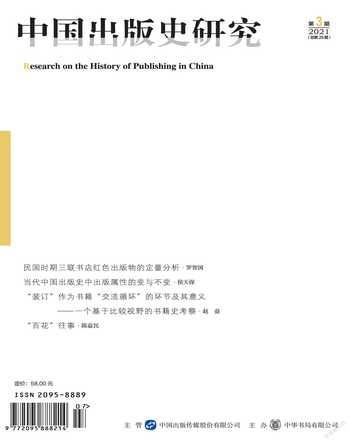《书业商之人格》序
按语:2021年是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先生逝世八十周年。为此,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推出《书业商之人格》一书,将陆费逵生前有关书业、教育与中华书局历史发展的主要文章结集出版,并邀请著名社会学家、教育家金耀基先生為该书撰写序文。本期刊登这篇序文,以纪念陆费逵先生献身书业,为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一
一部中国的现代史,它的主旋律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鸦片战争后,曾(国藩)、李(鸿章)主导的自强运动,其重心是国防现代化,基本上只局限于器物层次的现代化,最后以失败告终。甲午之败,面临亡国之祸,遂有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戊戌维新运动,着眼点已在政治、教育、商事等制度层次的改革,而以君主立宪之国体改革为重中之重,维新结局“六君子”被杀,康梁亡走日本,变法戛然终止。君主立宪之路百日而斩,1911年辛亥共和革命则成为政治现代化之最后选项。但戊戌维新最直接之效果,应是教育现代化的开启,戊戌年(1898)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是一个重要指标。事实上,百日维新失败后,教育现代化的事业,涉及学术、知识、文化的传播与人才培育诸方面,却是继绳不绝,一波接着一波,其荦荦大者,如1905年清廷之“废科举,设学校”(晚清新政之一)。1912年民国元年临时国民政府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之新教育(共和教育)政策(如教育部所颁《大学令》),一直影响到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不夸大地说,自戊戌清末到民国时期一连串教育现代化的作为,铺垫了此后中国百年现代化之路的基石。
回眸百年,在教育现代化上,风起云涌,豪杰辈出,而从晚清到民初,具有象征性并代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是两所大学与两家出版社。戊戌变法之年(1898)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有维新意义的高等学府,民国元年改称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手上,更成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型大学。早于戊戌一年(1897)成立的商务印书馆,则是中国第一间有现代意义的出版社,此后更成为中国出版业之重镇。1911年,辛亥共和革命之年,清华大学诞生,之后更成为与北大比肩竞胜的大学双尊。而1912年,民国元年,则诞生了中国第二家现代出版社,即是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一开始就与商务有争雄之心,此后终成为与商务齐名的大出版社。
二
月前,香港中华书局总经理赵东晓博士带来厚厚一叠书稿,他说2021年是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先生在港逝世80周年,为此,他搜集陆费伯鸿先生生前有关书业、教育与中华书局历史发展的主要言论,结为一集,准备出书以纪念这位他深为敬慕的中华书局的前辈、出版大家。东晓并随即表示我金某曾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做过事(我曾任副总编辑,王云五先生自任总编辑),对出版事业有认识、有同理心。他更说,我金某一生从事教育(我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三四年),对于陆费伯鸿以出版为教育事业的看法,必更多有体会与认同,所以他邀我为《书业商之人格》一书作序。我听后,未多说一语,便欣然应命了。我生也晚,我六岁时伯鸿先生已离开人世,当然与他未曾有一面缘。我十分乐意通读书稿,从中结识这位民国时代中国出版界的风云人物。
全书分三辑,第一辑是“献身书业”,第二辑是“书业商之人格”,第三辑是“言为心声”,三辑都是陆费逵先生的夫子自道,很可窥见他以书业推动教育、以教育导引国家社会发展之思路。同时,本书也记录了他创立与卅年经营中华书局的奋斗不懈、生死以之的心路历程。本书之“附录”另编收有舒新城、沈芝盈、王云五、刘立德、吴永贵等人纪念陆费伯鸿的文字,对陆费伯鸿其人其事及其对教育、文化之贡献,都有真实的评述,很帮助我们对陆费逵先生有一整体的认识。读了书稿后,深自庆幸,因是为了作序,我对陆费逵这个人、对中华书局这个出版社才有了一个真切的阅读,我下面想写几点我个人的观察与感想。
三
(一)
舒新城在《陆费伯鸿先生生平略述》中说:“先生素性好学深思,于学无所不窥,而于教育研究尤精深。”舒新城先生是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也是《辞海》的主编,学识渊博,为学界所重,从他口中说陆费逵“于学无所不窥”是极不寻常的。我们知道,伯鸿先生一生只有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十三岁(戊戌变法之年1898年)读四书、《诗经》《易经》《左传》《尚书》《唐诗三百首》等书,十四岁后就开始独力自修,每日读古文、看新书各二小时;十五岁,隔日去“阅书报社”阅读新书刊,早九晚五,如是者二年,把五大间的书籍杂志,尽兴看够,此后数十年即使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日子,伯鸿先生都是无日不读书,此所以他的识见、学养是与时并进、自新不息的。陆费逵的“于学无所不窥”的博学,完全是从自修而来,这使我想起民国时代三大出版家(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中,陆费逵与王云五二位都是自修成才的博学之士。业师云五先生出身学徒,但自少至老,手不释卷,眼不离书,曾通读大英百科全书,传为美谈,自言:“中文,我想老翰林也没有我读的古书多,而英文,博士和专家也没有我看的书广。”我从陆费逵、王云五身上看到学问的博通是成为大出版家重要的知识装备。
陆费逵似乎是命定要走上出版事业的,而这又与他之醉心教育是不可分的。刘立德先生说他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陆费逵的时代,有志有为之士,莫有不思救国强国之道者。他曾说:教育得道,则其国昌盛;教育不得道,则其国衰弱而灭亡,此一定之理也。……治国者……必先谋夫教也,生计教育得道,则人心必变而善;人心而善,则社会之风俗习惯良,而国家以立矣。(见刘立德《陆费逵教育思想试探》一文)陆费逵的人生事业起始于十七岁时在南昌创立正蒙学堂,这是他的学校教育之路的初试;十九岁在武昌创办“新学界书店”,则是他以出版做教育之路的初试。之后,他就决定性地走上以出版做教育之路了。他二十一岁任文明书局编辑;二十三岁因受高梦旦先生之赏识,进入当时已是执出版业牛耳的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部长,并为《教育杂志》主编,这使他亲身体认到出版事业在国家社会的发展中可产生的作用与价值。四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他预见到共和政体必然来临,所以他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决定,离开商务印书馆,另建独立出版大业。正在民国诞生之年,他二十七岁,与戴克敦、陈寅、沈颐、沈继方四人,在上海成立中华书局,自任局长,主持全局业务。这是陆费逵生命史中的大事,也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大事。伯鸿先生以“中华”为书局之名,显示了他天下、国家的情怀。自1912年中华书局创立,到1941年(他五十六岁)他离世,整整三十年,他与中华不离不弃,历经多次磨折,一秉初心,勇往向前,终于把中华书局打造成与商务印书馆齐名于中国的第二家大出版社,时人有誉陆费逵为出版业巨人,亦不足为奇了。根据吴永贵先生的一个统计,中华书局在1912—1949年的37年中,共计出版的图书总种数为5908种,12702册(商务印书馆在1902—1950年48年中,出版图书总数为15116种,稳居中国出版业第一的位置)。吴永贵指出,这是一“骄人的成绩,更应该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记下重彩的一笔”。我更以为,民国以来,万千之数的中国读书人、知识人,可以有未进过大学的,但未读过中华、商务出版之书的,恐怕绝无仅有。
(二)
2011年,中华书局成立百周年时,吴永贵先生写了《陆费逵:坐言于教育,起行于书业》的长文,来纪念伯鸿先生。他说:陆费逵被时人所知晓,最先还不是他出版家的身份,而是他一系列见解独到、说理透彻而又平实可行的教育改革主张。他1905年发表的《论设字母学堂》《论日本废弃汉字》,是我国改良文字、统一语音运动的先声。他1909年发表的《普通教育当采俗体字》,被后人称为汉字简化运动的开场锣鼓。他是清末学堂中推行尊孔读经的坚决反对者,对男女不能同校共学的论调,更是深恶痛绝,予以尖锐抨击。诚然,陆费伯鸿生于清末,深感社会、文化之落后,民智不开。他认识到欲开民智,非通过发展教育不可。1905年,伯鸿先生二十岁,也是清廷诏令“废科举,兴学校”之年,他在任《楚报》记者时曾写《论群蠹》一文,痛言国人之无公德(他称之为“群德”),而国人之所以无公德,则起于国民“智育缺乏者”。这就是陆费逵一生以开启民智,振兴教育为职志之初心。他在1912年创建中华书局,并亲自起草《中华书局宣言书》,明确提出了“教育革命”的呼声。宣言书说:“清帝退位,民国统一,政治革命,功已成矣,今日最急者教育革命也。”事实上,陆费逵在民初之际,提出过许多教育改革的主张,并且不少都得到落实执行,值得特别一记的是如下一事。民初年,南京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部长,因国体既经变更,旧法令不再适用,而新规制又迫于时间未能颁布,蔡先生于就任之初就去上海商之于陆费逵和蒋维乔,最后应蔡先生之托,陆费逵本其夙见起草了暂行办法,并与蒋维乔商定一稿,此即是元年一月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底稿。陆费逵多年后提及该暂行办法及四条通电时说:“其内容大体根据我三年中所研究的结果,如缩短在学年限(中小学改为共十二年),减少授课时间,小学男女共学,废止读经等,均借蔡先生采纳而得实行,其愉快为何如也。”史家对于《暂行办法》和《课程标准》两令,称之为民国教育史之“绝续汤”。刘立德先生说:“陆费逵与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著名教育家蒋维乔共同商讨新教育事宜,揭开了民国教育史的序幕。”
(三)
陆费逵先生可说是一位醉心于教育、立身于书业的人。他喜欢称出版业为书业,也似乎更容易把出版业与教育形象地联结起来;教育不外教书、读书,出版业则是出书、供书。所以在他言,教育与书业是一事之两面,互为作用、互为表里的。陆费逵于1905年,在上海与同业发起成立上海书业商会,后被选为首任会长。1924年,他以会长身份为《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作序,序中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这是陆费逵为出版业的定性定位,这也可以说明陆费逵为什么自创中华书局后,从未改换人生跑道(至少一度外交部请他做官,被他婉谢),而以出版业为安身立命之所。
陆费逵把书业和教育看得如此密切,最显著的是他对教科书的看法。上面我提到他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提出了“教育革命”的口号,实际上他把“教育革命”更集结到“教科书革命”上,他说: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毋庸置疑,教科书是对青少年教育之利器,清末民初千百间中小学校,教科书便是中小学生的知识之津梁。对大多青少年言,读书便是读教科书,教科书实是开发青少年智育的不二法门。应指出者,教科书是一巨大市场,是书业商必争之地,所以,并不令人惊讶,陆费逵创立中华书局就是以中华小学、中学的教科书打头阵的,并且谋定而动,一举成功。可以说,中华因出版教科书而奠定了在出版界的地位,它打破了民前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独步十年之久的局面,也因此开启了中国出版界中华与商务比肩竞胜的局面。在这里我想指出,陆费逵是反对教科书“国定制”的,他主张“审定制”。他说教科书决不可“国定”,要“仍任民间编辑,学部监督审定”。民国时代,教科书就是由民间出版社负责编辑的,也因此,教科书市场变成书业商攻城夺地的激烈战场。1924年,中国第三大出版社世界书局首次加入教科书市场,中华与商务这两家竞斗不已的大书局居然联手合设国民书局一所,编印新国民小学教科书,不计成本用“价格战”压制了世界书局。价格战的结果,受损失的是出版商,但客观上却因课本费之下调,大大推动了国民教育的普及。不过,书业商要想拓展占有教科书的市场,根本上还必须在教科书编辑上精益求精,以争取学校当局的选用。
陆费逵的中华书局以教科书起家立名,面对商务、世界的强力对手,当然全力以赴。诚然,中华书局精英荟萃的庞大编辑所始终是出版教科书的灵魂与大脑。中华书局自1912年横空出世,出版中华小学、中学教科书,此后二十余年,几乎每数年就有新猷问世,并且从中小学教科书进入大学用书。回看民国时代,教科书的出版不止在量上越做越大,品质上也做得越来越精。论者有言:“它不仅确立了我国现代教科书编纂的基本范式,奠定了我国现代教育的基础,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思想、学术、文化向现代化方向的发展。”(见本书附录吴永贵《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四)
讲中华书局就不能不讲陆费逵。陆费逵创建了中华书局,主持了中华书局三十年,陆费逵是中华书局的化身。我从阅读与听闻中,觉得陆费伯鸿先生具有鲜明的个人性格,中华在他管治下成为一个“家庭性质之集团”(舒新城语),他就是一个“大家长”,这当然是不尽合现代管理的风格的。不过,中华在他主持下,始终是一个有活力、有创新力、有效能的出版机构,这不能不归功于陆费逵个人的人格魅力。在我看,中华书局之所以能在出版业中蔚为大国,实因为陆费伯鸿先生能为中华书局组建一个相当庞大的强有力的编辑队伍。三十年代中华正盛时,编辑所人员有一百余人,其中大不乏知名飽学之士,早期有梁启超、范源濂(后任教育部长)、徐元诰、马君武、张相等人,以后有舒新城、金兆梓、田汉、张闻天、左舜生、陈启天、潘汉年、王宠惠、李登辉(后任复旦大学校长)、徐志摩、谢无量、钱歌川、张梦麟、郑午昌、吴研因、邹梦禅、陶行知、张宗麟、戴伯韬等人。而与编辑所编辑人同为中华书局的源头活水的作者则数目远远更大。至1949年中华累计出书五千九百余种,作者当以千计,其中固不少是大学学科领域中卓有建树者,更有的是名闻当代的文士、艺术家,举其著有声名者有梁启超、马君武、黎锦熙、李劼人、谢无量、薛暮桥、陶菊隐、徐志摩、郁达夫、王卓然、阿英、郭沫若、周谷城、郑振铎、陈望道、千家驹、丰子恺、章伯钧、于光远、宦乡、巴金、王亚南、徐悲鸿、刘海粟、傅雷、胡乔木、杨宪益等(见引于吴永贵《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中华书局学厚才高的近百位编辑人,有星光耀眼数以千计的作者群,这是任何第一流大学都会羨妒的大阵容。
正因为中华书局有如此优秀强力的编辑群与作者群,所以,在陆费逵主持的三十年中,中华先后能出版一系列富共和精神的教科书,能出版一系列宣扬新思想、新观念的杂志(如《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大中华》《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能出版一系列量大质精、惠益读者的工具书(《中华大字典》《辞海》《中华百科辞典》),能出版大部头惊艳当代的文化综合古籍(《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这般辉煌的出版成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华书局不能不说是一个成功的出版社,而陆费逵不能不说是一位成功的大出版家。写到这里,我不由不想起与陆费逵同代同行的大出版家王云五先生《悼念陆费伯鸿》之文。王云五先生在悼文中说:“伯鸿先生的成功,除了少年时期的奋斗以外,他的深远的眼光也是一种要素。”
(五)
王云五先生指出“深远的眼光”是陆费逵成功的一个要素,这绝对是“知人”之言。眼光就是识见,识见的深远除了学养之外,更有天赋为慧识。陆费伯鸿先生生于一个新旧时代交替、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交替的历史时刻,他敏锐地感知到新时代的来临,并坐言起行,抓住新时代下的机遇,1912年,他创立中华书局,与中华民国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中华书局一开始就出版富于新时代精神的教科书,正是他为构建中国现代文明所做的教育现代化事业的先声。民国初年,他倡导的语言文字改革(如《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和提出的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并重的主张,都成为此后新教育的基本主张。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他更以中华书局为平台,通过出版多种杂志、书籍,成为宣扬、推动新文化的一股不可轻估的力量。中华书局成立后三十年中,其出版主调便是为催生与建成新文化、新文明(现代文明)服务,除了教科书,中华先后出版多种多类的丛书,试举例如次:《新文化丛书》、《新文艺丛书》(徐志摩主编)、《社会科学丛书》、《教育小丛书》、《实业丛书》、《商业英文丛书》、《国际丛书》、《中华百科丛书》(舒新城主编)、《世界文学全集》、《新中华丛书》、《英文文学丛书》等,很显然的,陆费逵致力于催生建成中国的新文明的主题思维是通过学术、思想、文艺、教育等诸方面的书籍出版呈现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与商务这两家中国出版业的双尊都在学术、教育、文化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这两家出版社却同时又因出版中国古籍而闻名于世。陆费逵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先驱人物,但他对于蕴藏中国传统文化的古籍则抱有深情与敬意。他对他的高祖宗伯公陆费墀在乾隆时编修震古烁今的《四库全书》并担任总校官是引以为傲的,他曾说:“小子不敏,未能多读古书,然每阅《四库总目》及吾家家乘,辄心向往之。”毫无疑问,他是同情、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但是他与新文化中一派“打倒孔家店”“把线装书丢到茅厕”的激烈粗暴之论是截然不同调的。我在此特别要说说陆费逵对经书的看法。经书(四书五经)简单说,在中国学术思想中居中心地位。自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独尊儒学,罢黜百家”后,儒学升为经学,成为中国人的“思想的君主”(冯友兰语),传统中国的教育(太学、国子监)的“养士”与科举的“取士”,皆以四书五经为核心要素。陆费逵十三岁时,已读了四书五经,但同时也接触到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新思想。二十岁时(1905)清廷颁布诏令“废科举,设学校”,经书的魅力已大减,但清末新式学堂中仍维持尊孔读经的传统,而陆费逵则是小学堂尊孔读经的坚决反对者。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陆费逵究竟是如何看待经书的?简单说,陆费逵是肯定经书的价值的,他之反对小学堂尊孔读经,只是觉得儿童不宜“专读一经”,以免“食而不化”。他主张把经书区分开来,分别地纳入到新式大学的不同科目中去,他说:(经书)其中的精义格言,采入修身课本可矣;其中的治平要道,编入法政大学及专门法政学堂的讲义可矣;其中可资风诵的古雅文章,选入国文读本可矣;其中古史所征的事实制度,作为讲习历史的参考可矣。(陆费逵:《论中央教育会》,《教育杂志》,1911年第8期)写至此,我不由不说说与他同时代的蔡元培先生是如何对待经书的。在我眼中,蔡元培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第一人,在中国学术思想上他把以经学为中心转到以科学为中心。在大学殿堂中,他以科学取代经学而登居主位。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废去了“忠君”“尊孔”等封建信条,取消了“经学科”。蔡元培之取消“经学科”不啻是翻转了董仲舒的“独尊儒学,罢黜百家”之两千年来的学术与教育的规范,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蔡先生之取消“经学科”,并不是消灭经学,而是去掉经学为“思想之君主”的位序,把儒家著作从“经学”还原到先秦“子学”的位置。换个角度说,蔡先生是把儒家典籍作为传统教育的“信仰”系统,转为现代教育研究对象的知识系统。儒学作为知识的一种,蔡先生是完全肯定其价值的,他主张把“经书”收纳到现代大学的新知识谱系中去,所以,他认为当时京师大学堂的经学十四则,其中《周易》《论语》《孟子》可归入哲学门,《诗》《尔雅》可归入文学门,《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可归入史学门。简言之,他主张把经书并入现代大学的文科。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蔡元培对经书的态度与处理方式与陆费逵所持者是若合符节的,是谁影响谁?我不知道,应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陆费逵对经书的珍惜态度,很能反映出他对传统文化正面的立场。中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但以儒典、历史、思想、文学等先人主要精神遗产悉数都在古籍中呈现。此即是传统经史子集四部所赅的学术著作。十分有意思的是,商务在五四运动后的第一年(1920)开始出版震撼书界的《四部丛刊》,不二年(1922)中华亦开始预约发售《四部备要》。《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皆是卷帙以万计,册数以千计的大部头古籍,二者都是从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中汇集最要之书、最佳之版本,编辑整理,或影印(商务)或排版(中华以聚珍仿宋版排版),动员人力之大,需时之久,称得上中国出版业的巨大文化工程。“以商务《四部丛刊》开其先,中华《四部备要》继其后的这两大文化工程,代表了中国古籍出版的一个新纪元。”(吴永贵语)主持这样巨大的文化工程者,如商务的张元济、王云五,中华的陆费逵,除了精于商业的考量外,更必须具有一定的学术素养以及一份对于“保存国粹”(陆费逵语)和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陆费逵在出版《四部备要》之后,1934年又影印出版《古今图书集成》,全书一万卷,字逾一亿,原为清代陈梦雷、蒋廷锡等辑,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外国人称之为“康熙百科全书”。陆费逵在古籍出版上所展现的心力与魄力,实令人敬佩。
综观陆费伯鸿先生三十年的出版人生,可谓充满传奇,辉煌而精彩。他一方面欢呼共和时代的来临,夙夜匪懈,为新教育、新文化之建设开道,出版新书;另一方面,为保存传统文化,为往圣先贤之绝学续命,出版古籍,不遗余力。究其用心,亦在“返本开新”,为中华谱写新章。
陆费伯鸿先生有眼光,有魄力,他看得准时势,并能乘势而起,创造时势,诚民国时代出版界的豪杰之士。
四
2021年是陸费逵先生逝世80周年,赵东晓博士出版《书业商之人格》诚是一件美事。陆费逵于1912年创立中华书局于上海,1927年在香港设立中华书局分局(即今之香港中华书局),1937年日本侵华,长江流域多所分局相继沦陷,陆费逵移赴香港,成立香港办事处,主持中华各分局业务。1941年抗日战争正处关键时刻,先生不幸逝世于香港,并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场。伯鸿先生与香港真可说有特殊之缘。先生离世前一年(1940),他的民国新教育同道蔡元培先生亦在香港辞世,也葬在香港华人永远坟场,孑民与伯鸿二位先生都是对中国教育现代化有巨大贡献之人,也都埋骨于香港之青山,真是香港之幸!
我有缘为《书业商之人格》一书作序,因而对伯鸿先生其人其事及其创建中华书局之功业有所认识,并知先生与蔡元培先生生前的同道之谊,则是我之幸事。是为序。
金耀基2020年12月18日
〔作者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