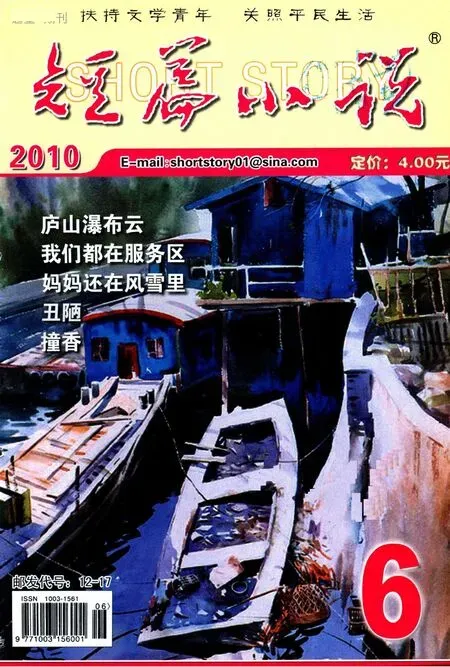1976年的豆瓣和鸭脚
◎柳恋春

1976年,我10岁。
豆瓣
空气是干净的,地上是干净的,到处都很干净。风一吹,树上的黄叶就往下掉,还没有站稳脚跟,就被妇女们用靶子装到了背篼里。地上的青草,刚冒尖泛绿,还没有很好地享受阳光和空气,不是被牛啃了,就是被小孩割了。就连猪牛羊拉下的粪便,还在冒着热气,都被农民们争先恐后地抢到了粪筐里。树叶柴草是家里必需的燃料。青草是猪牛羊的食物。粪便是庄稼的肥料,且可以给自己挣工分。如此一来,大地光秃秃的了,就只剩下庄稼和一些树木还在空气中孤独地摇摆。
同样干净的还有大家的一日三餐。说是三餐,其实,很多家庭都是吃两餐的。特别是家里的小孩子和老人,都在约定俗成地吃两餐,吃三餐的只有家里的男劳力,他们必须要有足够的体力和精神,才能挣回度日的工分。
响水公社石涧大队的地和人尤其干净。地干净就不说了,整个公社或者周边公社,都差不多。人呢?干净可以在穿着和餐桌上看出来。穿的,一年四季都是那一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样看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当家衣服。稍好的那件,就是逢年过节、走亲戚吃酒参加重大活动时,还是那一身轮流着穿。
大哥不说二哥,全都差不多。没有人笑话谁。穿戴虽然五花八门,长年累月的当家衣服,就成了家里的标志性服饰。应该说,说“单一”比干净更加恰当。比较统一的是脚,基本上都是光脚板。穿得起鞋的甚少,长年累月地赤脚,脚板宽大、脚趾有力,当然也造就了很多“实心脚板”,这样的脚板,是不能去当兵的。每到人群聚集的时候,再干净的地面,都会被各种稀泥巴弄得如冬水田,满地泥浆、满地脚板印。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妥,习以为常,无人抱怨。
最干净的要数餐桌。主食是红苕稀饭或者红苕干饭,红苕多米少,稀饭清汤寡水,干饭中少得可怜的米粒掩映在红苕中。红苕干饭不是随便吃的,“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大家约定俗成地遵守着这一定律。下饭菜是泡萝卜、泡青菜、泡海椒以及萝卜叶子、青菜叶子做的干盐菜,最好的当属大头菜……
每年的七八月,就是妇女们最忙碌的季节。她们要挣工分,要张罗一家大小的一日三餐,要缝缝补补,还要喂猪喂鸭喂鸡喂牛,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做盐菜,盐菜,又称咸菜。她们把萝卜叶子、青菜叶子洗净晾干,待干透后,再加水清洗,再晾干水汽,然后切碎,加上盐、海椒面搅匀装坛,几个月后,就成了下饭的咸菜。只有条件好的家庭,才在用餐的时候,把咸菜用少量的油炒一炒,如果加上油渣,这样的咸菜,就算待客,也是上品。
每到吃饭时间,大家都爱聚集在一起。聚在街沿上或聚在坝子里或站或蹲,只听得“呼哧呼哧”的吃饭声音和“嘎吱嘎吱”咀嚼咸菜的声音,没有统一要求,吃得却惊人的一致。萝卜叶子、青菜叶子是一成不变的,不用看,闻着味道就知道。不用看,也知道哪家的咸菜是用油炒过的,那带油的香味,可以盖过一切味道。为此,常有一些人,端着饭碗往油炒咸菜的人身边靠,期待着互相匀一勺咸菜尝鲜。
可以说,谁家条件怎么样,不用去看他家的猪圈、鸡鸭,也不用去看粮仓,粮仓都差不多,分下来的粮食,当宝贝一样地守着,就连人人喊打的耗子也没有办法,它们闻着粮食的味道干瞪眼,只能狠狠地咬粮仓的木头来解气。随便去哪家看看,被耗子咬过的地方,都带着血迹,甚至还有耗子的断牙,可见,为了一口粮食,耗子也是拼了。婚嫁不用调查走访,看一下下饭菜就知道。下饭菜的好坏,既是家庭条件的象征,也是检验这家人会不会过日子的凭证。
再普遍的现象,都是有例外的。这个例外,就是我们家。我父亲是人民教师,太阳晒不着、雨水淋不着,还有供应粮和固定工资,农村而言,这样“半工半农”的家庭,就有鹤立鸡群的意思了。每到一个月开供应粮的时候,很多社员就找到我父亲,希望开一斤或者两斤面条。
我们石涧大队主要产的是水稻、红苕、玉米,根本不种小麦。一是小麦产量低,二是种植小麦费工费时。因此,面条就显得尤为金贵。只有在过年过节或者来了贵客的时候,才煮一大碗面条出来作为下酒菜或者下饭菜。社员们需要面条没有其他途径和办法,就用稻米或者玉米到我家来换。我父亲的供应粮中,每个月可以开3斤面条或者面粉。有的社员为了吃面条,甚至到了不管不顾的程度。
我曾经见过社员们打赌吃面条。大队的七大汉是全公社、全大队公认的全劳力。每天挣的工分是11分。个子有一米八以上,体重在170斤。很多人想不通,人人都饿得面黄肌瘦,七大汉居然长了一个高个子。当然,个子高用力多,饭量就大得惊人,每天出工,刚到半上午,七大汉就喊饿了。全劳力的工分是10分,七大汉居然每天是11分,当然,对于七大汉多挣的一分工分,没有人有意见。重体力活路,比如,抬石头修渠、担稻谷交公粮,二百来斤的担子,其他全劳力看着都心惊肉跳,在他七大汉眼里,跟玩似的,唱着歌儿都完成了,真是不服不行。
不知道怎么的,有一天队里打谷,突然就说到了吃上,王登科自言自语,说,面条可能吃一斤没有问题。此时,大家站在稻田里,打稻谷、收稻谷、运稻谷、晒稻谷是最累的活路,早已经饥肠辘辘了,说到吃,就更加饿了。七大汉立即反驳:“吃两斤都没有问题!”王登科在心里掂量了一下,七大汉吹牛过头了。很多家庭都试过,一斤面条煮出来,可以够两个人吃,你七大汉再狠,一个人勉强吃一斤半,大家还是相信的。
王登科犟劲上来了。立时,开始了争吵。社员们在心里反反复复掂量,有的还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比画着肚子的大小和容量,慢慢得出结论,王登科会占上风。吵来吵去没有结果,队长罗凯说:“还争吵个卵,中午就搞一下,是骡子是马见见就晓得了!”
本来,在打谷的时候,由于劳动强度大、抢时间,各生产队安排了统一的甑子干饭做午餐。以前队长罗凯一声令下,都奔甑子去舀饭,哪怕是疲惫不堪,仍然健步如飞。但是,这天中午,大家吃饭或者叫抢饭的激情不高了,都把打赌吃面当成了百年不遇的喜事,重视程度竞远超那份甑子干饭。
在大家的商议和见证下,规矩是这样制定的:面条先由队里垫着,用5斤稻谷在我家先换两斤面条。如果七大汉能够吃完两斤面条,算王登科输,用面条去换的5斤稻谷,就在王登科家的应分口粮里扣除。如果七大汉输了,就输一天的工分给王登科。当然,如果按实际标准,11个工分是值不了两斤面条的,由于王登科自感胜券在握,所以,很干脆地答应了。
在30多人的见证下,开始了赌吃面条。由于煮面条没有任何佐料,七大汉提出了一个额外要求,那就是需要我家的小半碗大头菜,对于这个要求,队长罗凯出面,我爸爸妈妈欣然相送。水在锅里沸腾,周围站满了社员。大家还推来搡去地打趣,猜测着输赢,气氛很是融洽。只有七大汉和王登科两个人的心在紧张。七大汉便去了一趟厕所,一身轻松地开始了煮面:他先把大头菜倒进锅里,再把两斤面条煮下锅,立时,香气扑鼻,引得大家肚子咕咕叫。
七大汉把煮好的面条倒在一个脸盆里,就埋头开始狼吞虎咽,声音“呼哧呼哧”像拉风匣。一会儿,就下去了一大半。他故作轻松的样子,站起来,拍拍自己的肚子,很是自得地说:“争气!”面对众人,七大汉还故意把我家的大头菜嚼得“嘎嘣嘎嘣”响,大家闻着香气,跟着流口水,还没有忘记呼喊助威,七大汉在欢呼声中吃得越发起劲。王登科的侥幸心理在逐渐消失,脸也随之慢慢变色。七大汉吃完了,连续打了几个香喷喷的饱嗝。
“吃完了?”有不相信的就挤进来看,拿着脸盆看,盆里干干净净,连汤都没有剩一口。
七大汉拍拍圆滚滚的肚子:“再有2两就好了!”
都说,七大汉这身体,能吃能睡,壮如牛,活一百岁都没有一点问题!这个下午,生产队就热闹了。七大汉在田里和晒场走了一个下午,专门找重活路干,还去了三趟厕所,不时有饱嗝声音响彻一路。王登科两口子早已经打得四季花开,老婆先是哭,二斤面条,心尖尖都痛麻木了,继而,就开始抓王登科的脸,王登科自知理亏,没敢还手,就开始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地跑,老婆提着菜刀狠命地追!
队长罗凯望着天:“这都啥鸡巴事啊?”
不管怎么说,从此,七大汉就成了全大队的能人。比吃,第一;比挑重担,第一;比抬石头,第一……全劳力个个服气。在我们这些十来岁孩子的心中,七大汉就是英雄,就是人物,形象超过了解放军。他既让人敬,更让人害怕。有些小孩子不听话,大人就会说:“信不信,老子喊七大汉来收拾你!”孩子一下就老老实实了。
除了我家一年四季备有面条外,还有让大家嫉妒的就是我家的下饭菜。我妈妈特别能干,不但会做普通的萝卜叶、青菜叶咸菜,还会做大头菜。我们家的自留地里,除了萝卜青菜大葱蒜苗外,往往会种几十棵大头菜。大头菜的做法和其他咸菜的做法基本上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做起来工序要烦琐很多。大头菜进坛子后,要把坛子倒扣在水碗里,用竹片、稻草封住坛口,这样既过滤出了大头菜的水汽又隔绝了空气,大头菜才能又香又脆。无论是下饭,还是煮汤,还是作为任何食材的辅料,都是万能的。在全大队,种植大头菜的人,不超过30家。他们都把有限的自留地用来种植玉米、红苕了,以补贴工分不足而分粮不够带来的饥荒。
后来,包产到户后,生活渐渐好转,很多家庭都开始种植大头菜,再到后来,大头菜居然成了石涧大队的主要经济作物。
几十年后,光大头菜种植户,都有上百家,并由此发家致富。本来,大头菜作为下饭菜,我们家就与众不同了,更为不同的是,我爸爸每到领工资的时候,还会拿出一毛钱来叫我去公社供销社打(买)豆瓣作为下饭菜。那个时候,豆瓣还是稀罕物。农民们见过的多,吃过的基本上没有。豆瓣又叫胡豆瓣,或者豆瓣酱,通过把胡豆(有些地方叫蚕豆)加工发酵加盐加花椒海椒生姜等而成,本来是一颗胡豆,通过加工后,成了两瓣,汤色红红的、黏黏的,豆瓣软软的,入口即化。
发明豆瓣的本意是饭馆用作炒菜的佐料,我们家却另做他用。由于盐味较重,一碗干饭或者稀饭,一小勺豆瓣就可以解决。特别是吃面,只需要一小勺,面条就有盐有味了。
弟弟妹妹尚小,这样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的身上。每当这个时候,爸爸就把一个搪瓷口缸洗干净给我,我就去到5里外的供销社买豆瓣了,无须看秤,每次相同的钱,都在离缸沿三个指头的地方。爸爸也以此来判断,售货员是否少秤或者我在路上是否打倒过、摇晃出缸子过。去公社供销社,要翻越一座山,路窄坡陡。前几次,我没有经验,在返回的路上,用双手捧着搪瓷缸,不眨眼睛地盯着豆瓣,就看见豆瓣在缸里荡来荡去,赶忙停下脚步,待豆瓣平静后再走,没有走几步,又开始荡来荡去了。
后来,我慢慢地摸索出了门道,手把缸子端平,眼睛只看路,一脚一脚地走平稳,果然,豆瓣不再荡了,汤汁荡漾的高度,不会超过一个指头,这样我就能够足斤足两地把豆瓣带回家。这大概就是卖油翁的理论——唯手熟耳!
翻过山头,就看见七大汉一个人扛着锄头从山间走来。收工后,经常有社员扛着锄头在山里挖树篼用来做柴火。估计七大汉也是找了树篼下来。我想躲,但是被七大汉看见了,他喊:“柳大娃,端的啥子?”七大汉的声音和体魄都让我害怕,这一喊,就像用了定身法,让我不敢动弹。
七大汉走近我,从我手里拿过缸子,很是惊喜,毫不犹豫地就喝,“咕嘟咕嘟”的,我可怜巴巴地喊:“七俵爷,我回去要挨打!”
七大汉住了口,缸里只剩下了一半了,我的天,他一口气居然喝了七两下去。要知道,我是买的一斤半豆瓣啊!
这可怎么得了,让我回去怎么交差?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七大汉舔着嘴唇,咂巴着嘴,一时间也慌了。要知道,他这次惹着的是德高望重的柳老师,而且,他还是我爸爸扫盲班的学生。在面上在心里,对我老汉都是很尊重的。
别看他牛高马大,其实脑壳也很简单,经我这样一说,他开始为自己的一时冲动后悔了。他跟着坐下来,陪着我愁眉苦脸。
七大汉怯怯地问:“你家有秤吗?”
“没有!”
七大汉气壮了:“没有秤,咋晓得斤两不够?”
我气得号啕大哭:“没有长眼睛吗?我爸爸晓得应该到什么位置!”
我用手比画着:“刚才,豆瓣在这个位置!”
七大汉蒙了。试探着问:“要不,干脆加水!”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七大汉就带着我来到水田边,把水加到原来的位置。
回到家已是晚饭时间,爸爸妈妈吃着豆瓣,始终感觉不对头,我爸爸问:“怎么这么稀?”我眼泪巴巴,很无辜的样子望着我妈求救。我妈果然出手了,她说:“哪有那么均匀,有干有稀嘛!”
我妈妈一句话化解了危机,爸爸没有再纠结这个问题了。
第二天开始,七大汉就吃不下东西了,他老婆问怎么了,七大汉老喊:“心头烧得慌!”“肚子痛得厉害!”“屁眼上有火!”老婆就不断地给他喂水,喝进去,又吐了出来。七大汉还要喝,还连带着吐出了没有消化或者消化不了的海椒皮。
老婆问他究竟吃了啥子,七大汉一口咬定,啥都没有吃。老婆后来去请端公做了法事,七大汉仍然上吐下泻,不见好转。这样,在拖了半个月后,七大汉被活活地饿死了,享年40岁。
对于七大汉的死,有很多种说法,有说七大汉去山里撞了邪,有说七大汉饭量太大,是阎王来收他的,不然,他一个人吃了两三个人的饭量,别人就得饿死,还有的说,七大汉……
当然,更多的议论是“可惜了”,队长罗凯说,可惜了一个壮劳力。
七大汉老婆说,可惜了那么好的牯牛身体。
王登科最疑惑,能够吃下两斤面条、挑两百斤重担的人,怎么半个月后不声不响地就死球了?
只有我,从来不加入他们的议论。很多时候,我就望着家里的搪瓷缸子发呆。吃饭的时候,豆瓣一入口,就有想吐的感觉。
后来,爸爸工作调动,我们家搬离了石涧大队,后又离开了响水公社,那个令我家骄傲的搪瓷缸子,我悄悄地丢进了西河,爸爸妈妈没有发现,也可能发现丢失了,没有声张。
人生一世,经历的事情太多,丢失一个搪瓷缸子毕竟不是什么大事情,就好像这个缸子,在我们家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鸭脚
在石涧大队,我和罗二娃耍得最好。他既是我的同学,也是我们一个大院的伙伴。彼此两家之间,只夹着蔡姓一家人。我们院是个大院,住着20多户人家,房子挨着房子,就形成了一个院子。
在大院里,不相上下年龄的孩子有十来个,我们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割草,一起放鸭子,一起玩打仗的游戏,一起偷生产队的瓜……就算做作业,大家都在一起,我做好后,他们照着抄写一遍就行了。当然,那个年代,基本上没有啥作业,有的是时间供我们玩乐。
玩伴经常换。有时候是打仗,需要的人多,要有人演敌人,还要有人演特务,还有日本鬼子,就只能一起玩,大家端着自制手枪,或者随便拿一根木棍当枪,杀声震天地打得有声有色。
有时候是去下河洗澡,就只能两三个,人多要走漏风声,会挨大人打。有时候办“家家酒”,这就更加要挑选人了。
下河洗澡和办“家家酒”是大人最不能容忍的。前者有溺水危险,后者有失火引发山火的隐患。只要发现,大人们绝不姑息。但是,这两样却是我们的最爱。
所谓的“家家酒”,就是小孩子之间的打平伙。每到热天,上课就少了,说是农忙假或者是什么假,让大家回家帮着队里收割庄稼。
其实,我们回家后,大人们根本不要我们去队里,他们的看法是,我们是帮倒忙。我们呢,也乐得自在。再加上,大人们忙着收获,对我们无暇顾及,我们就成了一群胆大妄为的小鬼。
其中,最考验胆量的就是“家家酒”。
一般来说,办“家家酒”就只能三到四人,人多肯定要出事。每次核心人物,都是我和罗二娃。很多小伙伴都知道我们的秘密,想加入进来,我们就分期分批地每次喊两人,这样统筹兼顾,“家家酒”就成了我们共同的秘密。人多力量大,每到危险时刻,有了小伙伴的掩护,总能逢凶化吉。
之所以办“家家酒”乐此不疲,不是因为好玩,更多的是饥肠辘辘,找东西充饥。每天在家吃得清汤寡水,加上活动量大,一天中,超过一半的时间,肚子都在咕咕叫的状态。
在家里,我们不敢要求爸爸妈妈给我们吃什么,于是就自作主张去野外办“家家酒”。
要办“家家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要准备好炊具。这个最考验人,每个人的家里就那么几样锅碗瓢盆,眯着眼睛都知道放在什么地方,自然不敢偷出来。
因此这个任务通常交给罗二娃。他爸爸罗凯,队长当得好,公社奖励了一个很大的搪瓷缸子,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刚开始的时候,他爸爸经常端着这个缸子在人群里喝水,后来,或者是爱惜缸子,或者是感觉这样喝水和环境格格不入,或者是感觉没有拿碗瓢喝顺手,总之,改变了,他把缸子洗得干干净净放在了柜子里关着,隔几天拿出来看看。这就给了我们机会,罗二娃趁机偷出来用用。我们已经使用过两次了,都没有被发现。
其次,要准备必要的盐和火柴。这个我可以偷出来。我家的条件,显然比清苦的社员们要好一些,盐和火柴从来没有缺过。撕下一张作业纸,把盐包上就行。在火柴盒里,拿出三五根火柴就揣在口袋里了事。平时我们都收集了几个用过的火柴盒。
有了这两样,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半。我们四个人背着背篼,装着去给猪割草,或者给牛割草,就大摇大摆地出门了。这个时候,大人们都在饭后休息,在打百分,等太阳稍微温顺一点,就出工。
罗凯见了,夸奖道:“这几个娃儿今天还真勤快哟!”我们低着头,匆匆忙忙地往外走,打牌的人跟着说:“娃儿大了嘛,懂事了嘛!”
听见大人们的夸奖,罗二娃追上我,对我眨了眨眼。我们会心地笑了。
找了一个僻静的小山包,我们就开始分工合作。我负责挖灶和捡拾柴火,罗二娃负责带着其他两人去田里捉泥鳅和黄鳝。那个年月,田里到处都是泥鳅黄鳝和小鱼虾。特别是打谷时节,那些泥鳅黄鳝被社员们抓起来,直接甩在田埂上,到处都是干死的泥鳅黄鳝鱼虾,臭烘烘地围着一群苍蝇,看着都烦。这些东西腥味重,需要油和佐料来煎炒,谁家都不愿意吃。
我用三块石头垒了一个灶,把缝隙用泥巴捂住,免得漏风跑火,比了比缸子大小,刚好合适。又爬上一棵大树,砍了几根较粗的枯树干,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一会儿,罗二娃他们也回来了。背篼的底下,有几根泥鳅,有一条拇指粗的黄鳝。罗二娃喜滋滋地问:“怎么样?”
我们都笑。
接下来,就开始生火。这就比较谨慎了,我派了一个人上树放哨。在野外生火,如果被大人发现,会“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
罗二娃专门捡拾了一只很大的蚌。把壳搬开,就出现两片肥肥的蚌肉,我们都很兴奋,罗二娃扬扬得意地说:“炼油!”火燃烧起来,搪瓷缸子的水珠“滋滋”一响就没有了。我们学着大人做饭炒菜的样子,罗二娃马上丢进蚌肉,又“滋滋”几声,我们没有看见蚌肉炼出油,却看见缸子里冒出一股青烟。
罗二娃大喊:“糟了,快加水!”水倒进去,青烟熄灭了。我们一股脑地把泥鳅、黄鳝、盐倒进缸子里。水在翻滚,由清慢慢变白,一股香气也随之扩散开来。
树上放哨的着急地问:“好了没有?”我向他做了一个“下来”的手势,我们四个人就开始用竹签当筷子,在缸子里找吃的。
吃一口就在地上躺一会儿,望着天上的太阳,阳光从林间的树梢照射下来,中间是一根一根的光柱,特别漂亮。
闻着香气扑鼻,吃着却腥味很重,但是我们都说:“好吃!”
我们把泥鳅黄鳝吃完了,就躺在地上休息,开始谈理想谈人生。
罗二娃的理想是当队长,每年公社都要请队长们团年,吃一餐好伙食。他爸爸多次说过,以后让他接班。我的理想是当老师,像我爸爸一样成为国家人,家里有面条吃。张二毛的理想是开拖拉机,到处跑,到处吃好的……不管谁的理想,最大愿望就是有吃的,不被饿着。
正谈得热火朝天,突然有一股什么东西被烧焦的味道,大家连忙爬起来,原来,火并没有熄灭,熊熊大火还在起劲地烧着缸子,罗二娃首先奔向缸子,用镰刀把缸子提到地上,然而,为时已晚。
那个被他爸爸视为至宝的大号搪瓷缸子已经快报废了:缸子底部有点变形,周身的搪瓷被高温烤炸裂了,最惨不忍睹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服务”不见了,烧出了两个坑!
罗二娃忧心忡忡,大家跟着沉默,一起动手开始了亡羊补牢。罗二娃招呼我们去找来沙土,我们用这些沙土轮流着狠命地擦搪瓷缸子,以前两次我们也这样,把被烟熏黑的地方,擦几遍用水一冲,就看不出来了。这次却不一样,变形的地方,怎么都擦不掉。罗二娃试着给缸子整形正型,没有想到,镰刀石头一碰,就更加破落不堪。
罗二娃垂头丧气,我们也没有了好心情,就劝他:“你爸爸不会打你。”我们商量,罗二娃回家就坦白交代,不是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他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是家里唯一可以接班当队长的男人,平时爸爸妈妈都很惯着,气急了,最多嘴上骂骂,还从来没有动手打过。不像我们几个,三天两头的,不是被爸爸打,就是被妈妈打。
走投无路的罗二娃,被我们一劝,就听从了。当晚的结果,没有我们想象的轻松,也没有罗二娃担心的惨烈。罗二娃挨了打,打得不轻不重。脸上被他爸爸狠狠地扇了一巴掌,五个乌青的手指印,就像胎记。
罗二娃腮帮子痛了一个月,不痛后,乌青却留了下来,一辈子贴在了脸上。他的坦白,也顺便带出了其他三个人,我们三个人没有挨打,却挨了骂。骂得很有力,我妈妈还跳脚了,就差耳光响亮了。
这次“家家酒”的暴露,最大的损失是,我们以后再也不敢去办“家家酒”了,几个当事人的大人,以及所有大人结成了联盟,形成了一致意见,发现一个,收拾一个。不管是谁家的孩子,谁发现都可以下狠手!
罗二娃很哲学地总结:“真是好事不过三啊!”
自此,我们的行动,被置于大人们的监控之下,再没有了以前的自由。特别是夏天的中午,他们都要聚在一起打百分,让我们坐在周围不能乱跑。我们几个孩子感觉百无聊赖,先是到处看,哪家牌好,看了几把牌,就没有兴趣了。就你看我我看你,人人都愁眉苦脸。
大人们玩兴正酣,我们心里却像猫抓,心里慌,肚子也跟着咕咕叫。
罗二娃突然喊:“爸爸!”
队长罗凯拿了两个王四个二,很是兴奋,听见罗二娃喊他,就扭过头问:“想搞啥名堂?”
罗二娃捂着腮帮子,痛不欲生的样子,可怜兮兮地说:“想要5分钱!”罗凯把牌反扣在桌子上,盯着罗二娃。队长一扣牌,都停了下来。这个时候,罗二娃就成了焦点。
罗二娃吸着气说:“想去公社供销社买支圆珠笔,写作业用。”
罗凯伸伸脖子,像是良心发现,突然笑了:“好事情嘛,咋还不好意思了?”罗凯大声地招呼老婆:“给二娃拿5分钱!”
拿上钱,罗二娃就站起来要走,罗凯问:“现在就去?”罗二娃回答:“赶早不赶晚!”罗凯很是满意,罗二娃开始得寸进尺:“我想让柳大陪我一起去!”说完,就对我挤眼睛。
罗凯望望我妈妈,我妈妈大度地说:“去吧,早点回来!”
一离开大人,我们就自由了,飞快地来到公社街上。那天恰逢当场天,赶集的人还有一些,公社只有3条街道,最长的主街上最热闹,有供销社、有冰糕厂、有打铁铺、有饭馆、有理发店……
我们没有直奔供销社,而是优哉游哉地走过一家一家的店铺。路过饭馆的时候,一阵奇香。
罗二娃说:“进去!”我们来到店里。柜台上放着一个米筛,里面放着没有卖出去的小半边卤猪头肉和半只卤鸭子。香气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我们闻着香气,流着口水。这香气使我们的口水更加寡淡,还有一丝丝过夜的酸味道,自己都讨厌。
我们围着筛子看。罗二娃问:“猪头肉怎么卖?”
围着白围腰的店员回答了。
“我买5分钱的!”
店员用刀在猪头肉上比画了一下,说:“5分钱不好下刀,卖不了!”
罗二娃咽了一下口水,我也跟着咽了一下。他又转头看卤鸭子。店员明白了,就说:“5分钱只能买鸭脚,不过,我可以给你们多加点鸭腿上面的肉!”
罗二娃毫不犹豫地把5分钱给了店员。店员很认真,果真给了我们一只鸭脚,还有一小块鸭腿肉。罗二娃就讨过刀,把鸭脚一分为二,递了一半给我。
我们把鸭脚攒在手里,把紧握的手藏进裤兜,再没有心思逛街了,急匆匆地往回走。走到半山腰,四下无人,我们便坐在石头上,开始吃起来。鸭脚真香啊,我们先是闻味道,让鼻子过足瘾,然后再用舌头舔,让口腔过足瘾,最后才用牙齿轻轻地慢慢地咬,半只鸭脚,我们吃了足足一小时。吃完后,我们互相探头闻闻对方,香气萦绕。
罗二娃拍拍肚子:“老子以后有钱了,天天吃鸭子!”
这个时候,我又开始担心罗二娃了:“买的圆珠笔呢?”
“就说钱丢球了,”罗二娃揉着乌青的腮帮子,咬牙切齿地补充说,“不要我办家家酒,我给你读卵的个书!”
罗二娃读书确实不在行,平时作业都是抄我的,他爸爸也睁只眼闭只眼,还认为我是在帮助罗二娃。用他爸爸的话说就是“眼睛不抢字”,因此,他爸爸并没有要求他靠读书成才。这样一来,罗二娃没有任何学习压力。作业本和书本都像油渣一样,乱糟糟的。
我们心情愉快地往回走,我突然又发现了问题,我们身上的香味还在,连出的气息都是香喷喷的,怎么瞒得过大人。于是商定暂时不能回家,当务之急是清除香味。罗二娃建议下河洗澡,我们就去了堰塘,在泥地里滚来滚去的,互相闻闻,味道还有。
“妈卖麻花的,卤味道硬是厉害!”我们感叹着。
我又建议,我们去偷苦瓜吃,这个苦味可以改香味,我们去了几家人的自留地,吃了苦瓜、海椒,直到吃得肚子很不舒服才罢手,再互相闻闻,香味就淡了一些。
我和罗二娃手牵手地往家走。
……
三十多年后,当市委、市政府要求在全市找一些今昔对比、发家致富的典型人物和事例宣传宣传时,我突然就想到了石涧大队(此时已经改为村),虽然几十年再没有回去过,也失去了那里的消息,一有这个念头,那里的人和事居然很清晰,我想变化肯定是少不了的。作为日报的副总,我想亲自采写一篇典型报道。
报社的车经过3个多小时的行驶,终于到了石涧村。几十年不见,罗二娃一眼就认出了我,他也没有什么变化,特别是脸颊上的那块乌青,仍然存在着。罗二娃很是热情:“昨天晚上接到电话,一个晚上没有睡好!”拉着我往他家走,他现在住的是三层小洋楼,是全县有名的养殖专业户,专门饲养本地的麻鸭。
罗二娃带着我去他的养殖场看了一圈,就回来了,养殖场依一条小溪流建成,加了围栏,隔老远,都能听见鸭子“嘎嘎”的叫声,规模确实很大。
罗二娃老婆已经准备好了一桌丰富的全鸭宴,有老萝卜带丝鸭、卤全鸭、仔姜丝炒鸭脯……我伸手就把卤鸭脚扯下来递给罗二娃,他接了,腼腆地笑了。
老婆很惊奇。罗二娃就把鸭脚放在一边。
我明知故问:“怎么想起养鸭子了?”我带着不怀好意的笑,罗二娃脸红了。
罗二娃老婆插话:“刚开始时是养的泥鳅黄鳝,罗二娃是第一个搞养殖的!”
罗二娃很谦虚笑了:“赶早不赶晚嘛!”
我好奇了:“莫非养泥鳅黄鳝不赚钱?”
罗二娃老婆笑了:“养得再好,都不够他吃,他也舍不得卖,就自己吃!”
罗二娃老婆说着话,就把罗二娃的专用餐端了上来——爆炒鳝鱼丝、红烧泥鳅!
罗二娃老婆的厨艺特别好,全鸭宴的每个菜,味道都很合胃口,色香味一点不比城里大宾馆的差。我拿着另外一只鸭脚,示意罗二娃和我一起啃,没有想到,罗二娃却说:“不吃那个了,吃伤球了!”
我一愣,随即放肆地笑了起来。罗二娃也受了感染,捂着腮帮子跟着我笑,笑着笑着,我俩对峙,我们都发现,对方眼里有泪珠在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