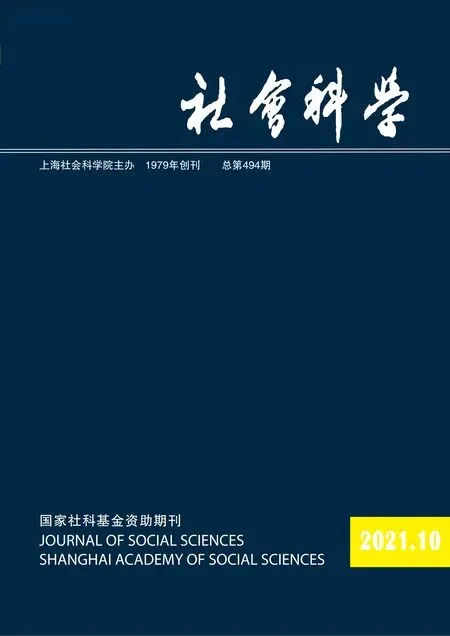真宗西祀探微:兼及盛唐至宋初的礼制改革
吕变庭 梁韵彦
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亲祀汾阴。这一事件与泰山封禅、圣祖降临等系列活动一道,在“澶渊之盟”后,昭示着北宋的“太平”景象。然而,自提请之日起,西祀就遭到了众多文人士大夫的非议。《宋史》对此评价极为负面,叹当时“一国君臣如病狂”。(1)(元)脱脱:《宋史》卷八,本纪第八,真宗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72页。学术界对此研究众多,不少沿袭北宋仁宗以后士人的观点,认为此系列事件源于真宗以“城下之盟”为耻,因强化自身“威权”而作政治表演,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北宋朝廷的“三冗”问题。(2)刘静贞:《威权的象征——宋真宗大中祥符时代(1008-1016)探析》,载《宋史研究集》第二十三辑,“国立”编译馆1995年版,第43-70页;张其凡:《宋初政治探研》,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256页;汪圣铎:《宋真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7-142页;杨高凡:《宋代“三冗”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3-173页。近二十年来,相关研究对真宗朝各类大型礼制活动的评价,由负面逐渐转向理解。有研究指出,“东封西祀”有“尊王攘夷”的政治目的,符合中古社会“神圣政治”的特性;(3)刘静贞:《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北宋前期》,(中国台北)稻香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129页;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11-326页;闫化川:《论宋真宗时期的“东封西祀”》,山东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亦有学者认为东封遵循了儒家经典中“易姓而王,太平必封泰山”的传统,能帮助强化真宗皇权的合法性;(4)张维玲:《宋太宗、真宗朝的致太平以封禅》,(中国台湾)《清华学报》2013年第3期;汤勤福:《宋真宗“封禅涤耻”说质疑——论真宗朝统治危机与天书降临、东封西祀之关系》,《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甚至有学者指出,史书中对于“天书”系列事件的非议,是仁宗朝以后的趋势而非真宗朝实况。(5)林鹄:《天书封祀补证——兼论仁宗以降对真宗朝历史的改写》,《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八辑,2018年,第293-305页。
真宗西祀前,河中府的父老乡亲曾多次祈请。已有学者指出,诸多祈请活动表明,真宗西祀符合当时社会各界的期盼。(6)何平立:《宋真宗“东封西祀”略论》,《学术月刊》2005年第2期。然而,目前学界对这股地方势力的关注甚少。 后土庙在中原北方地区的流行,以及后土圣母在佛、道神谱中地位的确立,主要发生在真宗朝以后。(7)韦正春:《中国古代“后土”形象的起源与嬗变》,《天府新论》2020年第2期;沈旸、布超、于娜:《山西后土庙建筑遗存探析》,《兰州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9月;尹虎彬:《河北民间后土地祇崇拜》,学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1页;萧登福:《后土地母信仰研究》,(中国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93-137页。在这一神灵崇拜的发展过程中,汾阴后土祭祀圈内的地方势力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从这一人群的角度出发,或者能为理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是故,本文将以微观视角考察地方社会对于西祀活动的参与,以此探讨由唐入宋以后王朝礼制因应社会变革所做出的调整,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场“闹剧”背后的历史因由。
一、汾阴的战略地位与真宗朝堂的南北势力之争
汾阴后土之祀,可以追溯到西汉,但历史上亲祀后土的皇帝却不多。唐宋时期,帝王多数在都城北郊祭地,仅唐玄宗与宋真宗曾亲祀汾阴。从礼制的仪式过程到政治动机,真宗西祀的重要参考对象为唐玄宗的三次亲祀。
玄宗重视西祀,与汾阴在唐朝的重要战略地位有关。开元十一年(723),玄宗自东都洛阳北巡,幸太原,在还京途中幸汾阴、祠后土,改汾阴为宝鼎县。(8)(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八,本纪第八,玄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5页。宝鼎县地处蒲州,是河东地区与关中平原之间物资运送的重要通道,亦是唐首都长安的重要军事屏障。(9)牛忠菁、冯俊:《唐宋时期河中府的迁革》,《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供奉后土祠的脽上,地处汾河与黄河交汇处的高地,无论从军政抑或五行风水的角度,皆具特殊地位。(10)唐玄宗御制的《后土神祠碑并序》称:此地“汾水合河,梁山对麓,地形堆阜,天然诡异”。《后土神祠碑并序》,载(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八七八,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634-4635页。玄宗开元八年(720),朝廷改蒲州为河中府;同年,罢中都,仍为蒲州。十二年(724),即玄宗亲祀后土后的第二年,朝廷将蒲州升为“四辅”,与同州、华州、岐州共同拱卫京畿。(11)《旧唐书》卷三十九,志第十九,地理二,第1469-1470页。张九龄在《后土赦书》中对玄宗祀后土于汾阴有这样一段叙述:“故勒兵朔陲,先展义于枌社。迴旌脽上,遂有事于郊坛。”(12)(唐)张九龄:《后土赦书》,载(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六十六,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73页。天子巡狩,除祭享神明之外,对外展示王朝军事实力,对内巡视战略要地以及犒赏军民,都是其中的重要动因。实际上早在唐朝建立之初,蒲州就已经成为了唐朝的军事战略要地。唐高祖李渊建国后,每有攻伐,常陈兵蒲州,或作援军,或防外患。(13)《旧唐书》卷一,本纪第一,高祖,第10、11页。玄宗亲祀汾阴的做法与唐高祖幸蒲州、命祀舜庙的举动相似,带有视察以及慰问北境军民的目的;因而在唐时,帝王亲幸汾阴,其所受到的阻力要远比宋真宗时少。
唐代的蒲州,即宋代的河中府。真宗西祀亲临的后土庙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重修的。重修以后,太宗命河中府每年岁时以中祠礼致祭。(14)(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3,礼二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7页。然而,对于定都开封的北宋王朝,河中府作为京师屏障的意义大为减弱,且开封距离汾阴路途遥远。这就成为了北宋大臣孙奭反对真宗西祀的重要原因。他在大中祥符四年上疏的八项谏议中,点明了唐宋时期河中府地位的差异,疏曰:“河东者,唐王业所起之地,唐又都雍,故明皇间幸河东,因祀后土,与圣朝事异。今陛下特然欲祠汾阴,其不可五也。”(1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六册,卷七十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00页。
史书未载真宗对孙奭的回复,但在北宋与西夏的对峙中,河中府作为物资与人员调度的枢纽地位仍非常重要。景德三年(1006),与辽及西夏签订和约后,真宗即诏西边州军仅留屯戍量步兵,其余屯河中府、鄜州、永兴军就刍粟。(16)《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五册,卷六十四,第1429页。仁宗康定元年(1040),与西夏的战事又起,朝廷欲用兵陕西,知延州范雍随即上言:“宜令大臣以重兵守永兴军、河中府。”(17)《续资治通鉴长编》第十册,卷一二六,第2979页。可见,河中府作为陕西的后援,在与西夏的军事对抗中有重要作用,宋夏间的任何摩擦,都直接反映在此地的兵丁调配中。那么,真宗时在此地举行带有“尊王攘夷”之意的西祀活动,其巡视与展示军事力量的意图,恐怕是当时不少大臣赞成这一活动的重要原因。寇准的《和御制祀后土》对于帝王西祀的队伍就有这样的描述:“箫鼓闻脽上,旌旗过渭滨。天声惊远野,兵气慑边邻。”(18)(宋)寇准:《和御制祀后土》,载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二册,卷八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96页。
大中祥符年间的东封西祀能够顺利进行,与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尧叟等一批南方官员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根据任爽的研究,北宋统一全国后,继承了唐、五代以来南北地方势力的矛盾,并将这种矛盾带入统治集团内部;寇准与王钦若的矛盾,有这两股势力博弈的因素。(19)任爽:《唐宋之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地域特征》,《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在景德元年(1004)宋辽之间的战和问题中,这一矛盾表现得尤为明显。面对辽军主力,王钦若、陈尧叟力劝真宗幸金陵或成都,而寇准“心知钦若江南人,故请南幸,尧叟蜀人,故请西幸,乃阳为不和,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又以留守北方“将臣协和”“庙社所在”,力主帝王亲征,并前往交战的最前线。(20)《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五册,卷五十七,第1267页;《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列传第四十,第9530页。这件事以王钦若自请离开中枢,判天雄军府结束。但朝中南北势力的博弈,似乎并没有因王钦若离开中枢而结束。景德二年十二月,王钦若因与寇准不和,请罢参知政事。然而,真宗却并不想让王钦若就此离去,设资政殿大学士安置王钦若。(21)《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五册,卷六十一,第1376-1377页。战争的胜利使寇准的声望达到最高点,(22)徽宗朝时,右正言陈瓘尤言:“当是之时,若无寇准,则天下分裂久矣。”(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第一册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可是,作为北宋帝王的真宗皇帝,对于这位素有威望且深得北方政治势力拥戴,但行事却有些跋扈的宰相,还是有所忌惮的。而且,面对和约以后较为安定的社会,北宋朝廷也有理由更换一种执政风格。景德三年(1006)二月,寇准罢相,出知陕州;此后,王旦拜相,王钦若升任尚书左丞,与陈尧叟同在中枢。(23)《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五册,卷六十二,第1389-1390页。在之后的东封西祀活动中,南方籍的官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因直接参与“天书”系列事件,在后世被诋为“五鬼”的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全部出身于南方地区。根据《宋史·列传》,王钦若为临江军新喻人;(24)《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列传第四十二,第9559页。丁谓为苏州长洲人;(25)《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列传第四十二,第9566页。林特祖揆,家南剑州顺昌;(26)《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列传第四十二,第9564页。陈彭年为抚州南城人;(27)《宋史》卷二百八十七,列传第四十六,第9661页。刘承规为楚州山阳人;(28)《宋史》卷四百六十六,列传第二百二十五,第13608页。此外,被真宗委任为祀汾阴经度制置使的陈尧叟,为阆州阆中人。(29)(宋)王称撰,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东都事略》卷四十四,列传二十七,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344页。然而,这些南方籍官员得到重用,并不意味着北宋朝堂中,北方官员占主导地位的情况有所改变,抑或南方地区的重要性有所增加;相反,为提防随时可能反扑的辽与西夏,北宋王朝尚需要依靠西北诸路军民的大力协作。因此,在真宗西祀的过程中,主要事务由多位南方官员负责;然而,河中府及周边的父老、士子们却在其中得到了各种封赏与优待。而真宗本人亦藉此活动,展现出了对陕西、河东诸路,及西北边境前线军民的关怀,消弭了宋辽战争中因朝廷曾考虑南迁所带来的不良影响。那么看来,真宗当时重用这批南方官员,在重要战略枢纽施恩乡民,弱化权臣,重塑圣君形象,以此作为一种制衡朝堂的手段,是有可能的。
二、真宗西祀前后的君民互动
对于儒教国家的统治者而言,举行泰山封禅、汾阴祀后土这一级别的国家大礼需要充分的理由;而民间奏报的祥瑞以及百姓的祈请,正是天下太平的明证,可以作为重大礼制活动开展的依据。与唐玄宗西巡相比,真宗西祀前,来自民间的祥瑞奏报以及请祀活动纷繁而有序,正反映了其背后有朝廷主导的因素;而以河中府为中心的地方社会,对来自中央的诱导,进行了积极的回应。
(一)祥瑞奏报
在真宗即位至西祀前,河中府及周边的民众曾多次向中央反映有祥瑞出现。仅史册记载的就包括:咸平四年九月,知河中府献《嘉禾合穗图》;五年八月,临汾县嘉禾合穗;(30)《宋史》卷六十四,志第十七,五行二下,第1401页。大中祥符元年八月,宝鼎县嘉禾合穗;(31)《宋史》卷六十四,志第十七,五行二下,第1402页。十月,河中府酒厨梁上生玉芝;(32)《宋史》卷六十三,志第十六,五行二上,第1389页。大中祥符三年八月,解州池盐不种自生,东池水自成盐;(33)《宋史》卷六十二,志第十五,五行一下,第1361页。九月,有云物之祥;(3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四,第1689页。十月,河中府民报告山谷中藏有帛书;(3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四,第1691页。十一月,宝鼎县黄河清;(3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四,第1696页。十二月,宝鼎县黄河再清;(3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四,第1696页。大中祥符四年二月,有黄云随天书辇,宝鼎县瀵泉涌,有光如烛;(3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五,第1711页。祭后土时,司天言:“黄气绕坛,月重轮,众星不见,惟大角光明”;(3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五,第1711页。十一月,河中府献芝草;(40)《宋史》卷六十三,志第十六,五行二上,第1390页。六年冬,大宁庙圣制碑阁生金芝;(41)《宋史》卷六十三,志第十六,五行二上,第1391页。七年十月,大宁庙石双茎芝生。(42)《宋史》卷六十三,志第十六,五行二上,第1391页。其中,大中祥符年间的祥瑞奏报更为频繁,且等级更高。
这一系列祥瑞的奏报与查验,需要经过州县乡民及朝廷各级官员间的鼎力合作。在参与的人当中,祀汾阴经度制置使陈尧叟与经度制置副使李宗谔,作为朝廷大员,直接受皇帝的委派,是真宗西祀的重要执行者;知河中府郭尧卿、通判曹谷、屯田员外郎何敏中等人为河中府的地方官员,在上报与查验祥瑞的过程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河中府民巨沼、临汾县民吉遇、洪洞县民范思安、宝鼎县民张知友等是祥瑞的发现者,事后得到了朝廷的封赏,并名留史册。可见,在祥瑞奏报的过程中,朝廷中枢机构的高级官员、地方低级官吏以及乡民连成了一张由中央延伸至地方的关系网络,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奏报活动的利益相关者。
这些祥瑞出现的次序以及种类是经过精心编排的。根据《唐六典》:“庆云”“醴泉”与“河水清”属于“大瑞”;而“嘉禾”与“芝草”属于“下瑞”。(43)(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尚书礼部卷第四,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14-115页。上述祥瑞中,“大瑞”的出现集中在大中祥符三、四年,即真宗西祀前后,在这段时间之外,河中府报告的祥瑞皆为“下瑞”。此外, “黄云随天书辇”和“瀵泉涌,有光如烛”等祥瑞,与唐玄宗亲祀前“黄云盖于神鼎”(44)(唐)张说:《后土神祠碑铭并序》,载(宋)姚铉编《唐文粹》卷第五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1页。及“荣光出河”(45)(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上,卷七十六,郊社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96页。等记载有一定的相似性,反映真宗西祀有继承唐代政治传统的意味。还有不少祥瑞象征了上天对帝王的认可,如:巨沼所献的“帛书”埋藏地下,与天书相对,为帝王亲祀后土的合理性提供了直接依据;(46)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48页。“大角光明”表明“王者敬诸父有善”;(47)《开元占经》中“王者敬诸父有差”应为“王者敬诸父有善”。(唐)瞿昙悉达,常秉义点校:《开元占经》卷六十五,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9页;(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八,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4页。而“黄河清”则是“圣人生”的瑞应。(48)(魏)李萧远:《命运论》,载(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五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页。由此可见,此系列事件的编排出自谙熟儒家经典的士大夫之手;多数乡民是参与者,而非策划者。
(二)请祀与助祭
祥瑞的奏报可能仅需鼓动小部分的乡民,但对帝王亲祀的祈请与迎接,则需要地方各界人士的广泛配合。与东封泰山一样,真宗西祀的直接原因,是河中府父老、僧道的祈请。东封后第二年,知河中府杨举正言:“得本府父老、僧道千二百九十人状,请车驾亲祀后土”。(49)《续资治通鉴长编》第六册,卷七十三,第1673页。七月,河中府进士薛南又联同文武官、将校、耆艾、道释三万余人诣阙,请祀汾阴后土。(50)《续资治通鉴长编》第六册,卷七十四,第1681页。
在这一系列的请祀活动中,地方官员知河中府杨举正以及河中府进士薛南作为父老、僧道群体的带领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真宗更因薛南的带头诣阙请祀,用为试将作监主簿。(51)《宋会要辑稿》第三册,礼二八,第1294页。薛南在地方的号召力,与河东薛氏在河中府的声望有关。河东薛氏有“蜀薛”之称,其宗族是蜀汉灭亡之后,迁往汾阴的。(52)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126页。历两晋南北朝,汾阴地区的薛氏西祖房因祖居之地有盐池,积累了雄厚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成为河东地区的豪强大族。隋唐时期,薛氏家族已进入统治集团,并保持着较高的任官比例。(53)许蓉生、林成西:《河东薛氏研究——两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豪强的发展道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1期;刘淑芬:《北魏时期的河东蜀薛》,载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281页;张晶:《中古时期河东薛氏研究》,西北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李晶:《隋唐时期河东薛氏家族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虽然在初唐,薛氏西祖房因所参与政治集团斗争的失败而走向衰落,但河东薛氏仍为河中府的一股重要地方势力,直到两宋时期家族成员仍屡屡入仕。北宋太宗朝时的薛奎、薛颜,真宗朝时的薛田,南宋孝宗时的薛叔似等,皆属河东薛氏。(54)《宋史》卷二百八十六,列传第四十五,第9629页;《宋史》卷二百九十九,列传第五十八,第9943页;《宋史》卷三百一,列传第六十,第9987页;《宋史》卷三百九十七,列传第一百五十六,第12091页。
薛南、杨举正、氐昭度之外,大量河东及陕西地区州县的官吏及士人亦对西祀持欢迎态度。真宗西祀之后,河东及陕西地区的村落间,乡民们自发创建或重修了众多的后土行祠。这些庙宇的营建有地方州县官员或士人的直接参与。其中,天禧四年(1020),乡贡进士裴仅为万泉县新建的后土庙撰《河中府万泉县新建后土圣母庙记》一文,题记显示该县县令杨德润及多位杨姓胥吏参与营建。(55)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三十八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此外,乡贡进士郑滋于元祐七年(1092)为新落成的晋州洪洞县后土庙撰《大宋晋州洪洞县重修后土庙记》;(56)(清)孙奂仑修,韩坰等纂:《洪洞县志》卷十五,载《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区第七十九号,(中国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306页。政和二年(1111),解州上舍贡士武镐亦为陕西大荔县的后土庙撰《重修后土庙叙文碣》。(57)(清)周铭旂修,李志复纂:《光绪大荔县续志》卷八,载《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20,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25页。参与撰文或营建活动的裴氏、杨氏、武氏皆属河东地区颇具势力的族群。其中,河东裴氏作为隋唐时代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有“三河领袖”之誉,势力范围遍布河内、河东、河南。(58)周征松:《河东裴氏及其族源》,载《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83页。这一世家虽随唐朝灭亡而退出统治集团,但在宋代的河东地区仍保持了其家族世系,家族成员亦屡屡凭借科举入仕。(59)中共闻喜县委宣传部编:《中华宰相村》,中国发展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5页。而河中府及河东地区的杨氏,则为弘农杨氏的上谷房分支。杨氏为隋朝国姓,该分支在唐代为宰相者有三人,入宋后入仕者众多。河东杨氏更以将才著称,其族子弟包括杨业诸子及杨宗闵等人。(60)谢婧:《北宋陕虢杨氏家族的播迁与生存发展》,上海师范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6-36页。
隋唐时期的世族弟子,在门阀制度彻底衰亡的北宋,积极入仕,并凭借地方官吏或士人的身份参与到宋代的国家及地方祭祀活动中。这一现象反映了真宗西祀能够获得地方社会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地方豪族与底层官吏期待通过参与请祀及助祭活动,彰显其特殊地位,巩固个人及宗族在该地区的声望。真宗西祀后,山西与陕西地区官吏及士人所建的后土祠庙香火极为鼎盛,直至明清时期,其祠庙数量亦远较其他北方省份为多。这一现象,正从另一角度说明:后土祠庙的祭祀,与河东地区地方势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宋初汾阴后土的祭祀等级与供奉形式之变
唐宋两朝皆将地神称为“皇地祇”。北宋自太宗时起,就在都城北郊祭地,而在汾阴脽上以中祀礼祭后土;直到真宗景德四年(1007),才改以大祀礼祭汾阴后土。(61)《宋会要辑稿》第三册,礼二八,第1287页。祭祀等级的变革,不单关乎祭礼的规模,同时亦反映帝制国家对于祭祀对象性质与重要程度的判定。然而,宋初后土庙祭祀等级提高的同时,伴随的却是后土祭祀仪式中民间祠庙性质与道教气息的增强。
中原帝制国家祭祀的分级,源自《周礼》。然而,《周礼》谈及春官肆师之职时,仅言及大祀、次祀、小祀所用牺牲的差别。对此,郑司农解释认为:“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郑玄再注,谓:“大祀又有宗庙,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岳,小祀又有司中、风师、雨师、山川、百物。”(62)(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第十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9页。而在《大唐开元礼》的序例中,祭祀等级的划分沿袭了此二者的说法,并进一步细化。(63)(唐)萧嵩等撰,周佳、祖慧等点校:《大唐开元礼》卷第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大体而言,其国家“大祀”的划分沿袭了《周礼》的原则,祭祀范围非常狭窄,仅包括天、地二祭与帝王宗庙,这一原则在宋代仍有纲领性作用。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唐宋两代的帝王都会因应各自的政治需要及政府财政状况,调节诸神的祭祀等级,如: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就将日月五星升为大祀;(64)(宋)王应麟撰:《玉海》第四册,卷第九十九,合璧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1876页。宋高宗绍兴初,曾将五帝、神州、蜡祭等十三祭归为中祀,绍兴二十七年(1157)又复为大祀。(65)《玉海》第四册,卷第一百一,第1922页。玄宗以后,儒家“三祀”制度的涵盖范围有扩大趋势,不少民间祭祀被逐步纳入国家礼制系统中。根据朱溢的研究,北宋太祖至英宗时期,被划为“大祀”的祭祀对象包括:昊天上帝、感生帝、五方上帝、九宫贵神、五福太一、皇地祇、神州地祇、太庙、皇后庙、景灵宫、朝日、高禖、夕月、社稷、蜡祭百神、五岳;皇地祇虽属“大祀”,但未有明文将后土之祭纳入“三祀”制。(66)朱溢:《唐至北宋时期的大祀、中祀和小祀》,(中国台湾)《清华学报》2009年第2期。
真宗用“大祀”礼祭后土,是因为其将汾阴后土祠视为地神皇地祇之原庙。谈及西祀的必要性时,真宗诏:“前史所谓郊天而不祀地,失对偶之义也。”(67)《宋会要辑稿》第三册,礼二八,第1288页。然而,从太宗皇帝命河中府依先代帝王用中祠礼祭后土的情况可以看出,在宋初士人的眼里,汾阴后土庙的祭祀与诸州的岳镇海渎是同等级别的。脽上后土庙是地方祠庙,尚不能与帝王亲临的天地大祀同日而语。在真宗以前,北宋王朝认可的祭地仪式亦仅为北郊方丘的皇地祇之祭。这种认知可见于孙奭反对真宗亲祀的谏议,文曰:“古者圜丘方泽,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汉初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无祀,故武帝立祠于汾阴。自元成以来,从公卿之议,遂徙汾阴后土于北郊。后之王者,多不祀汾阴。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远祀汾阴。其不可三也。”(68)(宋)孙奭:《谏幸汾阴》,载吕祖谦编《宋文鉴》卷第四十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汾阴后土之祀,虽有汉武与玄宗先例,但“事不经见”,与北郊祭地意义重复,因而在孙奭看来帝王亲祀并无必要。
而依神像的供奉形式及坛位布局来看,汾阴后土之祀与北郊祭地,源自两种截然不同的神灵崇拜模式。宋初的北郊制度奠基于太祖时期,根据乾德元年(963)的诏书,祭祀皇地祇的方丘因循唐制营建,设在宫城北十四里。(69)《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册,卷四,第101页。根据《大唐开元礼》,方丘为一处祭坛,坛上设“神座”以表现诸神形象,其文曰:“设皇地祇神座于坛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设高祖神尧皇帝神座于东方,西向,席以莞。设神州地祇神座于第一等东南方,席以藁秸……”(70)(唐)萧嵩等撰,周佳、祖慧等点校:《大唐开元礼》卷第二十九,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7页。这种设神位而祭的做法更符合儒家理念。根据古礼,祭祀中参拜的对象为抽象的木主或虚位的神座,而非人格化的偶像。这一悠久的上古传统在唐宋时期的大部分天地祭祀活动中得到延续。
与北郊的方丘不同,脽上后土庙中供奉的是人格化的后土塑像。西汉中期以后,国家祭祀中的山川神已有被制作成偶像的例子,并因为于礼不合,遭到了一些士大夫的批判。(71)吴丽娱主编:《礼与中国古代社会》隋唐五代宋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5页。而后土神人格化的趋势可追溯至唐代(72)李玉洁:《汾阴后土祠神灵形象演变探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廖奇琦:《晋中南地区后土图像流变及原因述论》,《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9年第4期。。在佛教文化的浸染下,设像而祭的供奉方式在唐五代的宫观、祠庙中兴起(73)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0-42页。。唐宋时期后土神形象的出现,离不开民间的后土夫人崇拜。在宋初成书的《太平广记》中,韦安道初见后土夫人时,以为是“天后游幸”。对于后土夫人的衣着、相貌,故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伞下见衣珠翠之服,乘大马,如后之饰,美丽光艳,其容动人。”书中又称,后土夫人的眷属包括:四海之内岳渎河海之神、诸山林树木之神、天下诸国之王。(7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九,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375-2379页 。在此,后土眷属与《开元礼》中皇地祇的配祀一致,但诸神对后土夫人的朝拜却被描绘得如同帝王朝会。这种理解影响到了真宗时期礼院对后土庙像设的安排。大中祥符二年(1008)正月,礼院制后土庙衣冠时即上言:“《礼令》不载后土衣冠之制,今请用皇后礼衣修制。(75)《宋会要辑稿》第三册,礼二八,第1287页。”但以皇后之礼供奉后土神的做法,在真宗以后却遭到了怀疑。陈旸在《乐书》中指出:“(汾阴后土庙)大中祥符中,诏用皇后礼。然黎民所食者,土神而已。以后礼祭之,臣恐未合礼制也。”(76)(宋)陈旸撰,张国强点校:《祭后土》,载《〈乐书〉点校》卷一百九十一,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014页。更多宋代的文献则对《太平广记》所录的这则故事持怀疑态度,认为此不过是“唐人记后土事,以讥武后耳”。(77)(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八,人民文学出版1962年版,第126页。
事实上,真宗时期的汾阴后土庙布局可能比故事中的描述更不符合古礼,而带有浓重的道教气息。大中祥符年间的汾阴后土庙,在后土殿之外还有“司命天尊殿”;后土殿内设后土圣母圣像,曾诏选道士焚修。(78)《宋会要辑稿》第三册,礼二八,第1294页。而根据刻于金天会十五年(1137),明天启三年(1623)重刻的《蒲州荣河县创立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庙像图》,汾阴后土庙中还设有二郎殿、判官殿、五岳殿、六丁殿、真武殿、六甲殿、五道殿。(79)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161页。这些殿阁供奉的神祇均可在道教神谱中找到对应。此外,真宗祭后土时所用的玉牃、玉册,有“通仙”意味,延续了汉武帝与唐玄宗时封禅的传统,(80)吴丽娱:《汉唐盛世的郊祀比较——试析玄宗朝国家祭祀中的道教化和神仙崇拜问题》,载孙家洲、刘后滨主编《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7页。亦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
综上所述,真宗重修后土祠,在殿阁中供奉人格化的后土神,并亲临祭祀,以大祀礼祭之,这一事件本身已经带有国家礼制向民间祠祀及道教信仰妥协的味道。
四、效法唐玄宗的礼制改革
真宗西祀是参照唐玄宗亲祀汾阴而进行的一次国家大礼。“澶渊之盟”后,北宋的对外战争暂告一段落,依照儒教国家的惯例,此时需要一系列的仪式活动及相关典籍的编修,树立天水一朝作为中原王朝正统继承者的形象。而唐玄宗基于帝制国家现实对古礼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正符合了宋真宗这位将宋朝带入“文治”之世的君王所想。
作为武周以后李唐王朝的实权继任者,唐玄宗对国家礼制进行了改革,把九宫贵神、老子等诸多道教神祇与崇拜形式带入国家礼制体系,并以帝王身份亲祀汾阴后土庙。玄宗的这些改革,有推翻武则天与韦后时期崇佛政策的政治动机,同时亦希望藉此为自身祈求长生不死。(81)Victor Xiong, Ritual Innovations and Taoism under Tang Xuanzong, T’oung Pao, Vol.82, 1996, pp.258-316.吴丽娱更指出,玄宗礼制改革的重点是将道教祭祀与国家礼制融合,使其正当化与经典化。(82)吴丽娱:《汉唐盛世的郊祀比较——试析玄宗朝国家祭祀中的道教化和神仙崇拜问题》,载《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2-37页。
随着佛道信仰的滥觞,唐人已逐渐相信,统治者以帝王之尊进行祭祀,可福泽万民。开元十年,在亲祀后土的前一年,玄宗皇帝曾下诏指出:其亲祀后土是“欲为人求福,以辅升平”。(83)《旧唐书》卷第二十四,志第四,礼仪四,第928页。真宗西祀前,亦强调此行有“冀民获丰穰”的目的。(84)《宋会要辑稿》第三册,礼二八,第1288页。但这种强调国家“大祀”是为民祈福的动机,有别于儒家“三礼”的原意。其信仰逻辑强化了“君”与“民”两极的互利关系,而淡化了“诸侯”这一先秦礼文中的重要角色;与之相随,申明等级差别不再是国家礼制活动的核心,祭祀作为天子特权的意义亦被削弱。
先秦经典所述的礼教原则是服务于分封制的。其祭祀仪式的相关规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厘定诸侯与天子的权力范围,使其互不僭越,以帮助周天子实现“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其“三祀”制也不例外。对此,《礼记》“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祭法”则谓:“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85)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王制第五,祭法第二十三,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59、885页。大体而言,普天之下皆是天子之“望”,天子既可巡狩,亦可望祭;诸侯却要遵守分地而祭、祭不越望的原则。
这种观念到了施行郡县制的时代,就失去了其原有意义。唐宋礼典中对于“三祀”制度祭祀者的划分,从分封的各级诸侯,变成了中央或地方的各级朝廷命官。大体而言,中祀和小祀由各州县的地方官员负责,如:“(天宝)四载敕风伯雨师并依升入中祀,乃令诸郡各置一坛因春秋祭社之日同申享祀。”(86)(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三十三,帝王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63页。而大祀则需要由皇帝委任的常参官前往,如:“(仁宗景祐元年)礼官议曰:‘……昊天上帝、太庙二祀,太尉则中书门下摄,司徒、司空以尚书省五品摄。余大祀,太尉以尚书省四品、诸司三品摄,阙则兼五品。宜从令文定制。’诏自今夏至祭皇地祇,遣大两省以上官摄事。”(87)《宋会要辑稿》第三册,礼二八,第1294页。当祭祀成为了受皇帝任命的各级官员之职责,祭祀级别的差异与“地望”的关系就变得越发模糊,宋代士人对于民间信仰中的“神灵越界”现象也越发宽容。(88)皮庆生:《经典的重新解释:从合法性到有效性——宋人对神灵越界现象的回应》,《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2期。
随着制度的变革,帝王宗庙及天地大祀不再作为天子的专属祭祀对象而被强调。较之通过划定祭祀范围防范诸侯僭越的举措,盛唐至宋初的君王似乎更想通过制定一体化的祭祀系统将帝制君王的权威传遍王朝的每个角落。
李唐王朝将老子封为“太上玄元皇帝”,至玄宗开元二十九年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要求在庙中设玄元皇帝真容像,及侍立左右的玄宗、肃宗真容。(89)(唐)王泾:《大唐郊祀录》卷九,载(唐)中敕《大唐开元礼》,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88页。在此,供奉老子及肃宗、玄宗像的玄元皇帝庙,虽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但与太庙的性质相同。当然,这些遍布天下的庙宇,大部分无需帝王亲祀。其更重要的作用是象征皇家的形象,在王朝权力所到达的地方,接受官员与部分民众的朝拜。时至宋代,这一传统得到延续并成为通例。宋代朝廷在各州寺庙或道观建造神御殿,奉安先代帝王御容,(90)《宋会要辑稿》第二册,礼一三,第717-740页。接受四方香火。
除此之外,北宋真宗朝以后,朝廷批准各地建造东岳及后土庙,这一举措直接打破了古礼对于百神祭祀区域的限制。明代的《东岳行宫泉石记》云:“宋真宗祥符九年,有事泰山,岳神效灵。诏天下郡县悉建东岳行宫。”(91)(明)田艺蘅:《香宇集》续集卷十九,《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这一诏令缺乏宋代文献佐证,但东岳庙在全国各地的流行,的确始于真宗封禅后。根据周郢对《大宋忻州定襄县蒙山乡东霍社新建东岳庙碑铭》的考察,大宗祥符三年(1010),真宗以东岳地遥,晋人难以致祭为由,“敕下从民所欲,任建祠祀”;从此,东岳庙在北宋全境内兴起。(92)周郢:《东岳庙在全国的传播与分布》,《泰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即使在宋代士人的眼里,允许各地建东岳祠的做法仍是有违古礼的。这点在南宋时期韩元吉所撰的《东岳庙碑》中已被提及,其文曰:“三代命祀,齐鲁大邦,得以望而致祭,非其地也。他诸侯虽礼备莫敢越焉。自秦汉一四海,无有远迩,毕为郡县。凡山川不在其境,祷祠之盛,犹或举之,而阴骘降监庙而徧天下者,亦惟是东岳为然。宋兴三叶,升中告成,册以帝号,由是冠服宫室,率用王者之制。盖古者以神事山川,以鬼事宗庙,其曰岳渎视公侯者,特其牲、牢豆笾等用而已。坛壝有地,非必庙为也。去古既远,事神之仪,悉务鬼享。故虽山川,而筑宫肖像,动与人埓,土木崇丽,至拟于明堂太室,无甚媿者。将礼与时变,其致力于神当如是耶。”(93)(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3-374页。虽然他指出了各地东岳庙存在的神灵越界与人格化现象,甚至认为这是将古礼中的事鬼之礼用于事人,但韩元吉并没有对此进行反对,而是将这种行为理解作“礼与时变”的反映。这一观点符合宋代诸多文人的共识。事实上《礼记》已有“礼”可以“义”起的说法;而在分封制瓦解、众多古代生活习俗被改变以后,宋代儒家士人更不再执着于古礼中的具体仪式,而强调礼制所体现的教化意义。(94)惠吉兴:《宋代礼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164页。

诸多祠庙碑文反映,北宋时期的后土及东岳祭祀在民间具有广泛的支持;而在各地祠庙创建或重修过程中,真宗藉由东封西祀所展现的“戴天履地”“恭成上化”之天子威仪被一次又一次地叙述与宣传。由此看来,盛唐至宋初通过摄入民俗及宗教成分完成的礼制改革,较之于单单流传于儒家士人间的“古礼”,对于寻常百姓更具说服力。王朝的威仪亦可凭借祠庙的修建,深入官僚机构无法渗透的地方。
结 语
真宗西祀与泰山封禅等大中祥符年间的系列活动一道,是唐玄宗时期开始的国家礼制改革在宋初的延续。“澶渊之盟”后,北宋对外环境由“战”转“和”,政治路线由武治转向文治,是东封西祀举行的直接原因。西祀以前,宋真宗的支持者们,通过制造祥瑞、引导地方耆老士人助祭等形式,广泛地激励了地方势力对国家祭祀活动的参与。在祭祀活动中,真宗朝则通过提升后土神祭祀等级,崇饰供奉人格化神祇的后土庙,举行富有道教色彩的祭祀仪式等多种方式,混淆了后土与地神祭祀的概念,将“古礼”与民间祠祀及道教信仰活动融合,使礼制与地方士民社会产生更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通过批准乡民自发营建国家祭祀体系中的部分祠庙,北宋王朝的威权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并前所未有地深入地方;包含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也得以藉由宗教信仰广泛传播,在各个地区的不同族群中取得统一。这一系列改革,使国家“大祀”从贵族社会的权力垄断活动,演变成帝制国家王朝形象的宣传。东封西祀以后,宋真宗直接在民间树立了帝王权威,并获得了河中府这类战略要地代表民意的地方豪强的支持。
虽然,大中祥符年间的系列活动在仁宗朝后逐渐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但这正是地方分权政策与官僚社会逐步完善的结果。仁宗时期,科举取士真正成为了广大士人的上升阶梯,儒学重新获得了荣光;真宗东封西祀中,因融入民间信仰而散发的迷信色彩,才在此时成为了话柄。与此同时,仁宗朝日益突出的“三冗”问题,激发了朝廷内部对于先代帝王诸多大型礼制活动的诟病。换句话说,正是宋初改革的成功,使权力移交到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手中,后代的文人才有机会对前朝的做法议论纷纷。
而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系列活动,在粉饰太平的同时,正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的相互协同与超负荷运作,掩盖了此期国家权力由主战派转向主和派、从地方军政机构转入中央朝廷、从贵族势力让渡到官僚集团,而形成的过渡时期交织引发的诸多问题。在“一国君臣如病狂”的神道设教活动中,歌舞升平的唱和之音掩盖了权力移交时可能发生的种种冲突,太祖太宗两朝的诸多重大军政改革至此得以落实与巩固。如此看来,东封西祀这类迷信活动,虽理应受到历史的批判;但对于刚刚走出“中古”迈向“近世”,尚需要以神圣性强化统治合法性的真宗朝,这种劳民伤财的国家祭祀活动,或者存在着迎合地方社会需求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