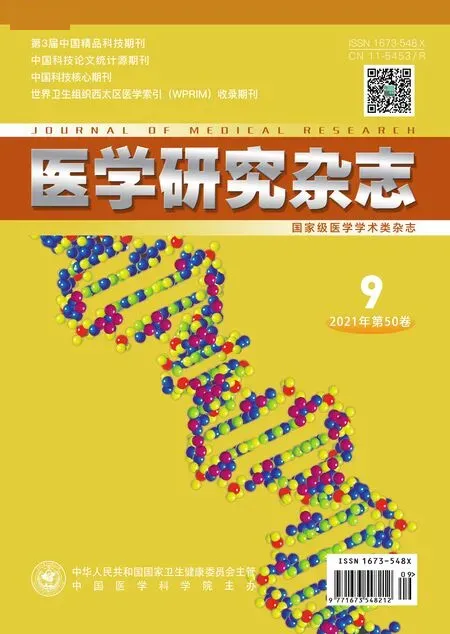缺氧微环境调控肝细胞癌血管新生的研究进展
朱婷婷 程紫薇 邢东炜 张闽光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全球第四大癌症死亡原因[1]。在我国,超过60%的HCC患者确诊时已为中晚期,治疗选择受限,预后较差[2]。血管新生是癌症的十大特征之一,HCC作为一种高度血管化的实体肿瘤,血管新生在其发生、发展和转归中起着关键作用,如果没有血管新生,HCC生长不会超过1~2mm。经导管动脉化学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是临床上HCC最常用的治疗方式,但其5年生存率仅为10%左右,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HCC血管新生导致肿瘤向其他脏器的侵袭转移。因此,肿瘤的血管新生也是HCC患者TACE临床治疗的最大障碍。
缺氧是血管新生最重要的刺激因素,血管新生本身就是肿瘤细胞对抗缺氧环境的一种反应。作为实体恶性肿瘤,HCC在短期内会迅速增大,而血管生长相对滞后,进一步导致瘤体组织和细胞的局部缺血、缺氧,这种局部缺氧微环境又进一步激活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等血管生成因子,启动异常的血管新生程序。结构和功能异常的新生血管又加剧了以缺氧为特征的异常肿瘤微环境,形成恶性循环,促进HCC的发展与转移。因此,本文就近年来缺氧微环境下,HCC血管新生的机制研究进行综述(图1)。

图1 缺氧微环境下参与调控肝细胞癌血管新生的相关因素
一、缺氧诱导因子对HCC血管新生的直接调控
1. HIF-1α:缺氧诱导因子-1(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HIF-1)被认为是肿瘤缺氧适应性反应的中心启动因子,HIF-1由α、β亚基以异源二聚体形式组成,其中HIF-1α是唯一的氧调节亚基,决定 HIF-1的活性。细胞核产生的HIF-1α对氧分压敏感,常氧下希佩尔林道抑癌基因VHL(von Hippel-Lindau,VHL)能使HIF-1α泛素化并导致其降解,但在缺氧条件下,HIF-1α的降解途径受阻,可以通过涉及羟基化、乙酰化、泛素化和磷酸化反应的翻译后修饰来控制HIF-1α稳定性和转录活性,使其在细胞核内积聚,持续表达增高[3]。
HIF-1α在HCC及其基质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转录调控作用。HIF-1α刺激血管生成因子的表达,如VEGF、葡萄糖转运蛋白1(glucose transporter protein-1,GLUT1)和碳酸酐酶9(carbonic anhydrase 9,CA9)等。这种转录程序促进血管新生,从而提供营养和氧气,维持肝癌细胞存活。Wang等[4]研究发现,HCC细胞中赖氨酰氧化酶相关蛋白2(lysyl oxidase-like 2,LOXL2)的表达能够被HIF-1α升高,并诱导上皮间质转换(epithelium-to-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和血管新生,促进肝癌转移。在缺氧条件下,HIF-1α调控的下游基因与肝癌血管新生关系密切。Wen等[5]研究表明,HIF-1α活化能上调VEGFA、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EPO)、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fibroblast growth factor-2,FGF-2)等下游血管新生相关基因的表达,并在体外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HUVEC)模拟血管形成实验中促进HCC细胞毛细血管新生。
2.HIF-2α和HIF-3α:与HIF-1α一样,HIF-2α也可诱导多种血管新生基因的表达,如VEGF或血管新生素,但不同的是,二者在肿瘤缺氧环境中的作用存在差异:HIF-1α主要在缺氧急性期发挥作用, 而HIF-2α则是随着缺氧环境进展而逐渐发挥作用。有研究发现,在缺氧微环境中,HIF-2α促进脂肪性HCC发展可能是通过上调PI3K-AKT-mTOR途径来实现的[6]。对HIF-3α的研究相对较少,HIF-3α具有转录活性还是抑制活性,其对HIF-1/2α具有正反馈调节还是负反馈调节,这些问题尚存在争议,所以,HIF-3α在缺氧微环境中的抗HCC血管新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7]。但是近年来研究发现,在缺氧环境下,HIF-3α能够调控长链非编码RNA促进其他消化系统肿瘤的侵袭转移,基于此,HIF-3α是否能通过促进HCC的血管新生引起侵袭和转移也期待有最新的研究汇入[8]。
二、缺氧通过诱导自噬调控HCC血管新生
缺氧是自噬(autophagy)激活的重要诱因之一,自噬在HCC早期可以通过防止氧化应激、调控炎性免疫反应等维持细胞内稳态,是细胞在缺氧微环境下赖以生存的关键[9]。Park等[10]研究发现,自噬能够为病理组织提供充足的氧进而促进血管新生。其机制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自噬能够调节氧化还原稳态,虽然轻度氧化应激可以改善内皮细胞功能,但在高水平的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中,自噬能够促进血管新生。另一方面,自噬对血管新生相关细胞因子具有双向调控作用,既可以促进血管新生,也可抑制血管新生[11]。
自噬发挥促进血管新生作用主要通过调节受体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VEGFR2)免受胞质分裂和胞吞,当内皮细胞处于静止状态时,VEGFR2的周转减少,自噬可能通过调节内吞途径干扰VEGFR2的激活状态进而调控血管新生[12]。ROS是自噬的上游调节器,ROS的产生可能是自噬参与血管新生的重要机制,诱导自噬促进血管新生,而抑制自噬可以抑制血管新生。Zou等[13]研究表明,ROS引发的自噬可以通过激活 VEGF等血管生长因子进而启动血管新生途径。
三、缺氧通过刺激外泌体分泌调控HCC血管新生
肿瘤细胞主动产生、释放和利用外泌体(exosomes)来促进肿瘤的增殖、迁移和血管新生。肝癌细胞在缺氧条件下会分泌更多的外泌体,此时释放的缺氧外泌体富含血管生长因子。研究表明,缺氧条件下肿瘤释放的外泌体可以导致血管新生和血管渗漏[14]。外泌体通过携带血管生成蛋白而参与肿瘤血管新生:血管生成蛋白被内皮细胞捕获或者外泌体微小核糖核酸调控内皮细胞血管生成功能[15]。但外泌体在肝癌细胞中发挥调控血管新生功能的分子机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认识与研究。
四、缺氧通过协助肿瘤免疫逃逸影响HCC血管新生
低灌注和缺氧有助于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病理性血管新生存在的肝癌缺氧环境,其环境压力和代谢压力通过影响基质和免疫细胞组分,诱导免疫逃逸并维持连续的缺氧状态[16]。
1.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缺氧会导致肿瘤相关的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TAM)的聚集。TAM包括M1型和M2型巨噬细胞,前者主要发挥抗炎和抗肿瘤作用,后者被发现能促进免疫抑制,激活肿瘤微环境中的细胞因子、生长因子和蛋白酶,并有利于肿瘤微环境中导致肿瘤进展的异常血管的形成,从而促进肿瘤进展。韩晨阳等[17]研究发现,CD68+CD163+M2型巨噬细胞可以通过分泌VEGF等促血管生长因子,激活 VEGF-VEGFR2- Notch1/DI4信号通路促进肝癌血管的新生。
2.肥大细胞:在缺氧微环境中,肥大细胞可以刺激其他炎性细胞释放血管生长因子和细胞外基质降解蛋白酶,以此来促进肿瘤血管新生,从而导致肿瘤的生长和发展[18]。在肿瘤发展的早期,肥大细胞募集,造成肿瘤血管新生和组织重构,随着肿瘤进展,嗜酸性粒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被招募,进而激活体液免疫反应和细胞免疫反应。随着HCC组织中分泌的肥大细胞密度增高,肝窦内皮细胞逐渐血管化表现,且基膜逐渐增厚,促进了血管新生。此外,肥大细胞还可以通过衍生的金属蛋白酶来实现降解间质肿瘤基质的作用,来释放VEGFR、FGF-2、TGF-β等与细胞外基质结合的血管生长因子。
3.NK细胞:NK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s,NK cells)使用受体和信号通路的组合来保护宿主免受肿瘤侵害,然而研究显示在缺氧微环境中,NK细胞上细胞毒性效应子和激活受体的表达均降低,导致肿瘤从NK细胞介导免疫逃逸[19]。肝脏是人体NK细胞最大的储存场所,但在HCC中,NK细胞由于缺氧微环境,往往处于功能性衰竭的免疫抑制状态,最近有研究指出,外源加入具有抗肿瘤活性的NK细胞能重新激活肝癌小鼠肿瘤中衰竭NK细胞的抗肿瘤活性,重塑肝脏的免疫系统,进而激活抗血管新生反应[20]。
4.T细胞及调节性T细胞:T细胞的毒性作用可抑制HCC血管新生,促使肝癌细胞凋亡。但缺氧微环境能能够抑制T细胞的毒性作用,最新研究提示其有两方面机制:一方面,HIF可介导 CD73和CD79的表达,使腺苷在细胞外积累,通过识别T细胞A2A受体增加环腺苷酸表达,抑制T细胞的细胞毒性[21]。另一方面,HIF可介导CD8+T表达,CD8+T细胞在缺氧培养时更有效地分化为细胞毒性T细胞,抑制HCC血管新生。VEGF能够招募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s),同时,Tregs也参与介导肿瘤血管生长因子释放,缺氧可以增加Tregs的聚集,并通过抑制CD4+效应T细胞功能和促进Tregs活性来增强免疫抑制。
五、缺氧通过调节干细胞功能影响HCC血管新生
肿瘤干细胞是肿瘤组织中具有“干细胞样”特征的小细胞亚群,其可能来源于骨髓间充质细胞的异常突变和分化。干细胞与HCC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并促进了HCC高侵袭、耐药、易复发、易转移、预后差的恶性特征。
1.骨髓间充质细胞:骨髓间充质细胞(bone marrow stromal cells,BMSCs)广泛存在于骨髓基质系统中,作为一种多能干细胞,BMSCs可以在各种条件和因素诱导下实现多方向分化。有研究发现,动员后的BMSCs具备分化为成熟血管内皮细胞的能力,进而参与肿瘤血管新生,然而这一过程的激活因素尚未明确,目前猜测可能是VEGF参与了骨髓动员[22]。另一项实验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BMSCs被动员后,HCC组织中检测出VEGF也逐渐升高。这可能是由于局部微环境的趋化,HCC组织释放的VEGF入血动员BMSCs,进入循环后局部富集,最终分化为成熟的血管内皮而参与HCC血管新生。BMSCs还可以通过释放外泌体,经由JNK /HIF-1α信号转导促进血管新生。此外,有研究认为除了直接分化为血管内皮外,BMSCs也可在局部分泌促血管生长因子,以旁分泌方式参与血管新生。
2.肝癌干细胞:肝癌干细胞(hepatic cancer stem cells , HCSCs)主要通过释放促血管生长因子和外泌体来驱动血管新生。在缺氧条件下,肿瘤干细胞比肿瘤中的非肿瘤干细胞群体产生更高水平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增加促进内皮细胞迁移,并形成新的管型血管。因此,血管新生和肝癌干细胞之间可能存在正反馈回路,一方面肝癌干细胞可以通过自噬或者直接形成新生血管以获得血液和氧气来对抗肿瘤内缺氧。另一方面,缺氧微环境中的血管生态也通过旁分泌机制释放生长因子,以维持肝癌干细胞的高干性。这种正反馈回路导致了肝癌的进展和不良预后。
3.人肝脏干细胞:人肝脏干细胞(human liver stem cells,HLSCs)与肝癌干细胞动态失衡可能是导致HCC发生、发展的机制,当HLSCs向HCSCs转化时,HCC发生及转移进展风险增加。有研究发现,HLSCs衍生的外泌体处理后的肿瘤来源内皮细胞,其miR-15a、miR-181b、miR-320c和miR-874的表达显著增强,这些微小核糖核酸能够通过下调EPHB4、ITGB3、FGF1和PLAU等血管新生相关基因来抑制血管新生进而发挥抗肿瘤发生的作用。
六、展 望
目前,抗血管新生治疗已成为抗肝癌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对于HCC血管新生的研究颇多, 现已经发现多条肿瘤血管新生通路, 也相继诞生了多种针对血管生成的靶向药物,以索拉菲尼为代表的抗肿瘤血管新生的药物大量进入临床。近年来,随着肿瘤微环境、免疫逃逸、外泌体、干细胞等领域的研究深入,肝癌血管新生的机制研究也取得了诸多进展,但仍然存在尚待解决的问题:①HIF-3α在缺氧微环境中是否对调控肝癌血管新生有作用,需要未来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揭示;②外泌体在血管新生和远端肝癌转移前微环境形成中的作用分子机制还尚待明确;③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是促进肿瘤生长,还是靶向生物治疗的一个新希望,但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个全新的领域中,其作用机制及潜在风险需要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