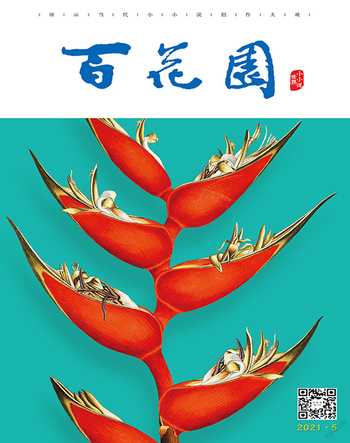我家就在吕西村
罗箫
鹿回头
正月初二是闺女走娘家的日子。这天吃罢午饭,小妹香凤说:“进入庚子年,娘就八十有六了,我作为末生女儿,得趁小年前缝纫厂没活儿,伺候娘一段日子。前年冬,我和姐伺候娘才两个多月,大哥就拦着不让我们两家伺候了,难为你伺候娘又整整一年,加前边,六年有余了。”
我退休后回老家居住,一者为伺候痴呆老娘,二者为熟悉生活,有利于写作。此外没别的活儿干。姐和香凤两家都有责任田,还放羊割猪草剪兔毛啥的,都是起早忙到日落山,不能待在家守着娘。香凤在村里缝纫厂打工,娘恨她见天没影儿,经常发火。
与其他嘴碎的老人一样,娘也嘴碎。不同的是,娘整天胡言乱语,颠三倒四,还老骂人,脏话一嘟噜一串,难听得扎心。
“这个黑心烂骨头的,躲哪儿去了?”
“一天到晚不着家,咋不死在外边?”
娘声大音高,香凤听到从来不反驳,权当耳旁吹过一阵风。过后,香凤还那样,吃罢饭,锅碗瓢勺洗涮毕,拔腿就走,头也不回。
娘拽不住人,阴森了脸,咬牙切齿地咒骂:“又疯去了!又疯去了!我咋生这么个(尸从)妮!早知是这样,当初该把她摁进脚盆里淹死了!”
前事已远。此刻,香凤哄娘说:“我会分分钟待在您身边,学您耍贫嘴骂人。”
娘说:“有你守在跟前,我骂谁?骂东南西北风啊?”
没料到,香凤接走娘的第二天,村支书就找上门来。见他戴着口罩,我赶紧找口罩戴上,隔着四米远跟他对话。
村支书说:“奶奶在家吗?镇卫生院派来医生,要逐户逐人做身体检测,尤其老人,不能漏掉一个。”
我说:“香凤把她拉走,说元宵节后送回来。”
“去张庄了?赶紧接奶奶回来!”
“为啥?”
“张庄出现一位发热病人,镇里刚通知的。”
“哦,我这就去接娘回来!”
“记得给奶奶备口罩。镇领导讲,人人要戴口罩,必须的,以防人传人。”
我开电动三轮车出门,上到漳河大堤跑不多会儿,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雪花大如席也挡不住人心急切如箭,我把车开得更快了。
到张庄进到香凤家,将近十一点。娘坐在客厅沙发上,正在吃香脆核桃饼干,旁边开着电暖扇。娘见我进门,停止咀嚼,打招呼道:“老大你来叫我的?我不走,你回去吧。”嘴里的碎渣喷了一地。
我说:“我走中,不过,您得跟我走。”
“为啥?我不走,你能咋的?”
“香凤会撵您走的。”
“为啥?”
“几句话跟您说不清,我跟香凤说。”
见香凤从厨房出来了,我问她:“你庄那位发热病人打哪儿回来的?”
“他在武汉上大学,寒假回来没几天就咳嗽不止,走路乏力,买了一堆感冒药,不管用,家人送他去县医院,确诊为新冠肺炎,立马就被隔离了。”
“那你为啥不打手机告诉我?”
“他家庄西,我家庄东,这段时间没见过他和他家人,就没当回事。”
“你家近邻跟那人和他家人有接触过吗?”
“不知道,没问过。那人的情况我是听村里大喇叭广播的。”
香凤忙洗菜、切菜、切肉,问我:“猪肉炖粉条白菜,你爱吃吗?”
“东北名菜,当然爱吃了,可我想麻利拉娘走,回到我那个没有嫌疑的家。”
香凤咯咯笑着说:“我们有预防,那不,娘也戴着口罩哩!”
我瞅瞅香凤和娘的口罩,也笑起来:“这是你手工缝制的吧,吸水,不隔气味,我在电视里听专家讲过。”
“镇卫生院和康德大药房都把口罩卖光了,网购缺货,将就着用呗。”
“幸好我带来几个。”
我递给香凤四个口罩,他们夫妻俩以及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各一个。那是我儿子从北京带回来的,他只在家住了两天就返京了,临走时还显摆过那几只口罩,我没当回事。孰料才过几天,口罩就成了人人眼气的日用珍品。
妹夫回来了,见我在,扭头跑小超市买回一只烧鸡和一兜小菜。他家有红星二锅头,拿出一瓶,拧开盖,咕咚咕咚往玻璃杯里倒。
我说:“开着车哪,我不能喝酒。小品《代驾光临》里不是说‘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吗?”
妹夫不当回事:“一辆电动三轮也是车?”
“当然是车了。再说,雪太大,车滑下去就糟了。”
“慢点儿开,不会出事的。”
我硬着心,滴酒没沾。不到半个钟头,妹夫竟独自喝下一瓶。
吃罢饭,我拽娘上车,娘却坠着身子不肯走:“我在这儿可高兴啦!我问一句,你妹就答一句,你能吗?”
我说:“我写文章时,怕走神,有一搭没一搭的,惹您恨了不是?打今儿起,我学香凤好榜样,句句顺遂您中不?”
“中!那我高兴得能猴蹦。”
娘蹦不了高,只是不用拽了,自个儿往车上爬,我赶紧从后面她一把。
许多事预料不及,这不,往回开两里多路,三轮车就滑下大堤了。那是个拐弯处,迎面过来一辆救护车,堤面雪积成冰,我扭动车把将三轮车往堤边靠,车轮突然打滑,滑下去两米多。
娘扯着嗓子喊:“踩刹车呀!踩呀!”
我回应:“踩了!刹不住!”
三轮车一直滑到堤脚,不动了。我把娘抱下车,往上推车,推上去一米,又滑下一米,等于白费力气。我打妹夫的手機,没人接。那家伙嗜酒如命,准是躺床上蒙头大睡了。
正为难之际,从救护车上下来一位戴口罩的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大爷,我来帮您!”
电动三轮车不重,加上那位年轻人力大如牛,我俩连推带抬,很快就把车弄到了堤顶。我给年轻人递烟,他看看牌子,“新石家庄”,两块五一盒,没接,转手掏出一盒烟,拆开,弹出一支给我。
当着生人面,我不好意思摘口罩,就接过来夹到耳根,说:“好烟!”“黄鹤楼”,十八元一盒,确实是好烟。
年轻人说:“我没瘾,很少抽烟,干脆把这盒烟给您吧。”
我说:“你这是送病号住院吧?耽误你时间了,真对不起。”
“我送一位胃溃疡的老太太出院回家了,这是空车回县城,不急。”
突然听到手机嘀嘀响,他打开瞥一眼,拔腿就跑,边跑边说:“领导发来短信,说有发热患者呼叫120,我走了啊!”
我回到堤脚,往上背娘。
娘问:“他为啥帮咱?”
我摇摇头:“不知道。”
“那人不孬。”
“鲜见,大大的好人。”
重新上路,开出一段距离我还在想,搭手帮忙就让人感激不尽了,为啥还要给我烟呢?想着想着,脑瓜里倏地一亮,闪出一个词——“鹿回头”。年轻人见三轮车打滑溜下去了,仍继续往前开,越开心里越不落忍,就停车跑了回来。或许,他知难而上,习以为常了。
我回头张望,白雪皑皑,直晃人眼睛。
驴跑了
说起我爹,他可真够倔的。六年前我退休刚回老家居住,就把娘接到西院我家了。我家在吕西村西南角,与东边老院相隔四百多米。爹硬是不来我家住,还说:“我正想一个人住呢,这两年守着你那痴呆娘,我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她住你那儿了,兴许我能多活几年哪。”
老三在县城开着个“宏天制衣有限公司”,没法儿回来伺候爹,但他给爹在村医疗室、小卖部和小餐馆都留了钱。老三还给爹买了头毛驴,并雇工把那辆破旧排子车修缮一新。爹没法儿硬着两条腿去南河滩放那些胡窜乱跑的山羊,却爱赶集赶会,拾起了多年前当过木材经纪的行当。有毛驴车在,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
这几年,作为老大,我没外待过爹,但凡改善生活,都要喊他过来吃个肚饱。每次我去到老院,爹就让我帮他铡草。我捉铡把,爹续草,“嚓!嚓!嚓!……”铡草的声音,美妙耐听。大冬天,堤坡与河套光秃秃的,没法儿放驴,但院里有个干草垛,高达房檐,那是秋季里爹放驴时顺便割的,搁排子车上拉回,摊院里晒干,积少成多,小垛渐成大垛。
开春,草长花开,爹开始放驴。爹让驴拉着空排子车逛河套,哪儿草旺,爹“吁”一声,驴就止步,低头吃草。嫩草含有乳味,乐得毛驴“呜哇呜哇”欢叫。附近有好大一片小柳树,爹爱吃开水烫熟加盐、醋、香油、蒜汁凉拌的柳芽,就走过去抬手捋柳芽。小柳树间距窄,驴拉着车,进不去。
爹把提篮即将捋满时,突然打了个激灵:“家伙咋不吵闹了?”那头驴往常一旦不见主人就会吵闹,“呜嗷呜嗷”的,类似婴儿撒娇。此刻却哑然无声。
手机响了,我瞥一眼号码,是爹打来的,忙摁接听键。
爹呼呼喘着粗气说:“驴……驴……驴跑了!”
我不信:“您跟驴形影不离,有您在,它舍得离开吗?”
“我……我有好大会儿,没在驴跟前儿……”
娘见我神色紧张,忙问:“咋啦?出啥事啦?”
我说:“我没出事,是那个老惹您厌烦的腌臜老头儿出事了。”
我跑出门,见人就问,都说没见驴。爹走路难,跑不了远路,我身强体壮,外出找驴舍我其谁。
我递给娘三个“达利园”蛋黄派,说:“您简单吃点儿,回来我再给您做饭。”
娘说:“光吃这个不得劲儿,你先给我熬碗黄糊涂吧。”
我拿起电动三轮车钥匙,边走边说:“我急着呢,回来再说。”
娘在后边嚷嚷:“又是那腌臜老头儿!又是那腌臜老头儿!他叫你上天你就上啊!叫你拱地你就拱啊!”
我没回话,开车出门。
娘刚住我院那年,爹偶尔过来蹭饭,娘让吃让喝,还说:“他爹,你饿了过来就是,老大有退休金,吃不穷他。”后来变了,娘见我爹进门,就翻白眼嘟囔:“又来了,又来了,咋吃不够呢?”痴呆日趋严重的娘,竟然以为我爹已去阎王爷那儿报到了。
天黑得真快,上堤不一会儿,我就不得不摁亮大灯。往东去了四个堤口,又返回去了西边四个堤口,哪个村子也没进去,因为每个堤口都搭有防控棚。把守者如临大敌,虎视眈眈,拒绝生人下堤进村。有个人我认识,他却笑着摇头拒绝了我的请求。“疫情关乎生命,防控人人有责。”那条横幅甚是抢眼。堤顶四米多宽,是混凝土硬面,与县内其他公路一样,允许人与车通行,但堤口和公路旁的村口一样,生人生车免进。
回家路上,我给老三打手机,几次都占线,改发微信:“有急事,速回话。”
不一会儿,老三回复:“大哥,有啥事?”
“驴没影儿了,你能回来一趟吗?”
“县城街道封闭,车开不出小区,我咋回去?”
爹守在西院我家等消息呢。娘正拧头皱眉跟我爹耍脾气。
我进门,也苦着脸说:“我去了八个堤口,人家都统一口径——外人免进。县城街道封闭,老三没法儿开车回来。”
爹气呼呼地说:“我就不信那个邪!你和老三一样笨,幸好我那干儿子王寅在家,我这就去找他。”
我劝爹:“恁晚了,您甭乱跑,我打王寅手机,看他咋说。”
王寅和村里好多经常外出打工的人一样,被疫情囿在家中。我打过去还没说话,王寅就说:“三哥回不来,方才他打手机把丢驴这事跟我说了。我估摸,驴跑不远,十里八村我都有熟人,不信做下这事的人能捂盖恁严。”
五十年前,王寅刚出生那天,他娘就大出血没了,他奶奶抱他去我家让我娘喂奶,其时我家老三不满三周岁,还没断奶。爹看孩子可怜,就让我娘把他留下喂养。两年后,王寅的奶奶过来要领王寅回自家,王寅哭喊:“不走!就不走!这儿有干爹干娘,别地儿没有!”爹说:“你啥时想干爹干娘了,就回来看看我俩呗。再说了,两家只隔一堵墙,推倒墙,跟一家一样,明白不?”王寅虽幼小懵懂,也明白这个理儿,就跟奶奶走了。至今,那堵墙还在,但墙再厚,也隔不断人情,心与心紧贴着,很温暖。
正如王寅所说,这附近的几个村他都有熟人。他经常去附近几个村庄干建筑活儿,并且,跟前新屯的工头是磕头朋友。工头朋友在电话里告诉王寅,有个邻居拾到一头驴和驴拉的排子车。那就是了,王寅断定。这叫碰巧,一个电话就搂出了大头小尾巴。
驴是被一位到处拾废品的汉子赶走的。当时,那汉子顺着大堤拾废品,拾呀拾,拾满背篓,正打算往回走,见一头驴拉着排子车过来了。驴突然不走了,还扭动长脸往后瞧,像是在等人。那汉子撅一根柳条,抽几下驴屁股,驴就乖乖听令而去。
前新屯距离我们吕西村约七里路,那汉子拾废品附带拾到驴和車,自己也觉得好笑,本打算卖掉驴,可封村也封集、封会,没法儿成行。他愤懑地想,驴主也日怪,仅隔一天就号准脉了。
娘见我又要跟人出门,编排道:“好人的忙该帮,你不该帮那个腌臜老头儿的忙。”
爹那张脸老阴天,不知何时,娘视他为刁德一了。
前新屯不让进也无妨,那汉子和王寅的工头朋友把毛驴连同排子车赶出来,王寅、我和爹迎了过去,形同交接战俘。
?[责任编辑?王彦艳]